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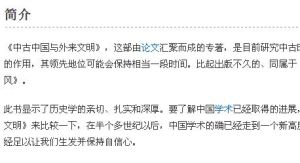 《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
《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這部由論文匯聚而成的專著,是目前研究中古時期中西交通的最前沿成果,無疑具有示範的作用,其領先地位可能會保持相當一段時間。比起出版不久的、同屬於“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的林梅村《古道西風》。
此書顯示了歷史學的親切、紮實和深厚。要了解中國學術已經取得的進展,可以拿此書與向達先生《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來比較一下,在半個多世紀以後,中國學術的確已經走到一個新高度了,這雖然還不足以讓我們驕傲,但是已經足以讓我們生髮並保持自信心。
目錄
序(張廣達)(1)
絲綢之路:東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代前言)(1)
第一篇胡人遷徙與聚落(17)
1.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19)
2.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37)
3.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內部形態(111)
4.隋及唐初并州的薩保府與粟特聚落(169)
第二篇胡人與中古政治(181)
1.高昌王國與中西交通(183)
2.胡人對武周政權之態度——吐魯番出土《武周康居士寫經功德記碑》校考(204)
3.安祿山的種族與宗教信仰(222)
4.一個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238)
5.敦煌歸義軍曹氏統治者為粟特後裔說(258)
第三篇“三夷教”的流行(275)
1.襖教初傳中國年代考(277)
2.粟特襖教美術東傳過程中的轉化——從粟特到中國(301)
3.《釋迦降伏外道像》中的祆神密斯拉和祖爾(326)
4.《歷代法寶記》中的末曼尼和彌師訶——兼談吐蕃文獻中的摩尼教和景教因素的來歷(343)
5.摩尼教在高昌的初傳(369)
第四篇漢唐中西關係史論著評介(387)
1.赫德遜《歐洲與中國》(389)
2.D.D.Leslie和K.H.J.Gardiner《漢文史料中的羅馬帝國》(393)
3.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399)
4.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406)
5.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413)
6.《中國與伊朗:從亞歷山大到唐朝研究論集》(419)
7.富安敦《質子安世高及其後裔》(427)
8.羅豐《固原南郊隋唐墓地》(441)
9.E.Knauer《駱駝的生死馱載——漢唐陶俑的圖像和觀念及其與絲路貿易的關係》(447)
10.龔方震、晏可佳《祆教史》(452)
11.森安孝夫《回鶻摩尼教史之研究》(460)
後記(469)
索引(473)
出版後記(489)
序
張廣達
新江的新作《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即將問世。多年來,新江在敦煌學、吐魯番學、隋唐史、西域史、民族史、宗教史諸多學術領域辛勤耕耘,先後出版專著多部,論文、書評近兩百篇。今天,新書的出版是他在以上諸多學術領域做出貢獻之後的又一豐碩成果,可喜可賀。新江的新作,使人們看到了他的整體研究的又一組成部分。他的這一新課題的研究符合他歷來治學的路數,可以說是他整理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隋唐史、西域史的自然延伸。多年來,他辛勤蒐集分散在國內外的文書寫卷,可謂嫻習而樂道於茲,心不旁騖。在網羅放失方面,經過他的全方位求索,除了私人藏家手中秘不示人的卷子之外,逸出他的記錄或注錄之外的殆無孑遺。對於門類繁多、內容龐雜的敦煌卷子和吐魯番卷子,他在整體上有清晰的概觀和通識;在處理個別文書殘片的分類歸屬和定名等具體問題上,他有深入獨到的見解。因而他不僅在編目、校錄、整合、考釋文書寫卷自身和結合文獻研究文書寫卷等多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並且通過對文書的悉心爬梳、過濾、鉤沉、索隱而積累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大量史料。文書殘片的片言隻語發出的微弱的史實信號,經過他置於歷史時空系統之中考察其關聯,往往顯示多方面的文化內涵。近年,在一點一滴做完網羅散失文書寫卷的工作之後,他又開始整理碑銘文獻,研究中古中國與中亞、西亞的伊朗語世界的關係。他筆下的著述源源不絕,正是他二十年來辛勤努力的結果。
新江在治學過程中,講究窮盡材料,重視綜合利用諸多領域的研究成果。這使他的研究不局限於僅就敦煌、吐魯番而言敦煌、吐魯番,進而注意敦煌、吐魯番與更廣闊的外界的歷史聯繫。我們還看到,他在撰述上,無論是通論還是專題研究,都從學術史角度注意國內外學術發展的前沿狀況。從他已經發表的論著看,總是既概括或融會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反映當前研究的最新狀況。功力的深厚,視野的開闊,使他在史料梳理和課題論證上獨具見地。也正因為是這樣,他的很多工作是在和國內、國際的前沿學者對話,很多時候是接著國際上許多學者的話頭講,做出獨到的結論,顯著的例子是將西方學者所說的吐木舒克語(T1lmshuqese)根據唐代文獻定名為“據史德語”。
新江的這部新書《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以較多的篇幅探討了中古粟特人的歷史及其對周邊國家的文化貢獻。自古以來,我國中原地區文化就和異域文化糾結在一起。僅以西域而言,在亞洲腹地的沙漠或砂磧邊緣的綠洲廢墟,荒蕪曾經青翠,粗獷有過柔媚,寂寥洋溢過生命,落寞孕育過壯麗。正是通過這一廣袤的荒漠地區,中國和中亞、西亞文明進行了長期交流。但是,長期以來,人們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於塔里木盆地的綠洲定居文明及其與我國中原和草原遊牧文明的交涉。晚近烏茲別克境內粟特城邦遺址的考古發掘,近年我國中原地區粟特後裔墓葬的不斷出土,促使人們越來越重視研究粟特人,即昭武九姓胡的來龍去脈及其歷史作用。粟特商胡,即昭武九姓,富有經商才能,具有高度組織性,他們由於經營國際中轉貿易而足跡遍及中亞東亞,並在他們所到之處建立起聚落,聚落與聚落之間再形成空間極其廣袤的網路。新江的新著成功地重構了昭武九姓胡的聚落的網狀分布,翔實地敘述了他們的商務活動及其與本土居民的互動,以中古中亞史和中國史中湮沒已久的一章補足了PhilipCurtin與JerryBentley等人僅就海路研究前近代舊大陸跨文化的商業關係之不足。粟特商胡不僅是經商能手,而且長時期內在歐亞內陸扮演著傳播多元文化和多種宗教的角色。新江的新著詳盡地考證了祆教、摩尼教、景教的東來過程,繼GezaUray、H.--J.Klilimkeit、DavidScott與RichadFoltz等人研究絲綢之路上各種宗教的互動影響之後接著講,做出了見解獨到的補充。
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除了自身具有科學研究旨趣之外,又具有現實意義。我國的漫長歷史從來沒有脫離過與另外的民族、另外的思想、另外的信仰、另外的風俗的交光互影,文獻中保存著與另外的文化、另外的社會實踐、另外的心靈交際的豐富記錄。這使中國認識了“他者”和異域,並且藉助於與“他者”的來往和與異域的交流而更好地認識了自己。對於這種與“他者”的對話,過去人們更多地體認到的是如何豐富了我國物質文化和藝術生活的內容,實際上.這樣的對話也同時引發了人們對另外的思維方式的注意。中外文化異同的比較有助於破除思想上的畛域之見,改變僅憑自我存在、自我經驗而形成的思維定勢。在西力東漸之前,佛教的漢化和宋明理學的發展是借“他山之石”以促成新思維之綻開的最佳例證。朱熹和王陽明之重新闡釋“吾儒”,正是由於有了釋氏之“他異’’的對照。西力東漸後,新舊思潮無一不以“他者”為襯托,所有的主張無一不以西方為參照系。以繼“國粹派”而起的“學衡派”為例,他們在反對當代主流思潮時,仍以白璧德(IrvingBabbit)的新人文主義的理論為參照,支持其“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主張,意在以理性的批判精神對待傳統,補偏救弊,突破清末以來沿用多年的“中體西用”的思想架構。
上個世紀的西方也是同樣,一些西方學者正是出於與西方以外的“他者”的深化接觸,才開始越來越自行質疑西歐中心論,考慮西方的重新定位。法國文化學家米謝爾·德·塞爾多(MicheldeCerteau,1925-1986),學問極其淵博,足跡幾乎遍及天下.他正是基於廣泛的閱讀和遊歷才提出,在歐洲,“史學編纂起源於歐洲與原來不知道的他者的接觸”。在當今世界,跨文化的相遇日益頻繁,異質文化的互動日益加強,我們已經看不到有什麼地區還能游離於世界整體之外。今天,人們討論的重點不再是跨文化的接觸本身,而是頻繁接觸中的文化認同問題。在這種形勢之下,西方越來越多其他領域的專家也把“西方中的東方”(theEastintheWest)納入研究和著述之中,例如英國劍橋大學的JackGoody即是。1984年,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啟動了供全國高等院校本科使用的“哥倫比亞大學核心課程方案的亞洲教學計畫’’(ColumbiaProjectOnAsiaintheCoreCurriculum),參與考慮方案的有七十五所學校的百餘位專家。該計畫現已刊出教學指導書(AGuideforTeaching)三種,繼《社會科學中的亞洲案例研究》(Asia:CaseStudiesintheSocialSciences)、《比較觀下的亞洲文獻菁萃》(MasterworksofAsianLiteratureinComparativePerspectives)之後,1997年出版了《西方史和世界史中的亞洲》(Asiain’WesternanclworldHistory)。
該書收有專家撰寫的基本教材四十篇,這表明,在西方,亞洲在西方與世界中的歷史與現狀的重要意義越來越為人所認識,相關科目已正式納入大學本科的基礎課程。從當前這一研究趨勢看,我國學者無論是在實證方面,還是義理方面都大有可為。在疏證、考信史實層次上,我們有豐富的傳統文獻和層出不窮的考古文物和文書,可供研究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的具體過程;在義理層次上,我們有大量的新穎資料可供探討什麼是“他者”(theother)、“他性”(otherness/alterity)、“異己性”(foreignness)和怎樣“涵化”(acculturation)、怎樣“認同”(identy)的“他者學”(heterology)理論。考據與義理的相互為用,不僅有助於今後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將促進近代歷史上的西方的概念讓位於世界的概念,並為人們今天在實際生活中遇到的跨文化問題提供某種啟示,打破西方某些論述話語的壟斷地位。從這一意義上說,新江從事的新研究領域不僅僅是考證文化交流中早已存在的有趣史實而已,他的研究也將有助於啟發人們思考人類存在、人類交往中的異向理解問題。
我長期游離於國內學術界之外,孤陋寡聞,每次閱讀新江的論文,總能在豐富或幾近完備的材料、廣泛吸收的研究成果、獨到的見地等許多方面受到啟發,以致每當他有新作發表,我都先睹為快,略減與國內學界現實脫節的遺憾。令人非常喜悅的是,新江的業績使人感受到目前學術群體的銳進勢頭,由陳垣、向達、馮承鈞、張星烺、方豪、韓儒林、朱傑勤、韓振華、孫培良、章巽等先輩開創的研究中西交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傳統,因新江和他的許多同一代學者的新穎研究而得到繼承,而邁入新境界,而發揚光大。今天,新江藉助於整理文書和古籍的深厚功力、學術上的開闊視野,在追蹤既往,喚起廢墟遺址中酣睡的文化的性靈,再現中古中國與西亞伊朗之間湮沒已久的文化聯繫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績。繼此而往,新江以他的優越的主客觀條件而肆力於深入探索古代中世紀的歐亞腹地及其周邊的多種異質文化,必將對中外交通、中西文化交流領域的研究做出更多、更新的貢獻。2001年7月
代前言
絲綢之路:東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代前言)
今天,如果我們乘飛機西行,無論是去西亞、印度,還是歐洲,最多不過二十多個小時。然而,在遙遠的古代,我們的先民們在西行時,不論是走陸路,還是走海路,都要花費不知多少倍的時間,也不知要克服多少艱難險阻。與外界交流的需要,促使我們的祖先早在距今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就開通了連線東西方文明的陸上通道,這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
一、為什麼叫“絲綢之路”?
早年,人們對這條東西往來的通路沒有給予一個統一的固定名稱。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在他所寫的《中國》一書中,首次把漢代中國和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的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theSilkRoad)。其後,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A.Herrmann)在1910年出版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由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因為大量的中國絲和絲織品經由此路西傳,故此稱作“絲綢之路”,簡稱“絲路”。
絲綢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另外一個名字,如“玉之路”、“寶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但是,都只能反映絲綢之路的某個局部,而終究不能取代“絲綢之路”這個名字。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於公元前後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後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于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乾納)。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軒(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喀拉蚩),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後形成的絲綢之路的基本幹道,換句話說,狹義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上述這條道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比如敦煌、羅布泊之間的白龍堆,是一片經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當東漢初年打敗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遷,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領了伊吾(今哈密)以後,開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從伊吾經高昌(今吐魯番)、焉耆到龜茲,就和原來的絲路北道會合了。南北朝時期,中國南北方處於對立的狀態,而北方的東部與西部也時分時合。
在這樣的形勢下,南朝宋齊梁陳四朝與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長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龍涸(今松潘),經青海湖畔的吐谷渾都城,西經柴達木盆地到敦煌,與絲路幹道合;或更向西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與絲路南道合,這條道被稱作“吐谷渾道”或“河南道”,今天人們也叫它作“青海道”。還有從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進人中亞地區。這條道路後來也被稱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最為興盛。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從漢代開始,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後,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二、絲綢之路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演變
陸上絲綢之路所經過的歐亞大陸(Eurasia),主要是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內陸亞洲地區。這一地區的地理特徵是氣候異常乾燥,降雨量極其稀少。在絲綢之路的中部地帶,有號稱為“世界屋脊”的帕米爾高原,以帕米爾高原為中心,向四周延續出喜瑪拉雅山、崑崙山、喀喇崑崙山、天山、阿爾泰山、阿賴山、興都庫什山等山脈,冰峰峽谷,行走艱難。這裡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和景觀是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瑪乾大沙漠、裏海東部的卡拉庫姆沙漠、伊朗的卡維爾沙漠等,對於行旅來說,更是乾渴難行。此外,由鹽殼沉積而形成的崎嶇起伏、犬牙交錯的雅丹地形,也是一個重要的地理障礙。唐代詩人所描寫的“映雪峰猶暗,乘冰馬屢驚”(楊師道《隴頭水》),“黃沙西際海,白草北連天”(岑參《過酒泉憶杜陵別業》),正是這些地理景觀的生動寫照。而西行取經僧人筆下所描寫的“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是親履其地的感受。
然而,從聳立在沙漠邊緣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來的河水,灌溉滋潤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綠洲,填補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也提供了中西往來路途上的中間站。我們的先民並沒有因為不利的地理條件而陷於孤立,由於交換的需要,人們很早就開始了對外界的探索。東西方出土的考古資料,揭示了先秦時期東西方交往的存在。如遼寧喀左蒙古族自治縣東山嘴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陶質裸體女神像,即西方考古學所謂“維納斯女神像”,與中歐、南俄以及西伯利亞地區出土的同形女神像十分相像。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俄羅斯阿爾泰山西麓巴澤雷克(Pazyryk)大墓發現的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紀的中國銅鏡和絲織品,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北方和西北方的遊牧民族,如匈奴人、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扮演著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
秦、漢王朝統一中國,積聚了中原王朝的實力。到公元前二世紀的漢武帝時,為了打敗稱雄漠北、搔擾中原農耕居民的遊牧王國匈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聯絡被匈奴人從河西趕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帶的大月氏人。張騫經過千難萬險,雖然沒有搬來大月氏的兵,卻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況。隨後漢武帝又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這一次使團的人數總共有三百人之多,張騫及其隨行者的足跡也更為廣遠,到了大宛(費爾乾那)、康居(以今塔什乾為中心的遊牧王國)、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亞王國)、身毒(印度)等國。張騫的兩次西行,打破了遊牧民族對絲路貿易的壟斷,使中國和中亞、南亞、西亞諸王國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貿易往來關係,張騫等人帶回的報告,也是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實見,而且由司馬遷和班固分別寫入《史記·大宛傳》和《漢書·西域傳》,從此結束了我國古代對西方神話般的傳聞認識。正因為張騫的這一創舉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所以人們把張騫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稱之為“鑿空”。
張騫西行的直接後果,是促使漢朝打敗匈奴。結果,漢朝不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個郡,還進而派兵遠征蔥嶺以西的大宛,獲得武帝夢寐以求的天馬――汗血馬。到了公元前60年,漢朝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漢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個綠洲王國的供應,西行變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於道,往來不絕。西漢末年,王莽專政,中原與西域的關係一度中斷。東漢初,漢明帝派班超經營西域,重新恢復了西域都護對塔里木盆地的統治。與此同時,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北匈奴在南匈奴和漢朝的聯合打擊下,西遷到黑海北岸,引起了西亞和歐洲許多民族的遷徙。在絲綢之路的歷史上,甘英的西行是中國人的又一壯舉。公元97年,西域都護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一直來到波斯灣頭的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人海處的條支(Antiochia),準備渡海西行,但安息人為了壟斷東方與羅馬的貿易,向甘英誇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艱險,阻止了甘英進一步西行,自條支而還。甘英雖然沒有達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他仍可以說是中國第一位走得最遠的使臣,是一位讓人崇敬的時代英雄。他親自走過了絲綢之路的大半段路程,還了解到從條支南出波斯灣,繞阿拉伯半島到羅馬帝國的航線。
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後二世紀,沿著歐亞內陸交通幹線,自西向東,有四大帝國並列其間,即歐洲的羅馬(公元前30年一公元284.年)、西亞的安息(帕提亞,公元前三世紀中葉至公元226年)、中亞的貴霜(公元45年一226年)、東亞的漢朝(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在公元前後,四大帝國都處在國勢昌盛的時期,積極向外擴張,如羅馬帝國在圖拉真(MarcusUlpinsTrajanus,98-117年在位)時,把版圖擴大到幼發拉底河上游一帶;又如貴霜帝國也曾把勢力伸進塔里木盆地;漢朝則成功地打敗匈奴,控制河西走廊,進駐天山南路。張騫的鑿空和甘英的遠行,使東西方世界直接聯繫起來,這是時代英雄的創舉,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其結果是使得中國、印度、西亞和希臘羅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響,此後,任何文明的發展再也不是相對孤立地進行了。
從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漢代開闢的這條絲綢之路時而因為政治對立、民族矛盾乃至戰爭而一度中斷。文明的發展,勢力的擴張,商業民族的活躍和草原遊牧民族與農耕定居民族的依存關係,使得東西方的精神與物質的文化交往兩千多年來從未斷絕。東漢末年,中原戰亂頻仍,秩序混亂。作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沒有太守,當地豪強大姓雄張,兼併土地,使小民無立錐之地,前來貿易的西域商胡也備受欺詐。227-233年間,倉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強的兼併和勒索,為西域商人前往內地買賣提供種種方便,也使得敦煌成為漢族與西域各族民眾交往貿易的一個國際都會。1907年,英國考古學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長城烽燧下,發現了一組用中亞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寫的粟特文信件,這是在涼州(武威)的粟特商人寫給家鄉撒馬爾乾(Samarkand,在今烏茲別克斯坦)貴人的書信,不知什麼原因而埋藏在敦煌長城腳下。
信中談到,這些以涼州為大本營的粟特商團,活動的範圍東到洛陽,西到敦煌,經營中國絲綢等商品的長途販賣。這組書信寫於西晉末年(312年前後),它們真切地反映了當時絲綢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動。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天下大亂,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紛紛遷居河西以避戰亂,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涼王朝的先後建立,也集聚了大批人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為本地區接受外來文化提供了知識的基礎,也為向中原輸送外來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論是東晉十六國,還是後來的南北朝,都不斷有東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絲綢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圖澄至洛陽;399年,東晉僧人法顯等西行取經;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諸國;468年,北魏遣使韓羊皮出使波斯,與波斯使俱還;518年,宋雲與惠生自洛陽出發,西行取經;530年,波斯國遣使南朝;此外,還有大量沒有留下名字和事跡的使者往來於東西各國。
隋朝統一南北,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全盛時期。隋煬帝時,讓黃門侍郎裴矩往來於張掖、敦煌之間,通過西域商胡,聯絡各國首領。從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寫的《西域圖記序》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絲綢之路通向東羅馬、波斯、印度的情況。
進入唐代,民族的進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廣闊開拓,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極大的力量,生產發展,商業繁榮,文化昌盛,並以博大的胸懷,大量接受外來文化,使之融會到中國文化的整體當中。從唐太宗到武則天,唐朝的勢力不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諸王國,而且成為天山以北、蔥嶺以西廣大區域內各個王國的宗主國,中西往來更加暢通無阻,當時的文化交流也呈現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象。西方的珍禽異獸、珠寶香料、玻璃器皿、金銀貨幣紛紛傳來,中亞、西亞的穿著、飲食等生活方式,音樂、舞蹈等文化娛樂活動都源源進入中原,佛教進一步盛行的同時,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興的伊斯蘭教都在此時正式傳人中國內地,唐朝的兩京長安和洛陽以及絲綢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涼州,都紛紛呈現出國際都市的風貌。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藉助唐朝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傳人西方,深淺不等地影響了西方各國。公元十世紀中葉以後,宋王朝先後與北方的遼、西夏、金處於敵對的形勢中,影響了陸上絲綢之路的中西交往。南宋建都於東南的杭州,加之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繁盛起來。相對來講,陸上絲綢之路要比從前有所衰落,但在某些特定的時間裡也被頻繁地利用,如馬可波羅來華前後的蒙元時代。這些已經溢出本書的範圍,就留待以後再講述吧。
三、通過絲綢之路的東西方文化交流
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維持,對中西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絲綢之路上,也流傳著許多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佳話和傳說。說到絲綢之路,人們自然首先會想到中國絲綢的西傳。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絲綢就已經大量轉運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羅馬,絲綢制的服裝成為當時貴族們的高雅時髦裝束。因為來自遙遠的東方,所以造價昂貴,羅馬為了進口絲綢,流失了大量黃金。我們今天在雅典衛城巴台農神廟的女神像身上,在義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館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希臘羅馬時代的人們所穿著的絲綢服裝,輕柔飄逸,露體動人。絲綢服裝的追求已經到了奢侈浪費和傷風敗俗的地步,使得羅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穿用絲織服裝,但並沒有起多大作用。
羅馬帝國的古典作家們把產絲之國稱之為“賽里斯”(Seres)。公元一世紀的博物學家老普林尼(GaisPlinytheElder,23-79)在《博物志》中說:“(賽里斯)林中產絲,馳名宇內。絲生於樹葉上,取出,濕之以水,理之成絲。後織成錦繡文綺,販運到羅馬。富豪貴族之婦女,裁成衣服,光輝奪目。”賽里斯就是中國,這是當時絲綢遠銷羅馬的真實寫照。老普林尼和以後相當一段時間裡的西方學者,並不清楚絲綢是如何織成的。中國的養蠶和繅絲的技術是很晚才傳到西方的。唐朝初年西行取經的僧人玄奘,在公元644年回國途經于闐(今和田)時,聽到一則傳說,在現存的有關於闐佛教史的藏文文獻中也有大同小異的記載。這個故事的主要情節是講于闐王曾娶東國(一本作中國)女為王后,暗中要求對方將蠶種帶來。新娘下嫁時,偷偷把桑蠶種子藏在帽絮中,騙過了關防,把養蠶制絲的方法傳到了于闐。從此以後,于闐“桑樹連蔭”,可以自制絲綢了。于闐國王為此特別建立了麻射僧伽藍,以為紀念。近代考古學者曾在和田東北沙漠深處的丹丹烏里克遺址,發現一塊八世紀的木板畫,上面描繪著一位中國公主帶著一頂大帽子,一個侍女正用手指著它。研究者都認為,這裡所畫的正是那位傳播養蠶制絲方法的絲綢女神。解放後,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盆地的古墓中,發掘出大批高昌國時代(502—640)的漢文文書,證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各綠洲王國生產的絲織品情況。
至於更遠的西方世界,是遲到六世紀東羅馬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theGreat,483—565年在位)時,才由印度人(一說波斯人)從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國那裡,用空竹杖偷運走蠶種的。物質文化的交流總是雙向的,中國奉獻給西方世界以精美實用的絲綢,歐亞各國人民也同樣回報了各種中國的需求品。
我們今天所常見的一些植物,並非都是中國的土產,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一批帶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蔥、胡荽、胡椒、胡桐淚、胡蘿蔔等等,十有八九是來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獻中往往把這些植物的移植中國,歸功於第一位中西交通的美好使者――張騫。實際上,現在可以確指為張騫帶回來的物產,只有苜蓿和葡萄,前者原產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亞(Media),後者是西亞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的一種植物。漢初以來,西來的不僅僅有植物,還有羅馬的玻璃器、西域的樂舞、雜技,到了東漢末年,史書記載:“靈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續漢書·五行志》)
從魏晉到隋唐,隨著屬於伊朗文化系統的粟特人的大批遷入中國,西亞、中亞的音樂、舞蹈、飲食、服飾等等,大量傳人中國。
粟特人,在中國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就簡稱作“胡”,他們的故鄉在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粟特地區,以撒馬爾乾(在今烏茲別克斯坦)為中心,有九個綠洲王國,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國。這些粟特人大多以經商為業,他們組成商團,成群結隊地東來販易,並且有許多人就逐漸在經商之地留居下來。所以,就今所知,南北朝到唐朝時期,沿絲綢之路的于闐、樓蘭、龜茲(庫車)、高昌(吐魯番)、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和長安、洛陽等許多城鎮,都有粟特人的足跡。他們的後裔漸漸漢化,但不少人的外表還是深目高鼻。在中國歷史上,曾有不少人或好或壞地影響過歷史車輪的運轉,比如武威安氏,曾經幫助唐朝平定涼州李軌的割據勢力,後被唐朝皇帝賜姓為李。又如發動安史之亂的河北叛將安祿山,和割讓燕雲十六州而作兒皇帝的石敬瑭,都是分別來自安國和石國的粟特人後裔。
粟特人在文化上很早就接受波斯的伊朗文化影響,他們的到來,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滿了一種開放的胡風。我們看看唐朝最盛的開元天寶年間的有關記載,就可以感受到這一時代風潮。李白《前有樽酒行》詩:“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全唐詩》卷一六二)是說當年長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徠賓客。岑參《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詩:“琵琶長笛齊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渾炙犁牛烹野駝,交河美酒金叵羅。”(《岑參集校注》卷二)說的是酒泉地方官的宴席上,胡人演唱的情形。自居易《胡鏇女》詩:“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環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鏇。”(《全唐詩》卷四二六)太真就是楊貴妃,她是唐玄宗最寵愛的妃子,其善跳胡鏇舞,說明了這種舞蹈在當時的風行。史書記載安祿山“腹緩及膝”,極力描寫其臃腫肥胖的樣子,大概是有些誇張。他作為粟特人後裔,跳胡鏇是其家常,史書說他“作胡鏇舞帝(唐玄宗)前,乃疾如風”(《新唐書‘安祿山傳》),可以與楊貴妃媲美。已故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向達先生曾撰有長篇論文《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我們可以從這篇史學名作中,一覽唐代長安的種種胡化景象。
在物質文化交流的同時,自古而來,通過絲綢之路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斷地進行。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漢末年就傳人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為佛教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到了隋唐時期,佛教已經深入民心,並且由中國的高僧創立了中國化的宗派。今天,佛教已沒有古代那么盛行,但人們頭腦中的因果報應思想;語言中常常使用的一些辭彙,如“剎那”、“影響”、“水乳交融”等等;隨處可見的佛寺山窟;小說彈詞等文學藝術形式;都是佛教直接或間接留下的影響。特別是沿著絲綢之路留存下來的佛教石窟,著名的如龜茲的克孜爾、吐魯番柏孜克里克、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靈寺、天水麥積山、大同雲岡、洛陽龍門等等,這些石窟大多融會了東西方的藝術風格,是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它們連成一串寶珠,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遺產。
從魏晉到隋唐,西亞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也先後傳人中國,都產生過一定程度的影響。其中的摩尼教本是產生於古代波斯的一種宗教,在波斯受到鎮壓,幾乎絕跡,但卻在中國,特別是中國的維吾爾先民回鶻人中間廣為傳播,甚至在九、十世紀建都吐魯番的西州回鶻王國中,被立為國教。敦煌吐魯番發現的漢文和各種伊朗語、回鶻文的摩尼教文獻,與埃及發現的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獻一起,構成今天我們認識古代世界的摩尼教的基本文獻資料。相對而言,在宋元之前,中國思想的西傳遠遠不如她所接受的那樣多,但中國物產和技術的西傳卻是難以統計的,造紙、印刷、漆器、瓷器、火藥、指南針等等的西傳,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直到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到來,才將中國思想文化大規模地介紹到西方,同時也開啟了西方近代文明進人中國的時代。
絲綢之路的道路漫長而久遠,而且無始無終。在古代,它是傳播友誼的道路,也曾經是被戰爭鐵蹄踐踏過的道路。今天,人們已經忘卻昔日曾經有過的苦難,而把絲綢之路看作是連結東西方文明的紐帶。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絲綢之路研究計畫”,把絲綢之路稱作“對話之路”,以促進東西方的對話與交流。對於中國人民來講,今天的絲綢之路,是開放之路,是奮進之路,是通向二十一世紀的光明之路。
盤點考古書籍
| 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的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中國近代“考古學”一詞,可能是從西文Archaeology一詞翻譯而來的。考古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範圍是古代,所以它與近代史和現代史是無關的,自人類的起源始,下限隨考古學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又由於各地區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所以無法統一,各國考古學都有它們的年代下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