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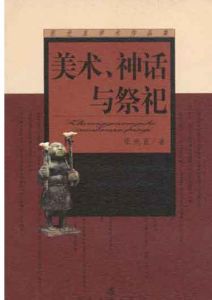 《美術、神話與祭祀》
《美術、神話與祭祀》張光直著作《美術、神話與祭祀》等,深受國內讀者的喜愛。他的許多重要作品都是英文的,像《古代中國考古學》是世界範圍內的考古學教材,影響巨大;還有《商文明》、 《考古學再思》等,有些已經被譯成日文或韓文,但始終沒有譯成中文。
古代中國的藝術與神話同政治有著不解之緣。我們已經相當習慣於把政治看做當代中國社會中的一個決定因素,然而,認識到它對古代中國也具有同樣重要性的人卻並不多。
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將得之於考古學的,以及文學和藝術的材料與觀點結合起來,對此作一番論證。《美術、神話與祭祀》提供一個基本的視界,從性質與結構兩個方面對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古代中國文明進行觀察;同時力求證明:如果我們能跨出傳統的專業局限,這對於古代文明,至少對古代中國文明的研究會大有裨益。這是這部專著的雙重目的。
編輯推薦
古代中國的藝術與神話同政治有著不解之緣。我們已經相當習慣於把政治看做當代中國社會中的一個決定因素,然而,認識到它對古代中國也具有同樣重要性的人卻並不多。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將得之於考古學的,以及文學和藝術的材料與觀點結合起來,對此作一番論證。
本書具有雙重的目的:其一,提供一個基本的視界,從性質與結構兩個方面對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古代中國文明進行觀察;其二,力求證明:如果能跨出傳統的專業局限,這對於古代文明,至少對古代中國文明的研究會大有裨益。
作品風格
 《美術、神話與祭祀》
《美術、神話與祭祀》作者綜合了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美學等相關學科的知識,在本書中對中國古代的政治權威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並藉此想回答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中國古代文明是如何產生的,相對於西方文明,它有什麼自己的特點。作者對不同學科知識合理的運用,充分體現了他在前言中所說“跨出傳統的專業局限”綜合各學科知識來分析問題的方法。
書中尤為明顯的運用了大量人類學理論,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莫斯、列維-史特勞斯等大師的影子。或許,這並不奇怪,儘管張光直通常更多是被人稱作考古學家,其實從其學術生涯一開始,他就和人類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早年他在台灣求學的時候,就受到了深具“南派”(王建民,1997:160-166)傳統的人類學薰陶,他當時的老師凌純聲、李濟等就極力強調將考古學與人類學、民族學等結合起來(張光直,1999:134-135;168-175)。在美國念博士期間,張光直還是專攻考古,但就讀於哈佛大學人類學系。這是因為在美國,考古學是人類學下的分支學科(其它幾個是語言學、體質人類學、社會文化人類學),後來他又任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主任。凡此種種都表明,對人類學民族學與考古學之間有何關聯這一問題,應該說他有著至為深刻的體會。
本書是本考古學著作,但在我看來,從其宏偉構架到具體的細節,無不透出作者的人類學關懷。本書寫作的最終目的,在於闡明中國文明的產生和西方文明不一樣,有著自己的特點。這一視角和人類學一直所推崇的“文化的多樣性”異曲同工。在後來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對此作了進一步的理論闡釋:“中國文明,以及其它相似文明的產生的特徵,是在這個產生過程中,意識形態作為重新調整社會的經濟關係以產生文明所需的財富之集中的一個主要工具”(張光直,2002[1986]:114),而西方文明,卻是用“生產技術革命與以貿易形式輸入新的資源這種方式積蓄起來的財富為基礎而建造起來的”,對於前者來說,在此過程中並沒有造成人與自然的關係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仍然將人與自然都看作是整體宇宙的部分,而後者卻不同,把這兩者分割開來。因此,作者將前面這種文明發生的形態稱作“連續”,而後者稱作“破裂’。並且,他對以前“西方中心主義”的文明觀進行了修正,指出從世界範圍看,中國、瑪雅這種“連續”才是文明產生的常態,而西方確實是個異態。
張光直的這一論述,對我們有什麼樣的啟發?這涉及到他一向所提倡的,從中國的具體材料中,我們應該對社會科學的一般理論有所貢獻。他教導我們應該清楚的認識到這一重要的事實,“即一般社會科學上所謂原理原則,都是從西方文明史的發展規律里歸納出來的”(張光直,1999:55)。因此,用一些非西方的材料我們應該能夠對社會科學理論做出很好的補充和修正。當然,和一般高喊“本土化”口號的學者不同,他冷靜地指出,“對社會科學做重大的貢獻的話,頭一件要做的便是把西方社會科學學好。中國史料裡面與社會科學有關的種種真理,不是不言自明的,也不是閉關自守的學究能發掘出來的”。這一看法,確實比國內一些只注重“本土化”或“國際化”的學者要高明許多。並且,他身體力行,以上對世界文明產生的比較就為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作者對青銅器及上面的文字、紋樣等“物”的具體分析,是書中尤為精彩的部分。照張光直自己的話說,這些“青銅紋飾(是)具有含意的”,而非單純的藝術品。這裡的“含意”如何理解?我覺得就是社會學、人類學所一直所強調的,將“物”納入社會、文化、宗教、或宇宙觀中去理解,正所謂“事物分類就是人的分類……事物被認為是社會的固有組成部分,它們在社會中的位置決定了它們在自然中的位置”(涂爾幹、莫斯,2005:87-88)。張光直讓我們懂得需要從一個大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之下去理解一些細微之“物”,同時也可以反過來說,從這些細小之物——如青銅器上的圖像來看到整個社會、文化。有時,“這東西或許只是一片陶片,或者是其它可以給你一個探討整個古代人類時代的線索的物品,你可以用它去研究他們的宗教概念、他們的社會”(張光直,1999:230)。人類學民族學能夠讓考古學家知道把“物”與當時的社會、文化等聯繫起來,而不是將其活生生的分離開。反過來,從考古學家對細微之“物”的深究中,我們理應得到這樣一種啟示:即一個“物”本身能展現一個社會、一個文化,它是社會眾多關係的集合體,或者說,一個“物”就是“微型宇宙”,具備了宇宙存在的所有可能性。
古代中國文明有著天與地、人與神、生者與死者這樣一種二分的世界觀。在祖先和神靈那裡掌握著人類所需的知識。因此,就有一些“人”和“物”在這之中扮演溝通這二者的角色,這些“人”就是巫師,“物”就是文字、藝術、青銅器等。這些“人”、“物”之特點,正如列維-史特勞斯所說,他(它)們“處於對立兩項中間,就必然保持某些二元特性(即自相矛盾的和模糊不清的)”(列維-史特勞斯,1995[1955]:425)。瑪麗·道格拉斯將此觀點作進一步引申,認為社會中的許多事物之所以成為禁忌,那是由於它們違背了事物自身的秩序,無法分類(瑪麗·道格拉斯,1995[1966])。
藉助這些分類學理論,我們能夠更好的理解張光直在書中關於紋樣、文字、青銅器等“物”的論述。那就是,天地、人神、生死的對立是古代中國最基本的分類。其間的“中介物(人)”是具有“二元特性”的,“自相矛盾”、“模糊不清”。或許,在道格拉斯看來,這是禁忌。但正是這些無法分類的“人”、“物”恰恰具有了溝通天地的能力。為了能更清晰的看到這其中的種種關係,我們來看以下這個簡單的圖示:
目錄
《美術、神話與祭祀》的新版序
譯者的話
中譯本作者前記
序言
鳴謝
第一章氏族、城邑與政治景觀
第二章道德權威與強制力量
第三章巫覡與政治
第四章藝術——攫取權力的手段
第五章文字——攫取權力的手段
第六章對手段的獨占
第七章政治權威的崛起
附錄三代帝王表
後記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的草稿
注釋
作者簡介
張光直,1931年生於北平。1954年台灣大學考古系畢業,1960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曾先後任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系主任,哈佛大學人類考古學系教授、系主任,美國科學院及文理科學院院士。1994年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任哈佛大學講座教授。著作《中國青銅時代》《美術、神話與祭祀》等深受國內讀者的喜愛。張光直著有多部英文專著,如《古代中國考古學》是世界範圍內的考古學教材,影響巨大,還有《商文明》 、《考古學再思》等。
圖書評價
 《美術、神話與祭祀》
《美術、神話與祭祀》在序言中,作者提到寫作本書的兩個意圖:其一,提供一個基本的視界,從性質和結構兩個方面對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古代中國文明進行觀察;其二,力求證明:如果我們能跨出傳統的專業局限,這對於古代文明,至少對古代中國文明的研究大有裨益(張光直,2002[1983]:1)。本書作者以考古學材料和三代文獻為依據,力圖回答:文明以及與其形影不離的政治王朝是如何在中國興起的?(同上:5)以下便是本書正文的具體內容。
全書正文共有七章,照我的理解,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作者在此主要論述了古代中國由不同氏族和宗族之間的宗系關係而聯接起來的政治景觀,以及維持這樣一種政治結構而需要的道德權威和強制力量。
作者以再現三代的政治景觀為開篇。在他看來,夏、商、周三代王朝分別由不同的氏族所建立,這些氏族又由不同的宗族所組成,不同宗族甚至同一宗族的成員之間在地位上都是各不相同,有著高下之分。伴隨著宗族的裂變和分支,各分支宗族紛紛有了屬於自己明確空間的領地。其中,“王族”居住的“都邑”,自然是整個氏族內各分支宗族的中心,而各分支宗族在自己的領地內,也建有自己的中心,即“城邑”。最初的城市就是這樣產生的。但這時的“城”並非市場中心,而是政治心臟、權力中心。“而城邑的分級體系大體上與氏族與宗族的分級分層相吻合”(原書第12頁,下同)。並且“古代中國的每個‘國’,都是一個由若干等級不同的城邑構成的網狀組織”。作者在此特別指出,構成這一切的關鍵,是由於,中國古代國家最顯著的特徵是“以血緣紐帶維繫其成員的社會集團左右著政治權力”(第3頁)。
“城邑、氏族和宗族構成的分級分層,組成了一幅理想化的政治結構圖”(第19頁)。然而,作者認為,由親族制本身並不能嚴格的維持層序體系,要想達到平衡,不得不引入其它因素進來。“對維持眾多競爭者的政治平衡最有影響的因素之一,便是以“功”為基礎的價值評判。生而具有治人的資格還不夠,還必須得到被統治者的擁護”(同上),這樣才能成為天命的統治者。統治者主要通過祖先祭祀以及對其英雄神話的的不斷強調,以藉助死者的力量來證明這些在生統治者的合法性。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核心,包括整整第三章到第七章。作者論述了三代的統治者如何利用儀式、藝術、文字等尤其對幾項關鍵資源(如青銅器)的占有來與天、神、祖先的溝通,從而壟斷政治權力。
這時的人們以為,統治的權力來源於“天”,“順乎天意”正是當時統治者得以立足的原因。照我對書中的理解,三代的宇宙觀是一種“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在“上天”和“世人”的政治、生活之間,有一種非常緊密的關聯。“天”是神明和祖先所在之地,同時,“也是全部有關人事的知識匯聚之處”(第29頁)。因此,取得了這種知識,也就“順乎天意”,從而能夠謀得政治權威,反之亦然。統治者用什麼手段來實現與“天”、“神”、“祖先”的溝通來獲取這種知識,從而壟斷權力呢?
這種溝通的實現,有一類叫做“巫”的群體在其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因之,巫也就成了宮廷中不可缺少的成員。許多帝王其實就是巫師的首領。巫與神明的溝通,需要藉助其它活動和“物”,比如迷人的舞蹈、音樂、飲酒、藝術,文字等。作者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來討論這時期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這些動物紋樣,一類是寫實的動物,另一類則並不常見於自然界,只能用古文獻中神話動物的名稱來命名,如肥遺、龍、虬等。作者推論到,既然巫覡作為溝通人神世界的特殊群體,而青銅器是其儀式中必不可少之物,那么這些青銅器上的紋樣在其中也一定具有同樣類似的功能。有些人獸在一起的紋樣,則極有可能體現了當時人們的宇宙觀以及巫師正在藉助“物”與上天溝通時的情形。並且,從這些紋樣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制度。相對於藝術紋樣,文字的這種功能更加明顯,也更容易為人們理解。掌握書寫的人自然掌握了與祖先溝通的能力,由此獲得了從死者那裡得來的知識。由於文字在其中扮演了與祖先溝通的角色,因而文字本身也具有了一種神秘性。巫師很可能就是最早的“知識階級”。實際上,階層和階級產生的歷史,就是文字產生的歷史。
至此,我們看到作者對古代中國擁有顯赫政治權威並行使權力的人們勾畫出了這樣一個輪廓:“它們出身於某個合適的氏族(尤其是宗族),並與合適的對象婚配;他們恰好處於宗系的中心,並與合適的神話相聯繫;他們的行為能得到民眾的支持,並最終控制甚至獨占從儀式、藝術和文字中得來的祖先的知識和預言能力”(第72頁)。除這些必不可少的條件以外,對於這些古代的權力競爭者來說,還有至為關鍵的一項,“以控制少數幾項關鍵資源(尤其是青銅器)的方式,以積聚手段的方式來達到占有手段的目的”。這是因為青銅禮器“象徵著財富,因為它們本身就是財富,並顯示了財富的榮耀;它們象徵著盛大的儀式,讓其所有者能與祖先溝通;它們象徵著對金屬資源的控制,這意味著對與祖先溝通的獨占和對政治權力的獨占”(第74頁)。
第三部分為本書的最後一章,作者在此對全書進行了總結,並且提出了從中國歷史材料中,我們應該對社會科學理論做出重大貢獻的希望。
“文明”、“城市化”、“國家”等名詞,對中國而言,僅是同一問題的不同方面。“村落擴展和複雜化,便成為城市中心或城市網路;城市結為新的分層體系,便組成政治單位,其中有的可稱作國家。文明是物質財富積聚的體現,它既是政治權威興起的結果,也是它存在的條件”(第98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資源(文明)的最初集聚,是通過政治手段(國家社會)而不是技術突破來實現的”(同上)。在此張光直還對西方學者如馬克思、韋伯等關於中國早期文明和政治權威的論述進行了一定的修正。作者指出,通過中國文明史的研究,我們可以對社會科學理論做出重大的貢獻。儘管在該書中,他並沒將自己這方面的理論直接陳述出來,但我們可以看到他以下這番滿懷激情的言語:“我們有可能在其它文明發展的基礎上做出歷史理論的總結;這些理論會賦予我們新的眼光……中國的歷史也同西方一樣的驚心動魄,一樣的宏偉壯觀”(第102頁)。當然,在提出巨大希望的同時,作者並沒有忽視腳踏實地的工作,指出我們需要以紮實的材料作為基礎,這樣才能對西方理論進行適當的補充和修改。
盤點考古書籍
| 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的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中國近代“考古學”一詞,可能是從西文Archaeology一詞翻譯而來的。考古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範圍是古代,所以它與近代史和現代史是無關的,自人類的起源始,下限隨考古學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又由於各地區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所以無法統一,各國考古學都有它們的年代下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