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簡介
《明夷待訪錄》成書於公元663年,“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辭有日:“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謂“明夷”指有智慧的人處在患難地位。“待訪”,等待後代明君來採訪採納。《明夷待訪錄》文字的特點是,他對於封建的現狀,批判很尖銳,而且是披著夏、商、周三代外衣的理想,托古改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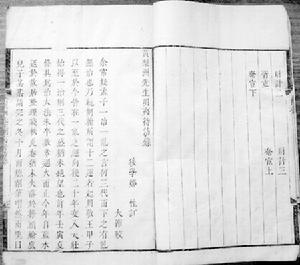 《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明夷待訪錄》計有論文21篇。《原君》批判現實社會之為君者“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實乃“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責任,乃“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原法》批評封建國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學校》主張擴大學校的社會功能,使之有議政參政的作用,說:“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屬是非於學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黃宗羲所構想的未來學校,相似於近代社會輿論中心和議會的機構。
黃宗羲雖然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設定,但主張君主開明立憲制,加強平等因素,擴大社會對執政者的監督權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這種思想並非受西方文明的影響,而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發展出來的,因而更加可貴。這部書受到清朝統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見天日,受到譚嗣同、梁啓超等人的重視和讚許。
作者小傳
黃宗羲(1610-1695年),
 黃宗羲
黃宗羲1645年,當清兵侵略中原時,黃宗羲毀家紓難,和浙東人民團結在一起,展開抗清運動。他組織起一支抗清的“世忠營”,有3000多人。後來他又聯合了太湖一帶的豪傑,抗拒清兵達半年之久。當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後,宗羲渡海到舟山,和張煌言等繼續搞復國活動。1664年,張煌言殉難後,宗羲遂改名換姓回到故鄉,聚眾講學,著書立說。
黃宗羲學識廣博,研究過天文、地理、算學、音樂、歷史和哲學等。他留下了許多著作,有《南雷文定》、《南雷詩歷》、《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在他54歲時,寫下了明夷待訪錄》。
主要內容
《明夷待訪錄》計有《原君》、
 《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黃氏在《原君》篇中,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惡,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賊。他說:“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
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這些話在300年前,是沒有人敢說的,黃宗羲卻大聲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剝者”。因此有人稱讚《明夷待訪錄》是“人權宣言”。
他對封建專制進行猛烈的批評,說它是公私不分,權利義務不平,沒有公法可言。因此他反對“一家之法”,主張“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原法》)。他為了求得人權平等,主張非廢除秦漢以來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廢除專制的君本制度,而改為民本制度不可。
他呼籲,現今應當是“天下(人民)為主,君為客”(《原君》)。他同時也提醒封建時代的臣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剝”百姓的服役者,而應該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他得出這樣的結論: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原臣》)
黃宗羲的思想意識中已有責任內閣制的因素,他認為宰相,一是賢人,二是有職有權的人;而君主的職位不過是虛名罷了。他在《置相》篇中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認為宰相既當責任內閣之權,“四方上書言利弊者……皆集焉,凡事無不得達”。
黃氏也有近代代議制的意識,他在《學校》篇中,已流露出議會政治的萌芽思想。他把東漢的太學清議的歷史意義理解為近代的議會政治,這是托古改制。黃宗羲的理想是,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學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類似議長)有權批評政治的得失。在地方政府,郡縣官都要在地方學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學官對於地方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
明、清之際,隨著都市經濟的成長,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工場手工業,反映到意識形態上,產生了黃宗羲具有資本主義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學說。中國封建社會,一向是“重農抑商”的。而黃宗羲鑒於社會的變動,面對現實,卻提出“工商皆本”的學說。他說:“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
 《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財計三》)在經濟學說上,黃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張廢止金銀貨幣,使用“寶鈔”,而以金銀作為寶鈔的基金。他這種經濟思想,有利於商品流通,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並啟發了近代的經濟政策。在黃氏看來,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崩潰的前夜,此時,“土力日竭”了,市場停頓了,人民生活的條件被皇帝奪去了,加稅加餉永沒有限制了。他站在市民的立場,還呼籲減輕軍費負擔,主張實行徵兵制度;反對募兵制。
當時農民無地可耕,而土地都被皇室、外戚、閹宦和地方的豪強所霸占,賦稅苛役特重,就拿江南一帶來說,“一困於賦,再困於役,蓋已皮盡而骨存矣”(《復社紀略》)。黃氏為了減輕農民的負擔,主張減賦稅(現代研究的事實是,明代的稅收過低,明末賦稅收入已經少到了不正常的地步)。
為了使人民能生活下去,他又提出“天下大公”的制度。在黃宗羲看來,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理想是恢復井田制度。所以他主張“齊之均之”,認為土地應收回為國家所有,然後再平均分配給農民耕種。他還主張“授田於民,以什一為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為則。其戶口則以為出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不足。”(《田制三》)宗羲“齊之”而“均之”的改革論,是在土地制度上的民主主義。他所憧憬的前途是“富民”的世界。他認為,如果按他的想法去做,這就可以取消封建土地的占有,給農民以土地,使之成為自由人。
主要版本
《明夷待訪錄》現存鈔本、刻印本20餘種。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黃宗羲全集》第一冊,內收《明夷待訪錄》,並加以點校,頗便於閱讀。單行本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55年鉛印標點本和中華書局1981年重印標點本。
貢獻影響
黃宗羲發揮了孟子的民本論“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
 《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同時代的思想家顧炎武說:“讀了這部書,可以知道過去歷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當洋務運動隨著甲午戰爭的失敗而破產後,人們開始關注西方的近代民主制度及其思想,把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作為引入西學的橋樑,其政治思想也隨之轉向維新。鄭觀應撰寫了《原君》、《學校》、《閹宦》、《建都》等文(均收在《盛世危言》一書中),都是《明夷待訪錄》原有的篇目名稱。儘管這些文章內容均已打上了時代烙印,但無法否定它們受到黃宗羲明顯啟發和深刻影響的事實。
戊戌變法時期,黃宗羲的著作對梁啓超、譚嗣同乃至康有為等人影響至為深遠。1897年梁啓超在長沙時務學堂講課時,將一知半解的西方民權思想與黃宗羲的新民本思想作了混同,但起到了宣傳民主思想的作用。梁啓超曾自述道:“梨洲有一部怪書,名曰《明夷待訪錄》,這部分是他的政治理想。從今日青年眼光看去,雖象平平奇奇,但三百年前——盧騷《民約論》出世前數十年,有這等議論,不能不算人類文化之一高貴產品”,“實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興奮劑”(梁啓超,1996年a,第56-57頁)。他還自稱自己與譚嗣同等人為“倡民權共和之說”,將《明夷待訪錄》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作為宣傳民主主義的工具”,結果“信奉者日眾”,“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同上,1996年b,第18頁)。
思想最為激進的維新派譚嗣同,對《明夷待訪錄》等新民本思想代表作極為推崇,指出:“孔教亡而三代以下無可讀之書矣!乃若區玉檢於塵編,拾火齊於瓦礫,以冀萬一有當於孔教者,則黃梨洲《明夷待訪錄》,其庶幾乎!其次為王船山之遺書。皆於君民之際,有隱恫焉。”(譚嗣同,第177頁)譚氏思想來源較為複雜,有墨家、佛家和儒家等,但他反君主的思想則明顯來源於黃宗羲,在《仁學》中有很清晰的承繼痕跡:“豈謂舉之戴之,(君主)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盤樂怠傲,驕奢而淫殺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欲傳之世世萬代子孫,一切酷毒不可思議之法,由此其繁興矣。”(同上,第178頁)這幾句議論與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中的語意極為相似。譚嗣同還痛斥那些“以天理為善,人慾為惡”的混帳的“世俗小儒”,指責他們“俗學陋行,動言名教”。這種口氣和觀念,可以說是與黃宗羲抨擊“小儒”固守綱常名教的議論一脈相承。侯外廬指出,譚嗣同的社會思想“一望而知為《明夷待訪錄》的繼承者”(侯外廬,第111頁)。
 黃宗羲
黃宗羲由於堅信黃宗羲是立憲政治倡始人,維新派主將康有為也對黃氏進行了高度讚美:“梨洲大發《明夷待訪錄》,本朝一人而已。梨洲為本朝之宗。”(《萬木草堂講義》,見《康有為全集》第2冊,第587頁)康有為在闡發“孟子立民主之制”時,指出“蓋國之為國,聚民而成立。天生民而利樂之。民聚則謀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禮樂政法,皆以為民也。但民事眾多,不能一一自為。公共之事必舉公人任之。所謂君者,代眾民任此公共保全安樂之事。為眾民之所共舉,即為眾人所公用……民為主而君為客,民為主而君為仆”。這裡的“民為主而君為客”,即引自《明夷待訪錄》,所以有學者評論說,康氏的言論“不少地方與其說來自孟軻,不如說來自黃宗羲”(馮天瑜,第267頁)。
清末,革命派繼續對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及其所代表的新民本思想保持濃厚的興趣,將之視為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作為革命派的章太炎,最初對黃宗羲是十分欽佩的,徑將《明夷待訪錄》闡釋為近代民主思想。他指出:“昔太沖《待訪錄》‘原君’論學,議若誕謾,金版之驗,乃在今日。斯固瑋琦幼眇,作世模式者乎?”(《致汪康年書》,見《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3頁)這裡承認,黃宗羲所提出的天下為主君為客、虛君重相的“立憲”主張,已在世界各國得到驗證。他在《冥契》一文中指出,黃宗羲主張公天下,否定君主的至尊地位,由近代“五洲諸大國,或立民主,或立憲政”而日治可證:“黃氏發之於二百年之前,而徵信於二百年之後,聖夫!”《冥契》從世界政治趨向民主制度的角度,對《明夷待訪錄》進行了富有時代感的定位和詮釋。1908年7月10日所寫的《王夫之從祀與楊度參機要》一文中,他一邊批評黃宗羲,還一邊承認他的歷史地位:“餘姚者(按:指黃宗羲),立憲政體之師。觀《明夷待訪錄》所持重人民、輕君主,固無可非議也。”(《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426-428頁)
以章太炎為盟主的國粹運動,在1910年章氏發表《非黃》一文以前,一直都對黃宗羲的思想十分推崇。黃宗羲的名號頻繁地出現在國粹學派的筆下,《明夷待訪錄》等論著也愈來愈多地受到人們的讚揚。
國粹派先驅鄧實主辦的《政藝通報》,於1903年冬刊載馬敘倫的《中國民族主義發明家黃梨洲先生傳》,把《明夷待訪錄》否定君權與排滿革命相聯繫,並稱道黃宗羲是秦以後二千年間“人格完全,可稱無憾者”的少數先覺之一。
由林獬主辦的《中國白話報》,於1904年初發表劉師培的《黃梨洲先生的學說》,更直接把《明夷待訪錄》與盧梭的《民約論》相比較,表示對黃宗羲“五體投地而讚揚靡止”(參見朱維錚,第357頁)。
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於1902—1903年寫成震驚中國的《革命軍》,以尖銳、犀利的文字抨擊君主專制,指斥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君主們“私其國,奴其民,為專制政體”,“以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的家天下行為,並指出“初無所謂君也,無所謂臣也。若堯、舜,若禹、稷,其能盡義務於同胞,開莫大之利益以孝敬於同胞,故吾同胞視之為代表,尊之為君,實不過一團體之頭領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後世之人,不知此義,一任無數之民賊獨夫,大盜巨寇,舉眾人所有而獨有之,以為一家一姓之私產,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無一自由”(參見吳雁南等,第181頁)。這些言語都十分類似黃宗羲的《原君》篇,可以說受到了《明夷待訪錄》的明顯影響。
溫家寶在《致史曉風先生函》中說:“我喜讀黃宗羲著作,在於這位學問家的許多思想有著樸素的科學性和民主性。身為天下人,當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過於‘萬民之憂樂’了。行事要思萬民之憂樂,立身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明夷待訪錄》是黃宗羲的政論和史論專著,該書通過對歷史的深刻反思,提出了獨到的政治見解,具有鮮明的啟蒙性質和民主色彩,被梁啓超稱為“人類文化之一高貴產品”。這部書堪稱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在有2000多年封建傳統的中國,它不啻暗夜火炬,隆冬春雷。同時代的著名學者顧炎武讀了這本書的手稿,讚嘆不已。事隔200多年,梁啓超還驚詫地稱其為“大膽之創論”。然而當時的封建統治者將黃宗羲的學說視為洪水猛獸,《明夷待訪錄》也被列為禁書,不許流傳。直到戊戌運動時期,譚嗣同等人出於維新變法的需要,把《明夷待訪錄》印刷了數萬本,秘密散布,使這顆火種重新燃燒起來,對於鼓動民主思想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明代筆記目錄(一)
| 明代筆記包括小說故事類的筆記、歷史瑣聞類的筆記、考據辨證類的筆記等多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