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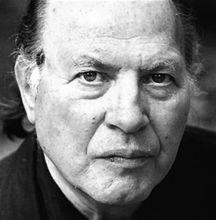 凱爾泰斯·伊姆雷
凱爾泰斯·伊姆雷1929年11月9日,凱爾泰斯·伊姆雷生於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一個猶太人家庭。
1944年夏,凱爾泰斯被關進了德國納粹設在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後來又被轉移到德國境內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1948年被盟軍解救並返回布達佩斯。
1946年起,凱爾泰斯在布達佩斯《火花》報社擔任記者,1953年開始了自由撰稿人生涯。凱爾泰斯曾長期從事文學翻譯工作,主要翻譯德國作家的作品,這對他後來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
20世紀60年代,凱爾泰斯開始創作處女作《命運無常》,1975年,《命運無常》經過十年周折得以出版。凱爾泰斯還先後寫過三部音樂輕喜劇,並獲得成功。
 凱爾泰斯·伊姆雷
凱爾泰斯·伊姆雷2002年,凱爾泰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晚年凱爾泰斯和太太移居柏林,後又返回匈牙利。
2016年3月31日,凱爾泰斯·伊姆雷在布達佩斯的家中去世,享年86歲。
2016年4月22日,凱爾泰斯·伊姆雷的葬禮在布達佩斯最知名公墓菲烏邁伊路國家公墓舉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德國聯邦議院議長拉默特以及匈牙利政府官員、文化界人士等數百人出席了葬禮。
主要作品
| 作品名稱 | 作品類別 | 創作時間 |
| 《命運無常》 | 長篇小說 | 1975年 |
| 《尋蹤者》 | 中篇小說 | 1977年 |
| 《慘敗》 | 長篇小說 | 1977年 |
| 《為了未誕生孩子的祈禱》 | 長篇小說 | 1990年 |
| 《英國旗》 | 中篇小說 | 1991年 |
| 《船夫日記》 | 日記 | 1992年 |
| 《大屠殺是一種文化》 | 文集 | 1993年 |
| 《筆錄》 | 中篇小說 | 1993年 |
| 《另一個人》 | 日記 | 1997年 |
| 《行刑隊子彈上膛一刻的死寂》 | 文集 | 1998年 |
| 《被放逐的語言》 | 文集 | 2001年 |
| 《命運無常》 | 電影文學劇本 | 2001年 |
| 《清算》 | 長篇小說 | 2002年 |
| 《K檔案》 | 自我對話錄 | 2006年 |
| 《世界公民與朝聖者》 | 短篇小說 | 2007年 |
| 《歐洲的沉鬱遺產》 | 文集 | 2008年 |
| 《表述的歷險》 | 文集 | 2009年 |
| 《哈爾迪曼書信》 | 書信集 | 2010年 |
| 《另外儲存》 | 日記 | 2011年 |
| 《最後的酒館》 | 日記 | 2014年 |
以上參考
創作特點
主題
 凱爾泰斯·伊姆雷
凱爾泰斯·伊姆雷大屠殺是凱爾泰斯小說永恆的主題。凱爾泰斯的作品儘管內容各不相同,但實際上都從各個不同角度傳達著同一個主題———大屠殺,在凱爾泰斯的作品中,大屠殺從來無法用過去時態表現。他認為生存就是屈從,作家不可能創造一個比上帝所創造的還要愚蠢的世界。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苦難經歷,讓伊姆雷一輩子都帶著倖存者的記憶活著。他似乎用餘生的寫作在反思這場慘絕人寰的人類災難,在他的許多作品中,對生與死,對看似對立的兩者作出過精妙的評論。凱爾泰斯的作品探究了在一個個人對社會權力的附屬走到極端的時代,個體生命繼續生存和思考的可能性。他在作品中堅忍地重返自己生命中決定性的事件:在奧斯維辛的歲月。在納粹對匈牙利猶太人進行迫害的狂潮中,少年凱爾泰斯被投入了此集中營。對他而言,奧斯維辛絕非存在於西歐正常歷史體系之外的一次異常事件——它是有關現代社會中人類退化的一次最本質的真相。
凱爾泰斯在作品中以親歷者的敘述,揭露了強權對人性的壓迫和對人生的剝削,放到特定的歷史背景中,以毒氣殺人的集中營和以全面控制使人窒息的社會之間便建立起了一種讓人絕望的聯繫。凱爾泰斯書中另一個主題是凱爾泰斯對自己身份的反覆思考。1975年,他否認自己是猶太人,不然就會因為這個身份及其命運而“否定所有人類的尊嚴,否定安全感,否定寧靜的夜晚,否定平和的精神生活,否定因循守舊,否定自由選舉,否定民族的驕傲”。但十年後,在幾個荷蘭人問他是否是匈牙利人時,他卻用德語承認自己是猶太人。到了1991年,他想明白了他是那個被作為猶太人遭受迫害的人,但是,不是猶太人。作者本人既不願接受歷史事實和他的猶太身份,又難以忘懷那段決定了他一生的過去。作者在作品中表現出了一種強烈的悲觀宿命論色彩,在潛意識下所不得不一直延續著奧斯維辛主題。
 2007年近照
2007年近照從奧斯維辛倖存的凱爾泰斯·伊姆雷的日記,所有的寫作都指向了死亡的終極追問。不斷地寫作,或許成為了他擺脫或尋找苦痛的一種辦法。在日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凱爾泰斯·伊姆雷如何創作自己的作品,如何通過翻譯維持生計,更多的時候,不是看他如何活著,是看他如何死去。既然活著如同死去,這種生存事實上就為作家的寫作提供了另外一個維度,從死亡的角度寫作。但與小說不同,他在日記中苦苦追索人生的終極意義,甚至不惜為之進行偏執狂般的思考。他大量引用歌德、叔本華、尼采、卡夫卡、加繆和伯恩哈德等人的觀點,並與這些先哲對話。曾經在生死邊緣徘徊過的他,對生死問題早已看得透徹,所以他說:“對我來說,最適當的自殺——看起來就是生活。”那些家國之痛,也僅僅化作一句毫無歸屬感的“我的國家,就是流亡”。儘管曾置身於德國人的殘酷壓制下,但凱爾泰斯·伊姆雷始終與同時代的匈牙利知識分子一樣,受德國文化影響極大。
風格
 凱爾泰斯·伊姆雷
凱爾泰斯·伊姆雷凱爾泰斯的寫作風格具有極為典型的後現代派特徵,擅長以內心獨白的意識流手法,於時空交錯之中,把各種支離破碎的畫面無序、零亂地組合在一起,呈現於人們眼前。其小說的內容往往充滿了悖謬和荒誕,讀來極易讓人產生疑惑和不解。如《無命運的人生》中的少年,雖身陷納粹集中營,卻對裡面發生的一切並不反感,他不僅自然地接受了命運的安排,而且偶爾還會產生某種讓他重返社會後依舊懷念的幸福感。在《給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禱告》一書里,作者也描寫了一個倖存者聚會時玩的遊戲:每個人爭相自報曾經待過的集中營地名,看誰最牛,結果竟是喊出“奧斯威辛”的人成了比賽的贏家。而對“二戰”的倖存者來說,這一切原本應該和不堪回首的痛苦記憶聯繫在一起,可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地名居然被當作非凡的經歷來炫耀,讓人如數家珍般的引以為豪。與通常揭露、聲討“二戰”期間納粹排猶迫猶的作品不同,凱爾泰斯對那段恐怖經歷的文學處理,類似於一種不帶感情色彩的白描,將殘酷的事實如同日常生活的場景娓娓道來,字裡行間似乎看不出痛斥、鞭撻和譴責之意。這種反常變異的寫作手法,使得他的主要作品被貼上了“平靜的大屠殺文學”的標籤。其實水靜則深,看似平淡的表面下,潛藏著砭骨鑽心的痛苦和悲哀。作者要告訴人們的正是,當這種恐怖已被人習以為常、司空見慣到了對其麻木不仁甚至深感幸運的地步,那才是最殘酷最恐怖不過的事情。
 凱爾泰斯·伊姆雷
凱爾泰斯·伊姆雷凱爾泰斯·伊姆雷的作品不屬於好讀的那種,他艱深的思想及冷靜的文字,甚至擋住了很多文學愛好者的閱讀熱情。在凱爾泰斯的眼裡,集中營里發生的一切都很自然,儘管環境惡劣,但也並非沒有幸福的時光。正是這一類題材通常所需要的道德憤慨和形而上之抗議的缺席,反而使作品充滿開放性以及疑懼的玩笑。
凱爾泰斯·伊姆雷歷經苦難仍內心平和,並以旁觀者的心態靜觀自己的命運。凱爾泰斯·伊姆雷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勇於面對過去與創傷,也勇於面對現實的一切暗面。採取第一視角的小說,筆調平靜,時而流露天真,甚至會發現集中營里一些小幸福,如人與人之間的友情,如仰望天空,又如飢餓時傳來的蘿蔔湯香氣。凱爾泰斯·伊姆雷認為集中營是異常複雜的場域,善惡並不那么涇渭分明,反抗與妥協同樣不是兩個極端,其中有許多難解的迷惑與人性的幽光,單純的批判也許並不能說明所有問題。,他始終拒絕情緒化。作為一個經歷過兩種極權政治的人,他沒有小清新式的人文感動,也沒有一邊倒的憤怒,而是數十年如一日地告訴我們,當一個人在無法選擇的情況下,該如何面對自己的生命。
獲獎記錄
| 文學類 |
|
| 榮譽類 |
|
以上參考
人物評價
 凱爾泰斯·伊姆雷
凱爾泰斯·伊姆雷“他(凱爾泰斯)作品的主題連續不斷地返回到給他的生命帶來決定性影響的奧斯維辛經歷之中。對於凱爾泰斯而言,奧斯維辛並不是存在於西方歷史之外的一個例外的事件。奧斯維辛是現代生存方式中人類墮落的最為根本的真實的表現。”“(諾貝爾文學獎)表彰他對脆弱的個人在對抗強大的野蠻強權時痛苦經歷的深刻刻畫,以及他獨特的自傳體文學風格。”—— 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
“少年時代,他被‘弱智’的祖國送進奧斯維辛;青年時代,他被專制的祖國剝奪了個人命運;壯年時代,他經歷了屢次退稿和被迫的喑啞;老年時代,雖幸遇改革,但當他作為‘匈牙利作家’被邀請到德國講學時,自己的政府卻表示他不能代表他的國家。”“在獲得諾獎的作家中,他不是走紅的那種諾獎作家,但他是一個選得對的作家。因為沒有諾獎,他就會被忽視,他就會消失。這就是諾獎的意義。諾獎選10個作家,只要能有一個像凱爾泰斯那樣的作家,就是有意義的。”—— 餘澤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