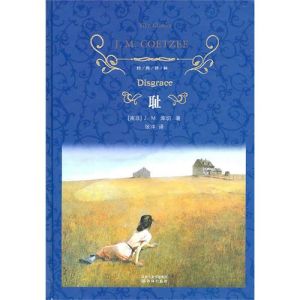前言
越界的代價庫切(J.M.Coetzee,1940— )是南非當代著名小說家,自1974年起,先後出版了《幽暗之鄉》(Dusklands,1974)、《國之中心》(IntheHeartoftheCountry:ANovel,1977)、《等待野蠻人》(WaitingfortheBarbarians,1980)、《麥可·K.的生平與時代》(LifeandTimesofMichaelK.,1983;獲1983年布克獎)、《敵人》(Foe,1986)、《鐵的時代》(AgeofIron,1990),以及《彼得堡的主人》(TheMasterofPetersburg,1994)等多部小說,被評論界認為是當代南非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99年,他完成並出版了小說《恥》,作品為他再次贏得了標誌小說創作成就的英國布克獎。在這部作品中,庫切以幾乎不加藻飾、令人心怵的筆調,講述了開普技術大學文學與傳播學教授,五十二歲的戴維·盧里的故事。小說情節主要由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以盧里的一樁醜聞(勾引了一位大學二年級女生並與之發生性關係)為主線。事發後,盧里拒絕了校方給他的公開悔過以保住教職的機會,來到邊遠的鄉村,他在那裡和幾乎是獨自謀生的女兒露茜的共同生活形成了情節的第二部分。此時他不僅要努力與多年不在一起生活的女兒溝通,還要和許多他以前根本就看不起的人共事,要做他從前想都不會去想,而且肯定會嗤之以鼻的事情,例如在護狗所里打雜。小說的第三部分是全書情節最直接給讀者以震撼的部分:露茜遭受了農場附近三個黑人的搶劫和蹂躪,而其中一人居然還是個孩子;盧里也在這一事件中受傷。事件本身,事後父女兩人和其他有關的人對事件的態度及處理方法,傳達著作品的主要信息。而盧里創作歌劇《拜倫在義大利》的努力穿插在小說各處,與主情節若即若離,似乎總在向讀者暗示著什麼,這是第四部分。故事結尾時,搶劫強姦案不了了之,露茜懷孕,盧里要寫的歌劇始終還在腦海里縈繞,同時,他還最終放棄了“拯救”一條終將一死的狗的生命的企圖。
庫切的作品大都以南非的殖民地生活和各種衝突為背景,《恥》也不例外。不少評論認為,《恥》這部作品通過各種細節描寫,揭示了新舊交替時代發生在南非大地上,發生在南非各色人等之間的種種問題,對殖民主義在南非對殖民地人民和殖民者本人及其後代所造成的後果表現出深切的憂思和相當的無奈。然而,正如有評論指出,《恥》是一部從內容到寓意都具有十分豐富的層次的作品,單從小說題目“恥”來說,就有“道德之恥”(盧里的數樁風流韻事所指的道德墮落),“個人之恥”(女兒遭強暴搶劫),“歷史之恥”(身為殖民者或其後代的白人最終“淪落”到要以名譽和身體為代價,在當地黑人的庇護下生存)等等意義。小說情節敷演到後半部時,從鄉下回到城裡的盧里又一次聽到了他醜聞案中的受害者——那個叫梅拉妮的女孩子的名字,心裡一陣悸動。可是這一次,他立刻警覺起來,“篡越與和諧結合,這太有違正常了”。他突然明白了醜聞初現時學校里組織的聽審會的意義:“要是把審判時所用的漂亮辭藻全數剝去,審判要懲罰的正是這樣的結合。”庫切在這裡用了Cronus來表示“篡越”的意思,而該詞是希臘神話中天神與地神的兒子,他陰謀篡位統治世界,後來被自己的兒子宙斯廢黜。在這裡,“篡越”也許正是解讀庫切這部寓意豐富的作品的一個切入點。
事實上,如果我們把“篡越”理解為廣義上的“非法越界”,即隨意超越政治、社會、道德等為個人所規定的界限的話,這樣的越界在《恥》中比比皆是,而且在各種各樣的關係層面上反映出來。盧里教授對女學生梅拉妮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正是一種雙重意義上的“越界”:他越過了被社會認可的師生關係界線,同時也越過了被傳統習俗認可的長幼界線。盧里是大學教師,教室里的講台就給他在人際關係中定了位。而在師生關係中,教師因其年齡、地位、學識、經歷一般總是處於強勢地位,是握有權力的一方,學生則處於弱勢。小說中的盧里,不顧梅拉妮反對往她的飲料里加烈酒,私闖後者的住處,私自改動後者的缺席記錄乃至考試成績(梅拉妮沒有參加考試,盧里仍然給了她70分的成績)等行為,明顯是在濫用自己的權力。而他對作為弱勢一方的梅拉妮的勾引,完全是他利用自己的強勢力量,越過了師生界線的行為。他為此受到懲罰完全是咎由自取。
然而庫切似乎並沒有把這一事件完全放在道德層面來討論。平心而論,盧里在第一次和梅拉妮發生性關係之後,開始隱隱體會到一種從前沒有過的激情,最後一次同梅拉妮在一起時,他還感覺到對方似乎在(下意識地)做著某種配合,他後來甚至還動過越界之後認真對待兩人關係的念頭。然而,梅拉妮男友的出現,給他的這一想法當頭一盆冰水,五十二歲的男人同二十歲的女孩子之間,是不能——也不允許——有什麼事情發生的:年齡差距本身就為他們劃下了界線。他的越界行為,單從社會習慣上看就不能被接受。其實,盧里最後很不情願地明白了這一點:對他的聽審實際上審的是“篡越”(五十二歲的教師)與“和諧”(二十歲的女學生)的結合,是“對他生活方式的審判。因為他的行為有違正常,因為他試圖傳播上年紀的種子,傳播疲乏的種子,傳播缺乏活力的種子,有違自然”。小說後半部里,他從鄉下回到開普敦,聽說梅拉妮排的戲已經上演,忍不住動了再去看她一眼的念頭,卻在戲院里被其男友發現,一句“和你自己一類人呆著去”讓他放棄了對梅拉妮的最後一點慾念。
其實,即使在同妓女索拉婭的交往中,盧里也本該認識到越界的“代價”的。小說一開始就描寫了盧里每周在索拉婭那裡度過一個下午,兩人還算和諧,但從不相互過問對方的事情。直到有一天,盧里走過一家餐館時,看見了坐在裡面的索拉婭,她還帶著孩子。索拉婭從此在他生活中消退、消失了。撇開這一細節的道德考慮,它似乎在告訴讀者,即使在這樣的人際關係中,仍然有界線存在。無論你是有意還是無意,只要越界,其代價就可能是這種關係的終結。索拉婭本身的生活就是有界線的,“也許她不過每周替代理公司乾一兩個下午,其餘時間則在郊外,在賴蘭茲或阿思隆,過著體面的生活”。與盧里的不期而遇威脅著她生活中的這種劃分,抽身退出是十分本能的自我保護行為,而盧里仍不罷休,甚至雇了私家偵探去尋找其蹤跡。這種過分的越界行為,最終使索拉婭永遠從他生活中消失。
小說著力描寫的幾條線索中,盧里和女兒露茜的關係也是較重要的一條。在這裡,“越界”的問題同樣呈現出豐富的層次。首先自然是父女關係。當盧里來到女兒在邊遠鄉村的小農場後,發現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對事情的看法,自己同女兒之間橫隔著很深的界溝,而且露茜似乎不太願意讓他闖進自己的生活和內心。對於女兒的“自甘墮落”,心甘情願地在偏僻鄉村當農民,盧里十分不滿意,感到這是自己的恥辱:大學教授的女兒竟落到這種地步。因此他幾次三番想闖進露茜的生活,說服她改變現在的生活方式,賣掉農場,跟他回大城市開普敦去。然而他發現,哪怕同露茜推心置腹地談談都很困難,露茜似乎在牢牢守著自己的領地,不讓父親跨進去。盧里每一次“越界”的嘗試,幾乎都以父女兩人的爭吵告終。小說作者庫切以第三人稱發出感嘆:“為什麼別人不劃界限,他們自己卻要相互劃出界限呢?”漸漸地,盧里也感到要想在一個屋頂下和平共處,遵守界線的約定似乎是一種必須:“他得小心點,別讓老習慣不知不覺中又溜了回來,那做家長的習慣:什麼別忘了用完擦手紙後把它放回捲筒架上去啦,人走關燈啦,別讓貓上沙發啦,諸如此類的。”即使是做父親的,也不能隨便越界進入女兒的生活。
盧里和露茜間越界和抵禦越界的衝突在露茜遭遇強暴後表現得尤為激烈。施暴歹徒剛一離開,盧里就趕緊去看看露茜到底怎么樣了。可任他拚命敲門,露茜許久都沒有把門打開;當她最終開門出來的時候,已經穿戴整齊,受蹂躪的痕跡不很明顯了。更令盧里無法理解和接受的是,露茜一再堅持不報案,並且遲遲不把當時的真相告訴盧里。在這段情節發展中,兩人的關係已不僅是父女,而泛化成男女兩性之間的關係了:女性自有其生活的界線,有權利不允許男性進入,任何形式的違背女性意願的越界,都是對女性權利的侵犯。對女性的強暴就是一種殘忍的、極端的越界,強暴具有同性戀傾向的女性更令人髮指;然而從一定意義上說,盧里在事後再三詢問露茜,希望她說出事實真相,實際上也是一種越界企圖,試圖重新打開露茜因受暴力越界而緊閉的情感之門,進入露茜的生活,而露茜則明白地告訴父親:“這與你沒關係……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完全屬於個人隱私。換個時代,換個地方,人們可能認為這是件與公眾有關的事。可在眼下,在這裡,這不是。這是我的私事,是我一個人的事。”一句話,不要越界。
越界與否似乎成了盧里和幾個女性之間的關係的內容:與索拉婭,因他先偶然而後故意的越界而中斷;與梅拉妮,由於他強行越界而受到懲罰;與露茜,他的越界企圖時時受到抵制,甚至他一向看不起的貝芙(露茜的一個朋友),當他試圖向她詢問露茜遭強暴後的情況時,對方用一個搖頭,明白無誤地告訴他:“這不關你的事。”——不要越界。難怪幾經挫折的盧里最後被激怒了:因為他感覺自己完全被當成了局外人,他想進入露茜生活的所有努力都失敗了。
上文里露茜告訴盧里,“在眼下,在這裡”,她被強暴完全是她的私事時,盧里反問道,眼下是什麼時候?這裡是什麼地方?露茜回答,眼下就是現在,這裡就是南非。這句話,立刻使發生在個人生活層面上的事件帶上了強烈的歷史和社會色彩:這一切,都發生在殖民主義消退、新時代開始的南非;而這樣的時代和社會背景(在小說中其實是前景),更使越界的主題具有了超越個人經歷的更普遍、更深刻的社會、政治和歷史意義。
在某種意義上,在偏僻鄉村裡的那個農場上的露茜,指稱的正是歐洲殖民主義,而從根本上說,殖民主義就是一種越界行為:它違反對方意願,以強制方式突破對方的界線,進入對方的領域,對對方實施“強暴”。不過,庫切的注意力似乎並不在回顧殖民主義對南非的越界這一歷史問題上,他真正關注並通過小說中各種細節來表達的,是對歷史上的越界在當前現實中的後果的思考,對越界的代價的思考,而這一思考同樣具有豐富的層次和深刻的意義。
殖民主義越界的代價首先在最為個人的層次上表現出來,那就是露茜遭遇強暴這一事件。露茜事後回想起來,令她最感可怕的是,施暴者似乎並不是在宣洩情慾,而是在噴發仇恨,一種產生報復的快感的仇恨。她的感覺是正確的,但她可能並不十分明白,這股仇恨中積澱著歷史和民族意識。那三個黑人要報復的並不是露茜這一個人,而是她所指稱的整個殖民主義。他們要像當年白人殖民者“強姦”南非(非洲大陸)那樣強姦(露茜所指稱的殖民主義者)白人。這樣來看,露茜這時候不去報案,理由恐怕不僅是個人的,更深層的原因很可能是:當殖民主義勢力在南非消退時,殖民者賴以庇護的那一整套社會建構也隨之而去,報不報案,結果沒有兩樣。報案的目的是索求賠償,可這是殖民主義欠了南非的、應付的代價,根本不存在什麼(向南非)索求賠償的問題。當然,小說中的露茜不一定能看清這一層;但是,從白人鄰居善意卻毫無意義的幫助,警察笨拙、遲緩、荒唐的反應等細節來看,露茜被強暴的實質是:她成了殖民主義的替罪羊,是殖民主義越界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就像盧里同他前妻爭論時所說,神死了,需要有具體的實在的人或物來替罪。他這么說是在為自己辯護,可不幸卻應在了女兒露茜身上。
其實,白人殖民者更是在總體上為他們的越界付出了代價的。一方面,越界進入非洲(南非)的殖民者顯得十分孤單。露茜的農場遠在偏僻的鄉村,處於當地黑人的包圍之中,簡直就是一塊殖民飛地。在佩特魯斯慶祝建新居的晚會上,盧里和露茜形影相弔,是惟一的兩個白人,其處境十分尷尬,和周圍的環境很不協調。更重要的是,白人不僅在(農業)裝備良好、經驗豐富的當地人面前節節後退,農場朝不保夕,連自己的地位都悄悄發生了質的變化:從前聽慣了“老爺”一類的稱呼,現在卻完全倒了過來:曾經是大學教授的盧里,曾經是僱主的露茜,現在一個給佩特魯斯打下手,另一個不得不以自己的身體和尊嚴為代價,做“前幫工”佩特魯斯的第三個老婆,為的是能留在農場上(除了農場她還能去哪裡,做什麼?)。為追查強暴女兒的元兇,盧里對佩特魯斯緊追不捨,可後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對他的追問置若罔聞,裝聾作啞。對此,盧里十分惱怒,可又無計可施。他不由得感嘆道,要在過去,一句話就能讓佩特魯斯丟了飯碗;可他清楚地,也很悲哀地意識到,這是現在,表面低聲下氣的佩特魯斯,手裡正捏著他女兒,甚至是他自己的命和前途,如果他們還有什麼前途可說的話。回想起盧里剛到鄉下,聽說要讓他給佩特魯斯打下手時,他自我解嘲地說,他喜歡這具有歷史意味的刺激。其實,喜歡倒不一定,刺激是會有一點的,歷史意味肯定很濃:那是歷史的反諷——殖民者突然發現,自己的身份和從前的被殖民者換了位置!
最後,似乎殖民主義在殖民地所代表的整個西方(歐洲)文明也為這樣的越界付出了代價:盧里的滿腹才能、滿口外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等)在遇到突發情況(家裡遭搶劫、女兒遭強暴)時,什麼用場都派不上;他動不動要求得到正義的呼聲如對牛彈琴;他在佩特魯斯家的聚會上撞見了施暴嫌疑人,立刻想打電話叫警察這樣典型的西方式反應,顯得那么滑稽可笑而又蒼白無力;作為有西方文化教養之人,他居然沒想到參加正式聚會應當戴條領帶,如此等等。甚至連西方文明和殖民文化的載體,本身就具有一種力量,並賦人以某種權勢和力量的英語,在南非這塊大地上也失去了明晰性,用小說中盧里的話來說,變得像頭陷在泥潭裡的恐龍,僵硬而不自然,又像是被白蟻蛀空了內容,說出來空洞無物。真正有力量的,真正能恰當真實地傳達人在此時此地的思想感情的,仍然是當地的土語。這樣,越界進入非洲(南非)的西方文明從根基到形式,都被消解掉了。
庫切的筆調是震撼人心的,庫切的思考是嚴肅的,庫切提出的問題是發人深思的,但庫切似乎並不想下什麼結論。個人之間也好,社會形態之間也好,進而文明之間,文化之間,都各有其界限,強行越界,代價是一定要付的。但是,這是不是意味著個人之間,社會形態之間,文明或文化之間,就一定不可能相互進入呢?相互的界限是不是一定不可逾越呢?庫切提出了問題,把尋求回答的事留給讀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