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鼠疫》
《鼠疫》作者簡介
生平:
長篇小說《鼠疫》的作者
 《鼠疫》
《鼠疫》加繆1935年開始從事戲劇活動,曾創辦過劇團,寫過劇本,當過演員。戲劇在他一生的創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劇本有《誤會》(1944)、《卡利古拉》(1945)、《戒嚴》(1948)和《正義》(1949)等。除了劇本,加繆還寫了許多著名的小說。中篇小說《局外人》不僅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荒誕小說的代表作。該作與同年發表的哲學論文集《西西弗的神話》 ,在歐美產生巨大影響。長篇小說《鼠疫》(1947)曾獲法國批評獎,它進一步確立了作家在西方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因為他的重要文學創作以明徹的認真態度闡明了我們這個時代人類良知的問題”,1957年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60年春,加繆乘坐伽里瑪駕駛的汽車出遊時,翻車身亡,時年四十七歲。
加繆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義者,儘管他自己多次否認。1951年加繆發表了哲學論文《反抗者》之後,引起一場與薩特等人長達一年之久的論戰,最後與薩特決裂,這時人們才發現,加繆是荒誕哲學及其文學的代表人物。
特色:
加繆的創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極其客觀地表現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筆簡潔、明快、樸實,保持傳統的優雅筆調和純正風格。他的“小說從嚴都是形象的哲學”,蘊含著哲學家對人生的嚴肅思考和藝術家的強烈激情。在短暫的創作生涯中,他贏得了遠遠超過前輩的榮譽。他的哲學及其文學作品對後期的荒誕派戲劇和新小說影響很大。評論家認為加繆的作品體現了適應工業時代要求的新人道主義精神。薩特說他在一個把現實主義當作金牛膜拜的時代里,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作品:
《誤會》 、《卡利古拉》 、《戒嚴》 、 《正義》 、 《局外人》 、 《西西弗的神話》 、《鼠疫》等。
內容簡介
《鼠疫》是一部寓言體的小說。它是一篇有關法西斯的寓言。當時處於法西斯專制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一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長期過著與外界隔絕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著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繆繼續他的存在主義主題: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加繆自己曾這樣說:“《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已;《鼠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儘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但是從《局外人》到《鼠疫》加繆的思想已經發生了變化。里厄醫生不再如莫爾索那樣對一切都漠不關心,他與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展開鬥爭,而且在鬥爭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的幸福。里厄醫生的人不是局外人,他看到了只有道德高尚、勇於奉獻畫的人聯合起來戰勝瘟疫,人類社會才有一線希望。
《鼠疫》的作者雖然具有明顯的局限性,但能形象地反映他那個時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這部小說在藝術風格上也有獨到之處,而且全篇結構嚴謹,生活氣息濃郁,人物性格鮮明,對不同處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變化刻劃得深入細緻;小說中貫穿著人與瘟神搏鬥的史詩般的篇章、生離死別的動人哀歌、友誼與愛情的美麗詩篇、地中海海濱色彩奇幻的畫面,使這部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
創作背景
 《鼠疫》
《鼠疫》思想價值
加繆在《鼠疫》的開篇引用了了《魯濱孫飄流記》的作者,英國十八世紀著名作家丹尼爾·笛福說過的一句話:“用另一種囚禁生活來描繪某一種囚禁生活,用虛構的故事來陳述真事,兩者都可取。”
《鼠疫》是加繆的第二部最有影響力的小說,它描述的是在北非的一個叫奧蘭的小城發生的一場持續了將近一年的鼠疫之災。作者生動的描寫了在那個恐怖的時期,人們經歷的從肉體到精神的折磨,以及對幸福和安寧的渴望之情。主人公們不斷遭受著鼠疫對他們在精神上的折磨,而仍能用“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力量面對死神。最後,鼠疫消滅,小城重獲自由,而里厄終於獲得內心的平靜。加繆把在納粹鐵蹄下慘遭蹂躪的法國搬到了小城奧蘭,而把那殘酷的戰爭轉換為了肆虐的鼠疫。不過,這些變換並不妨礙作者重塑人們在與世隔絕的恐怖氣氛下的恐懼、焦慮、痛苦以及生離死別的心情。故事開始引用的的“用另一種囚禁生活來描繪某一種囚禁生活,用虛構的故事來陳述真事,兩者都可取”就表明了作者的意圖。而故事中,主人公里厄和他的朋友塔魯面對鼠疫的種種態度正代表了加繆本人的對待戰爭和奴役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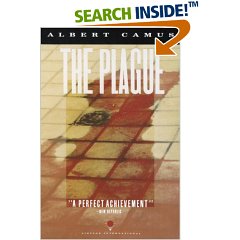 《鼠疫》
《鼠疫》從《局外人》到《鼠疫》,加繆表現了一些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獨,活著沒有意義。因此,加繆雖然再三否認自已是存在主義者,西方文學史家仍然把他列為這一流派的作家。加繆自己曾這樣說:“《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已;《鼠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儘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這部後期代表作中,表現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變。《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醫生面對著同樣荒謬的世界時,態度就完全不同:莫爾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連對母親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著局外人的態度;里厄醫生在力搏那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時,雖然有時感到孤單絕望,但他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就是跟那吞噬千萬無辜者的毒菌作鬥爭,而且在艱苦的搏鬥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幸福。里厄醫生不是孤軍作戰,他最後認識到只有通過一些道德高尚、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無忌憚的瘟神,人類社會才有一線希望。
加繆的存在主義哲學不象薩特和海德格爾的那般艱深,至少在這篇小說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認為世間的混亂和荒謬是必然的,人作為一種存在,是沒有他的必然的意義與目的的。在故事中,加繆描寫了一個神甫的兩次布道,從而否定了宗教的可以帶來的意義。他通過主人公的態度表明了一個人面對虛無的人生的態度,就是以愛情、友誼和最重要的--同情心來充實內心。
存在主義本身就否定了“意義”,把人放逐到了荒蕪的沙漠。可是和這種哲學相反,存在主義哲學家往往都是“良心”的虔誠追隨者。薩特的洋洋巨著《存在與虛無》用了90%以上的篇幅來論述存在,來論述自由的本質,卻只用最後很短的章節來幫助人們重鑄道德。不難看出,薩特和加繆一樣,強烈的個人主義思想,以及強調“自由”的本質導致了了他們的存在主義,使他們放棄了一切信仰,而用內心的同情和愛,以及正義、美和幸福來構築生活賴以生存的基礎。但這種補償相對於之前的放棄來說,的確是微弱了一些。
存在主義之“放棄”,只有象加繆這樣的人物才能承受的住!
在西方,早已放棄了信仰,“虛無主義的復興”在20世紀使整個西方的文化遭受了絕望的打擊。只需要看看那世紀末的西方文明,看看那每日在電視上,銀幕里,畫廊中反覆出現的影像,收音機,唱片,CD不停的播放的聲音,以及與日俱增各種社會問題。全世界人們面對的是,似乎可以掌握自己命運的時代到來時,他們卻發現,無事可做!
很多人認為存在主義導致了信仰的放棄,或者至少是放棄了重新抓住信仰的機會。相反,正是因為信仰的消失,存在主義提供了人們另外一條道路,雖然這是一條置身在荒漠之中的小路,但是它仍然是有希望的。
困難源於個人,也只有個人本身可以解決。加繆寄希望於人的感情和激情,雖然那可能是很脆弱的。但他正是用他心中無限的愛,道德感,友情鋪成了這樣一條路,可以說,這就是他的信仰。
“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的環境似乎遠離了加繆在“鼠疫”中描述的那種情境。那時外部造成的巨大壓力和恐懼使放棄信仰的人類無以依靠,加繆唯以存在主義的人道精神當作火把去照亮前路。而如今,世界已無這樣的威脅(當然,不是絕對的),我們怎樣生存呢?20世紀60年代以來,存在主義的黯淡,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興盛表明,在和平時期,尤其是在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西方,人類在迷失的路上已經走到了盡頭。
 《鼠疫》
《鼠疫》批判存在主義的人們往往看到的只是存在主義的前提,但是這個前提往往是每個人都面對著的。這是無法迴避的,就象每個存在主義哲學家說的--是“本質”。而存在主義的核心--那個面對世界的“良心”,卻正是我們這些人,所缺少的。,存在主義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至少,當你理解了它,再去思考你面對的這個世界,你可以清楚的了解到你需要做些什麼。
影響評價
“他作為一個藝術家和道德家,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表現了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
—— 瑞典文學院授予加繆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辭
“加繆在荒誕的車禍中喪身,實屬辛辣的哲學諷刺。因為他思想的中心是如何對人類處境做出一個思想深刻的正確回答……人們毫不感到意外,我們的時代接受了加繆的觀點。血腥的再次世界大戰,可怕的氫彈威脅,這一切使現代社會能夠接受加繆嚴肅的哲學,並使之長存於人們的心中。”
—— 《紐約時報》
“《鼠疫》是個偉大的預言, 很少有人讀過它而無動於衷,這是為什麼?恐怕是加繆用了最簡單的語言敘述了一些普通人面對一場災難時一些最簡單的行為吧。引人入勝、瑰麗奇異、慷慨激昂當然也會使我們感動,但是這種感動不大會持久。真正能使我們的心靈深處燃燒起來的,還是戰勝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的平凡的、每日都在進行工作的人們。”
——周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