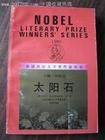作品介紹

《太陽石》一方面繼續在聶魯達開創的道路上探求,紮根於印第安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以一種更開闊的世界眼光,表現出印第安文化與西方文明的對話和溝通。(耐人尋味的是,在博爾赫斯的詩歌和小說中,少有印第安文化的影響。)
太陽石是古代墨西哥阿茲特克人的太陽曆石碑,1470年至1481年刻鑿而成,1790年出土於墨西哥城,是印第安文化的象徵。《太陽石》的結構,是根據印第安人神話的圓形時間來構思。但內容則是對“一個代、一個國家、一個時期的人不可重複的歷史”的沉思(即對西方文明的線性時間的反思):作為個體的人,只有一次不可重複的生命,但其生命的存在,在永恆的時間中只不過是瞬間;即便是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偉大人物和事件,也不過是眨眼的片刻。但是在每個個體身上,又包含著作為人類全體的可以不斷重複的基本體驗:愛情和死亡。也就是說,瞬間與永恆同時並存於個體的生命之中。(這就像印第安神話中的星星、鳥和蛇,可以是同一物。)
時間是《太陽石》的主題。對瞬間與永恆這種既矛盾又同一的令人困惑的現象的反覆沉思,就成為推動《太陽石》圓形時間不斷循環的內在動力。裹挾著敘事者個人回憶的人生碎片,和人類歷史上偉大事件的瞬間,而不停循環的永生的圓形時間,就成了這部世界詩歌經典的奇觀。因為在這之前,從不曾有人這樣寫過。
帕斯雖然是以印第安神話循環永生的圓形時間來構思,但不是簡單地認同,並否定其它不同文明的時間觀;而是以此為一元,並與西方文明的線性時間觀相比較,進行對話和交流,展示了多元文化的豐富和複雜。這種多元並置的思考,正是後現代主義的基本方法。實際上,也是對人類三個古老的哲學難題:時間、自我、生死,進行全新的思考。
《太陽石》不僅是時間性的結構,而且是史詩性的結構。因為它是在不同文明的不同時間觀的交叉中,重新沉思人類的基本境遇,具有博大的世界意識,以及集大成式的現代技巧。
《太陽石》中譯本已有四種。前三種系翻譯家所譯,最新的一種為著名詩人蔡其矯所作。蔡其矯有豐富的譯詩經驗,他翻譯過惠特曼、聶魯達、埃利蒂斯的詩作,曾受到詩界的讚譽。2000年所譯的《太陽石》,更是呈現出一種爐火純青的功夫。我想,凡是吟誦過蔡譯《太陽石》的讀者,都會懷著敬意感謝這位83歲老詩人的艱辛勞作,因為他使我們更順暢地進入帕斯那美妙絕倫的藝術世界。
帕斯除了詩歌以外,還創作了大量的隨筆和文論,具有廣泛的影響,被譽為百科全書似的作家。比如,他反對線性發展的時間觀。帕斯認為,那種把時間看成是無限發展和進步的時間觀,是錯誤的。“歷史進化論是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在社會領域裡的天真套用,是對歷史的生物性解釋。”帕斯認為:“歷史作為一種現象,其發展是無法預知的。歷史決定論是一種代價昂貴的血淋淋的虛構。歷史是無法預見的,因為作為它的主體的人本身並非個成不變。”
作者介紹
 奧克塔維奧·帕斯
奧克塔維奧·帕斯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Paz,1914~1998)墨西哥詩人、散文家。生於墨西哥城。父親是記者、律師,曾任墨西哥革命中著名將領埃米里亞諾·薩帕塔駐紐約的代表。母親是西班牙移民的後裔、虔誠的天主教徒。祖父是記者和作家,祖母是印第安人,帕斯的童年就是在這樣一個充滿自由與宗教氣氛的環境中度過的。帕斯從5歲開始學習,受的是英國及法國式教育。14歲即入墨西哥大學哲學文學系及法律系學習,閱讀了大量的古典和現代主義詩人的作品,後來又接受了西班牙“二七年一代”和法國超現實主義詩風的影響。1931年開始文學創作,曾與人合辦《欄桿》雜誌。兩年後又創辦了《墨西哥谷地手冊》。當時他對哲學與政治興趣很濃,曾閱讀大量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作品。1937年在尤卡坦米島創辦一所中學,在那裡他發現了荒漠、貧窮和偉大的瑪雅文化,《在石與花之間》就是那時創作的。同年他去西班牙參加了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會,結識了當時西班牙及拉丁美洲最傑出的詩人們。《在你清晰的影子下及其他西班牙的詩》就是在那裡出版的。回到墨西哥以後,帕斯積極投入了援救西班牙流亡者的工作,並創辦了《車間》和《浪子》雜誌。1944年赴美國考察研究。1945年開始外交工作.先後在墨西哥駐法同、瑞士、日本、印度使館任職。1953至1959年回國從事文學創作。後重返巴黎和新德里,直到1968年為抗議本國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而辭去駐印度大使職務。從此便致力於文學創作、學術研究和講學活動。主要詩作有《太陽石》(1957)、《假釋的自由》(1958)、《火種》(1962)、《東山坡》(1969)、《清晰的過去》(1974)、《轉折》(1976)、《向下生長的樹》(1987)等。其中《太陽石》是他的代表作,曾轟動國際詩壇。散文作品有《孤獨的迷官》(1950)、《弓與琴》(1956)、《榆樹上的梨》(1957)、《交流》(1967)、《連線與分解》(1969)、《仁慈的妖魔》(1974)、《索爾·胡安娜·伊內斯或信仰的陷附》(1982)、《人在他的世紀中》(1984)、《印度紀行》(1995)等。在《翻譯與消遣》(1973)中,他翻譯了我國唐宋一些詩人的作品。帕斯的詩歌與散文具有融合歐美,貫通東西,博採眾長、獨樹一幟的特點。1963年曾獲比利時國際詩歌大獎,1981年獲西班牙塞萬提斯文學獎,199O年由於“他的作品充滿激惰,視野開闊,滲透著感悟的智慧並體現了完美的人道主義”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同年出版了《作品全集》,《太陽石》、《假釋的自由》、《火種》、《東山坡》、《清晰的過去》、《轉折》、《向下生長的樹》、《太陽石》、《孤獨的迷官》、《弓與琴》、《榆樹上的梨》、《交流》、《連線與分解》、《仁慈的妖魔》、《索爾·胡安娜·伊內斯或信仰的陷附》、《人在他的世紀中》、《印度紀行》等,帕斯的創作融合了拉美本土文化及西班牙語系的文學傳統,繼承歐洲現代主義的形而上追索以及用語言創造自由境界的信念,在他的詩歌世界裡,強烈的瞬間經驗和複雜的歷史意識,個人的生命直覺和人類的文化傳統達到了強烈合一。他的後期詩作更自覺地將東西方文化熔於一爐,其詩作由繁複回到具體明澈,可以說是受到東方古典詩歌的啟示。他翻譯過王維、李白、杜甫等中國古代詩歌大師的作品。帕斯是1990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其代表作是1957年創作的長詩《太陽石》,時年43歲。
書籍評論
這是我有生以來最長的一次空中之旅——2008年10月9日,我和詩人楊四平、野賓經過15個小時的飛行,穿越太平洋,飛抵墨西哥城,參加第28屆世界詩人大會。我不喜歡開會,無論在國內或者國外,我都是一個逃會者,即使是詩歌研究會之類,超過一個小時,我也認為是一種懲罰和不尊敬。我去墨西哥的目的,除了想去領略、感受異域風光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試圖踏著奧克塔維奧·帕斯的足跡,尋找太陽石,在太陽石細密、複雜而又美麗無比的紋理中,尋找詩歌的光芒和核心。太陽石又稱阿茲特克石歷,1790年發掘於墨西哥城中心廣場,重24噸,直徑3.58米,對於帕斯來說,這無疑是一塊浸淫著月光和陽光的石頭,在苦釀和等待之中,1951年,他完成了584行的長詩《太陽石》,他在詩中這樣讚美它:“八月的雪,斷頭台的月亮/麥穗、石榴、太陽的遺囑/寫在火山岩上的海的字跡/寫在沙漠上的風的篇章……”帕斯出身於墨西哥城的一個書香之家,是印第安人與西班牙人的混血兒,書香與特殊的血統,造就了他的早慧、帥氣和日後成為國際公民的“宇宙氣質”。他19歲就出版了詩集《野生月亮》,不說“月亮”,單就“野生”這兩個字的界定,就可以看到帕斯對詞語的敏感和機智;23歲時在瑪雅文化發源地卡大坦半島創辦了一所中學,瑪雅文化的神奇和博大精深,讓帕斯著迷沉醉,這一年,他一邊教學一邊創作了詩集《在石與花之間》,再次奠定了他在墨西哥詩壇的地位。二戰爆發後,帕斯積極參與反法西斯戰爭,在血與火的洗禮中一手握槍,一手握筆,唱響了特殊年代裡的愛與和平之歌。戰爭結束,帕斯開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先後出使美國、法國、瑞士、日本、印度,與聶魯達、博爾赫斯、薩特、加繆等著名詩人、作家交往密切,共同切磋詩意,探討生死與貧富、短暫與永恆、過去與未來、戰爭與和平、地獄與天堂對人生和詩歌的影響,面對稍縱即逝的時間、虛無縹緲的天堂,帕斯以心中的血淚柔情,一次次呼喚並傳播著公正、平等、友愛和真善美。值得一提的是,帕斯博學厚愛,不僅對西方文化頗有研究,對中國文化也是情有獨鍾,他諳熟《周易》,喜歡《佛經》,翻譯過李白、杜甫和王維的詩,曾和艾略特合寫過一本《讀王維的十九種方法》。也可能是他與中國古詩古文的特殊關係,踏入墨西哥的土地,一步步走近帕斯,我的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帕斯去世於1998年4月19日,那天,我正和一批詩人朋友在北京798的一個咖啡屋裡小聚,立刻就有人朗誦起了帕斯的著名詩作《街》:“又長又靜的街/我身後有人緊跟/我慢,他也慢/我跑,他也跑/我轉身:沒人……”奧克塔維奧·帕斯離愛他的人遠去了,如詩中所云:“我轉身,沒人。”這損失的確不可估量,正像著名詩人北島在《失敗之書》中所寫的那樣:“帕斯是現代主義文學最後一個大師,他的死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這次赴墨西哥的主旨,是去墨西哥南部海濱城市阿卡布爾科參加第28屆世界詩人大會,但在我這裡,愛的天平傾斜了,我執意要尋找的是像帕斯詩歌一樣蘊藏著火焰與詩歌的太陽石。來到太陽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前,我抬頭仰望著,從一個方向轉向另一個方向,從太陽轉向月亮,我感到太陽和月亮在這美妙之地重疊了,而且在重疊之後靜止了,像一對戀人,以各自目光中絕無僅有的溫存注視著對方,在宇宙的更深處,它們的靈與肉交合在一起,大地上的亂石雜草、花鳥蟲魚和芸芸眾生,都是它有血有肉的子民——這是日落時分,我們從太陽金字塔登上月亮金字塔,太陽西移,月光升起,在它們清純自由的呼吸里,我分明聽到了太陽與月亮的心跳,分明聽到了帕斯《太陽石》中的聲音:“我在聲音的過道中穿行/我在響亮的現實中飄蕩/像盲人在光明中跋涉……”也分明感到我離夢裡尋它千百度的太陽石越來越近了!
是的,毋庸置疑,越來越近了。當我步入墨西哥國家人類學博物館的那一刻,我就步入了太陽石巨大的磁場,我急切地要求翻譯告訴我存放太陽石的準確位置,一心想著要直奔主題而去。其實不用翻譯,憑直覺,我就能在偌大的擺滿各色石頭的海洋中一眼認出“太陽石”。終於,我看見了,在展廳的中央,在眾多拜訪者的感嘆與流連之中,我看見了那塊帕斯讓它光芒四射的、巨大的阿茲特克石歷!但遺憾的是,當我舉起相機試圖聚焦這塊詩歌寶石之時,我被保全告知禁止拍照。為了能不虛此行,為了能在太陽石的光芒普照下佇立片刻,我不停地向保全講述著帕斯的偉大,講述著他與諾貝爾文學獎,講述帕斯的詩歌在中國、在世界的影響,講述這塊太陽石如果不是帕斯和他的詩歌,也許就是一塊普通的石頭,講述我之所以飛越太平洋不遠萬里來到墨西哥,就是想離太陽石近些再近些——我對帕斯的熱愛和虔誠得到了回報,而我情願理解是帕斯作為墨西哥人,讓保全引以為傲,才允許我和太陽石合影。他沒有說,只是給我一個友好的手勢轉身離開了,喔,此時,我又一次深切地感到,詩歌不僅超越膚色、信仰、語言,還可以讓鋼筋一樣的制度、戒規變得柔美。我先是給太陽石拍照,取全景、包括它周圍的事物;然後是近景,它的每一條紋路,每一個圖案;我向在不遠處的保全微笑,臉上有一絲幸福、羞愧和不安;接下來我和太陽石合影,試著融入它的柔韌、堅忍、孤獨和溫暖。我感到了它石質的親切的呼吸,感到了它靈魂附體般的無處不在的光芒,還有它廣闊生命中的垂柳、黑楊、鳴禽、波浪、令人眩暈的藤蔓、茴香的味道、有毒的花朵和無處不在的死亡與生機,在這塊看似很小卻足以顛覆整個海洋的岩石上,在這小鳥和魚群紛紛產卵、繁衍的地方,我的血液放慢循環,我的軀體被它聖潔的瑪瑙一樣的光芒一次次輻射,一次次過濾,一次次安置於仿佛並不存在的境地,我不禁又一次想到了帕斯《太陽石》中的詩句:“時間合攏起它的摺扇/當它的形象後面一片茫然/死神周圍的瞬間/墜入深淵又浮回上面……”
戀戀不捨地走出墨西哥國家人類學博物館,我一下子覺得我此行的使命已經完成,阿卡布爾科去不去都無所謂了,當心靈已經駛入嚮往的港灣,其他的碼頭一下子變得虛幻般可有可無。帕斯——阿茲特克石歷——太陽石——《太陽石》,這都是人世間不可多得的石種,可以種植但不可複製的石種,可以粉碎但不可以摧毀的石種——我多想帶一塊回去啊,哪怕是它的影子,它生命長廊中的回音,它細小密集紋路中的一個小小的皺摺!終於,我看見了一個“美女與骷髏”的加工廠,墨西哥是一個骷髏崇拜的國家,各種造型奇異、想像力極度誇張、跳躍,像我小時候見過的劇毒農藥瓶子上的恐怖圖案。我想選一塊石頭,但老闆不賣,聲稱只賣加工品。我拿起一塊棕褐色的石頭,它光滑、紋理複雜而優美,掂起來要比同等重量的其他物質重出許多。我又故伎重演地向主人講述著太陽石、帕斯,主人被我打動了,他說:“我們都熱愛帕斯和他的詩歌,他是墨西哥人的驕傲和自豪!”我如願以償地得到了這塊大約有3公斤重的“小太陽石”,現在,我把它置於書房臨窗的位置。無論是風聲雨聲,還是蟲鳴禽唱,我都能看見“小太陽石”在遐想中伸出的手臂和緊鎖的眉宇。誰說生命不能暫存,我已將卑微的靈魂如影相隨地寄托在帕斯的詩歌和他的太陽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