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
1839年3月16日,普呂多姆出生於法國巴黎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兩歲時父親去世,這位未來的詩人便與寡居的母親和一個姐姐一起住在巴黎和巴黎南部的夏特內。據《泰晤士文學副刊》說,他很小時名字前就加上了家人用於他父親的暱稱“蘇利”。
 法國巴黎
法國巴黎 普呂多姆以全班數學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後,準備進入一所理工學院,可是一場結膜炎打碎了他成為機械師的一切希望。他青年時代的另外兩個事件使他終身陷於憂傷,一是失戀:他少年時代就愛上的一位表妹嫁給了另一個男人;另一件則是失去信仰。他在里昂同篤信天主教的親戚生活在一起,經過一段短暫的信仰穩定期之後,他變成了懷疑論者,儘管他很渴望能有信仰。
普呂多姆於1860年轉而投身法律並在巴黎一家公證處謀到了職位。他得到了一筆遺產,經濟上獨立了,便從此離開法律專心從事寫作。可兩年不到就寫起了詩,並在日記中寫道,他對學業從他那裡奪去的用於藝術的時間感到惋惜。他之所以產生這一新的熱忱,原因之一是他加入了一群開始自稱為帕那斯派(即高蹈派)的年輕人,這個稱呼是為了表明他們同古典主義規範的聯繫,也表明同在20世紀中已露出過時跡象的浪漫主義的對立。普呂多姆可能在1864年見過這群年輕詩人的領袖德·里斯勒,其時普呂多姆已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詩,即1863年刊於《國內國外評論》上的《藝術》。據他在《私人日記》中說,起初他對自己作品的平庸感到不滿,後來便能極好地把握作品形式,並清醒地認識主體內容的啟迪。
輝煌時期
1865年,一位朋友資助印行了普呂多姆詩集的第一卷《長短詩集》。這些抒情詩作表現出深思、憂傷的氣氛,對人生之短暫的哀傷和快樂進行思考。普呂多姆那首經常入選詩集的詩《破碎的花瓶》即為一個典型例子。該詩將一隻表面看來完好無損實際上卻有一道幾乎看不見的裂隙的花瓶比作因所愛負心而傷悲的心。湊巧,夏特內的一位朋友將《長短詩集》呈送給了偉大的批評家和文學口味規定者查理-奧古斯丁·聖-佩甫,他肯定了這部詩集,這使它一舉成名。這位新起的詩人便全力投身於創作。
一年之後,普呂多姆出版了另一部抒情詩集《考驗》(1866年),集中包括一些以愛情、懷疑和行動為主題的十四行詩。緊接著又出了一本配畫詩集《義大利筆記》(1866年——1868年)和又一冊抒情詩《孤獨》(1869年),其主題是孤獨的個人對愛的欲求。普呂多姆為高蹈派詩人的期刊《當代詩集》寫詩,這說明他同高蹈派有聯繫。《當代詩集》中全是各類主題的用高蹈派工整結構寫成的詩歌,三卷《當代詩集》分別於1866年、1871年和1876年出版,而每一卷中均收有普呂多姆的作品。1870年出版的加布里埃·馬克的一首詩把普呂多姆列入屬於德·里斯勒弟子的17位年輕的高蹈派詩人之中,這證實普呂多姆確是高蹈派成員。
普呂多姆很早就對哲學產生了興趣。早在1863年,他便在日記中提到與一位中學朋友的一次會面。友人問起他的工作,詩人答道,他正在尋找人的定義;他接著說,一旦找到,就以此為題寫詩。他的抒情詩的確具有明顯的心理學、哲學和玄學含義。他對盧克萊修很感興趣,這表明他對尋求意義越來越認真,並在1869年用詩體翻譯了盧克萊修的《物性論》(約公元前60年)的第一部,普呂多姆改用了《盧克萊修:物之性》這一標題。
1870年,普呂多姆的生活又一次蒙上了陰影。一月,與他共同生活的叔叔、嬸嬸和母親相繼去世,使他遭受沉重打擊。繼而普法戰爭爆發,艱苦的軍旅生活徹底毀掉了他的健康。
普呂多姆的兩部主要詩作一出版就大受推崇。兩部作品都是關於理想的人類行為的長篇道德諷喻詩。《正義》(1878年)暗示,道德代碼可以建築在科學進步的基礎之上。《幸福》(1888年)是普呂多姆版的浮士德故事,毫無疑問,作品受這位獲獎者年輕時讀過的又很崇拜的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的劇本的啟發。在《幸福》中,中心人物同傳統的故事一樣,在尋找幸福的秘密,只是原來的次序被顛倒了:普呂多姆的浮士德一開始就有了各種情感,然後再去學習。最終,普呂多姆的浮士德像歌德的主人公一樣,在服務中、在改善人類的工作中找到了完美。
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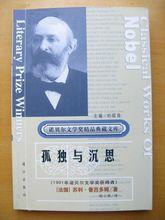 《孤獨與沉思》
《孤獨與沉思》 晚年的普呂多姆是否還應該被稱為高蹈派詩人,批評家們意見不一。答案隨定義而定,當然,普呂多姆從未放棄形式的精緻與思維的科學精確性,這兩點是針對浪漫主義激情過度而發的,而這正是高蹈派的定義。可另一方面,有些批評家認為,普呂多姆後期作品注重道德說教,這使他與其他高蹈派詩人產生不同,因為高蹈派詩人的定義是對美、而非對真理感興趣的詩人。然而謝弗認為,這樣定義過於狹窄,因為他在高蹈詩人中找出了7種不同的風格,重哲理就是其中之一,而普呂多姆便是其中重要一員。
1901年,瑞典學院授予蘇利·普呂多姆諾貝爾文學獎,由於健康原因,蘇利·普呂多姆本人未能出席12月10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盛大、隆重的授獎儀式,而是由法國駐瑞典公使代領。蘇利·普呂多姆作為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位“桂冠詩人”,為了發展詩歌事業,決定把獎金捐贈出來作為一種詩歌獎的基金,由法國作家協會負責頒發。
不幸的是他的健康狀況惡化了,風癱和失眠日甚一日地折磨他。他在夏特內度過了生命的最後15年,於1907年9月7日在妹妹的陪伴下坐在花園裡平靜地逝世。
作品特色
 蘇利·普呂多姆
蘇利·普呂多姆 普呂多姆同德·里斯勒一樣,從一開始就表明自己對哲學的關注。他畢生都希望能在生活中發現某種意義,使他得以擯棄自己的悲觀主義。普呂多姆與其他高蹈派詩人不同的另一點就是他對科學的偏好。
普法戰爭給普呂多姆這樣的年輕詩人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他同其他高蹈派詩人一樣,在對戰爭恐怖的害怕和對祖國的熱愛的困擾中苦苦掙扎。戰事初起,普呂多姆便出版了充滿和平主義觀點的《戰爭印象記》(1870年)。然而,經歷了戰爭、圍城以及最終的戰敗、被占領的屈辱之後,他創作了《法蘭西》(1870年),這是一組洋溢著愛國主義情調的十四行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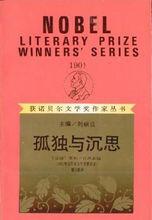 《孤獨與沉思》
《孤獨與沉思》 甚至在戰爭開始之前,普呂多姆就在尋求對他的社會加以觀察分析,由此尋找生活的意義。他在抒情詩中,就像在《破碎的花瓶》中一樣,討論人類內心的種種悲劇。在其他心理成分更少而哲學成分甚至玄學成分更多的詩作中,他就上帝是否存在、上帝是否公正等提出了質問,在他的《私人日記》1864年1月1日這段中,普呂多姆評論道,他無法理解上帝怎么會允許發生聖地亞哥教堂大屠殺,並注意到,這個題材十分適於寫成一首詩。8年後他出版了《命運》(1872年),這是一首哲理長詩,探究了聖地亞哥慘案的含義。普呂多姆越來越多地創作這類長詩,而不多寫那使他成名的抒情短詩。他的最後一部抒情詩集是《徒然的柔情》(1875年),再次討論了對愛情毫無希望的追求。此後他寫出兩首長詩《正義》(1878)和《幸福》(1888),前者顯示詩人對社會進步的關心,後者指出幸福僅僅存在於犧牲之中。其他詩集尚有《三稜鏡》(1886)、《殘存物》(1908)等。他的詩充滿寓意和象徵,有時不免有說教的成分。
從普呂多姆的散文作品表可看出他對玄學和美學的興趣。例如,與《詩歌藝術沉思錄》(1892年)和《詩誡》(1897年)並列的就有《我知道什麼?感性研究》,該書探索了人類知識的界限;還有《帕斯卡爾教理真義》(1905年),研究那位虔誠與深邃的法國哲學家布萊茲·帕斯卡爾。普呂多姆去世後,他的另幾部理論著作也出版了,還有一卷書信集《與女友通信集》(1911年),《私人日記》,以及一組詩歌《飄流物》(1908年)。1900年——1901年出了他作品的五卷本。不過,一部更充實的七卷本卻是在他逝世後出的:《蘇利·普呂多姆作品集》 (1908年)。
不過,許多人依舊喜歡他早期的抒情詩,還是有許多讀者把他的《破碎的花瓶》稱為他最優秀的詩作,這使普呂多姆很不高興。意味深長的是,瑞典文學院與這些讀者觀點一致,將授獎理由主要基於其抒情短詩,而將他的理想主義和道德說教簡單說成是作為第一位文學獎獲得者合適的素質。瑞典文學院過分抬高了普呂多姆在他那個時代的詩人中的地位,他們認定他年輕時的抒情詩是他最優秀的作品。
人物成就
蘇利一普呂多姆於1881年當選為法蘭西學士院院士。1901年,瑞典學院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特別表彰他的詩作,它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藝術和罕有的心靈與智慧的結晶”("in special recognition of his poetic composition, which gives evidence of lofty idealism, artistic perfection and a rare combination of the qualities of both heart and intellect")。
普呂多姆名氣很大,35年來,人們一直頌揚他的技巧,尊敬他的哲學觀點。1881年他入選法蘭西學院,1894年查理-瑪麗-勒內·勒貢特·德·里斯勒去世,人們認為普呂多姆可以繼他任高蹈派詩人的首領。當時該派頗受大眾歡迎。那時候,批評家們對所謂的浪漫主義感傷情懷業已厭倦,卻又尚未能接受新的象徵主義模式。在這樣的時刻,普呂多姆的高蹈派抒情詩便成了詩歌成就的規範。
同時代的人們不可能預見到,時間會將他淪為一個與象徵主義詩人相比其意義要小得多的運動中一個小小詩人的地位,而當初只有象徵主義詩人對他的入選提出質疑。
當法蘭西學院提名其傑出的成員普呂多姆為首屆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時,這一結果已不可避免。雖然已有個人和非正式的團體提出過別的候選人,但是新成立的諾貝爾評獎委員會不至於不考慮一個法蘭西學院這樣一個著名的團體所作的推薦。
人物評價
《詩歌評論》一類的法國雜誌歡呼普呂多姆中選,同時代的那些把他看成是“他國家主要的詩人哲學家”的批評家們也對評獎委員會的決定大加讚揚。然而,擁護象徵主義事業的期刊,如《法蘭西信使》和《西方》,則對此大加攻擊,認為這一決定表明鼓吹道德說教的保守主義文學派別戰勝了捍衛詩歌自由的人們。
《泰晤士文學副刊》於1907年普呂多姆剛一逝世便刊登了一篇長文 (9月13日),綜述了英國人對這位法國詩人的看法。“他是一位思辨詩人”,他宣傳了自然科學家、數學家和工程師們的“思想和感情”,而這一切,現實主義者雨果辦不到,象徵主義者波德萊爾和魏爾侖也辦不到。很清楚,人們認為,把普呂多姆看成新時代的詩人十分合適。在這新時代里,科學希望能改善人的命運,可科學家依然是平常的人,為疑慮和絕望所困。 《泰晤士文學副刊》說:“在這位詩人心底,埋藏著一位早夭的工程師。”
斯洛森在《獨立報》上說,普呂多姆是一位“為氣球、氣壓計歌唱,為海底電纜、攝影技術,為物種起源和特定引力測定而歌唱的詩人”。
E.E.斯洛森在《獨立報》(1902年1月25日)的一篇文章中,讚揚普呂多姆的成就:“比任何在世的人都更多地在其詩行中蘊含了科學所能聚集的新材料,並極好地表述了作為這一時代特徵的實幹與鑽研的精神”,斯洛森說,詩人的疑慮反映了科學思想特有的不確定性,而詩人將人道主義看作一種生活方式,正是失去了舊有穩定性的科學家們典型的反應。
美國新聞界幾乎沒有注意到首次文學獎,一位同時代的美國文學評論家將此歸因於他的同胞對法國詩歌的一無所知。
對普呂多姆來說,美與真理不可分,正如對約翰·濟慈一樣,這又可以在其《私人日記》中找到證明。在1868年6月5日那篇日記中,普呂多姆興奮地寫道,他終於認識了美與道德之間的關係。藝術家能創造一個在美學上使人愉悅的形式,人類也能呼應其道德觀念而使其自身的生活成為一件藝術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