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史大綱》
《國史大綱》基本介紹
《國史大綱》是一部簡要的中國通史,
 《國史大綱》
《國史大綱》《國史大綱》成於抗戰年代,作者的憂患之情躍然紙上。是書於1940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時洛陽紙貴,成為各大學的歷史教科書,風行全國,對學生積極抗戰,增強民族凝聚力起了積極作用。1974年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修訂再版本,到1992年已印行18版,1994年出版第二次修訂本。1994年6月北京商務印書館印製修訂二版本,後又多次重印。亦收入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之《錢賓四先生全集》。錢穆痛切警告:國人懶於探尋國史真諦,而勇於依據他人之說,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自食其惡果。他反覆強調中西文化演進不同,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歷史來套用中國歷史,必須肯定不同國家民族之間文化的特殊性、差異性,以及文化價值的相對性。
作者簡介
 錢穆
錢穆錢穆(1895.7.30-1990.8.30)是著名的國學大師,江蘇無錫人,原名恩,字賓四,民元改名穆。先生家世貧苦,幼時喪父,中學畢業即無力求學,以自學名家。原任中國小教師,1930年後執教於高等學府,歷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華西大學、江南大學等校教授,創辦香港新亞書院。
其代表著作有:《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政學私言》、《朱子新學案》、《中國學術通義》、《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等。著者畢生著書70餘種,約1400萬字。著者在中國文化與中國歷史的通論方面,多有創穫,尤其在先秦學術史、秦漢史、兩漢經學、宋明理學、近世思想史等領域,造詣甚深。
寫作背景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中日正式交兵。時任北大歷史系教授的錢穆,跟隨西南聯大眾師生一路輾轉了大半箇中國,轉移到昆明。靠著宜良縣長幫忙,在岩泉禪寺落下腳來。聯大南遷所帶圖書並不多,若繼續研究舊題,找起參考資料來不免捉襟見肘,錢穆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此前斷斷續續作為筆記摘寫了長達三年之久的中國通史的寫作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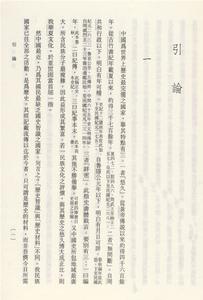 《國史大綱》引論
《國史大綱》引論《國史大綱》作於國難之秋,同時也是錢穆事業的低谷期:參考資料奇缺,生活困窘,在戰火紛飛、物資緊缺的時代,大後方的社會結構卻發生著激盪與交融:川滇的淳樸鄉民和時髦的“下江人”互視,,東部遷來的工業、學校給貧窮的西部注入嶄新的生活形態。外患的刺激、劇變的生活環境,迫使錢穆不停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會不會亡?這種思考貫穿了全書始末,最終凝成眼前這部充滿士人自覺精神,以政治、思想、經濟、軍事史為綱的中國通史。很顯然,錢穆把希望寄托在作為抗戰中流的精英分子身上,希望他們從這樣一部張揚“士”之人力的史綱里汲取力量前行。
1939年6月《國史大綱》正式殺青,立時以其博大的體例、細緻的考證、迭出的創見成為當時中國各大高校通用的國史講義,奠定了錢穆一代史學大家的地位。直至今日,岩泉寺依然將“錢穆教授著書處”作為鎮院勝跡,立碑紀念。
錢穆撰寫此書的目的可見《國史大綱》的《引論》。表達了著者的文化觀、歷史觀與方法論。他指出,研究歷史,撰寫中國通史的目的在於:(1)能將中國民族以往文化演進的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的人們提供所必要的知識。(2)應能在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今中國種種複雜難解的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的人所必備參考。前者在於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於消極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徵候,為改進當前方案所本。錢穆指出,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個任務,在於能在國家民族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中國歷史的演進,其基本精神表現在學術思想文化演進上是和平與大同,協調與融化,這與其它民族是不同的。錢穆痛切警告:國人懶於探尋國史真諦,而勇於依據他人之說,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自食其惡果。他反覆強調中西文化演進不同,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歷史來套用中國歷史,必須肯定不同國家民族之間文化的特殊性、差異性,以及文化價值的相對性。
錢穆認為凡讀《國史大綱》須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黃。)
內容特點
著者以獨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時代的變遷,如戰國學術思想的變動,秦漢政治制度的變動,三國魏晉社會經濟的變動等。有的章,如第六章春秋戰國“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第八章西漢“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第十章東漢“士族之新地位”,第十八章“魏晉南北朝之門第”(變相的封建勢力),第二十至二十一章關於田制、兵制、宗教思想,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關於唐代政治機構與社會情態,第三十二章關於北宋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第三十八至四十章關於唐至明代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等,都非常深入。能由一個問題延伸一兩千年,由一點擴大到全面,系統梳理。如田制,能將兩晉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調,由租庸調到兩稅法,合成一個整體。
 《國史大綱》
《國史大綱》著者揚棄了近代史學研究中的傳統記誦派、革新宣傳派和科學考訂派,分析了其見弊得失。著者認為,史學不等於技術,不等於歷史知識與歷史材料,不能純為一書本文字之學;史學是“人”的史學,不能做號稱“客觀”的無“人”的歷史研究;史學一定要與當身現實相關,但又不能急於聯繫現實,不是宣傳口號與改革現實之工具。他強調對於本民族歷史文化認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對其以往歷史無所了解,缺乏起碼的尊重,此必成為無文化的民族,無歷史意識與智慧的民族。他主張努力開掘國家民族內部自身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和內在的生機、動力。如果不深切理解國家民族背後的文化精神,則國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離散。
近代史學諸流派在政治制度、學術思想和社會經濟三方面研究的結論大體上是:在政治上,秦以來的歷史是專制黑暗的歷史;在文化上,秦漢以後兩千年,文化思想停滯不前,沒有進步,或把當前的病態歸罪於孔子、老子;在社會經濟上,中國秦漢以後的社會經濟是落後的。錢穆《國史大綱》在立論的標準上反對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識為依據,主張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歷史發展的個性與特性。他又以整體與動態的方法,把國史看作是一不斷變動的歷程。他認為,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學術思想是發展變化著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
就政治制度而言,綜觀國史,政治演進經歷了三個階段,由封建(分封)統一到郡縣的統一(這在秦漢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組成的政府演變為士人政府(這自西漢中葉以後到東漢完成),由士族門第再度變為科舉競選(這在隋唐兩代完成),考試和選舉成為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的兩大骨幹。錢穆十分注意中國行政官吏選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權力與四民社會的關係。就學術思想而言,秦以後學術,不僅從宗教勢力下脫離,也從政治勢力下獨立,淵源於晚周先秦,遞衍至秦漢隋唐,一脈相承,歷久不衰。北宋學術的興起,實際上是先秦以後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發展的新氣象。就經濟而言,秦漢以後的進步表現在經濟地域的逐漸擴大,而經濟發展與文化傳播、政治建設逐漸平等相伴而行,儘管在歷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趨勢是在和平中向前發展。
錢穆《國史大綱》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運作的背後有一個思想觀念存在。在學術思想指導下,秦以後的政治社會朝著一個合理的方向進行。如銓選與考試是《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宗旨所致。在全國民眾中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在這個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國家,有成績者可以升遷。這正是晚周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體現。秦漢以後的政治大體按照這一方向演進。漢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議,罷黜百家,專門設立五經博士,博士弟子成為入仕唯一正途。此後,學術地位超然於政治勢力之外,也常盡其指導政治的責任。三國兩晉時期統一的政府滅亡,然而東晉南北朝政府規模以及立國的理論仍然延續兩漢。隋唐統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淵源則是孔子、董仲舒一脈相承的文治思想。隋唐統一無異證明,中國歷史雖然經歷了幾百年的長期戰亂,其背後尚有一種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國再度走向光明之路。錢穆所講的這種精神力量是以儒家為主的優秀文化傳統,它才是民族文化推進的原動力,即“生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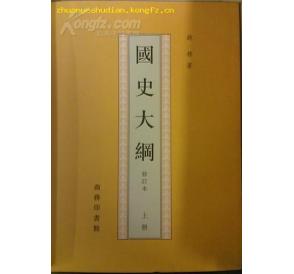 《國史大綱》
《國史大綱》錢穆《國史大綱》也分析了阻礙中國歷史發展的“病態”。如中唐以後的社會是一個平鋪散漫的社會,政治仍為一種和平大一統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會與政府之間的相隔太遠,容易招致王室與政府的驕縱與專擅。又如社會無豪強巨富,雖日趨於平等,然而貧無賑,弱無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賴於政府,而民間又苦於不能自振。再如政府與民間溝通在於科舉,科舉為官後出現腐敗等。這都是中唐以後的病態。宋儒講學主要是針對這種種病態而發。然而宋以後不能自救,中國政治進一步遭到損害。挽救這些病態則需要一種“更生”。這種更生是國家民族內部自身一種新生命力的發舒與成長。錢穆認為,“我民族數百世血液澆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充滿了生機,不僅能挽救自身病態,而且能回應西方文化挑戰,爭取光輝的前途。”
由於特殊的抗戰背景,此書在布局上詳於漢唐而略於遼金元清,詳於中原而略於周邊民族,在取材上詳於制度而略於人事,詳於文化而略於戰爭,在詞句上不用太平天國而用“洪楊之亂”。大約他內在的情結是:“周邊民族侵略中原,給中國歷史文化帶來了極大的倒退,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上起了消極的作用。如果治亂不分,內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國豈不是可以根據遼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順地擁有與統治我廣土眾民嗎?”
錢穆的這部著作代表了他的通史研究,這與他有關部門史(如政治史、學術史、文化史)及歷史人物、歷史地理的研究相得益彰,與他有關史學研究的方法論、中國歷史研究方法的探討,亦相互發明。通過本書,可以了解錢穆先生所提倡的史心與史識、智慧與功力之互動。閱讀本書,可以配讀著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國文化史導論》,其修訂本有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印本。
歷史觀點
《國史大綱》這本書將中國歷史斷為上古三代、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兩宋、元明、清代八部分,先略論大概情況,而後分章詳論政治制度、人才制度、經濟、軍事、時代特貌(如宗教門閥等)。很明顯,作者觀察歷史的視角是精英主義的,不同於馬克思主義者從階級矛盾著手的習慣,也不同於年鑑學派從物質生產及流通著眼的套路。
 《國史大綱》
《國史大綱》在《國史大綱》中,錢穆運用歷史地理學的積累考證出所謂空桐、熊湘、阪泉這些地名實則都密布在黃河中下游的河、汾地區,從而將傳說人物炎帝、黃帝的活動範圍與古文獻看似不經的記載精確地對應起來,大大提高了傳說的可信性。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記誦流”、“考訂流”和“科學流”三大治史傳統在中國史界激盪。顧頡剛的“古史辨派”力主“層類堆積”之說,斥中國古史悉屬杜撰。錢穆硬是憑藉對古文獻甚至神話傳說的紮實考訂,主張古文獻未必不可信。
舉唐宋為例,最出彩處在政治和經濟史。今人為了重塑民族自信,喜歡輕易稱頌唐朝,而實際上盛唐之盛和晚唐之敝都令人震驚。錢穆用戶口表、賦稅表等翔實的數據資料證明,由於北朝漢族世家出色的政治使命感、治國理念和南朝盛極一時的文學風流交融匯合,隋朝締造的繁榮甚至可與開元盛世持平。而唐幾乎完全繼承了隋朝的建制。著墨猶多的是“租庸調”制和“府兵制”,這兩項日後積重難返再難恢復的著名制度在翔實的數據下,富民安民的效果躍然紙上。而同樣令人注目的是唐中後期藩鎮割據時期的病因分析,很顯然,今天的通用教材刻意忽略了唐代藩鎮軍閥絕大多數係為胡人這一點,而勇武有餘、不懂禮義教化恰恰被錢穆歸結為藩鎮亂國的要因。在藩鎮、宦寺和回鶻吐蕃外患的合力下,唐末黃河流域遭受的災難和文化倒退也翔實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宋朝作為繁榮與積弱兼備的奇怪朝代,被作為重點標本詳細解剖。唐宋之際社會大亂,世族門閥損耗殆盡,宋人不得不大興科舉,從平民階層中取士養士,最終造成了一個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精神自律的平民政府。而同時北宋冗員的結果又造成財政高收入、高支出、高赤字。為說明其財政之弊,錢穆舉出了兩宋兩百多年間諸帝收支情況、養兵歲費眾多數據。整體而言,他把吏治得失與士人的責任感、能否介入政府組成代表平民的外廷以與帝王私家的內廷相抗衡視為政治得失的最重要因素,後者意味著錢穆把傳統社會政權裂作帝王貴族私家的“私”與平民的“公”,兩者分權並治的這種闡釋很有西方憲政的味道。
《國史大綱》和現行歷史教材的基本體例,區別還是很大的。一是用詞概念。錢穆沿襲的都是傳統史家的辭彙——黨爭、王霸、民變、流寇……這些在今日教材的話語體系里或已不用,或者變為農民起義,涇渭分明。二是基本立場。錢穆分析北宋軍事積弱,包括幽雲屏障之失、內政不振、武備朽鈍、兵制欠當、地方無權等等,而今日教材幾乎只論朝廷腐敗一點。相比而言,錢穆至少部分地接受當時的進步觀念,認為革命整體是合理的,雖然仍舊視大多數民變為災難。(但事實上中國的全部農民起義的確都不曾給社會帶來本質的進步,倒是破壞極大,因為主導者往往本身只是流氓無賴,除非像劉邦、朱元璋廣得讀書精英輔助,方能成事。)
在民族觀念、政治局面傳承流變等方面,錢穆《國史大綱》的觀點也與現行教材不同,因為教材是以政治觀點為綱組織史實,而錢穆以歷史觀點為綱,雖然都是“信念決定論點”,然而政治觀點顯然要比個人化的歷史觀點僵硬,所以現行教材與這部六十多年前的教材相比,也要僵硬、枯索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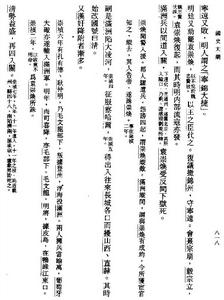 《國史大綱》
《國史大綱》除斷代章節外,錢穆還很有針對性地寫了《南北經濟文化重心的轉移》這類縱向比較的章節。這些其實是每個處入歷史門檻的人都會有的疑問:為什麼漢唐以長安、洛陽為中心,宋以後卻不得不仰仗江南一地?為什麼中華民族發源於黃河流域,如今黃河流域卻反而欠發達?在這個問題的解釋上錢穆又提出了創見。一般人們喜歡把這一“地氣東南傾”的歷史地理現象歸結到客觀因素上:氣候變遷、黃河水患、外族入侵。錢穆一一否定了。今天的歷史地理學已經證實,歷史上氣候冷熱、乾濕是周期波動的,北方占優的年月也有寒冷期和溫暖期,因此錢穆否定氣候說已獲支持。而黃河水患,錢穆援引史料證明,完全是人為造成的,一是因為軍閥諸侯爭相決河堤淹對方,二是因為數千年來壅塞水源,宋後水患完全是因為漕運,歷代政府“逆河之性,強使南行”,結果屢次改道,還把淮河弄壞了。除了漏說破壞植被、水土流失一點,均被今天的史學家接收下來。至於外族入侵,錢穆說,其實中國處處崇山大川,利於防禦,每被外族侵略都是因為內政失修,“中國易受外族入侵”是為了警醒國人,畢竟言過其實。很顯然,中國作為四大古文明唯一活到今日的一個,本身證明了它並不容易被侵犯。錢穆進而論證道,北方貧弱,正是因為唐末藩鎮破壞了歷代水利,並逼走了精英分子,而這些精英分子來到原本多澇、不適合耕種的江南,興修水利、改良土壤,這才造就了魚米之鄉。所謂地氣東南傾,純粹是人氣東南傾的結果。這個論斷的啟示就在於,中國的興衰與災榮,根子都在人事和內政,精英分子能否起到核心的指導作用,尤其重要。這層意思放在當時倭難臨頭的當時,無疑極具意義,放到今天,依然切中要害。
相關詞條
盤點中國民族史書籍(二)
| 任何民族都有極端民族主義,漢族也不例外,它是與這個民族同生共滅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