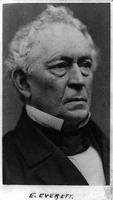早年經歷
1794年4月11日,愛德華·埃弗里特出生於麻薩諸塞州多徹斯特的一個名門望族。父親奧利佛·埃弗里特是位神職人員,在波士頓一帶頗有名氣。愛德華的長兄亞歷山大·希爾·埃弗里特是政界要員,與美國開國元勛們有較多的交往。良好的親職教育加上後天的勤奮與努力,成就了愛德華未來顯赫的學術地位和政治業績。
愛德華是哈佛大學著名的才子,青年時代就顯露出敏銳的文思和出眾的辯才。愛德華十八歲時便進入哈佛大學任教,1814年在波士頓神學院獲得理論學碩士學位。後來他來到德國留學,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
埃弗里特並不是鑽在象牙塔里的迂腐學究,他關注人世間的各種社會問題,有遠大的政治理想。1819年回國後,埃弗里特繼續在哈佛執教,此時期,他的演說才華開始為世人所矚目。1822年,他與夏洛特·格雷·布魯克成婚,其岳父皮特·布魯克斯是當地的富商巨賈。這樁美滿成功的婚姻為埃弗里特在政界施展才幹搭建了廣闊的平台。
1824年8月,埃弗里特在哈佛大學發表了一篇對他人生發生了重要影響的演說。當時,法國老英雄拉法耶特也坐在聽眾席上。在演說中,埃弗里特盛讚了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拉法耶特對美國獨立和美法友誼作出的重大貢獻。埃弗里特的演講以激越的愛國情懷,充滿詩意的詞句和具有感染力穿透力的聲音,形成了一股強烈的衝擊波,不僅感動了在座的拉法耶特本人,還傾倒了無數的聽眾,贏得了世人的掌聲,也為他開通了仕途之路。就在哈佛精彩演講之後的國會議員改選中,埃弗里特如願以償當選為國會眾議員,並連續任職十年。
從1835年起,埃弗里特連續四年出任麻薩諸塞州州長。他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做了許多具有開創性的工作,為麻薩諸塞人所稱道。例如,在他的主持下,許多中等、初等學校得以建立,採取有力措施推動了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完成了幾條公路幹線的建設工作。
在這一時期,埃弗里特在政治上持溫和保守的立場。他主張緩和各種社會矛盾,以穩定社會秩序,並加強政府對金融和經濟建設的支持力度。他認為奴隸制度在道德上存有嚴重缺陷,但出於對憲法的尊重和維護聯邦的考慮,他主張在這一問題上達成妥協,不要過分地刺激南方人。
1841~1845年,埃弗里特有過一段出使歐洲的經歷。卸職後受聘出任哈佛大學校長,是哈佛當之無愧的精神引領者和學術帶頭人,為美國的高等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
從政經歷
埃弗里特是一位天賦極高的外交家,在外交領域卓有建樹。在擔任美國駐英公使的四年中,埃弗里特充分顯現出嫻熟的外交技巧和文學家的才華,使英國王室和社交界對他讚賞不已,大大加深了兩國高層之間的交流與融通。
1850年,埃弗里特起草了致奧地利帝國一位外交官的信。在這封著名的信中,他以充滿激情的文字表達了他本人的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立場以及對匈牙利人民的同情,同時表明了美國對匈牙利民族革命的態度。
1852年11月,埃弗里特出任美國國務卿,任職至1853年3月。在這短短的一百多天裡,他日理萬機,處理了不少棘手的問題,如解決了同秘魯的領土糾紛;向英法表明了美國統治加勒比海的意願;著手結束日本的鎖國時代,等等。
1852年11月13日,埃弗里特為米勒德·菲爾莫爾總統起草了致日本天皇的信,信中用威嚇的口氣要求日本開放商埠,允許美國在日本建加油站,保護遇難海員等。信的落款有埃弗里特的副署簽名。美國馬休·佩里艦隊於次年1853年7月到達日本,在炮艦的威懾下將該信件轉交給天皇。
在古巴問題上,埃弗里特運用其高超的文字技巧向英法兩國明確無誤地闡述了美國政府的立場。1852年12月,埃弗里特發出書面照會,在重申了孤立主義傳統和美國對古巴沒有野心的同時,明確指出古巴問題主要是美國的問題。他在論述了古巴的戰略、商業價值和對美國利益的特殊重要性的同時,委婉地暗示:美國不會同意古巴被其他強國控制。在該照會中,美國還巧妙地避免涉及敏感的奴隸制問題。
在這份致英法的照會中,埃弗里特所張揚的仍然是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精神,同時也暗含了擴張主義情緒,因此在美國國內又引起了一片喝彩聲。
熱忱的愛國者
從國務院離任後,埃弗里特又進入了國會參議院。此時,圍繞奴隸制的爭論已席捲全國,變得愈加不可迴避。埃弗里特的立場雖有所進步,但還是時常扮演妥協者的角色。但由於南北衝突已變得不可調和,因此他的處境有時十分尷尬。
1854年,圍繞奴隸制的爭端及其引發的“內戰”造成了全國性的大動盪。埃弗里特的奴隸制立場雖有所進步,但此時他仍把維護聯邦置於首位,不願在奴隸制問題上與南方攤牌。埃弗里特認為,《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把整個西部開放給了奴隸制度,因此他對這個法案持有異議,但他又不願意參加議會中日益激烈的爭吵,遂於1854年6月主動退出議會。
此時期,美國政壇風波疊起,鬥爭愈演愈烈,堪薩斯內戰掀起的波瀾尚未平息,約翰·布朗起義又震驚了全國。面對動亂不已的局勢,埃弗里特只能大聲呼籲加強和解,要求人們把拯救聯邦放在首要位置上,此外,他沒有什麼更好的治國良策。
此時埃弗里特已年過花甲,他希望潛心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但巨大的名聲使他身不由己,各地不斷邀請他去發表演說。此時期他把研究重點放在美國第一次革命上面,他的巡迴演說也大多與這一主題有關,其目的在於宣揚國父們在創建聯邦的事業中立下的豐功偉業,以激發人們對聯邦的熱愛,投身到維護聯邦的事業中去。
在1860年大選中,埃弗里特成為立憲聯邦黨的副總統候選人,以捍衛憲法和維護統一為旗幟,以期彌合國人的分歧,挽救危局。他的黨沒有成功,最終,共和黨人亞伯拉罕·林肯當選為美國第十六任總統。
內戰不可避免地爆發了。埃弗里特目睹南部脫離聯邦、國土被炮火蹂躪的慘況,不顧年高體弱奔走於全國各地,用他充滿激情的演說,聲援林肯總統,鼓舞聯邦軍隊為恢復統一而英勇作戰。他的演說對於動員民眾支持聯邦的正義事業發揮了無法估量的作用。他於1863年11月19日發表了兩個小時的演說。他首先用動人心魄的語調錶達了面對英靈時的虔誠惶恐的心境,而後精闢地闡釋了內戰的原因和葛底斯堡戰役的景況,並斥責了分裂分子的殘暴罪行。他旁徵博引,妙語珠連,在講話中回顧古希臘文明史,並把它與美國發生的事情進行分析比較,令人備感親切。他還援引了雅典民主派政治家伯里克利等人的名言,以讚頌葛底斯堡的英烈們。埃弗里特的演說充滿雄辯和激情,給人以一氣呵成、大氣磅礴的感覺,充分體現了埃弗里特過人的辯才和民族主義精神。
此後,埃弗里特的身體每況愈下,但他仍然盡其所能參加政治活動,支持北方的正義事業。在1864年大選中,他發表演說,為林肯總統連任助選。他最後一次發表公開演說是在1864年聖誕節後,此時北方已勝利在即,老邁的埃弗里特在演說中再次呼籲全國和解,重建聯邦的大家庭。1865年1月15日,年逾七旬的埃弗里特在波士頓病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