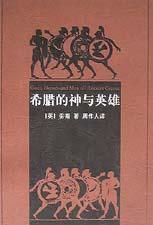簡介
新出的海南版裝幀精當,圖頁豐美,甚悅人目。另外,周氏《譯後附記》提到,1947年第一次翻譯時他曾附了自己一些關於希臘神話的文章,到這次1949年的第二次翻譯時只刪剩兩篇,現海南版蒐集了一批這類文章附在書後,可見編者的有心。但超文提到的,原著出版後的次年,周氏即寫了與原書名《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同題的介紹文章。
譯本序
作者勞斯,是著述甚豐的學者,深知今昔的希臘,且又懂得神話,周氏稱為“難得”(《譯本序》)。周氏對此書很讚賞,如在附錄的《關於本書》中如此稱許:“它的好處我可以簡單地舉出兩點來。其一是詼諧……與清教徒的紳士不是一路的。其二是簡單。簡單是文章的最高標準……內容頗是複雜,卻那么剪裁下來,粗枝大葉的卻又疏勁有致……”這說的是勞斯的書,同時也道出了古希臘的某種精神,更是夫子自道,說著周氏自己的文章宗旨了。
翻譯情況
周氏開頭不想翻譯它,是“因為嫌它是用英文寫的兒童讀物,並非希臘神話專門之書”,此說不當。《知堂回想錄》之《我的工作(三)》、《拾遺(癸)》談到,他認為在希臘人編的希臘神話(阿波羅多洛斯《希臘神話》)和神話研究理論之外,還應有理解神話的人再來寫一冊稍為通俗的給小孩子看的故事,而勞斯“可以算是最適任的作者了”。真正令周氏“嫌”的,是作者乃基督教國家人這一點,他總覺得希臘的“改教為可惜”,大概是認為基督教破壞了古希臘的傳統,使古希臘人的精神自由空間定格為侷促的一神教吧。然而後來也想通了:“已經過去的事是沒有辦法的”,“我們想要討教,不得不由基督教國去轉手”,這書“究竟要算好的,自己既然寫不出,怎么好挑剔別人呢。”(《知堂回想錄》之《拾遺(癸)》、《後記》)
此書的第一次翻譯是在一個特殊的時空里。1946年5月至1949年1月,周氏被關押在南京老虎橋首都監獄期間,主要做了兩件文字工作,其一是寫了一批舊體詩,再就是第一年在“忠舍”時,“把一個餅乾洋鐵罐做台,上面放一片板,當做一桌子”譯了本書。(《知堂回想錄•監獄生活》)但《知堂回想錄》沒有替詞學家龍榆生的家人記上一筆:當時,遠在北京的周氏家人托龍(時在蘇州入獄)的女兒龍順宜照顧他,龍順宜姐弟一直負起探監送物之責,這本書就是他們送進去的,譯好後可能也由他們代帶出送出版社(見龍順宜《知堂老人在南京》)。此後的情況大致如超文所述,可補充的是,1950年出的那個上海文化生活版,是巴金親自校勘的(《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二)》)。
對於譯了兩次,《譯後附記》中說:“重譯的事殊少興味”,“興趣較薄”,這也許與他其時剛出獄不久的心情有關,到晚年寫的《知堂回想錄》,態度就頗不同了,認為兩部希臘神話都譯了兩次(另一部見下述),這是緣分深,對希臘神話固執的、偏頗的愛好和熱心的反映,“我很高興能夠一再翻譯了完成我的心愿。”(《北大的南遷》、《我的工作(二)》、《我的工作(三)》、《後記》)
在上面這些價值之外,這個譯本還多少表達了周氏中年後的一種人生觀、文學觀。前述的《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一文中,他說:“好幾年前我感到教訓之無用,早把小鋪關了門,已是和文學無緣了”;到《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二)》談到本書又說:“古人有句話,敝帚千金,我雖然沒有這種脾氣,可是對於此書,卻不免有這樣感情。我因為以不知為不知,對於文學什麼早已關了門,但是也有知之為知之,這仍舊留著小門不曾關閉,如關於神話是也。”對這觀點這裡不作展開討論,但這些話本身的態度我是喜歡的:誠實,謙和,又不乏自負;自知,卻不自戀,然而又不是“太上忘情”。
海南版間有注釋,但看來應為出版者新加。周氏是非常重視譯本注釋的,此譯稿似乎也不可能沒有周注。《譯後附記》最後有沒頭沒腦的一句話:“至於此外注釋的話,說起來也一言難盡,只好因陋就簡罷了。”這話的意思,可能是初譯時作過注,到譯稿失去後,重譯就沒了再做的“興味”;或者當時的處境,手頭資料缺乏;又或者在當時情形下,不便強求出版社接受其注釋,就不作注了——但,“因陋就簡”,也可能是雖因上述原因不作詳註,到底有些簡注也說不定。實情如何頗費猜疑,所以說此書缺一細緻的出版說明是個缺憾,雖經耙疏得了一些大致情況,到底還是留有疑竇。
周作人相關著作
| 長期以來,周作人在中國文壇上可謂是寂寞的,在辭世後相當長的時間中,他的作品幾乎被人們所遺忘,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現代散文開山大師的地位。本集精選了周作人生平書稿、散文及翻譯著作等,旨在揭開塵封的歲月,為今天的讀者們呈現出一篇篇平和寬容、樸實有諧趣、飽含難以言說的美的知堂真味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