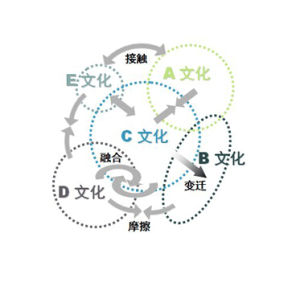概述
 文化圈
文化圈是社會學與文化人類學描述文化分布的概念之一。它涉及的地域範圍比文化區和文化區域更為廣泛。
文化圈概念是由德國民族學家R.F.格雷布納首先提出的。他在1911年出版的《民族學方法論》一書中使用文化圈概念作為研究民族學的方法論。他認為,文化圈是一個空間範圍,在這個空間內分布著一些彼此相關的文化叢或文化群。從地理空間角度看,文化叢就是文化圈。奧地利學者W.施密特主張,文化圈不僅限於一個地理空間範圍,它在地理上不一定是連成一片的。世界各地可以同屬一個文化圈,一個文化圈可以包括許多部族和民族,是一個民族群。在一個文化叢相關的不同地帶,只要有一部分文化元素是相符的,它們就同屬一個文化圈,如東亞文化圈、北美文化圈等。文化圈是獨立持久的,也可以向外遷移。一個文化圈之內的整個文化,包括人類生活所需要的各個部分,如器物、經濟、社會、宗教等。向外遷移的不僅是整體文化的個別部分,也可能是整個文化模式。
文化圈理論被後來的文化人類學家接受。美國學者A.L.克羅伯和K.科拉克洪都認為,這個理論對於研究民族學和文化傳播是很有價值的,人們可以從具有相同文化特質的那些民族中間,發現它們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淵源。北美學者在研究民族學時多用文化區域概念,而文化區域在時間和空間上過於狹小,文化圈包括較大的空間和經歷持久的時間,使用這個概念便於作更深入的研究。
文字元號文化圈
 文化圈
文化圈從文字字形來看,今天世界分為五大文化圈。
漢字文化圈,代表儒學文化和後來的佛教文化。包括中國、日本、朝鮮等國,以及以華語作為民族語言之一的新加坡。
印度字母文化圈,代表印度教和佛教文化。包括印度、孟加拉、緬甸、尼泊爾、斯里蘭卡、泰國、寮國、高棉等。
阿拉伯字母文化圈,代表伊斯蘭教文化。包括阿拉伯國家(埃及、沙烏地阿拉伯等)以及信伊斯蘭教的其他國家和地區(伊朗、巴基斯坦等)。
斯拉夫字母文化圈,代表東正教文化。包括俄羅斯、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一半)、外蒙古等。
拉丁字母文化圈,代表天主教(以及新教各派)文化。後來突出科技文化,包括英美等世界多數國家。
世界三大宗教文化圈
佛教文化圈
 佛教文化圈
佛教文化圈最先興起,它產生於公元前五世紀的古印度。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既有豐厚的文化土壤,又是一個宗教意識濃厚的地方。佛教產生於等級森嚴的“種姓”社會,它以反對維護“種姓”制度的婆羅門教而登上歷史舞台,贏得了許多人的心。在婆羅門與非婆羅門的劇烈鬥爭中,思想異常活躍,產生了婆羅門“正統六宗”和眾多的反婆羅門“沙門思潮”;佛教就孕育在這種哲學昌明的環境裡。佛教哲學偏重於社會人生,它以“苦”為出發點,要求人民面對慘澹的現實,把生、老、病、死以及愛、憎、別離、貪慾都看成是一個苦難的歷程,進而探求“苦”的根源,反覆論證事物的因緣關係,從而勸告人們行“八正道”而進入不生不滅、無憂無慮的“涅”境界。佛教文化圈的根源在印度,但它的擴散卻影響整個亞洲。八世紀後印度佛教衰落,而這個文化圈的中心轉向中國和東南亞。對中國文化影響最深的莫過於印度文化,它以佛教為先導,把中國與印度兩大文明古國聯繫起來,同時把印度人的智慧帶到中國,與中國人的智慧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大乘佛教與中國社會和漢文化結合產生了漢傳佛教,對中國的哲學、宗教、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建築、科技乃至民俗產生了深遠影響。以後,漢傳佛教又把中國文化帶到朝鮮、日本、越南及其他地方。密宗與藏傳佛教(喇嘛教)對西藏社會和文化有極深的影響,並擴散到青海、甘肅、四川、雲南藏區及蒙古、中亞、不丹、尼泊爾和錫金。小乘佛教與東南亞文化結合形成南傳上座部佛教,把印度文化傳到斯里蘭卡、緬甸、泰國、高棉、寮國等國。同時,中國的“西域”、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在歷史上也曾是佛教盛行一時的地區。
基督教文化圈
 基督教文化圈
基督教文化圈起源於公元一世紀的巴勒斯坦,形成於羅馬帝國,四世紀被羅馬帝國認定為國教,從此奠定了它在歐洲傳播的基礎。基督教淵源於猶太教,但一開始就與猶太教分道揚鑣,打破了猶太民族“特殊寵論”的狹隘觀念,宣布凡信上帝的人都是“上帝的選民”而可以得救,對一切苦難的人產生極大的吸引力。
基督教有三個重要觀念被繼承下來,其一是“至高一神”的信仰,其二是“救世主”的觀念,其三是信仰“先知”及其“啟示”,所以一開始便是“絕對一神的宗教”。猶太教的經典也被繼承下來,成為《聖經》的《舊約》部分,“安息日”演變為“禮拜日”,“愈越節”演變為“復活節”,教會組織形式和祈禱、唱詩、讀經、講道等禮拜儀式都沿襲下來。
基督教產生於東方,它通過猶太民族的歷史傳統,吸收了巴比倫、埃及、波斯文化,又在“希臘化”的背景下充分吸收了希臘、羅馬文化,從一開始便建立在東西文化兼容的台階上,是東西方文化交融的產物。古巴比倫《創世史詩》與《吉加美士史詩》中,有關創世和洪水的傳說,後來成了《聖經》中的“創世紀”、“伊甸園”、“洪水記”之類。古埃及的許多傳說,如奧西里斯死而復活以及死後審判、陰間冥府的描寫,都被納入基督教的神學體系。波斯的善惡二元論、末世觀念及天使、魔鬼,對基督教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形成基督教意識形態的重要因素是希臘哲學,特別是畢達哥拉斯的“靈魂輪迴”和數字神秘主義,蘇格拉底關於知識和善德的學說,還有柏拉圖的“理念世界”、回憶說“靈魂不滅論”及“世界等級模式”。古羅馬的文化也為基督教的誕生提供了溫床,新柏拉圖主義的“流溢說”直接對基督教思想觀念的形成起了作用,新斯多葛派的禁慾主義和宿命論也為基督教所採納。將希臘、羅馬文化與基督教思想結合起來的是猶太哲學家斐洛,集其大成者是羅馬帝國後期的奧古斯丁。羅馬帝國狄奧多西一世正式宣布基督教為國教,東、西羅馬分裂後形成了以羅馬為中心的西方教派(天主教)和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東方教派(東正教),對整個歐洲產生深遠影響,它的異端如景教還一度傳入西亞及中國。宗教改革後出現基督新派,影響波及歐美及世界其他地方。
伊斯蘭教文化圈
 伊斯蘭教文化圈
伊斯蘭教文化圈興起於七世紀的阿拉伯半島,是宣揚“服從真主意志”的宗教,《古蘭經》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啟示”,而《聖訓》便是穆斯林思想言行的規範和行教的重要依據。伊斯蘭認為今生短暫、後世永存,死亡只是連線今生和後世的橋樑,到了世界末日,一切都將毀滅,死者將被復活,在真主面前受審,或進天堂或入地獄,這便是“信後世”。“信前定”的思想,就是相信現實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因為信後世而重今生,十分重視實踐,所以在行動上有嚴格要求,必須履行“念詞作證、謹守拜功、完納天課、封齋節慾、朝覲天房”的五功。伊斯蘭教宣布“在真主面前平等”,既不放棄今生的努力又給人予未來的希望,因而易於為人接受。
伊斯蘭文化是一種特殊的文化體系,它以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為原質特色,兼取希臘、羅馬、印度文化和猶太教、基督教思想而形成,內容不僅包括宗教、哲學、政治、法律、教育、道德等方面的思想理論,而且包括語言文字、天文曆法、數學、醫學、文學、藝術等等,同時還包括以《古蘭經》、《聖訓》為準則的各種社會規範、行為模式和價值觀、人生觀、宇宙觀。伊斯蘭文化是在地中海孕育形成的,和基督教文化一樣兼有“東西合璧”的特徵。首先,埃及、巴比倫、敘利亞、波斯都是世界文化較早發展的地區,阿拉伯帝國建立後,把這些文化囊括起來並納入伊斯蘭文化體系,同時推廣阿拉伯文。八世紀至九世紀中葉是阿拉伯帝國最強盛的時期,控制了整個地中海,由於農業、手工業和商業、海上航運的蓬勃發展,促進了文化繁榮昌盛,在首都巴格達創建了智慧宮(包括研究院、圖書館和翻譯館),在數學、天文、物理、化學、醫學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文學、史學、哲學、法律、地理等方面也有不少成績,而且將希臘的、羅馬的、波斯的、印度的古典著作大量翻譯成阿拉伯文,使伊斯蘭文化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與此同時,中國的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火藥等也通過阿拉伯傳入歐洲,對溝通東、西方文化起了積極作用。“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各國學者紛紛來到西班牙,把大批阿拉伯文著作譯成拉丁文,這對歐洲的自然科學、哲學和文化藝術創新具有重要意義。伊斯蘭教擴散到世界許多地方,自然把這種有世界意義的文化傳播開來,並且與遊牧文化圈、佛教文化圈發生接觸碰撞,在某些地區擠壓了佛教文化圈,如巴基斯坦、孟加拉、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及中國的“西域”。
漢字文化圈
 漢字文化圈
漢字文化圈漢字文化圈,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限於漢族,而且影響國內許多民族,並輻射到朝鮮、日本、越南及東南亞華人地區,具有重要意義。漢字文化圈的內涵極其豐富,它以漢字為重要標誌,用漢字來表現各種特有的文化現象,包括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制度文化乃至風俗習慣等等。漢字既是文化載體,同時又是文化傳播的媒介。這一區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於中國而通行於四鄰的漢字。站在世界的高度看,漢字文化圈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它源遠流長,影響深遠。
這個文化圈產生於中國是必然的。在世界歷史上,中國文明的起源並不算最古老,但是,新巴比倫王朝在公元前536年被波斯吞併後便銷聲匿跡,埃及雖然延續了三千年最終卻淪為波斯治下的一個行省,印度在貴霜王朝極盛一時之後便漸漸衰落。曾經放射奇光異彩的古希臘在公元前338年竟被“馬其頓方陣”踏平了,雄峙地中海大約6個世紀的羅馬帝國也在公元395年分裂後一蹶不振。世界上古老的文明都相繼沒落,惟有中國文化,綿延五千年而不衰,至今仍然生機勃勃。漢字文化圈可分為三個層次:漢族、漢字和漢文化的形成為“本圈”;由於它的主導作用而影響國內其他民族形成“內圈”;而它在國外的擴散則構成“外圈”。
漢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人口超過10億。她的形成與別的民族不同,融合了許多民族成分,吸收了多種民族文化,逐漸成長壯大。考察漢民族的形成,無論如何不能脫離“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背景。歷史證明,她是民族融合的產兒,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壯大。漢族是一個開放的民族,可以接納各種不同的血緣成分的人,包容國內外多種文化,具有很強的融合能力。她的形成和發展主要靠文化,文化是她的基因,她的靈魂,是維繫這一族群的紐帶,並通過文化傳播來擴大群體,因而民族的認同感來自共同的文化而不是血緣。在漢族和漢文化形成中,漢語和漢字起了積極推動作用。有了漢字,有利於知識的積累;有了漢字,文化可以世代傳承,積澱目益深厚;有了漢字,漢文化方可得到充分發展,拓開許多領域;有了漢字,漢文化便可傳播到遙遠的地方。因此,漢字是漢文化的核心,是漢文化遠播的根源,是形成“漢字文化圈”的傳媒工具。
漢族的優勢之一就是人口多,分布廣,與所有民族都有接觸,就像是一種極強的粘合劑,把整箇中華民族團結起來。漢族的另一個重要優勢,就是經濟處於領先地位,中國的封建社會事實上是以漢族地主制為中心建立起來的,並在這箇中心的強力作用下,把周邊各民族先後納入封建化軌道,形成一個多民族、多層次、多類型的結構。中國文化是由多種民族文化構成的,漢文化始終是中國文化的主鏇律。隨著漢族人口的播遷,以人為載體把這種文化帶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造成多方面的影響,從而使漢文化成為“中國精神文明的旗幟”,南方民族絕大多數的語言屬漢藏語系,均為孤立語,且慣於具象思維,因而造字方法大同小異,文字多屬方塊字類型,如東巴文、哥巴文、水書、彝文。漢藏語系民族其語言與漢語有某種親緣關係,且因與漢族長期交往,比較容易接受漢字。阿爾泰語系不是孤立語而是粘著語,不便直接借用漢字,於是在使用過程中逐漸由表意向表音方向轉化,形成拼字文字,如契丹文、女真文。許多民族原先沒有文字,明清以來,隨著漢文化的傳播,到近代已有21個民族通用漢字。在清代,滿文與漢文並用,至清末滿人即多習漢字了。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蒙古族、朝鮮族都有自己的文字,但自近代以來,由於與漢族交往漸多,而且學校、報刊、圖書、廣播、電視、電影都使用漢字,因而漢字也成為溝通各種民族文化的工具。從歷史發展來看,以漢字為核心的漢文化逐漸擴大範圍,影響國內各民族。聯結整箇中國文化,加強中華民族的內聚力,意義十分重大。
遊牧文化圈
 文化圈
文化圈“馬背上的文化”,風貌與農耕民族迥然不同。首先,遊牧、狩獵、貿易、作戰構成了生活的基調,棲息、遷徙、雄踞形成一條滾滾的長河,因而人們具有一種勇武、浩蕩、豪邁、瀟灑、開闊、進取的特有氣質,不畏艱險,取於開拓創新,文化風貌顯得獨特。其次,由於經濟起伏、社會動盪、政權更迭頻繁,文化總是處在不斷破壞與重建過程中,因而文化積累遠不如農業民族,文化隨時變遷,很難形成世代相承文化傳統。其三,人口大幅度流動,各民族、各部落相互對流穿插,文化的傳播大於文化傳承,故同多於異,輕裘,寶馬,騎射,歌舞,氈房,肉食成為普遍的習尚。其四,遊牧民族四海為家,視野特別寬闊,能夠接納各種文化,對任何外來文化都不排斥,時有改變或幾種文化相兼。其五,遊牧民族的群體意識特彆強烈,一遇戰爭便迅速集合為一個整體,步調一致。力量集中,為了群體利益不惜犧牲自己,因而戰鬥力極強,堪稱“金戈鐵馬”。
隨著遊牧民族的興衰,“遊牧文化圈”時有盈縮,突然放大又突然收縮,極盛時越出中亞,進入中國、西亞、南亞及歐洲,使整個世界天翻地覆。長期影響中國歷史的是遊牧民族,匈奴與秦漢的對峙,魏晉時“五胡”進入中原,進而造成南北朝對立的局面,隋唐時期周邊存在許多遊牧民族政權,接著是宋與遼、金、夏的紛爭,元朝統一中國,清代是滿洲人的天下。西亞是遊牧民族南下的大通道,從公元前3000年起就不斷有遊牧民族進入這一地區,如雅利安人、波斯人、塞種、阿拉伯人等。深入南亞的雅利安人對印度文化有過重要影響,大月氏建立的貴霜帝國和蒙古人建立的莫臥兒帝國更是煊赫一世。在歐洲,匈奴西遷推動了“蠻族”大遷徙,顛覆了東、西羅馬帝國,蒙古人西征更成為震驚世界的特大事件。遊牧民族的馬蹄聲震撼歐亞大陸,在世界古代及中世紀的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遊牧民族是國際貿易的先驅,他們長途跋涉,穿越戈壁、沙漠、草原和高山開闢國際交通線,打破國界進行物資交流。中國歷史上的“茶馬貿易”和“草原絲綢之路”,就是遊牧民族的壯舉,通過他們把中國的絲綢傳到遙遠的歐洲。中亞的粟特人,是往來於歐洲、西亞及中國之間的國際商旅,不但進行長途販運,而且使粟特文成為一段時期較為通用的“國際通商用語”。遊牧民族介入其他各個文化圈,聯繫範圍最為寬廣。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波斯帝國、貴霜帝國、阿拉伯帝國和蒙古大帝國起了重要的橋樑作用。波斯將巴勒斯坦、兩河流域、埃及、北印度納入版圖,使這些古老文化相互交融,逐漸形成地中海文化的雛形。長達40多年的波希戰爭,打開了東、西文化交流的大門。與此同時,“絲綢之路”成為波斯與中國聯繫的一個重要紐帶,中國的絲綢、瓷器通過波斯傳到西方,“西域”的許多物產也傳入中國,並從波斯傳來了祆教、摩尼教和景教。貴霜帝國建都犍陀羅,促使希臘、羅馬文化與印度文化交融,產生了犍陀羅藝術,而佛教東傳對中國又產生重大影響。阿拉伯是“世界之橋”,它控制了整個地中海,使之成為東西亞文化的大熔爐。阿拉伯人又發展了海上貿易,把阿拉伯與印度、東南亞及中國聯繫起來。蒙古人西征,打通了歐亞大陸,文化交流範圍空前擴大,中國的“四大發明”傳入歐洲,伊斯蘭教也大量傳入中國。元代,基督教的景教、天主教再次傳入中國,統稱“也里可溫”。不但如此,“西域人”大量流入中國,以後逐步形成回族、東鄉族、撒拉族和塔吉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