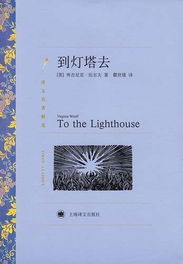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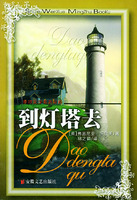 到燈塔去
到燈塔去《到燈塔去》是維吉尼亞·伍爾芙的代表作,也是意識流小說中的經典。作者通過莉麗·布里斯科對女性氣質從拋卻到認可再到超越的心路歷程,揭示了女藝術家在男性占主導的社會中為實現自己的理想所經歷的艱難和困惑,以及女性主義的真諦。指出只有培養雙性頭腦才是婦女解放的真正出路。
內容簡介
 《到燈塔去》
《到燈塔去》 《到燈塔去》
《到燈塔去》一個下午慢慢過去,拉姆齊太太到村子裡去看過一個病人,便在窗前打毛線襪子,準備送給燈塔看守人的小兒子。日常各種瑣事,—一在她心中掠過。晚上睡覺之前,風雨大作,第二天真的不能去燈塔了。 拉姆齊家離開別墅後一去10年不歸。在這10年裡,拉姆齊太太在一次安靜的睡眠中悄然逝去;普魯結婚後死於難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拉姆齊家的兒子安德魯應徵入伍,在法國被炸死。
光陰流逝,海濱別墅也在風雨的剝蝕下逐漸破敗。戰爭結束後的一天,看守別墅的麥克納布太太收到電報,要求她把房子收拾乾淨。拉姆齊一家、莉莉小姐和已經成為著名詩人的卡爾米奇爾先生都要來度假。 拉姆齊一家等人又回到別墅,一天上午,拉姆齊先生帶著最小的兩個兒女泛舟海上,向燈塔挺進。當帆船乘風破浪逐漸駛近燈塔時,拉姆齊先生想起了死去的妻子,想起了自己的軟弱和對子女的冷漠,他不禁百感交集。他仰望燈塔,心中豁然開朗:人們不僅需要理性,而且更需要溫情與理解。他終於明白,理性應該與情感互相結合,一個人在講究事實與邏輯的同時還應具有直覺與靈感。此刻,拉姆齊先生希望通過到達燈塔與妻子在精神上重新團聚,建立一種和諧與完美的關係。他與子女之間的隔閡和積怨也逐漸消溶了。長期在理性王國中生活的拉姆齊先生突然獲得了精神上的升華。
莉莉小姐這天沒有隨他們一起去燈塔,當她自送他們遠去時,拉姆齊太太的形象也浮現在她心中,她突然得到了啟示,於是一揮而就,完成了那10年前就因受思想的困擾而不能完成的那幅畫。當她作完畫放下畫筆時,她的精神得到了升華。而此時,拉姆齊先生的帆船剛好抵達燈塔。
結構特色
 《到燈塔去》
《到燈塔去》這是一部作者傾注心血的準自傳體意識流小說。小說以到燈塔去為貫穿全書的中心線索,寫了拉姆齊一家人和幾位客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片段生活經歷。拉姆齊先生的幼子詹姆斯想去燈塔,但卻由於天氣不好而未能如願。後大戰爆發,拉姆齊一家歷經滄桑。戰後,拉姆齊先生攜帶一雙兒女乘舟出海,終於到達燈塔。而坐在岸邊畫畫的莉麗・布里斯科也正好在拉姆齊一家到達燈塔的時候,在瞬間的感悟中,向畫幅中央落下一筆,終於畫出了多年縈迴心頭的幻象,從而超越自己,成為一名真正的藝術家。全書並無起伏跌宕的情節,內容分三個部分,依次為:窗;時光流逝;燈塔。最主要的人物拉姆齊夫人後來死去,其實際活動僅限於小說的前半部分。關於她的一系列描述,是以作者本人的母親為生活原型的,而拉姆齊先生則有作者父親的影子。此外,作者著墨最多的是莉麗・布里斯科。表面上看,莉麗語言寥寥,其主要行為主要是為拉姆齊夫人作畫,但該人物的思想活動相當活躍,作者以自己為原型塑造了這個人物,並“為小說結構安排了潛在的雙重線索和複合層次。……莉麗這個人物既在這部小說世界之中,又在它之外;拉姆齊一家的經歷是第一層次的故事,莉麗所體現的‘藝術―生命’主要是第二層次的故事,是包裹在小說外面的又一部小說。”
小說第一部分臨近結尾處,拉姆齊夫人——到第二部她就死了——的一段內心獨白,可能更其重要…… 伯·布萊克斯東在《維吉尼亞·吳爾夫:一篇評論》中說:“閱讀了《燈塔》之後再來閱讀任何一本普通的小說,會使你覺得自己是離開了白天的光芒而投身到木偶和紙板做成的世界中去。”這代表了有關《到燈塔去》的一種看法;讀過此書的讀者,也許還有別的乃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可能會嫌情節成分太少,人物面貌不清。歷來關於伍爾芙的批評,大多針對她的人物;人物性格通常藉助情節展現,所以連帶涉及情節;此外還責怪她視野太過狹隘。以上兩種意見,姑且不置可否,有一點須得指出:批評者——不管是論家還是讀者——所希望獲得的,伍爾芙壓根兒不打算供給,她另外奉獻一些別的。布萊克斯東因此否定其他作品雖未必可取,但《到燈塔去》的確不是一本普通小說。那么也就不能用讀普通小說的眼光來讀它。這句話說來簡單,實行並不容易。我們要 想與伍爾芙一類作家達成共鳴,卻又只能這樣。就像她所說的:“不要對你的作家發號施令,要試圖與他化為一體。你要做他創作活動中的夥伴與助手。”(《應該如何閱讀一部作品》)每種創作方法都是獨立的價值體系;不同的閱讀方法,適用於不同的創作方法。畫地為牢,乾脆不讀算了。 對於上述批評意見,伍爾芙自己早有回答。好比講到人物,她說:“我要弄清楚,當我們提起小說中的‘人物’時,我們是指什麼而言。”( 《貝內特先生與布朗夫人》 )
早在《到燈塔去》完成之前八年,也就是她即將轉向意識流小說創作時,所說就很明白:“讓我們考察一下一個
 《到燈塔去》
《到燈塔去》似乎與作家的看法相呼應,《到燈塔去》中拉姆齊夫人這樣想:“我們的影像,你們藉以認識我們的東西,都是膚淺可笑的。在這些影像下面是一片黑暗,無邊無際,深不可測;我們只不過偶爾浮到表面,你們就是依靠這個認識了我們。”所涉及的還是前述“內”與“外”的問題。但是伍爾芙的小說並沒有完全放棄“外”,而是藉助與“外”的聯繫來寫“內”;也就是說,在現實環境與內心活動接合處,選取一個足以充分展現人物內心世界的視角。正如埃·奧爾巴赫所說,“在維吉尼亞·伍爾芙手中,外部事件實際上已經喪失了它們統帥一切的地位,它們是用來釋放並解釋內部事件的。”(《摹仿——西方文學中所描繪的現實》)所以情節儘可能地被簡化,因為複雜非徒無益,反而有礙,不過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總體而言仍然需要一個事件的框架,就局部而言則在細節選擇上多所精心,人物所有的心理活動都被置諸這一框架之內,而為那些細節所觸發,所聯絡,造成無數如她所強調的“重要的瞬間”,其間針線相當綿密。Н·П·米哈爾斯卡婭所言不差:“她的作品結構,總是給人某種理性主義的感覺,讓人覺得裡面有一番周密的苦心思考。這種苦心思考,使她的小說區別於許多現代主義作家那些結構混亂而故作鬆散的作品。”
女性主義解讀
 《到燈塔去》
《到燈塔去》女性寫作是在六十年代末由法國激進的女性主義者西蘇、伊瑞伽利等提出 ,但是早在二十年代伍爾芙對此就有所感悟,並進行闡述 ,因為作家本人在創作中就受到男性邏各斯中心話語的困擾。在《一個人的房間》里她這樣寫道:“當女性作家提筆寫作時,她所發現的第一件事就是沒有現成的普通句子可以使用。”女性走進房間 ,她還沒來得及描述房中所發生的一切 ,英語的所有資源就已經用到了極限 ,成群的單詞必須歪歪扭扭地非法形成。
《到燈塔去》中的女性人物就面臨著交流的困境,數千年的男權統治使男性中心意識早已成為人類的集體無意識,滲透進包括語言在內的所有文化中 ,女性成了被剝奪聲音的群體,她們沒有自己的語言來表達女性特有的體驗和心理,以及女性相互間的理解。蘭姆賽夫人對自我的感覺,只能用“楔形的核心黑暗”來形容,“這黑暗的自我沒有任何累贅,自由地進行最奇異的冒險。 ”她無法用言語來表達她所知道的莉麗,無法把自己的體驗說出來讓莉麗明白,莉麗也只是感覺到夫人的神秘,兩人之間的相互了解局限於感覺卻無法言傳。留給莉麗的任務就是避開男性邏各斯中心的思維,摸索出語言之外的交流工具 ,以一種女性的眼光來理解作為女性的夫人。莉麗最終找到一種方式,那就是藉助於視覺形象藝術——一種更貼近女性心理和體驗、較少受到男性邏各斯中心思維污染的交流途徑。
 《到燈塔去》
《到燈塔去》在為男性中心意識所左右的傳統小說中 ,有故事情節,情節的發展有開端、高潮和結尾,有重大事件,強調通過行動來刻畫人物。但是在小說《到燈塔去》中,幾乎沒有故事情節,唯一貫穿全篇的就是小說開頭和結尾處提到的“到燈塔去”,也沒有行動來刻畫人物。男性化的、邏輯嚴密、線性發展的外在情節描述讓位於女性化的、散漫細緻的心理情感描寫。重大事件,如夫人去世、第一次世界大戰、安德魯和普茹的死,全放在括弧里一筆帶過。小說的中間部分即傳統小說的重心是充滿詩意的抒情散文,幾乎沒有人物。人的隱退是對傳統以人為主的小說的極大嘲諷。同時,作家的語言也體現了所謂的女性化特徵:句子鬆散、零碎、常常拉得很長。小說在女作家的手裡,已經變成了她抒發詩歌情感的出口,變成了她書寫女性獨特情感和體驗的工具,是一曲變相的抒情輓歌。
綜上分析,可以看出小說《到燈塔去》是一部帶有鮮明女性主義特徵的文學作品與後世的激進女性主義相比,其對女性主義理解的深度和廣度早已超越了時代的限制,也毫不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