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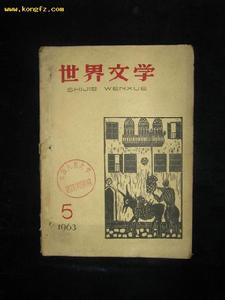 1963年的世界文學
1963年的世界文學創辦初期譯載的多是文學名著,如印度迦梨陀娑的《雲使》,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語》,俄國列·托爾斯泰的《舞會之後》,捷克哈謝克的《好兵帥克》,波蘭密茨凱維奇和匈牙利裴多菲的詩,法國伏爾泰與巴爾扎克,德國歌德與海涅,美國惠特曼與馬克·吐溫,英國莎士比亞與拜倫等作家的作品;近代與現代作家有蘇聯的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特瓦爾多夫斯基、波列沃依等人的作品;東歐作家有伐佐夫(保)、米克沙特(匈)、西格斯(民主德國)、薩多維亞努(羅)、努西奇(南)、恰佩克(捷)等人的作品;亞洲現代作家有普列姆昌德(印度)、涅辛(土)、達木丁蘇倫(蒙)、樋口一葉(日)、布羅山(菲)、阿笛布(巴基斯坦)等人的作品;非洲作家有阿·阿里-哈米西(埃及)、狄布(阿爾及利亞)、桑戈爾(塞內加爾)等人的作品;拉美作家有紀廉(古巴)、亞馬多(巴西)、聶魯達(智利)、阿斯圖里亞斯(瓜地馬拉)、勒翁(委內瑞拉)、杜尼昂(阿根廷)等人的代表作;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作家有海明威與福克納(美)、康拉德與毛姆(英)、阿拉貢與薩特(法)、溫都利和莫拉維亞(意)、茨威格(奧地利)等人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家是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來,使中國讀者更多的了解了外國文學,擴大了他們的視野。
 世界文學(1978)
世界文學(1978)50年代後期,國際上文藝思想鬥爭日趨尖銳、複雜。中國讀者已不滿足於唯讀翻譯文章,要求中國作者用自己的觀點評論外國作家與作品,對文藝論爭、思想鬥爭等重大問題,發表意見。根據新的形勢和要求,該刊內容有所改變,以一定篇幅刊載中國作者撰寫的評論,並就有關作品組織討論。這一時期中,發表了茅盾關於列·托爾斯泰的《激烈的抗議者、憤怒的揭發者、偉大的批判者》和《契訶夫的時代意義》,老舍的《馬克·吐溫—“金元帝國”的揭露者》,蕭三論法捷耶夫,曹靖華論魯迅,冰心談日本女作家,戈寶權有關中外文學交流的論文,季羨林論巴利文《佛本生的故事》,楊朔介紹朝鮮丁茶山(丁若鏞),徐遲分析紀廉的詩,王佐良評價50年代美國幾位進步作家的優秀小說等論著。
同一時期《世界文學》還推薦了很多中國讀者不太熟悉的外國作家和他們的代表作,如日本的井伏鱒二(《遙拜隊長》),塞內加爾的烏斯曼(《沃爾特人》),奈及利亞的阿契貝(《瓦解》),蘇聯艾特馬托夫的《查密莉雅》和雷特海烏描寫楚克奇民族生活的小說,瑞士杜倫馬特的《拋錨》,義大利皮蘭德婁的《西西里檸檬》等。
1966年《世界文學》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刊。1977年10月復刊,內部試刊一年後,公開發行。隨著國家撥亂反正,走向正常發展。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第一屆年會以後,《世界文學》注意譯介有教育意義、有借鑑作用、有藝術價值的外國文學作品,積極發表無產階級文學家的著作,熱情推薦新興國家的優秀新作,有選擇地發表西方資產階級文學名作;同時加強對外國文藝思潮的研究和介紹。對某些外國有影響的作家,如匈牙利文藝理論家盧卡契、智利詩人聶魯達、美國詩人龐德、英國小說家勞倫斯、奧地利小說家卡夫卡等進行重新評價。還發表了中國作者撰寫的有關荒誕派、黑色幽默、存在主義、結構主義、新小說派、魔幻現實主義等西方各種文學流派的論文。
 世界文學(1977)
世界文學(1977)新時期的《世界文學》重視反映外國文學現狀,介紹了不少在各自國家引起強烈反響的作品,如美國馮尼格和歐茨的小說,法國埃梅和特羅亞的短篇,聯邦德國伯爾、蘇聯阿斯塔菲耶夫、舒克申和瓦西里耶夫等的作品,匈牙利莫爾多瓦的諷刺小說,保加利亞維任諾夫的中篇,日本井上靖的《鬥牛》,朝鮮的《血海》等。對贏得世界聲譽的文學作品做了及時的報導與推薦,如關於希臘的埃利蒂斯的詩,哥倫比亞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小說《百年孤獨》,英國戈爾丁的小說,奧地利卡奈蒂和他的小說《迷惘》等。
《世界文學》除刊載作品、評論外,還辟有《文化交流》《文藝動態》、《文學家小傳》、《訪問記》等欄目,並選登美術作品。《世界文學》還編輯了《世界文學叢書》。
30多年來,《世界文學》向讀者介紹了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學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文藝界和廣大文藝愛好者的需要,為中外文學的交流,增進中國人民對世界各國人民及其文學的了解,作出了貢獻。
刊物內容
《世界文學》除刊載外國優秀的文學作品外,還辟有文化交流、國外通訊、評論、文摘、書評、譯壇縱橫、外國文學翻譯出版漫筆、作家談創作、編譯者序跋、外國文學資料、世界文藝知識、文學史話、作家逸事、中外作家答本刊問、中國作家談外國文學、中國詩人談外國詩、世界文壇熱點、中國文學在國外、世界文藝動態等多種欄
 世界文學叢刊之夜馳白馬
世界文學叢刊之夜馳白馬世界文學雜誌社還出版介紹世界各國文學現狀的雜誌《外國文學動態》,編輯過《世界文學叢刊》十五種、《世界文學小叢書》十種、《〈世界文學〉30年優秀作品選》(小說、散文類)、《外國優秀散文選》《世界文學精粹40年佳作》和其他選集。
最近二十年來,國內直接出版翻譯作品的出版社越來越多,出版速度也越來越快,而《世界文學》受到篇幅、出版周期等因素的限制,只能依靠編輯部人員的研究水平和文學判斷能力,力圖尋找一些經得起時間積澱的考驗,能夠體現出世界文學歷史發展方向,真正值得介紹給中國讀者的作品。尤其那些篇幅比較小一些的中短篇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紀實文學等體裁的作品。
《世界文學》內容豐富、譯文忠實、品位高雅、文圖並茂,長期以來深受國內廣大讀者喜愛,對繁榮我國社會主義文學,提高中華民族整體文化水平和促進中外文化交流起著重要的作用。
刊物影響
《世界文學》在海外也享有盛譽。它同世界上許多國家及地區的文學界、學術機構
 世界文學五十年作品選
世界文學五十年作品選進入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整個世界的文化越來越體現出商業化的傾向,閱讀—— 尤其是文學閱讀越來越讓位於視聽媒體的傳播。國內也已發生此類的轉向:文學不再作為人們業餘享受的主要精神食糧和娛樂形式。在這一文化轉型的大環境中,《世界文學》並不隨著世俗趣味的改變而改變自身原來的辦 刊方針,而是堅信,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人們文化結構多層次多差異的國家中,《世界文學》應該為那些渴望了解世界各國的經典文學、了解各國文學發展動向的人們,保留一個視窗,提供一片風景。
從2002年的第5期起,《世界文學》連載了文學資料“世界文學五十年”大事記,結合《世界文學》辦刊五十年的風風雨雨,以短小精悍的篇幅,回顧了世界各國五十年中的文學大事,力圖為讀者提供一幅世界文學的大致面貌。這一資料得到了一些讀者的好評。
《世界文學》的存在理由
左翼批評家歐文•豪在《異議》創刊的時候(一九五四年)曾說:“當知識分子不能做其他事時,就去辦刊物。”倒好像在麥卡錫主義的高壓政策下,辦刊物成了左翼知識分子本來充足的日程表上剩下的惟一一項可能有所作為的事。但把這句話略作修改,或許更恰如其分——“當知識分子能做什麼事時,想到的頭一件事也是去辦刊物。”對文學知識分子來說,尤其如此,或許他在文學知識分子之外還是一個革命者、一個密謀家、一個板球愛好者、一個集郵迷或一個引誘者,但只要他還是一個文學知識分子的話,人們就會根據他的文學作品和文學作為來評判他的本質。
一、魯迅創辦的《譯文》:《世界文學》的前身
魯迅那一代文學知識分子當然可以選擇成為文學知識分子之外的任何角色,而且他們當中的確有不少人後來轉而從事或者兼顧別的事業,但他們若要仍以文學知識分子自命的話,他們就只能通過自己的文學事業來表明這一身份,而文學刊物能使文學知識分子得以有形地存在,並以小群體的形式存在。前刊物時代當然也有文人和作品,但這不過是單個人的行為,是不時偶然出現的事件,但刊物卻是有著共同宗旨的一小群人的群體行為,它類似於政治密謀家們的結社。對魯迅那一代人來說,一份刊物就是一份宣言,一種思潮,一種同仁精神。所以它往往超越創辦者個人的意志,成了一種共同意志;此外,這種超越還表現為,在最初的創辦者謝世以後,一代代的後繼者仍以群體的形式服務於這個刊物,服務於這個刊物所體現的那種意志。意志仿佛具有了自身的生命力。也正因為如此,一份刊物的終結,就不僅是類似單個作家的死亡那樣的事件,而是一種意志的頹敗、一種思潮的衰落、一種同仁精神的瓦解的表象,它所引發的是對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的感嘆。
 譯文(1955)
譯文(1955)但魯迅為何棄醫從文,而不像其他人那樣棄文從政或棄筆從戎?在一個急需政治家和軍事家的時代,魯迅為何選擇成為一個文人?難道文學是比政治或軍事更緊要的事?魯迅自己在《吶喊•自序》中給出了一種解釋:“從那一回過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學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在魯迅前前後後創辦的那些文藝雜誌中,有一九三四年九月創刊的《譯文》,即一九五三年七月復刊的《世界文學》的前身。
二、感性的深化可為社會革命奠定深厚的人性
改造國民精神的東西,不徒文藝而已。政治學說、科學知識同樣可以有所作為,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口號。但魯迅對國民性的悲觀主義看法以及他的平民主義的主張,使他與同時代的那些激進的啟蒙主義者不同。在那些激進的啟蒙主義者看來,一場以精英分子為主體的暴風驟雨般的社會革命,能夠使民主的政治體制和科學的理性精神旦夕間成為現實。但魯迅卻認為這種不觸及國民精神的革命只不過是邪惡的歷史的又一次循環而已,無非是阿Q們取代趙老太爺們,不管阿Q們打出的旗號如何不同。沒有新人,就沒有新社會,而新人的塑造卻有賴於感性的改造。換句話說,現代社會的真正歷史主體是現代人。不能指望意識仍停留在蒙昧的古代的人完成一項真正現代的事業。作為一場社會革命的前提,必須有一場人類學或者生物學意義上的革命,以此鍛造作為未來新社會之基礎的新人。
這意味著魯迅所從事的是一項意義重大的基礎工作,是一項人類學或生物學意義上的工作,是對國民性的改造。在這方面,文藝大有作為,因為文藝直接訴諸人的感性;此外,感性的深化,可以為激烈的社會革命奠定一種深厚的人性。文藝運動就這樣成了魯迅的現代性計畫中最核心、最內在的一環。這當然不是魯迅的獨家發明,更早一些時候的梁啓超就曾把“小說界革命”視為“改良群治”和“新民”的必經步驟,是一系列革命的最初始的革命。他在1902年發表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云:“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無論是梁啓超,還是魯迅,都把“歐西”小說當作“新小說”的楷模。他們不僅是熱心的翻譯家,而且是受外國文學影響的作家。魯迅談到自己的創作時稱:“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國的作家。”
三、“世界”是它的視域,“文學”是它的立場
 世界文學(1981)
世界文學(1981)儘管梁啓超和魯迅對小說或者文學在意識現代性中的作用的理解過於誇張,但事實是,那一代人對西方現代性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對西方文學的閱讀,而且,的確,與西方現代政治學說和科學知識所包含的體制化的現代性不同,西方現代文學提供的是一種複雜的意識的現代性。這就是說,前一種現代性計畫可以歷史地完成,而後一種現代性計畫卻處於永遠未完成的狀態,但沒有後一種現代性計畫的完成,前一種現代性計畫的完成永遠處在殘缺的完成狀態。這樣,後一種現代性計畫就成了前一種現代性計畫的質疑者和批評者。《世界文學》的復刊和持續存在,是後一種現代性計畫仍然處在未完成狀態的表征。
我們生活在一個“終結”的時代,仿佛歷史的諸種計畫正在一個個地完結。但歷史若以這種殘缺的方式終結的話,那無疑是一場悲劇的寂靜的尾聲。不,歷史之門依然洞開,在我們面前依然不斷變換出自由、夢想、尊嚴和美的種種幻象。我們由此看出我們的世界和生活是殘缺的,是卑微的,而我們並沒有停止去夢想一個更自由、更人性的世界,一種更尊嚴、更美好的生活。《世界文學》依然與這一事業息息相關。“世界”是它的視域,而“文學”是它的立場。在一個充斥著小店主和總經理並且視野日益拘束於方孔之間的時代,它是一個不倦的守夜人。但那不是一個孤單的人,而是一小群人,在一種共同意志的激勵下工作。魯迅在《〈譯文〉復刊詞》里曾引莊子的一段話來描繪這種艱難時刻的同仁精神:“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相煦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
宗璞
| 致力於研究宗璞的相關信息,包括其出生、生長背景,主要作品等。 |
教科文藝期刊大全(十二)
| 教科文藝期刊雜誌涵蓋了各國民俗文化、民間藝術、民間傳統手工藝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國際文化、藝術,且對其保護與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