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劉寶瑞
劉寶瑞生平經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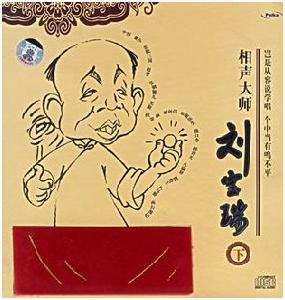 劉寶瑞
劉寶瑞劉寶瑞(1915—1968)相聲演員。北京人。自幼家境貧寒,曾隨崇壽峰學藝,後正式拜張壽臣為師,學說相聲。十四歲時,去天津與馬三立、趙佩茹、李潔塵等在南市連興茶社相聲大會上演出,並常到廣播電台播音,初露頭角。
抗日戰爭前,劉寶瑞曾赴濟南光明茶社演出,編演了相聲《韓復榘講演》,揭露當時山東省主席、親日派直系軍閥-韓復榘驕橫昏庸、不學無術的醜態。民國二十九年(1940),他從濟南回到北京,在西單啟明茶社相聲大會作藝,擅演《八扇屏》、《歪批三國》、《朱夫子》等“文哏”相聲。後去南京、上海等地演出。四十年代末,赴香港演出,首先把相聲藝術介紹給予港澳觀眾。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劉寶瑞赴南京、上海等地,與曲藝名家白雲鵬、高元鈞合作演出。他常演單口相聲,經與南方曲藝同行切磋琢磨,使他的單口相聲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汲取了南方獨腳戲及評話的藝術技巧,又借鑑電影、話劇的表演手法,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的風格,被人們譽為“單口大王”。他是把北方相聲藝術介紹給江南及港澳觀眾的先行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2年,他回到北京,參加了中國戲曲研究院實驗曲藝團。後調中央廣播說唱團任藝術指導。1954年春節期間,他到北京郊區為農民演出,同年4月,他到琉璃河北水泥廠下廠輔導工人曲藝隊伍。此後,他為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的曲藝訓練班堅持教學十二年,培養出大批青年相聲演員。他對新相聲的創作,對傳統相聲挖掘整理,對發展與提高單口相聲的表演藝術,均作出重要貢獻。
1959年夏天,他去福建前線慰問解放軍,在艱苦的條件下深入前沿陣地演出。為了體驗部隊生活,他一遍又一遍地練習持槍、臥倒、射擊。他訪問了偵察英雄紀瑞瑄,及時創作、表演了歌頌英雄的單口相聲《神兵天降》,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篇軍事題材的單口相聲。
六十年代初,他和侯寶林、馬季一起,經常去北京中南海,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做專場演出,並多次受到親切接見。
劉寶瑞單口相聲的代表作之一《連升三級》曾被編進中學語文課本,同時被譯成英、法、日等國文字,介紹到國外。
劉寶瑞為人謙恭和藹、誨人不倦。1960年,中央廣播說唱團附設相聲學習班,招收了十幾名學員,由他負責輔導,後來這些學員大部分成為各專業文藝團體的骨幹力量。為培養馬季掌握傳統段子,錄製《找堂會》、《扒馬褂》等段子時,他為馬季捧哏,並將許多傳統相聲傳授給馬季和唐傑忠。1960年,廣播說唱團挖掘整理傳統相聲,動員演員們口述筆記,劉寶瑞積極參加,他記錄下來的單口相聲文字稿及錄音在全團數量上占第一位。
“文化大革命”期間,劉寶瑞遭受嚴重衝擊和迫害,1968年10月8日下午,他在北京房山農場勞動時受到現場批鬥,當晚逝世。
劉寶瑞的學生有周文游、殷文碩、高洪順、唐傑忠等十三人。他生前口述的八十段單口相聲,經殷文碩回憶記錄,整理成文,輯為《劉寶瑞表演單口相聲選》,1983年由中國曲藝出版社出版。
人物生平
早年生平
劉寶瑞1915年生於北京,本名劉明光。自幼家境貧寒,九歲開始接觸相聲藝術,常遊走於北京天橋和東安市場相聲場子之間,曾隨崇壽峰學藝。十三歲正式拜張壽臣為師(張壽臣為其取藝名劉立棠),學說相聲。十四歲赴天津,與馬三立、趙佩茹、李潔塵等在南市聯興茶社相聲大會演出,並常到廣播電台播音,初露頭角。1932年,17歲的劉寶瑞與18歲的馬三立搭檔,去營口、煙臺、青島等地“跑碼頭”,演出相聲。在從營口開往煙臺的輪船上,由於身無分文,兩天沒吃東西,劉寶瑞餓昏了,馬三立迫不得已,偷了別人兩個燒餅,才救了劉寶瑞一命。從此,劉寶瑞和馬三立結下了十分深厚的友誼。
戰亂時期
1937年,劉寶瑞赴濟南光明茶社演出,期間編演了相聲《家務事》、《韓復榘講演》(《韓青天》),揭露當時山東省主席、親日派直系軍閥韓復榘不學無術、驕橫昏庸的醜態。1939年,天津水災,劉寶瑞前往唐山演出,水災過後返回天津。20世紀40年代,為維持生存,劉寶瑞一直不間斷地在各地“跑碼頭”。期間曾在天津、北京、濟南、南京、上海等地,與曲藝名家白雲鵬、高元鈞等合作演出。
1941年,劉寶瑞到開封演出兩個月,期間同張傑堯(張傻子)合作演出。1944年,劉寶瑞在濟南創辦“共樂茶社”相聲大會,邀請張壽臣、於世德、張立森、王長友、高桂清、來少如等演出。濟南相聲場子垮了之後,劉寶瑞從濟南回到北京,入“啟明茶社”演出,期間和郭榮起搭檔,互為捧逗,一連在電台播演了四個月的相聲節目,在北京城造成較大影響。
1949年,劉寶瑞與趙月華結婚並在南京成了家。沒過多久,為生活所迫,劉寶瑞只身前往香港,成為第一個把相聲帶到香港的藝人。
建國之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已在香港頗有人緣的劉寶瑞回到解放後的上海。1952年回到北京,參加中國戲曲研究院實驗曲藝團。後調中央廣播說唱團任藝術指導。從1954年起,劉寶瑞先後去過江、浙、魯、豫、內蒙古等地基層演出。1954年春節期間,到北京郊區為農民演出,同年4月,到琉璃河北水泥廠下廠輔導工人曲藝隊伍。此後,劉寶瑞為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的曲藝訓練班堅持教學十二年,培養出大批青年相聲演員。
1959年夏天,劉寶瑞去福建前線慰問解放軍,訪問了偵察英雄紀瑞瑄,及時創作、表演了歌頌英雄的單口相聲《神兵天降》,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篇軍事題材的單口相聲。
六十年代初,劉寶瑞和侯寶林、馬季一起,經常去北京中南海,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做專場演出,並多次受到親切接見。
1962年春節,為貫徹中宣部“國家暫時困難時期,物質生活貧乏,在宣傳上應著眼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使人們充滿笑聲”的指示,中央電視台(當時名為“北京電視台”)舉辦以相聲為主的“笑的晚會”,“大軸兒”是劉寶瑞等表演的多人相聲《諸葛亮升帳》,相聲的“底”由王決設計,是諸葛亮的一盤點心被帳下四員大將吃了,滑稽可笑,頗受歡迎。(這段相聲到“文革”期間被無限上綱,打成“毒草”。“底”被誣為“惡毒攻擊人民飢餓,搶點心吃,發泄對現實的不滿。”)
文革時期
“文化大革命”期間,劉寶瑞遭受嚴重衝擊和迫害,被下放北京房山農場勞動。1968年10月8日(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下午,劉寶瑞在北京房山路村勞動時受到現場批鬥,當晚逝世,年僅53歲。劉寶瑞死後其屍首被草草掩埋,至今遍尋無果,只留衣冠冢葬於北京朝陽陵園。名家點評
 劉寶瑞
劉寶瑞名家點評相聲藝術素有“演員肚,雜貨鋪”的美譽,非熟知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有豐厚的文化底蘊不可。劉寶瑞堪稱老一輩藝人中善使雜學兒的第一人……他的單口相聲正如藝諺說的“裝龍裝虎我自己,一個人好似一台大戲。”——當代學者薛寶琨。
劉寶瑞先生最突出的藝術成就表現在單口相聲方面,他繼承老一輩藝術家張壽臣先生的表演風格,集單口相聲之大成,他的藝術風格沉、穩、準、狠。觀眾聽他說相聲感到很舒服,耐人尋味。——相聲表演藝術家李增瑞。
抗日戰爭前,劉寶瑞曾赴濟南光明茶社演出,編演了相聲《韓復榘講演》,揭露當時山東省主席、親日派直系軍閥-韓復榘驕橫昏庸、不學無術的醜態。民國二十九年(1940),他從濟南回到北京,在西單啟明茶社相聲大會作藝,擅演《八扇屏》、《歪批三國》、《朱夫子》等“文哏”相聲。
流派師承
清代八角鼓有名丑角張三祿,以說、學、逗、唱四大技能作藝,自稱其藝為“相聲”。張三祿乃相聲發始創藝之一。其後相聲之派別,分為二大派:一為朱派,二為阿派,三為沈派。朱、沈、阿三大派,沈、阿的門戶不旺,其支派下傳流的門徒亦是很少,並且無有這么出奇角兒。朱派系“窮不怕”,其名為朱少文。
朱少文(窮不怕)的徒弟是徐永福,生意人都稱他為徐三爺。徐永福的徒弟,為李德祥(現在津埠)、李德鍚(即萬人迷)、裕德隆、馬德祿、盧德俊(即盧伯三)、焦德海、周德山(即周蛤蟆)。
劉寶瑞以單春(即是單口相聲)闖出名氣。說相聲最難的是單春。一個人的相聲能把聽主逗笑,實是不易。朱派朱少文就以使單春成名。在說相聲這行里使單春的,朱少文可算是他們的開山祖。
相聲名段
對口
 大師台上的風采
大師台上的風采劉寶瑞、郭全寶
《當行論》、《打燈謎》、《奉承人》、《高人一頭的人》、《找對象》、《做大褂》、《走馬觀碑》
《坐汽車》、《八扇屏》、《九點鐘開始》、《批聊齋》、《值班醫生》、《猜地名》、《吃飯我掏錢》
《寸步難行》、《飛油壺》、《趕考》、《蛤蟆鼓》、《韓青天》、《好啊好》、《買猴》、《繞口令》
《說字》、《我的歷史》、《西行漫記》、《學叫喚》、《支援新廠》、《住醫院》、《歪批三國》、
《韓青天》、《投其所好》、《乘客之家》
劉寶瑞、侯寶林
《文王卦簽》、《講帝號》、《非洲獨立進行曲》、《講貫口活》、《南方捷報》、《王二姐思夫》
劉寶瑞、郭啟儒
《北京地名對》
《蛤蟆鼓》《畫扇面》《學叫喚》
劉寶瑞、馬季
《連逗帶打》、《戲迷藥方》、《拔牙》、《找堂會》
劉寶瑞、李文華
劉寶瑞、張傑堯
《酒詩》
劉寶瑞、唐傑忠
《柳堡的故事》
劉寶瑞、郝愛民
《寧波話》《對春聯》
群口
《金剛腿》劉寶瑞、郭全寶、馬季
《一匹馬》劉寶瑞、郝愛民、於世猷
《開場小唱》劉寶瑞、郭全寶、侯寶林、郭啟儒
《賣馬》劉寶瑞、侯寶林、高鳳山
《扒馬褂》劉寶瑞、郭全寶、馬季
《拆字》劉寶瑞、郭啟儒、馬季
單口
《珍珠翡翠白玉湯》、《黃半仙》、《日遭三險》、《連升三級》、《假行家》、《兵發雲南》、《學乖》、《學徒》、《測字》、《文廟》、《書迷打砂鍋》、《扎針》、《天王廟》、《解學士》、《官場斗》、《鬥法》、《打油詩》、《化蠟釺》、《風雨歸舟》、《翻跟頭》、《狗噘嘴》、《知縣見巡撫》、《大鬧縣衙門》、《要賬》
經典相聲
1、珍珠翡翠白玉湯
 表演珍珠翡翠白玉湯劇照
表演珍珠翡翠白玉湯劇照呃,今天我說這段單口相聲啊,這可不是現在的事情。多暫的事情呢?反正那個離現在也不算遠,才六百多年!
在這個元末的時候啊,有個朱元璋,後來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義。打算推翻元朝,帶領著常玉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鬧武科場,寡不敵眾,敗出北京,弟兄失散。現在呢,我單說朱元璋一個人,單槍匹馬,落荒而逃,跑了有二三百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餓,實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個小破廟。哎,在廟裡頭歇一會兒吧!趕到這兒一下這個馬呀,就暈倒了,自己都不知道啦。過了很長的時間哪,來了倆要飯的。這倆要飯的就在小破廟裡住,要了好些個乾餑餑、剩餅子啊,還有一鍋剩餘和菜湯子。到這廟門口一瞧:喲!這兒怎么躺著一個人啊。一看這人模樣:長腦袋,大長下巴頜,怎么長的跟驢似的?過來一摸身上有熱氣兒,救人要緊!就給撈到廟裡頭去了。
到了廟裡頭呢,找了點樹枝子、爛柴火點著了暖一暖屋子,然後就給朱元璋盤起腿兒來,讓他緩過這口氣來。過了很長的時間,朱元璋緩醒過來了,可是心裡頭還發迷糊呢,他還以為呀,跟常玉春、胡大海在武科場那兒一塊兒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常玉春,“哎,常賢弟!”這一叫常賢弟呀,倆要飯的一聽一愣!這要飯的說:“喲?哎?奇怪呀!我不認識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先弟呀?”朱元璋那兒又叫:“啊,來!”那個要飯的也納悶兒啦,“喲?他也認識我姓來!”您瞧這巧勁兒的
“啊,你怎么回事啊?”“我餓啦!”噢,這人沒病。心說:這餓的滋味兒不大好受,因為我們哥倆常跟這餓打交道。這沒別的,得啦,咱們救人要緊。“乾脆,他俄啦。咱把這鍋剩菜湯子給他喝了得啦。”“那也得熱熱呀!”“對!”找了三塊小磚頭,沙鍋一支,柴火點著了。
“你光給他菜湯子喝,他也不飽啊!”“不要緊!我這兒不還要了點糊飯嘎巴兒嗎!”“哎對!”擱到沙鍋里啦!“哎!”這說,“好啊,我這兒還半塊餿豆腐哪。”也擱鍋里啦!還有點白菜幫子,撅巴撅巴扔鍋裡頭,還兩棵爛菠菜,一塊兒得啦!一會兒工夫熱了,把沙鍋端過去了。
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餓,雖然餿豆腐有味兒,也聞不出來,“咕咚咕咚”把這鍋剩菜湯子喝下去了。嘿,該著的事情,他這一路啊,疲勞過度,已經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現在呢,這鍋熱菜湯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這感冒好了,有精神啦。就問這倆人,“哎呀,你們二位貴姓啊?”這要飯的一聽怎么意思?開玩笑啊?以了半天又不知道貴姓啦?“你不是叫我了嗎?姓常,叫常先弟嗎?”“噢,對,對,對。”朱元璋他含糊答應,“那你們兩位給我做這鍋湯叫什麼名字呢?”倆要飯的這個氣呀!心說:雜和菜湯子,哪有名字啊?
這個說:“哎?他要問呢,咱就給起個名兒。”“起名叫什麼呀?”“就告訴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湯’”。“你別瞎扯啦!哪兒來的‘珍珠翡翠白玉湯’啊?”“哎,當然有啊。”“有?珍珠呢?”“珍珠啊,咱那個糊飯嘎巴碎米粒兒,那不就珍珠嗎?”“那么這個翡翠呢?”“翡翠呀,白菜幫子,菠菜葉,那不翡翠呀?”“白玉湯,那玉呢?”“啊,我那半塊餿豆腐,那不算呢?”“對,對對。我們這個叫‘珍珠翡翠白玉湯’。”“好,名字還挺好。謝謝你們二位。我還要打仗去哪,咱們是他年相見,後會有期。”說完這話出了廟門兒,上馬走了。
過了幾年的工夫啊,朱元璋真把這個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來了,就是朱洪武。他做了皇上怎么樣?做皇上以後,跟其他皇上沒有區別了。每天也是吃的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緞,娶的是三宮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順百從。皇上說什麼,群臣就得跟著說什麼。哪怕這皇上說這煤是白的,誰都不敢說是黑的。說黑的,抗旨不遵,殺!這就完啦。皇上要給大臣不論任何一樣東西,這個大臣呢,都得拿到家去,供到祖先堂,顯示顯示。哪怕皇上賜給大臣一張草紙,大臣都得拿黃綾子裱起來,供到祖先堂,當作爭光耀祖、顯耀門庭,御賜的——擦屁股紙,就這么厲害。
這個朱元璋坐了幾年皇上以後,吃喝玩樂,老是這套,他煩了。忽然間,有這么幾天,身上不好過,懶洋洋的,渾身酸懶,怎么這么個滋味啊?一琢磨:哎?這滋味兒就跟我當年落難在小破廟裡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難過。我想起來了,那年人家給了我一鍋“珍珠翡翠白玉湯”啊,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了,就好了。現在我又難過了,要再來碗“珍珠翡翠白玉湯”喝,也會好過。對,哎呀,不行。沒人會做呀?哎,找這兩個人,一個叫常賢弟,我記著呢。
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縣貼皇榜,選兩個會做“珍珠翡翠白玉湯”的人。一個叫“常賢弟”,那個不知叫什麼名字。 簡短截說,我就說當年他落難時的那個縣城,也貼了皇榜了。這個皇榜貼到什麼地方?縣衙門對過,有個影壁牆,貼在這影壁牆上去了。這皇榜一貼出去,老百姓不知什麼事,圍過來就看。正看著呢,嘿嘿,無巧不成書,正趕這倆要飯的從這兒路過。倆要飯的一看這兒圍著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過來了一撥拉這位:“哎,勞您駕,您看什麼呢?”
這位回頭一看是倆要飯的,“去!走啊!打聽什麼呀?打聽心裡是病,問這有什麼用啊,皇上找兩個會做‘珍珠翡翠白玉湯’的人,一個叫常賢弟,那個不知道叫什麼名字,你們倆人問什麼呀?你們會做‘珍珠翡翠白玉湯’啊?”倆要飯的一聽,啊?這說:“哎!大哥,好!小破廟裡喝雜和菜湯子那傢伙做了皇上啦!”這說:“是他嗎?”“當然是他呀!”“喲,他做了皇上了?那咱們得瞜去呀!”“對,走,咱瞜瞜他去。”倆要飯的打算瞜皇上去。
撕皇榜!“咔”一下把皇榜給撕了。兩個看榜的呢,就是縣衙門裡倆公差。倆公差這么一瞧:怎么著,要飯的撕皇榜?嗬,膽子太大了,一抖鎖鏈子,“嘩啦”這就要鎖。
剛一抖鎖鏈子,倆要飯的一瞪眼:“乾什麼呀?啊?怎么回事啊?難道說鎖著去給皇帝做‘珍珠翡翠白玉湯’嗎?”倆公差一聽:“喲,鬧了半天敢情是二位‘湯老爺’呀?”“誰姓湯啊?胡說八道!我們做湯。”“二位做湯的老爺。你跟我們縣衙門請吧。”
讓到班房裡頭,趕緊回稟縣官。知縣一聽怎么著?在我這縣找著做湯的人啦?嗬!該著我升官發財換紗帽。好!吩咐一聲:“即刻出迎。”
趕緊換上新官衣兒,降階相迎。縣官下台階往對面一瞧啊,差點把鼻子氣歪啦,怎么?對面站著倆要飯的:一臉的油泥,一身的破爛,光著兩隻腳丫子,站在那兒倒背著手,瞧縣官一下台階,沖縣官這么一點頭,笑嘻嘻的。 縣官這個氣呀,就您們倆人還面聖哪,我們這兒還有兩碗剩面。“真乃大膽!來呀,拿鎖鏈子鎖上,押解進京。”押進南京城。
朱洪武一聽怎么樣?他高興了。有人撕皇榜,做湯的人找著了,嗬,太好啦!即刻召見。這縣富呢,押著倆要飯的奔金鑾寶殿。
七品知縣呢,在明、清兩代都是這個制度:沒有見皇上的資格,非得有個特別的召見,他還得先到禮部裡頭言禮,三跪九叩、怎么磕頭、怎么說話,這才行哪。這縣富呢?全不懂,也沒到禮部言禮就來了。到金鑾寶殿往這兒一跪呀,淨剩了害怕了。沒別的,哆哆嗦嗦,顫顫驚驚,淨剩哆嗦了。可是縣官偷著這么一看這倆要飯的,這縣富納悶兒啦。倆要飯的怎么意思?見皇上三跪九叩?沒跪,站在那兒笑嘻嘻地沖皇上點頭呢。縣官一瞧:啊,這倆敢情見誰都這樣啊?嘿嘿!這皇上還不惱?
皇上沒惱。一看果然是小破廟裡頭給他菜湯子喝的那個,高興啦!高興可高興啊,一看這穿著打扮,心裡頭暗含著埋怨這縣官,心說:這縣官怎么這么廢物啊?你怎么不把他們倆人換兩身兒好衣服來見我呀?你這破衣囉嗦的,讓文武大臣、皇親國戚一看,皇上認識要飯的,我這面子往哪兒擱呀?趕緊地就拿話找轍,站起來了。皇上多咱見人站起來?這會兒站起來了,“喔!哈哈,兩位愛卿,你們為何裝作如此打扮來見寡人呢?”你為什麼裝的這樣啊?
倆要飯的他不懂啊,“不!我們老這樣?”
皇上一聽,行!我這句話白說啦。他老這樣。
“現在我們混整啦,您看見沒有,多混上一掛鐵鏈子。”這鎖著呢。皇上借題發揮,嚇罵縣官:“糊塗的東西,大膽!給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湯’的人,你怎么給上了鎖啦?啊?豈有此理!來呀,推出去把他殺啦!”這就完啦。 這縣官跪在那兒,好傢夥,磕頭猶如雞奔碎米,哆嗦得就跟蠍了虎子吃菸袋油子似的。哆里哆嗦。倆要飯的一瞧這縣官,樂啦!倆要飯的一瞧:“哎喲喲喲,嘿,這有意思啊,這別殺呀!這是個玩藝兒啊!啊,萬歲!看著我們倆人的面子,饒他一死吧,因為給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湯’啊,人不夠用的,缺一個買作料的小夥計兒。”
皇上一聽:“那好!起來!買作料去!”這縣官當了小夥計兒啦。
庫裡頭撥銀三百兩,另設御膳房,限三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湯”二百份。幹嗎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東西不能我一個人吃,大夥全得嘗嘗。
仨人到了御膳房,縣官就給倆要飯的跪下了,“謝謝兩位老太爺救命之恩!”“甭謝啦!”“讓你買東西會嗎?”“是,兩位老太爺吩咐吧!”“你買呀,買這個一百斤菠菜,二百斤白菜,明白嗎?三百塊豆腐,四百斤糙米,兩桶雜和菜,四瓢刷傢伙水,去吧!”縣官一聽這是要乾什麼呀?“兩位老太爺,怎么買這個?”“甭廢話,讓你買什麼你就買什麼,少了一樣,做得了湯不對皇上口味,拿你試問!”“哎,是!買去。”
半天兒的工夫都買回來了。
“兩位老太爺,東西都買來啦,就您說這個兩桶雜和菜呀,沒有。因為咱們也不能用外邊的,就得用膳房的。咱們這個御膳房裡頭啊,大師傅說啦,一天就下來一桶雜和菜,兩桶沒有。”倆要飯的一聽,“喔?那哪兒行啊,一桶怕皇上吃著不夠味兒啊。你再問問去!”“甭問啦,是沒有!”“沒有嗎?”“不是,膳房大師傅倒說了,有幾桶是有幾桶,因為那不是當天的,頭幾天的,那不能用。”倆要飯的一聽,“噢,頭幾天的?嘿,那才好呢!那皇上吃著才夠味兒呢!就要那個呀!兩桶都要頭幾天的!”“哎,哎!”
人不夠用的,又借了兩個御膳房的廚師傅,雜和菜也弄來了。仨人在這兒一站,“兩位老太爺,您吩咐吧,我們都乾什麼?”“乾什麼呀?你呀?”讓這御膳房的廚師傅,“你先去燜飯!啊,回來,燜飯會嗎?”“讓您說的,御膳房的大師傅還能不會燜飯嗎?”“廢話!會燜?做‘珍珠翡翠白玉湯’的飯也會燜哪?”“那不會!”“還是的!不會聽著,告訴你,做湯的這種飯,首先說燜飯時的這個米呀,不準淘!別洗!倒到鍋里就燜!切完了上面的乾飯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飯嘎巴。去!”“哎,是!”這個走啦。
“兩位老太爺,我乾什麼呀?”“你呀,把這個白菜,跟菠菜弄一弄!”“是。”
這縣官繃不住啦,“兩位老太爺,我乾什麼?”“咳,你這傢伙,眼睛裡沒活兒,你乾什麼呀?給那豆腐弄碎了。”“哎,豆腐是切丁兒啊,這是切片兒啊?”“不切!拿手抓!抓碎了,就擱那刷家飲水桶裡頭泡著。那個桶可不能擱陰涼地方,得搭到太陽地兒去曬,知道嗎?”
“還曬?曬多大工夫啊?” “不論時間,曬冒了泡為止。”
仨人一聽,這是要乾什麼呀?這說:“他讓咱怎么做咱就怎么做,等著吧。”那個燜飯,這個就抓豆腐。就這個切菜的這個難,白菜幫子去了八九成,就要當中那個嫩白菜心兒;那菠菜呀,甭說爛的,葉兒邊上有一點黃都不要,淨擇這嫩菠菜。擇了一點呢,打了一桶水,剛要洗,讓倆要飯的瞧見啦。
倆要飯的這么一瞧:“你吃飽了撐的!這不要的東西你洗它幹嗎?”“什麼您不要啊?我這不是白菜心,嫩菠菜!”“廢話,白菜心兒,嫩菠菜呀?分做什麼!‘珍珠翡翠白玉湯’這都用不著。”“那么您說用什麼?”“就要那白菜幫子和那爛菠菜,那堆兒那個。”“那我就洗這個?”“甭洗。”“甭洗我就這么切呀?”“不切!往鍋里揪!”“啊?”“讓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好,好!”那兒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陽地曬著去了。什麼月份兒您呢?七月中旬,那天多熱呀?一會兒就冒泡了。半天的工夫,都起了化學作用了,撲哧撲哧的,往外冒酸氣,冒臭氣!酸臭沖天。那個乾飯嘎巴兒也都鬧好啦,菜也都漚好啦,三個人站在那兒沖這堆東西發愣:糊飯嘎巴兒,白菜幫子,爛菠菜,兩桶雜和菜,刷傢伙水泡豆腐。
縣官實在繃不住了,“兩位老太爺,我們給皇上做湯不做湯?我們怎么辦呢?”倆要飯的一聽就樂啦,“哼哼,忙什麼的呀?給皇上做湯忙什麼呀?瞧!”用手一指這刷傢伙水泡豆腐這桶,“瞧,這不是嗎?‘珍珠翡翠白玉湯’十成已經完了八成了,就等著御宴開始時候,倒到鍋里一熱,見個開兒,然後端上去,皇上一喝,咱們就等著請功領賞。”縣官一聽:“還打算領賞呢?腦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這還想領賞啊?
那個說:‘你也不能這么說,咱們嘗嘗怎么樣吧?”弄個勺,舀了點湯,擱到嘴裡頭了。“行,有點意思啦!”那個說:“你光嘗湯不行,你得嘗嘗豆腐啊。”桶底撈點碎豆腐,嘴裡一吧嗒,“行啦!夠味兒啦,夠味兒啦!”這玩兒夠什麼味兒啊?仨人害怕。
到了第三天頭上,嗬!皇宮內院懸燈結彩,富麗堂皇,大宴群臣。好傢夥,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齊了。幹嗎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這天為什麼早去呀?嘿,嘿,皇上賜宴。 大家都打算嘗嘗這“珍珠翡翠白玉湯”什麼味兒。沒喝過這東西呀!都去啦。
文武百官去的早,皇上還沒去呢。他們大夥幹嗎呀?互相吹牛拍馬。“年兄,您喝過‘珍珠翡翠白玉湯’嗎?”“沒有。您喝過?”“我也沒有。我雖然是沒喝過,但是我聽家父說過,家父是聽徐達丞相說的。據徐達丞相說,這‘珍珠翡翠白玉湯’可是非同小可呀!據說裡頭有珍珠海味,鳳肝龍髓,真是窮天下之奇珍異寶,久蒸久煉,才得製成此湯。今天我輩深受皇恩,親嘗此味,哎,真是咱們的祖德不淺吶。”您說這不是倒霉催的嘛,他也沒聞見過那刷鍋水、臭豆腐是什麼味兒的。互相吹捧。
倆要飯的出來瞧:喲嗬!全來了。人還不少,皇上還沒來呢。皇上也快來啦。趕緊的預備。“噔、噔”跑到膳房裡頭,“哎!御宴馬上開始。趕緊弄,回鍋熱!”“回鍋熱?老太爺,先擱什麼呀?”“隨便吧!來。”“喀嚓”一下,白菜幫子、菠菜葉先弄裡頭了。“來,糊飯嘎巴、雜和菜、刷傢伙水泡豆腐!”“咚”,全折裡頭啦!“趕快燒火,趕快燒火!”
一會兒工夫,湯就開啦!這不湯也開了鍋了嗎?那屋子裡也呆不住人啦!酸臭酸臭的!熏腦漿子啊。
仨人溜出去啦。一會兒的工夫,倆要飯的也出去了——他們倆人也受不了啦。“哎呀,怎么樣啦?我看看,皇上出來啦!嘿,盛!端!”一喊“盛”,“端”!嗬,二十多個小太監排成一字長蛇陣,每人手裡托著一個描金朱漆的紅盤兒,盤裡頭放著這么大個兒官窯定燒的團龍小碗兒。碗兒裡頭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湯”。
小太監往上端湯。文武百官,皇親國戚一看小太監往上送湯,大家是交頭接耳。“年兄,什麼地方規矩也沒有皇宮內院規矩大!你看這小太監往上送湯,你看看他們多規矩,連正眼看這湯都不敢看,你看那不是,都偏著身兒,斜著臉兒呢嗎?”
一看這小太監往上送湯怎么樣?他是不敢正臉看呢,那味兒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樣嗎?
把湯端上來,頭一碗當然先給皇上啦。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這么一聞呢,也仿佛有點噁心似的。心說:這湯怎么這味兒啊?我那年在小廟裡喝它不這味啊。現在怎么這個味兒啊?一愣。再一看文武百官皇親國戚,一個個緊皺雙眉,荼呆呆沖這碗湯發愣,直往後躲。
皇上這兒想什麼呢?心說:這湯啊,實在是不是味兒,不是味兒是不是味兒啊,無奈有一截呀?啊,我是皇上啊,我說這湯好,我找人做的湯我哪能不喝呀?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夥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湯嘛!當然要喝。 文武百官這發愣啊,先是那樣,現在不是了,這樣。那意思:就這個湯,甭說皇上,連我們也不能喝。你看著吧,這倆做湯的人,非千刀萬剮不可。心裡淨這樣想呢。
皇上一看他們扭臉兒,皇上可惱啦。皇上一瞧。心說;好啊!合著你們就會跟我享福啊?這么一點罪都不能受啊?你們躲什麼呀?您們幹嗎呢?等著我呢?等著我好啊,來吧!今兒咱們一塊兒啦。小碗端起來了,往起一站:“眾位愛卿,隨寡人一同共飲‘珍珠翡翠白玉湯’。”說完這話端起小碗,一憋氣兒“咕咚咕咚”,把這小碗湯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兒一擱,坐下啦。
文武百官一看可嚇壞了。“年兄,皇上喝了。咱們怎么辦呢?”“那還怎么辦呢?一塊兒往下灌吧!”都把這碗湯端起來了,擱鼻子這兒一聞差點吐了。怎么辦呢?不往嘴跟前送,往遠處送。往遠處送呢,嘴裡還得拿話找轍。“年兄請!”這說;“廢話!我請你不喝就行啦!甭廢話,一塊兒喝!”甭管怎么說吧,一憋氣兒,總算把這小碗湯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兒一擱。
皇上一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興啦!站起來就問:“眾位愛卿,寡人請人做的這個‘珍珠翡翠白玉湯’,你大家喝著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聽這句話,站起來各伸雙指,倆大拇哥部挑起來了,可就是沒說話。怎么不說啊?他嘴裡還含著一口呢。
皇上一看,明白啦!皇上說:“啊,眾位愛卿,你等大家不語,各伸雙指,聯已明白你等之意——你們是想每人再來兩大碗哪!”
2、風雨歸舟
在過去,舊社會的大財主家都有錢。他那錢來得特別容易。為什麼哪?“錢賺錢不費難”嘛。噯,您別看來得容易,去得也馬虎。
有這么一檔子事。民國初年,在北京西城有個大財主,此人姓花,名字叫源泉,花源泉。叫別了呢,就是“花冤錢”,人稱花二爺。他家裡趁錢,可對窮人他是一個子兒也不花!天生的倒霉鬼。專愛花冤枉錢!
什麼錢他花呀?在民國三年的時候,他花兩千塊錢買了四個蟈蟈葫蘆兒——那時候一袋麵粉才一塊八——當玩意兒,這錢他花。要不怎么叫花冤錢哪!窮人是一文錢也沾不著他的,誰要是畫個圈兒騙他,那行;不然哪,沒用。
那時候北京有個著名的騙子,叫智多星,略施小計,騙了他五萬塊錢。智多星在東城租了一處大宅子,屋裡頭的古董玩器、家具擺設全是花錢租的;家裡的太太、小姐、廚子、丫鬟、用人,全是花錢雇的!設好騙局,專等花冤錢抻頭兒!這智多星轉著彎兒托人跟花二爺接近,交朋友。今兒請吃飯,明兒請聽戲,沒多少日子倆人還真交上朋友了。 有這么一天,下大雨,花二爺正在家裡坐著哪。這智多星登門恭請,坐著汽車——其實全是租來的——接花二爺上他們家吃飯去。“二爺,請到我家吃個便飯吧!”
“吃飯?好,好,馬上去。”
去了,到客廳這么一看屋裡的擺設,牆上的字畫,心說:嚄!比我還闊,比我家講究多啦!他哪兒知道,都是花錢租來的!談話之間,智多星說:“二爺,我們祖上多少輩都是喜好古玩字畫,聽說您也有這個嗜好,難得,難得。我家祖傳有一張古畫,今天特地請您給鑑別鑑別。”
“祖傳古畫,哎呀,那太好啦,今日有此眼福,我得好好瞻仰瞻仰。”
智多星到裡頭屋拿出一張畫來。打開一看,是什麼畫呀?《風雨歸舟》。背景是山,前面有河,河裡有小船,有一座木橋,在橋當中間有一個小孩,這小孩打著雨傘。畫上露出來狂風暴雨的意思。這個小孩哪,打著傘過橋,好像風挺大,很吃力似的。花二爺看完了畫連聲稱“好”。智多星一瞧有門兒,忙說:“畫固然是好畫,就是不知道出在哪朝,何人所作?”
剛看到這兒,老媽子進來了:“嗯,大爺,酒飯齊備。”“好,上桌吧!”就把這軸畫捲起來,隨手放到條案上了。八仙桌往前搭,各自就座。廚子、老媽,碗來盤往,撤酒上茶,這頓飯足吃了倆多鐘頭。等吃完飯哪,外頭雨也停了。智多星又接過飯前的話碴兒:“二爺,剛才這畫您看著怎么樣啊?”“好,就是沒看出哪朝的。”
“您再看看。”
順手把畫拿過來展開,又這么一看,還是看不出朝代。畫是夠老的,紙都黃啦。橋下草叢邊上署著作者落款:何明三。嗯,再往上一看,這花二爺納悶兒了,自己問自己:“不對呀,吃飯之前我瞧那小孩是打著雨傘過橋的,怎么現在把雨傘夾起來啦?”他倒吸涼氣,一個勁地撓後腦勺兒!
“要不怎么說是祖傳至寶哪。開始您看的時候是打著傘,對呀,那不是外面正下雨嘛;現在外頭雨住了,傘哪,也收起來了。傳家至寶得有點兒蹊蹺的地方。只要外頭一下雨,您再看畫,這傘就打起來啦;雨一住,那傘就夾起來了。”(向觀眾)您說有這個事嗎?
這花二爺一聽,信啦!哎呀,這可是件寶貝。因為什麼?他有這個愛好哇。花二爺心頭一動,想把這張畫買下來,又不便直說,回去以後託了好幾位朋友,說什麼也要買這張畫。智多星還死活不賣。花二爺直托人情,又請客吃飯,智多星才勉強點頭,要價十萬塊錢。花二爺又捨不得了,嫌價碼太高,中間經人再三說合,最後商定五萬塊把這張畫買妥了。
買畫的時候是晴天哪,沒下雨,這小孩的傘當然是夾著的。回來挺高興,看了一陣兒,馬上寫請帖,請親戚朋友吃飯,慶賀得到這張古畫。他這請帖寫得特別:多咱的日子沒準兒!什麼時候請客?哪天下雨,哪天來。幹嗎呀?就為下雨的時候好看這張畫。結果,有一天下了瓢潑大雨,親友都來了。花二爺滿面喜氣:“諸位,諸位,我買了一張古畫,人家的祖傳至寶,他忍痛割愛讓給我了。我先告訴你們啊,我買回這張畫來的時候,橋上小孩的傘是夾著的,可外頭一下雨,小孩這傘哪就打起來;要是天晴了哪,這傘就夾起來。諸位看看,現在外頭下雨,小孩小打著傘;雨一住,馬上收傘夾起來。”他這么一說,大家都感到新奇,全圍過來了。把畫展開這么一瞧,花二爺愣了:怎么這傘還夾著哪!有一位問他:“二爺,您不是說下雨就打傘嗎?他怎么還夾著?”把他問得臉通紅:“這,這雨下得還不太大,先捲起來,悶一會兒再瞧。”——那玩意兒有悶一會兒的嗎?這不是胡來嘛!一會兒,外邊那雨呀可就更大啦,嘩……大伙兒說,咱們再瞧瞧吧。打開一瞧哇,那傘還是夾著的。等了會兒,雨也不下了,再瞧那傘哪,還是夾著的。大伙兒也不好意思說什麼,吃完飯都走了。花二爺這個氣呀:“好個智多星,騙子手騙我!找他去。”上東城找去了。照例說,騙局成功,錢一到手就得跑,搬走。嗨,沒走,還在那兒等著呢。幹嗎呀,等著氣他哪!人家有說詞。花二爺找著智多星:“你不夠朋友,讓我花五萬塊錢買張廢紙,你怎么騙我呀?”
“二爺,我哪點兒騙您了?”
“哪點兒騙我了?你不是說,那張畫下雨打著傘,不下雨就夾著嗎?下那么大雨還夾著傘,你這不是騙人嗎?” 智多星一聽樂啦:“二爺,這怎么算騙您哪,我找您要十萬塊錢,您非給五萬塊錢?”
“怎么,差五萬塊錢就不靈啦?”
“它不是不靈啦。您沒明白,我說十萬塊錢哪,您是應當買一套。”
“什麼叫一套哇?”
“一套。一套是兩張:一張打著傘的,一張夾著傘的。下雨的時候,您看這張;不下雨您再看那張啊!”
噢,兩張啊!
女兒評論
 左二劉寶瑞女兒
左二劉寶瑞女兒我父親的一生,是艱苦的一生,也是對藝術追求不懈的一生,在我的記憶里,他向我講過兒時的苦,更講過共產黨給他的甜,他給我講做人的宗旨,強調為人的樸實。少年時的他,由於生活所迫,選定了從藝之路,拜在相聲大師張壽臣門下,從他拜師之日起,他也就開始品嘗舊社會藝人的辛酸——身份的卑微,世俗的白眼,黑勢力的壓榨,做人的艱辛。
在唐山演出,一場下來“零打錢”,輪到傷兵面前,放在笸籮里的不是錢,而是一把手槍。一貫以“膽小”聞名的父親,忘記了自己的怯懦,撲向傷兵,咬住了傷兵的耳朵。做人的恥辱,多年的積怨一時迸發出來,就連所有觀眾都驚呆了,當然,後果可想而知。日偽時期,一場“君臣斗”把王八說成日本人的翻譯官,被劉中堂提來面聖,聽眾開懷大笑,解了心頭之恨,可出了場子,一把手槍頂在了父親的腰間。父親說的這件事使我悟到,在舊社會受盡欺凌的父親居然也意識到了藝術是反抗的武器,是民眾的喉舌,他能把最犀利的語言運用到相聲當中,去諷刺賣國求榮的敗類,如匕首投槍。壞人的反應正說明他擊中了那些人的痛處,讓仇者痛親者快正是我父親藝術的追求和人格的表現。
在他藝術臻於成熟之時,由於種種原因,他帶藝南下,順濟南沿江而去,久居南京。業內人士一致認為是他此舉把北方的藝術帶到南方,使其在南方的土壤上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父親把北方藝術與南方藝術相互融匯,雖不是驚天之舉,但也是功德之一。
在我的記憶中,有一種感覺是刻骨銘心的,就是他對國家的親,對黨的愛,達到了超乎常人的狀態。解放前夕由於生活所迫他去了香港,在那裡他的生活境遇有了較大的改變,有了自己的聽眾群體、立足之地。1949年10月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父親就毅然立即返回祖國,加入進步藝術團體,寫新、唱新、演新,報效祖國母親。此時,他的藝術已廣為國人所知,但他的筆記中卻清楚地記著這樣一段話:“我是舊社會過來的藝人,身上肯定有不符新社會的毛病,藝術上也會留下舊的痕跡,故此,我要認真學習。”話雖樸實,但既有起點,又有目標,更可貴的,是他自我反省的精神。
在他的藝術顛峰期,他多次走進中南海,為領袖和開國元勛們展示才藝。都知道毛主席愛聽《關公戰秦瓊》,殊不知,主席、總理對我父親表演的具有豐富歷史和文學知識的相聲更是情有獨鍾,《解學士》、《君臣斗》使這些偉人讚不絕口。
生活上我父親是個瀟灑的人,在藝術上他卻是極嚴格的人。“許你不演,但不許你不懂”是他的座右銘。六十年代初春節,徒兒拜年,一句玩笑話,“師傅,慈禧的廁所叫什麼﹖”父親當時語塞。初四他便冒著大雪,連續四進北京圖書館查閱資料。最後在故紙堆中查到宮女生活一節中提及慈禧的便廁在宮中叫“官房”。他不僅查了名稱,連同使用中的規矩、附屬用品都一一記下。正月十五與徒兒們再聚時,“官房”的來龍去脈便傳到了徒兒們的耳中。
人民的藝術家,就是在這樣的“喜、怒、哀、樂、悲、恐、驚”中走完了他從九歲到五十四歲的道路。幾十年里,他受過軍閥、土匪欺壓,受過達官貴人的白眼,受過生活無計的清貧,受過拜師學藝的艱辛,他清清楚楚地記得這一切。而在他的一生中最不能讓他忘卻的是共產黨把他救出了苦海,是共產黨把他從一個貧苦藝人培養成為了一名藝術家。
現今父親離我而去已經三十餘載,但他的一句話始終在我耳邊迴響:孩子,記住聽共產黨的沒虧吃!
相關作品
劉寶瑞單口相聲 劉寶瑞選集
劉寶瑞選集《學乖》
《學徒》
《測字》
《文廟》
《扎針》
《黃半仙》
《賈行家》
《天王廟》
《解學士》
《韓青天》
《官場斗》
《打油詩》
《日遭三險》
《連升三級》
《化蠟扦兒》
《風雨歸舟》
《兵發雲南》
《書迷打砂鍋》
《珍珠翡翠白玉湯》
劉寶瑞郭全寶搭檔演出的相聲名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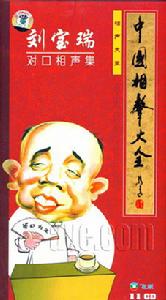 雙口相聲選集
雙口相聲選集《說字》
《趕考》
《買猴》
《當行論》
《打燈謎》
《奉承人》
《找對象》
《做大褂》
《坐汽車》
《八扇屏》
《說聊齋》
《猜地名》
《飛油壺》
《蛤蟆鼓》
《韓青天》
《好啊好》
《繞口令》
《學叫喚》
《住醫院》
《金剛腿》
《一匹馬》
《值班醫生》
《走馬觀碑》
《歪批三國》
《開場小唱》
《支援新廠》
《我的歷史》
《西行漫記》
《寸步難行》
《吃飯我掏錢》
《九點鐘開始》
《高人一頭得人》
關東大俠
劉寶瑞字玉亭,回族,出生在河北省臨榆,少年入山海關鏢局習武學習查拳,後來他多方尋師訪友,在河南向沙長老學查拳、雙鉤。二十歲時在北京幸遇武林大師沈福臣,沈大師武術造詣極深,精通太極、八卦、查拳、少林等,通過沈大師指教,劉寶瑞技藝大增,掌握了楊氏一百零八式太極拳、 查拳的縮、綿、軟、巧、錯、硬、脆、滑等要訣。後來劉寶瑞到了丹東,通過努力拜師於查拳大師趙熙川,趙熙川人稱趙四把,曾參加義和團運動,失敗後到此。通過幾年學習,武功大長,查拳、彈腿功夫日臻上乘,掌握了彈腿的用彈、跑彈的實戰技法。1923年,劉寶瑞來到瀋陽在北市場開辦了“劉記振遠堂鏢局”。
1931年,南京要舉辦國術大賽,為選拔武術高手,張學良在小河沿舉辦打擂比賽,東北各地武林高手雲集瀋陽,經過比賽,劉寶瑞技壓群雄,獨占鰲頭,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末能參加。
1932年,在偽滿洲國的首都新京(今長春),日本大力士擺擂,劉寶瑞登台輕取日本大力士,這在淪陷初期的東北傳為美談,後來被譽為瀋陽的“霍元甲”,新京打擂後他的名氣更大了,沈城一些大照相館櫥窗內掛有他比武的照片,以顯示中國人的榮耀。
從此劉寶瑞在瀋陽大力傳播武術,成為瀋陽彈腿、查拳的開拓者,他一生徒弟眾多,其中申金儒最為突出,在1946年東北抗日烈士獎學會為記念抗戰勝利一周年舉辦的擂台賽上,一人獨得刀、槍、手三項冠軍,威震沈城,劉寶瑞之子劉振東自幼習武學,深得父親真傳。他們為彈腿、查拳在瀋陽的流傳與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南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鼓樓醫院教授
劉寶瑞,南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鼓樓醫院腫瘤科行政主任,主任醫師,教授,醫學博士,美國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博士後,南京大學、南京中醫藥大學、南京醫科大學博士生導師,南京市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拔尖人才,南京醫學會腫瘤分會主任委員,江蘇省抗癌協會腫瘤標誌專業副主任委員,江蘇省抗癌協會常務理事,中國生物醫學工程協會腫瘤靶向治療專業分會副主任委員,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會員。負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項。主編著作2部,發表論著150篇,其中SCI論文10餘篇,影響因子達50分,國家發明專利8項。
深圳發展銀行-劉寶瑞
姓名:劉寶瑞
性別:男
學歷:EMBA
職位名稱:執行董事
任期起始日:2007-12-19
簡歷:
劉寶瑞先生,1957年出生,1986年12月畢業於天津師範大學行政管理專業,1998年5月畢業於天津財經學院貨幣銀行學研究生班,2003年3月至2005年4月就讀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管理學院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 理碩士(EMBA),碩士研究生,高級經濟師,中共黨員。現任深圳發展銀行副行長、黨委副書記。兼任中國銀聯監事會監事。1974年8月至1981年4月,在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天津寶坻支行工作。1981年5月至1998年8月,在中國農業銀行天津分行工作,歷任人事處幹部、副處長;國際業務部副總經理、總經理,天津港保稅區分行行長;資金計畫處處長。1998年8月至2000年3月,任深圳發展銀行行長助理、黨委委員;2000年3月至今,任深圳發展銀行副行長、黨委副書記。
![劉寶瑞[中國相聲演員] 劉寶瑞[中國相聲演員]](/img/4/8d3/nBnauM3XxEDN5cTM4ATM4cTO5MTM5gDMxITNyQTNwAzMwIzLwEzL1Q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