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書簡介
作者:(奧地利)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年)類型: 小說
成書時間: 1926年
背景搜尋
 弗朗茨·卡夫卡
弗朗茨·卡夫卡迫於父親的壓力,他學習法律,後入一家私人保險公司任低薪職員,一直湮沒在人群之中。他一生三次訂婚,又三次解除婚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怕結婚會破壞他已經習慣的孤獨生活。後來他患上肺結核病,更使他遠離熱鬧的塵世生活,沉浸在自己孤獨的內心世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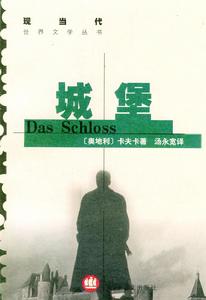 《城堡》
《城堡》二戰之後,世界在廢墟上重建,戰爭所帶來的人類心靈深重的陰影,使人們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了30年前死去的無名作家卡夫卡,他及其作品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熱潮,人們像投票選舉政界要員一樣把他列為現代派小說家的第一候選人。
推薦閱讀版本:湯永寬譯,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
內容精要
 弗朗茨·卡夫卡
弗朗茨·卡夫卡他前往客店投宿,可是客店老闆對他的到來有點不知所措。他告訴K已經客滿了,只好把K勉強安頓下來。客店裡的人得知K要去城堡,都用特別的眼神看他。一位年輕人告訴K,每個進入城堡的人都必須得有一張許可證,而要想得到許可證,就必須去找城堡里的伯爵。
第二天,K走向城堡,可是耗費了一整天的時間他也無法靠近城堡一步。天色暗下來,他只好先去找棲身之處。找來找去,又回到了昨天晚上的那家客店。在搭雪橇前往客店的途中,他遇到了兩個自稱是他的助手的人。他們非常熱情地幫助K,並且用電話聯絡城堡里的辦事機構,詢問具體何時能上城堡去,對方回答:“任何時候都不能來。”
 奧地利街景
奧地利街景在旅館的酒吧里,K認識了克拉姆的情婦弗麗達,K頓時使出渾身解數試圖靠近弗麗達,然而旅館里的人不停地添亂,助手們也在一邊添亂,使他無法和弗麗達親密地談一談關於克拉姆。他甚至用與弗麗達結婚的許諾想換得跟克拉姆談一次話的機會。但K最終發現弗麗達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因為她和信使一樣,是個無關緊要的小人物,她早已失寵。
K去見村長,村長告訴他,K來到村子完全是個錯誤,因為這裡根本用不著土地測量員。城堡里不同部門彼此封閉,造成了一些差錯,所以K才會收到公文,然而這份公文是早已無效的。村長承認他在幾年前收到一個招聘一位土地測量員的公文,然而他無論如何找不到那張可以證明K合法身份的薄紙片。村長表達了自己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他覺得K收到的公文其實是一封某個主管,比如克拉姆,對他表示私人關心的的信,不能代表城堡的意見,因此K應當趁早回去。
 卡夫卡舊照
卡夫卡舊照這時村里學校的教師奉村長之命前來,允許K帶家眷住進學校任看門人,同時他也強調,學校其實並不需要一個看門人,他完全遵從村長的命令。K感到受到了侮辱,他拒絕了這份工作。可弗麗達堅持K接受它,她說如果K不接受,連個安身之處都沒有,那么這對K對她自己都是十分羞愧的事情。
K對於進入城堡仍然抱著最後的希望,這已經不單純是執行公務,而是有關個人尊嚴的問題。他冒雪來到克拉姆的旅館,女招待說這會兒克拉姆正準備離開旅館,雪橇已在院子里等著他,K二話沒話,守到雪橇邊,喝著白蘭地等克拉姆出來。和以前一樣,克拉姆本人永遠不會出現,他的秘書摩麥斯出來告訴K: “不管你跟我走或者留在這裡,你都不會見到他。”K反而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地步,如果他離開,周圍人的神色舉止里就表明克拉姆就此脫身了;如果他堅持等下去,顯然也是沒有結果的。秘書拿出一份會談記錄,向K指出這是引K走向克拉姆的惟一道路,但首先K必須接受一番苛刻的審查,K覺得不可忍受,於是他們兩人大笑著分別了。
 作家卡夫卡
作家卡夫卡之後K回到他和弗麗達的新家,那是學校里的一間大教室,可是K和弗麗達的生活並不安寧。兩個助手不停地淘氣,爭食物,瞅準機會睡到惟一的稻草墊子上去。第二天,學校的女教師來了,她十分吃驚,繼而不斷地責罵K,K幾乎像個劣等動物一樣被欺辱,可他決不接受校方的解職通知。他遷怒於兩位無用的助手,宣布辭退他們,助手們施出渾身氣力哀求K。弗麗達反對K的決定,她說一旦辭退助手,K就永遠沒有機會見到克拉姆了。弗麗達鼓勵K不要喪失信心。
K來到信使家等待回音,信使的姐妹奧爾伽和阿瑪麗亞總向K暗示她們的傾慕之情,並且在閒聊中,暗示K,她們的哥哥巴納巴斯可能從未見過克拉姆,他總是給K帶來那些耽誤了很久,失去時效的信。就連克拉姆本人,也是可疑的,關於克拉姆的種種情況,很大程度上是村里人想像出來的。奧爾伽又告訴K,城堡里的官員如同暴君,他們可以隨時瞧上村裡的任何姑娘,給她們寫下流無比的信。他們的談話離正題越來越遠,奧爾伽講起了阿瑪麗亞因為拒絕城堡里另一位大官員索爾蒂尼的求愛而遭受的不幸,他們全家都被迫接受了一種幾乎整天無所事事的刑罰,城堡強制他們退出社會生活。奧爾伽提醒K,不要指望任何一位有同情心的官員為他說話。巴納巴斯為K送信,其實不過是想讓自己一家人不露痕跡地再受恩寵,對於K來說,沒有任何意義。這場繁冗而推心置腹的談話被K的一位助手打斷了,K很快意識到弗麗達和另一位助手呆在家裡,他趕緊回家了。
到家裡,K發現弗麗達不見了。原來她以為K跑去勾搭巴納巴斯的姐妹,於是和另一個助手達成協定,背叛K。這時,巴納巴斯又跑來找K,興沖沖地通知他,克拉姆的主要秘書之一艾朗格要和K當面談一談。K和一群人等候在漆黑的旅館門口,K被最先領了進去,但艾朗格卻睡著了,K只好等著。在等待的時候,他又重新見到了弗麗達,他們激烈爭論了忠實與不忠實的問題。弗麗達坦然地告訴K,她已經和那位助手同居了。K則十分平靜地回敬她:自從你相繼失去了克拉姆的情婦以及我的未婚妻這兩種身份之後,你早已經沒有了魅力。聽完此話後,弗麗達似乎被觸動了。但是她又見到助手時,馬上就改變主意。她說:她再也不想回到K身邊接受他的折磨。
小說就在此處戛然而止,卡夫卡未寫完它,他原來打算的結尾是K將精疲力竭而死。後世及研究者預計的結局是:K彌留之際,城堡終於來了通知,允許K留在村子里,但不許進入城堡,K永遠不可能到達那裡,一直到死。
專家點評
 法國名畫·月光下的古堡
法國名畫·月光下的古堡人們提到卡夫卡,總是會提起他的《變形記》,裡面的小公務員一早起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個大甲蟲。西方文學中常常用《變形記》來指代現代化文明中人的異化。然而在這裡所推薦的《城堡》,因其多義性更富於閱讀的快樂。中篇小說《城堡》與《審判》及《美國》合稱“卡夫卡三部曲”,它們都具有卡夫卡小說一貫的荒誕不經風格:異化現象,難以排遣的孤獨和危機感,無法克服的荒誕和恐懼。卡夫卡的小說揭示了一種荒誕的充滿非理性色彩的景象,個人式的、憂鬱的、孤獨的情緒,運用的是象徵式的手法。其中《城堡》更富於“卡夫卡式”的構思和語言風格。
和卡夫卡的其他小說一樣,《城堡》沒有惟一正確的解釋,解釋權授予了每個閱讀者,這來源於這部作品的多義性。表面上,這作品的故事再簡單不過了,一個土地測量員K來到一個村莊,想進入管轄附近地區的伯爵居住的城堡,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攤上一切也沒能達到目的。《城堡》所具有的荒謬、虛擬,無明確的時代地理背景的特徵使它抹上很濃的寓言色彩,無論評論家還是普通讀者都能夠獲得不同的結論,《城堡》究竟表達了怎樣的主題,這終了還是一個難解之謎,有人說它表現的是“人試圖進入天國而不得的痛苦”;有人則認為它集中反映了卡夫卡本人的精神世界的荒誕、孤獨與恐懼;有人則結合寫作年代背景,說明城堡實際上反映了奧匈帝國官僚體制與大眾的鴻溝,更有論者以為,《城堡》和《審判》、《美國》的主題相同,即“人們所追求的真理,不管是自由、安定,還是法律,都是存在的,但這個荒誕的世界給人們設定了種種障礙,無論你怎么努力, 總是追求不到, 最後只能以失敗告終。” 在《城堡》中,“城堡”是最大的謎團,它與主人公K的目標總是若即若離,也正因此,能夠激起人們相當的閱讀興趣,其中的人物如CC伯爵,以至於克拉姆部長等都神秘莫測,足以見卡夫卡這位小說家的天才的智慧。
 小說家卡夫卡
小說家卡夫卡1913年8月15日,卡夫卡在自己的日記里寫道:“我將不顧一切地與所有人隔絕,與所有人敵對,不同任何人講話。”6天后他又這樣寫道:“現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親愛的人們中間,比一個陌生人還要陌生。近年來我和我的母親平均每天說不上20句話;和我的父親除了有時彼此寒暄幾句幾乎就沒有更多的話可說;和我的已婚的妹妹和妹夫們除了跟他們生氣我壓根兒就不說話。理由很簡單:我和他們沒有任何一丁點兒的事情要說。一切不是文學的事情都使我無聊, 叫我憎恨”三年之後,這個不僅和整個世界格格不入,而且也和自己格格不入的猶太人,雖然尚未進入完全與世隔絕的城堡,卻終於從家庭里逃出,為自己找到了一條窄得像西服袖子一樣的幽深的死巷。這就是如今在布拉格頗為知名的黃金巷、又譯為“鍊金術士巷”。黃金巷22號的連棟屋中間,有座建於16世紀的、只有一個房間和一間小閣樓的小小藍屋,牆壁很薄,房舍低矮得伸手便可觸及天花板。這是被他的好友馬克斯·布羅德稱之為“一個真正的作家的修道士般的密室”的處所。卡夫卡在這裡繼續用謎一般的文字構築著自己靈魂的城堡。
 卡夫卡及家人
卡夫卡及家人卡夫卡生前默默無聞,孤獨地奮鬥,隨著時間的流逝,他的價值才逐漸為人們所認識,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動,並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一股“卡夫卡”熱,經久不衰。他一生的作品並不多,但對後世文學的影響卻是極為深遠的。他與法國作家馬賽爾·普魯斯特、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並稱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和大師。美國詩人奧登認為:“他與我們時代的關係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亞、歌德與他們時代的關係。”後世的許多現代主義文學流派如“荒誕派戲劇”、法國的“新小說”等都把卡夫卡奉為自己的鼻祖。
關於卡夫卡,我們還可以說上很多很多。據說在現代文學的研究中,關於卡夫卡的論文數量之大,僅僅列印題目就需要幾十頁。但是,理解卡夫卡最好的方法,就是進入他的文字世界,安靜地傾聽他通過語言表達的內心。這不正是我們現在這個浮躁的現代文明所缺少的嗎?
妙語佳句
他真要以為外面是灰色的天空與灰色的土地渾然一體的荒漠世界了。可是如果這一切的平靜、舒適與滿足都要想恐怖地告一段落,那該怎么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