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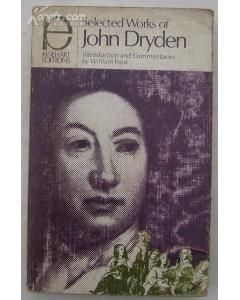 Selected Works Of JOHN DRYDEN(約翰・德萊頓文選)
Selected Works Of JOHN DRYDEN(約翰・德萊頓文選)《悲劇批評的基礎》是十七世紀英國古典主義流派的創始人,詩人,文藝批評家德萊頓撰寫。在《悲劇批評的基礎》專論中,就悲劇中的人物行為、人物性格和悲劇的目的等一系列論題提出了詳細的看法。德萊頓為英國文藝批評做出了的巨大理論貢獻。在《悲劇批評的基礎》講述說:“它沒有必要具有歷史的真實性,但是永遠有必要酷似真實,要有超過起碼的可能性。”在《悲劇批評的基礎》中曾說:“如果詩人旨在引起恐怖和憐憫,而他描寫的一個行為是喜劇的,另一個是悲劇的,那么前者就會取悅觀眾,完全使他的意圖落空。”這些觀點是他都認為詩也是理性的思維,它也揭示真理和規律,它也是對必然性的思考。
為自己的劇本寫的序言
《悲劇批評的基礎》是他為自己的劇本《特羅勒斯與克萊西德》寫的序言。序言論說了悲劇的目的、情節、人物及悲戲劇的區別,認為創造可能的而又引人入勝的情節是悲劇最艱巨的任務。他認為文藝的社會功能在於“使觀眾在愉快中得到教益。”論文對悲劇中人物的性格有更豐富的論述,強調一種綜合的個性以及使人物形象鮮明的性格刻畫。他還對朗加納斯的悲劇激情論進行闡發。總的看,德萊頓在論文中並沒有提出新的觀點,只是揉合了古希臘古羅馬大師們的主張,使之系統化。儘管只是師承前人,德萊頓作為英國文藝批評的創始人,其功績還是應該肯定的。
批評時代
從文藝復興到18世紀啟蒙主義時期,可稱之為西方文學研究的批評時代。據韋勒克考證,英語中的Criticism,在希臘文中有兩個意思相近的詞:Krités,意為“判斷者”;Krineín,意為“判斷”。含有“文學的判斷者”之意的“Kriticós”這個術語,最早出現在公元前四世紀末。在古拉丁文中,“批評家”(Criticus)這一術語也很少見。只是到17世紀,“批評”這個術語的含義才擴大起來,既包括整個文學理論體系,也包括今天稱之為實踐批評的活動和每日評論。韋勒克指出,批評這一術語雖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有關詩學和修辭學著作中已偶爾出現過,但“這一術語——在它各種各樣的意義中——似乎只是在十七世紀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才隨著莫里哀的《〈婦女學堂〉的批評》(1663)和R·西蒙的《〈舊約〉批評史》(1678)得到普遍承認。”(5)到1687年,拉·布呂耶爾甚至埋怨“批評家和評論家”蜂擁而起,拉幫結夥,妨礙了藝術的發展。在英語中,批評這一術語有著與在法語中類似的演變過程,同樣是在17世紀70年代才得以完全確立。1677年,德萊頓在《天真的國土》的前言中說:“批評最先是由亞理士多德確立的,它的意思是指作出正確判斷所使用的標準。”(6)1679年,德萊頓寫下了《悲劇批評的基礎》,使這一術語的意義明確地使用起來。
背景材料
戲劇理論家
在古典主義時期歐洲還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戲劇理論家,那就是英國的德萊頓,英國古典主義文藝理論的代表者。德萊頓(163l—1700)雖然是在錫德尼和本·瓊生之後引起理論界廣泛注意的,但由於他對於此前的英國優秀作家一一作了比較確定的評價,而這些評價又具有相當的系統性,因此人們往往把他在理論批評領域的地位置於錫德尼和本·瓊生之上,甚至稱他為英國近代文學批評的創始人。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
從本·瓊生到德萊頓,中間隔了一個劃時代的事件——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早在十七世紀初年,伊莉莎白女皇的去世和斯圖亞特王朝詹姆士一世的執政,已標誌著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君主專制政權與資產階級的同盟的解體。兩方面的長期爭鬥在一六二五年查理一世即位後發展到極為激烈的程度,國王與國會不共戴天,終於在一六四二年即倫敦劇院被封閉的那一年爆發內戰,七年以後,查理一世被押上了斷頭台,英國宣布共和。但是共和實際上很快被軍事獨裁所代替,經過幾年動盪,斯圖亞特王朝得以復辟,被處死的查理一世的兒子查理二世即位。在這動亂不息的多事之秋,一個曾大聲為英國革命辯護過的革命政府秘書走進了英國文學史冊,他就是彌爾頓。彌爾頓在為英國革命撰寫辯護文章、從事繁忙的革命政府活動時雙目失明,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後退出政治舞台,在貧病之中寫出了著名詩篇《失樂園》和《復樂園》,表達了一個民主革命鬥士的如火熱情和他對已逝的革命的評判。在王朝復辟時期極其淫逸放蕩的風氣中,這位盲詩人看得比誰都遠。在他素樸宏偉的詩句中,人們聽到了一六八八年推翻斯圖亞特王朝的政變、以至美國獨立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最初呼喊。他在創作方法上採用古典形式,是一個充分具有民主思想的古典主義者。是他的詩作,完成了詩歌從文藝復興到古典主義的過渡。他在戲劇理論上的唯一貢獻是寫於一六七一年的《論稱為悲劇的戲劇詩》一文,主要是複述亞里斯多德的意見,建樹不大。在彌爾頓寫出《失樂園》的次年,即一六六八年,英國出現了一篇重要的戲劇論著《論戲劇詩》,作者就是在政治品格上遠不及彌爾頓、在理論地位上卻超過彌爾頓的德萊頓。
年輕時候起就喜歡寫詩
德萊頓出身於一個清教徒的政治活動家的家庭,從年輕時候起就喜歡寫詩,十八歲就出過詩集,畢業於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他於一六六三年起開始寫作劇本,一生寫過二十七部戲劇,體裁和風格都很豐富,大多通過對愛情的謳歌和榮譽的崇尚來讚美君主制度,比較著名的如《印度女王》、《西班牙人征服格蘭納達》、《奧倫—澤比》、《一切為了愛》、《堂·塞巴斯提安》等。此外他還寫過一些著名的政治詩和諷刺詩。他在戲劇理論上除了那篇《論戲劇詩》之外,還寫過一些劇本序言,其中比較著名的是為劇本《特羅勒斯和克雷西達》寫的序言:《悲劇批評的基礎》。作為一個傑出的批評家,他公正地評論了莎士比亞、本·瓊生,以至喬叟、斯賓塞等英國文學的大匠宗師們,口氣穩健、流暢、樸實,一洗堆砌辭藻的頹風,在文藝批評領域可稱獨步一時。他的政治態度沒有彌爾頓那樣穩定執著,早年歌頌過資產階級革命之後以共和為標幟的軍事獨裁者克倫威爾,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後又向查理二世獻上過讚美之詞。因此他在王朝復辟時期的處境與彌爾頓形成了明顯的對照,憂鬱的盲詩人艱難地以口授的方式戰鬥著,而他則受封為桂冠詩人,任命為宮廷史官。一六八八年推翻斯圖亞特王朝前不久他成了天主教徒。晚年埋首於改寫喬叟作品和翻譯拉丁文學,逝世後葬於威斯敏大教堂。德萊頓曲折的一生,體現了處於兩個時代交界線上的一個敏感文人的尷尬狀態,新耶舊耶,此耶彼耶,抵消掉他不少才華。不象彌爾頓,矢志求索,寧可生活在共和的夢境裡也不隨順趨時。
基本的戲劇史觀
在《論戲劇詩》、《悲劇批評的基礎》等一系列文章中,德萊頓表明了他的一個基本的戲劇史觀:對於古代的法則,後人應在追隨中有所變動;“合乎法則”的法國古典主義劇作在各方面都不如“不合法則”的英國莎士比亞的作品。在具體地論述亞里斯多德的觀點時,他又在戲劇人物和戲劇中的情緒這兩個方面作出了獨特的理論貢獻。《論戲劇詩》是以四人對話的活潑方式寫成的,一般認為,其中尤金尼不斯代表了當時的伯克赫斯特勳爵,黎西狄爾斯代表了賽德雷勳爵,柯萊特斯代表了豪沃德勳爵(與德萊頓合寫《印度女王》者),而內安德則是德萊頓自己的化身,內安德的大段言詞可與作者的其他戲劇論文同等看待。
讓新的法則破壞舊的權威是不公正的
有一些理論家認為德萊頓已經全面地否決了古典主義的法則,這並不確實,他的戲劇理論從基本構成到基本命題都未曾割斷古典主義的制約,他贊同過這樣的意見:“讓新的法則破壞舊的權威是不公正的”,甚至他還認為不遵守“三一律”是莎士比亞的一個缺點。他對於已被人非難過的某些經典命題還進行過衛護,例如我們前面已經提及,法國有人指責過亞里斯多德有關“恐懼”和“憐憫”的提法,認為與亞里斯多德自己強調過的快感、愉悅原則有矛盾,德萊頓則借用當時另一個法國批評家拉賓(1621—1687)的話,調和並肯定了亞里斯多德的提法:“故事中沒有別的激情可以象恐懼和憐憫那樣恰當地引起我們關懷的;我們從關心得到樂趣,這是無疑的;當我們的心靈為這個人物的恐懼、那個人物的希望所激動的時候,我們在悲劇中取得了樂趣,由於我們對他們的事跡產生了興趣。”至於在他的戲劇理論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有關戲劇人物的那部分內容,也是以亞里斯多德的有關論述作為出發點的。在他的十分活躍的思想河道中常常可以看到幾支稱之為“總原則”、“基礎”之類的木樁。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文化史家大多還把他安置在古典主義的營盤之內,並非僅僅是由於他生逢其辰。但是,無可諱言,他是這個營盤中一個極不安靜、極不本份的活動性人物,甚至把他稱為古典主義的異己者也不為過。古典主義者通過對法則的嚴守來闡揚文藝合乎自然和可能的理性,而德萊頓則強調這個問題的另一個側面:正因為提出法則是為了保證合乎自然和可能的理性,所以法則不是目的,也不必嚴守。他曾很巧妙地引述了拉賓的另一段話作為《悲劇批評的基礎》的結語,這一段話是在闡述法則,完全符合古典主義的思想軌道,但正是在這種闡述中,為法則而法則的古典主義陋習也被否定了: 認真地考慮法則,我們將會發現它們不過是將自然縮成方法,亦步亦趨地追隨著自然,而不讓她最細微的足跡滑過我們的眼睛;只有依賴法則,虛構中的可能性才能保住,那是詩歌的靈魂。法則建築在明快的感性和正確的理性之上,而不是建築在權威之上的…… 沒有否定法則,只是把古典主義者很聽得進去的“自然”、“虛構中的可能性”、“正確的理性”來解釋它。但既然後者是不可或離一步的靈魂所在,那么法則倒應該是帶有依附性質的了。這段以古典主義校正古典主義的話雖然出自拉賓的手筆,但卻深合德萊頓之意,很能代表他的基本思路,所以用以歸結自己的論文。
三一律
德萊頓對某些古典主義者一再奉為不可逾越的法規的“三一律”,作了全面的檢查。他著重剖析了“三一律”中最穩定、也最經典的一項:情節(即事件、行動)的一致。他說制定這條法則的很自然的原因是明顯的,就是兩個不同的獨立的行動會分散觀眾的注意力和關懷,因而會損害作者的本意。他形象地把這一戲劇法則比之於透視:在透視中,必須有一個觀察點,所有的線條都在那兒終止;否則眼睛移動,作品也會不真實。這就把情節一致的理由說透徹了。但他緊接著又指出,戲劇史的發展事實早已突破了這種一致。希臘舞台上是按照這個法則做的,“但在羅馬戲劇中泰倫斯有了發明:他的全部劇作都有雙重行為;他習慣於把兩個希臘喜劇譯過來編成一個自己的劇本,它們的行為都是喜劇性的,其中一個是主要的,另一個則是次要或從屬的。這種做法在英國舞台上很流行,使我們獲得變化多端的樂趣”。羅馬已是如此,到了莎士比亞那就更放手了。德萊頓指出,如果嚴守情節、行動一律的法則,“這就否定了莎士比亞所有的歷史劇,它們表現了史實而不是悲劇,而且全都由雙重行為構成的。”為什麼戲劇實踐會逐漸地衝破這一法則呢?德萊頓在《論戲劇詩》中回答說:自然是複雜的,反映它的戲劇沒有理由不用複雜結構,問題只在於作者是否有本領把它寫得有條不紊而已。
把別人對於外在的量上的刻板規定,轉移為對內在秩序作“有條不紊”的處理,這是入理的。德萊頓認為,外在的簡單結構決不是戲劇成功的確實保證,他以法國古典主義的某些劇作為例:“許多人把法國乾燥無味、空虛貧乏的簡單結構捧到天上,真令人大惑不解。”“法國一人一事的劇本,……其中詩句之長篇大論、冷淡乏味,實在叫觀眾難以忍受。”結構強行單一化了,很容易造成內容的貧乏而不適應於豐富多彩的反映對象。德萊頓未必讚賞泰倫斯的二合一式的劇作和莎士比亞史實氣息過重的歷史劇,但比之於上述謹守行動一致的某些法國劇本,他的內心寧可傾向前二者,這是不難見之於字裡行間的。對於時間和地點的一致他就更不以為然了,何況對於這兩個一致前人已提出過不少非難。他說,許多需要有二三天延續時間的生動事件,強按在一晝夜的限制之內是不合情理的,而且這種事件所包含的主旨也不能在短促的時間內闡發完畢;至於限定在一個地點上演出各場,既限制了內容,又會產生許多荒謬。由此可見,德萊頓對“三一律”的異議是帶有全盤性的,一些誤認為“三一律”即古典主義的後世理論家把他當作一個堅決否決古典主義法則的人,倒是難怪的。實際上,他只是對古典主義理論結構中最招人眼目而又最顯示其弱點的部分打上了幾個很大的問號。
德萊頓對“三一律”的異議出於一個比較堅實的思想根據:戲劇實踐在發展,從亞里斯多德那裡抽繹出來的法則即便合乎亞里斯多德的原意,也未必合乎今天的現實。他在給當時另一位英國戲劇理論家萊默的著作《論前代悲劇》所寫的批語中說道:認為亞里斯多德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因而我們必須遵守,這是片面之言,因為亞里斯多德只是以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德斯的悲劇為範本,假如他看到了我們的悲劇,說不定早已改變他的主張了。
以一種得意自傲的口氣盛讚英國戲劇
在巍然高矗的古代權威面前都取得了如許自由,那對於出自當代的法國古典主義悲劇當然就更不會誠惶誠恐地景仰了。除了指出某些法國悲劇因追求簡單而墮入貧乏外,他還在其他許多方面表示了不佩服。在貶責法國悲劇的同時,他又以一種得意自傲的口氣盛讚英國戲劇。這裡無疑包含著強烈的民族感情,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出於對法國古典主義死板法則的深深不滿,在《論戲劇詩》中他故意用“合乎法則的法國劇本”和“不合法則的英國劇本”對立並提,就是這個道理。他說:不能以合乎法則與否來判斷兩個國家的戲劇孰優孰劣,既然對自然的生動摹仿是戲劇的定義,那么誰符合了這個定義誰就居於前列;法國的戲劇是對塑像的摹仿,而不是對活人的摹仿,這種摹仿沒有感情和靈魂,只能算是形存神亡;在這方面,誰都得承認,法國的喜劇和悲劇就比英國大為遜色了;高乃依的喜劇在英國演出時的效果,就遠不及弗萊契和本·瓊生,同時,莫里哀等人在黎塞留死後所寫的劇本,由於與英國的悲喜劇相似,並象英國某些劇作一樣與西班牙的小說、戲劇有了淵源關係,因而改變了它的面貌,但仍在本?瓊生之下;英國的悲喜劇是值得擁護的,它的成就已超過前人,並舉世無敵,這是我們的榮譽。
這裡的評價並不太公平,人們據此懷疑他抱有一些民族偏見也不是沒有理由的。他的可貴之處在於,威嚴的法則被他輕巧地剝奪了衡量戲劇高下的權利,讓戲劇的基本職能,從嚴謹地遵守法則回復到生動地摹仿自然。更有意義的是,他把以恪守法則為使命的劇作說成是對塑像的摹仿而不是對活人的摹仿,這個一針見血的比喻,為今後啟蒙主義者從美學上推倒古典主義開了先河。其實,一切按模式炮製的藝術形象都只是塑像而不是活人,古今皆然。塑像也有美醜高下之分,但它們的共同之處是沒有血脈的流注、肌膚的溫熱。把曾經獲得過不低的藝術成就的古典主義作品作過分的抨擊並不能令人心折,遠不如“塑像”的比喻深刻。
德萊頓對悲喜劇的肯定
也是建築在突破“三一律”的基礎之上的。照規矩,把一個喜劇行動和一個悲劇行動纏繞在一起,讓觀眾或悲或喜,會使作者的主要意圖落空。但德萊頓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視線完全可以在短時間內從令人不愉快的對象移到令人愉快的對象上去,而且由於相反的事物放在一起,可以通過反襯使彼此變得格外分明。這也就是說,悲劇和喜劇的結合,在觀眾席上可以獲得許可,在藝術效果上甚至還是必要的,完全可以成立。擺脫了束縛的人往往是自由而又放達的,德萊頓自感理由充足,遂出言少檢,偏激地把法國的莫里哀也放到英國的本?瓊生之下去了。這難免讓人在頻頻點頭之後又啞然失笑。
莎士比亞就是荷馬
莎士比亞就更不要說了。“莎士比亞就是荷馬,是我國戲劇詩人之父”,這是德萊頓的由衷之言。德萊頓在論述許多重要的戲劇理論問題時總免不了要拉出莎士比亞來作為成功的例證。也公正地談到過他的缺點,但是談著談著又想起了他的偉大,掩飾不住欽佩之情。而且,“我們的莎士比亞”一出場,德萊頓又總得以倒楣的法國劇作家來作為反襯。貶揚之間,尤勝莫里哀和本?瓊生之間的對比。然而由於莎士比亞本身的光華,德萊頓的揚莎抑法大體合理,看不出什麼民族偏見。那么,德萊頓是否要劇作家們都轉過頭來摹仿莎士比亞呢?他的態度比較慎重。既然他反對嚴守古代法則,那么,他也不贊成把今人的創作經驗匆匆忙忙地法則化。對此他保全了自己理論主張的一致性,沒有因為對新的光輝的過度讚美而忘了方才批判舊的法則時提出的一般原則。他在《悲劇批評的基礎》中特別探討了摹仿莎士比亞應該到什麼程度的問題。他認為,應該追隨那些創造了完美的戲劇的人們,摹仿和學習他們的優點,因為這是一座戲劇建築的基礎所在;但是,由於不同的宗教,各國的風俗,語言的習慣等等因素,戲劇的“上層建築”是會發生變化的。德萊頓試圖用“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提法,區分戲劇中的穩定性因素和變易性因素,認為可以追隨的是前者。此外他還認為,對自己要摹仿和追隨的對象的選擇要謹嚴,例如劇作家弗萊契的好多創造是從莎士比亞那裡借來的,“因此在這方面莎士比亞一般是值得我們摹仿的,摹仿弗萊契不過是追隨摹仿者罷了。”德萊頓說這些話,都是為了把人們的主要精力拉回到“生動地摹仿自然”上來。
承襲著自亞里斯多德以來的傳統意見
德萊頓也承認情節是戲劇的基礎,但是他認為,戲劇人物的塑造才是施工的開始。“基礎工程無疑是最最必要的,因為整個建築結構的穩固與否依靠這個基礎;但是它不會象性格、思想和表情的優美或不優美那樣的惹人注目。”這雖然大體上還固守著《詩學》對戲劇組成成分的排列次序,但人物性格的地位正在悄悄升高。德萊頓借用亞里斯多德關於戲劇性格的幾點論述作為自己闡發的起點和原則,實際上他是扎紮實實地根據現實戲劇經驗,重點剖析了戲劇人物創造過程中的三個大問題:性格的鮮明性、複雜性和可信性。鮮明性和複雜性是相反相成的兩個方面,兩者不可分離,而可信性則關及這種既鮮明又複雜的性格藉以立足的充分依據。由此可見,德萊頓的戲劇人物論,有著相當完整的自足結構。
鮮明性
戲劇人物的性格鮮明性,也就是傾向性。德萊頓深刻地指出,“所謂性格是指人物身上先天或獲得的某些傾向,那些傾向在戲中推動和帶動我們去做好的、壞的、或者不好不壞的行為;或者說,那種使得人物去做這種那種行為的東西。”性格即傾向,而且在戲劇中這種傾向不能深深埋藏起來,“它們必須很明顯,即是說,戲中每個人物必須表現出他們的一些傾向,這些傾向表現在行動中和言談中。”不明顯,無以見之於舞台。
性格鮮明有什麼好處呢?首先,可以把一個戲裡眾多的人物一一區別開來,德萊頓為此還引用了賀拉斯的定義:性格是把一個人和別的人區別開來的東西;其次,更重要的是,只有鮮明的性格才能引起觀眾的關心,起作用於觀眾。反之,沒有性格的人在戲裡無事可做,更不要期望通過他們帶給觀眾什麼美德了。在這一點上,德萊頓特彆強調,悲劇如果要真正引起觀眾的恐懼和憐憫,必須把主角的性格寫得鮮明,讓他的美德勝過惡行,否則觀眾是不會因關心他的痛苦而引起恐懼和憐憫的。由此他說明,戲劇主角的性格鮮明性問題尤其重要,戲劇的主旨如果分散到許多次要人物身上來表達,作用甚小。
德萊頓反對戲劇人物在性格上的朦朧隱潛、模糊不清。他說:要是人物身上的傾向是隱潛的,這就表明詩人無知,不曉得他想對你表現何種性格的人物;因此你對那個人物無法認識或者只有不明確的認識,你也不能判斷他應當下什麼樣的決心,什麼樣的言行對他合適。那么,在什麼情況下最容易造成性格的不鮮明呢?德萊頓認為是在作者追求驚險曲折的情節的時候:多數由突發事件或冒險行徑所構成的喜劇很容易犯這種錯誤,曲折多變的悲劇也容易為它所制,因為當命運的奇蹟主宰全部舞台之際,當詩人更致力於告訴你某個人物的遭遇,而不是他本人之際,人物的性格就不會鮮明。
是切中要害之論。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德萊頓又把莎士比亞與弗萊契作了一個對比。他認為性格刻劃是莎士比亞的一大長處,“他人物的性格常常是鮮明的”,他讓觀眾清晰地看到人物的“意向”和“傾向”;弗萊契呢,卻總是讓觀眾看“連續的探險行徑”,結果,“人物的性格只露出朦朧的微光”,“都象呈現在薄暮中的人影”。在這裡德萊頓指出了兩種創作傾向:究竟是向觀眾顯示人物的遭遇還是人物本身?究竟是讓人們看到驚險行徑還是人物意向?這個問題提出的本身就相當深刻,因為這裡展示了情節和人物性格這兩大戲劇要素間的矛盾。亞里斯多德把情節置之戲劇諸要素首位,但未能論及情節可能損害人物性格;他權衡取捨的結論,是在兩者不可得兼的情況下寧可要情節。現在,德萊頓作了相反的選擇,而且觀點也很決絕:不僅不可捨棄人物性格,連情節影響到人物性格的鮮明性也不可容忍。
複雜性
在德萊頓看來,賀拉斯關於性格是“把一個人和別人區別開來的東西”這樣一個定義過於簡單,必須作一個重要補充,那就是:一種性格,或者說一種把一個人和其他所有的人區別開來的東西,不能認為只包含某一種特殊的美德、惡行或激情;它是許多在同一人物身上並不矛盾的因索的綜合。
這個重要補充說明了一個鮮明的性格不應是簡單化的。一種質素不能構成一種性格,就象一種化學元素構不成一個生命體一樣,因此,決不能把性格寫成一種美德或一種惡行的擬人化,一種激情的化身。落實在創作上,要求戲劇家“不應該使他的最優秀的人物有完美無缺的性格”,“也不要壞到超過必需的限度”,兩方面都不要單一純淨。德萊頓解釋此中道理說,人物的性格總是由多種複雜原因形成的,可以是生理上的原因,也可以是性別、年齡、氣候、品質、處境等等方面的原因。戲劇家不僅不能對這么複雜的組成作簡單化的處理,而且需要大大地擴充自己有關自然哲學、倫理學和歷史等方面的知識,使自己有能力把握住每一個由多種因素綜合而成的性格。顯然,這是對性格類型化理論的一種否定,比布瓦洛等人高明。當然,綜合體也不是各部分平分秋色的混沌組合,還是有重點和軸心的。德萊頓在說了性格的綜合性之後,立即又不厭其煩地重複一句:“不過仍然需要指出,每個人身上必須顯出某一種壓倒其它的美德、惡行或激情。”這樣,他縱而復收,把複雜性與鮮明性結合了起來,說得十分圓到。
在性格的綜合體中除了要突出重點之外,另一個關鍵是要取得內在和諧,錯縱複雜而能共處。德萊頓舉例說,“同一個人物可以又大方又勇敢,但不能又大方又貪財。”這是因為,大方和勇敢可以取得統一,大方和貪財則勢不兩立。把不可統一的東西雜湊一鍋構不成一個有機生命體。當然,也未必要象大方和勇敢那樣接近的性格質素才可取得統一,有些互相間頗有距離的性格質素和性格特性也能在一個人身上協調地綜合,德萊頓舉例說,“一個騙子,一個懦夫,一個貪婪者和一個滑稽人物”,“所有這些品質可以在同一人身上協調起來”。幾種相近的性格特徵的統一和綜合難度較小,人物複雜性和豐富性的程度較低;反之,如能把乍看未必能相容共處的幾種性格特徵溶於一爐、化為一身,難則難矣,卻能造就成一個具有足夠豐富性的高級有機體。可見,德萊頓在強調性格統一性的時候沒有捨棄豐富和複雜,而在論述性格的豐富和複雜的時候更是緊緊地注視著各因素的統一。總之,在德萊頓心目中戲劇人物的理想性格,是一個傾向鮮明而又組成複雜的有機統一體。
可信性
如果說,以上所述著重於性格內部因素之間的關係,那么,可信性的問題則涉及整個有機統一體的邏輯依據。判斷是否統一和諧,也以此為基礎。德萊頓把人物性格可信性的問題明確概括為“它是否與人物的年齡、品質、國家、地位相適合”的問題,頗具現實主義精神。說到這一點,他又不滿意法國古典主義者了。他說,“一般人都責備當代的法國詩人說他們的戲不管取景於哪個地點,哪個時代,他們的主角完全是法國人的性格”,他是同意這種責備的。他不滿意拉辛劇作中那些他鄉異邦的角色也都散發著凡爾賽宮裡彬彬有禮的氣味。莎士比亞就不同了,他不僅沒有以自己的,或者以一邦一地的風格強加於劇中人,而且當他在處理象亨利四世這樣既要顯示國王的一面,又要顯示父親的一面的複雜性格時,竟也能“賦予他這二種身份的完美性格,不管在他與兒子們還是與子民們打交道的時候”。這就是說,劇作家為劇中人設立的身份、地位、處境,都要在劇中人的性格中看到它們烙印,性格的可信性,或曰合理性,就是憑藉著這條連結線取得的。不能使性格和依據兩相分裂,德萊頓指責拉辛給非法國人按上法國人的習性,就是從這種自我分裂著眼的。
與許多高水準的文藝理論家一樣,德萊頓所說的可信性和充分依據,並不是指與歷史上或現實生活中的真人實事的契合。戲劇人物的身份、環境本身也是作者給予的,因此這仍然是藝術天地內部的事情。性格與身份不符,即使兩方面都有生活根據可尋,也不可信;反之,不可能存在於世的幻想中人,也能在性格與身份的巧妙呼應中取得可信性。許多歷史劇中有名有姓的皇帝的性格塑造往往不符合他們的身份和時代,但是莎士比亞連妖怪的性格都能刻劃得相當可信。德萊頓很有說服力地舉出了莎士比亞在《暴風雨》一劇中塑造的妖怪凱里班的例子:“詩人最最明智地把人身、語言和性格給予了他,而這些無論從父親方面或母親的傳統來說都是合適的。除了恰如其分的重大罪惡以外,這個妖怪有巫婆和魔鬼的全部不滿和惡意;他的貪食、懶惰和淫慾是明顯的;同樣他也有一個奴才的頹唐情緒和成長於荒島上的人物的愚昧無知。他的軀體可怖,他是不自然的淫慾的產物;他的語言就如他的身體一樣妖里妖氣;在一切方面他是有別於其他人們的。”面對著這么一個世界上並不存在但又具備了足夠的藝術合理性的形象,德萊頓說,能否創造妖怪的問題可讓哲學家去答覆,而在藝術上則可認為是可信的。德萊頓借生活中不存在的形象來說明性格的可信性問題是別具深意的,他實際上是要戲劇家在這個問題上承擔更多的藝術權利和藝術責任,不要把可信性的重擔卸給歷史。當然,說到底,戲劇作品中人物身份和性格的統一還是來自於生活中人物身份和性格的統一。德萊頓也曾順便指出莎士比亞創造妖怪是從他對生活中的惡魔和巫婆的感覺出發的,就象人們可以從對生活中的馬和人的感覺創造出生活中並不存在的半人半馬怪物一樣。這就牽涉到文藝與生活的關係問題了,不是德萊頓的著眼點所在,他把它推給了哲學家。
德萊頓在論述戲劇性格的可信性時已無可避免地觸及了性格與環境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是近代戲劇理論領域中各家都要留連一些時日的熱鬧處所,一些比德萊頓更為傑出的學者將會一一對此發表不少精闢的見解。與後來者相比,德萊頓的這些意見未免粗糙,但他在十七世紀古典主義時期通過對古典主義劇作的批責來論述這個問題,已經比亞里斯多德所說的“適合”、“相符”前進了不小的一步。即使在這么一個具體問題上,歷史的步履也是清晰有致的。
戲劇情緒
是指戲劇作家和演員如何把角色的感情把握有度、駕馭自如,並以此來激發和控制觀眾的情緒。在德萊頓的全部論題中,這個問題對戲劇理論史來說特別顯得新鮮。
節制,是德萊頓對於戲劇情緒最基本的要求。他十分欣賞古羅馬朗吉弩斯關於要巧妙地運用激情的意見,認為用得不當的巨大激情是最可笑最淺薄的。一個藝術家的熱情如果沒有藝術的規約和控制,內在力量只會表現為急促的喘息;一個劇作者如果光有激情,他只能把靈感撕得粉碎,瘋狂地從一種比擬奔向另一種比擬,最能迷惑人、也最要不得的莫過於演員的激情泛濫了:熱情的呼喊確實可以討觀眾的歡喜,四分之三的觀眾愚蠢地認為一切大聲疾呼都能感動人,這就會使野心勃勃的演員擴大他的肺部,他為了博得如雷的掌聲情願當場送命;不過這對於明智的人不能引起別的情緒,只有憤怒和輕蔑。
無論是編劇者還是演員,沒有控制的激情對內容造成的直接損害是使觀眾分不清他們所表現的戲劇人物的性格。這就象把一個樂器的所有的弦線都撥到最高的音調必然會造成同一的聲音而奏不出樂章一樣,滿台激烈呼喊必然使所有的人都變成一個人,一個“最狂妄的英雄”。
在各種藝術之中,感情失度對戲劇來說更要不得。德萊頓表示不相信先哲會說詩“屬於天才或瘋子”這樣的話,說可能先哲是說“屬於天才而不屬於瘋子”,被後人讀錯了。其實德萊頓是以戲劇藝術的標準在要求著其他藝術。不管後人讀錯不讀錯,認為詩人有時不妨帶點瘋狂的因素不失為聊備一格之說;只是對戲劇詩人來說,不可沾染這種因素。原因很簡單,戲劇不是作者主觀感情的單方面宣洩,必須通過引發觀眾的情緒才能完成自己的藝術創造,而這種引發應該如抽絲,如浚泉,來不得急躁莽撞。被引發的觀眾,開始來到劇場沒有戲劇家這樣的情緒基礎,那么戲劇家應該懂得,“如果觀眾是靜穆的,他發氣是無用的,他必須逐步地感動他們,點燃他們的情緒,否則他會遭遇到這樣的危險:他把自己的一堆殘梗點燃,燒得一乾二淨,而站在他四周的人卻一點也沒有暖和。”高明的辦法是在情感的路途上先與觀眾拉起手來,“從容地輕輕地和他們一同出發,一直等到逐步使他們熱情起來;然後他加速步伐,用自己的激情席捲著他們前進,但又這樣安排他的呼吸,使他們需要的時候不會換不上氣,一直到最後保持著他最大限度的能力。”顯而易見,只有這樣的戲劇家才是自己的情緒和觀眾情緒的勝利駕馭者,因而也是整個劇場的駕馭者。
節制戲劇情緒,並非要為感情的渠道安置幾塊不合時宜的礁石。戲劇情緒不可滔滔無羈,但也要力求流瀉自如。德萊頓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坦然地拿自己的劇本《印度皇帝》來開刀。這個劇本讓一個遭到敵人追捕、正在尋找避難之地的人在沒有掩護的情況下站著談話,語詞間又堆砌著一系列優雅巧妙的比喻,這既打斷了這個角色的情緒線,也打斷了觀眾關心他的情緒線:“因為他既然還有餘暇去創作比喻,他們就不能構想危險就在眼前。”類似的毛病在莎士比亞的劇本中也在所難免。莎士比亞有時也會用一些誇大的話,這就“無法在觀眾的心中注入自然而然的激情”。但是這位戲劇大師即使犯錯誤也非同尋常,“如果把莎士比亞描寫激情的誇張之詞全部刪去,而用最庸俗的字句來表現它,我們仍舊能夠發現留下來的美麗的思想;如果把他的虛文都燒盡了,熔爐的底里仍舊有著銀子。”由此可見,關鍵在於情緒的實質性內容;而德萊頓所追求的,則是戲劇情緒從內容到表現形式都合乎自然。概而言之,“在觀眾的心中注入自然而然的激情”,這是德萊頓戲劇情緒論的歸結。
德萊頓的戲劇理論的各個方面都有一個特點,一切都以自然、可信為本,不為繩索所縛,不為矯情所害。這一點,實際上是強化了古典主義理論中最為出色的部分,使它對古典主義理論內部的其他部分產生排斥力,並容納一些新思潮的萌芽,這就使德萊頓在好幾個方面都成了古典主義連結今後的過渡性人物。
萊默與康格里夫
與德萊頓同時代還有兩個人發表過一些引起了社會影響的戲劇見解,那就是論述了悲劇的萊默和論述了喜劇的康格里夫。
萊默(1641—1713)進過劍橋大學,學過法律,當過律師。德萊頓很喜歡引用的法國批評家拉賓論亞里斯多德的著作就是由萊默在一六七四年翻譯成英語的,他一生影響最大的戲劇理論著述是一六九三年發表的《悲劇簡論》。這篇論文指出,照亞里斯多德的意見,戲劇是通過視覺和聽覺來使觀眾得到快感的,因而舞台上的發音和動作同等重要;有的觀眾重於“看”戲,有的觀眾重於“聽”戲,戲劇家要滿足觀眾的這兩種要求,不可偏廢;動作是對眼睛說話的語言,但莎士比亞卻往往用大聲疾呼來代替動作。萊默不僅在這一點上對莎士比亞表示不滿,他甚至說,《奧瑟羅》里埃古這個人物不能成立,因為埃古是軍人,一切軍人都很忠誠,以德報德。一眼就可看出,萊默是從古典主義理論中的消極部分——人物類型論出發而墮入了荒唐的。他對莎士比亞的批評並非都這樣沒有道理,但總的說來,他是黯昧於莎士比亞的偉大的。在許多問題上他不失為一個有眼力的批評家,但作為一個古典主義營壘里的保守派,他對莎士比亞和伊莉莎白時代其他劇作家的不滿之情是從古典主義刻板信條出發的,常常顯得吹毛求疵。很自然,就憑這一點他就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滿,甚至還被責斥為邪惡之徒,當然這也是過份的。萊默在戲劇理論史上的意義,主要是挑明了古典主義與莎士比亞的實際距離,從而使古典主義的戲劇觀在莎士比亞的映襯下顯得更明晰了。
英國文學作品集
| 英國文學發端於中世紀,經歷了古英語、中古英語、文藝復興、17世紀、18世紀、19世紀 、20世紀文學7個時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