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劇情
 《山清水秀》
《山清水秀》青年農民阿水夫婦,為了籌錢賄賂法官,以期能給弟弟阿沖免判死刑,決定賣掉他們還在腹中的孩子。之間,阿水曾遇到一對傳教士夫婦,也經歷了情感和道德的壓迫,有過質樸的負罪感和精神上的一線盼望。
在張校長的幫助下,籌夠了錢,但還是沒有趕上阿沖的判決。阿水奄奄一息,老婆投潭自盡,孩子卻又被警察弄回來了。最後,傳教士夫婦帶走孩子,阿水和他的村莊被黑夜吞噬。
藝術風格
 《山清水秀》
《山清水秀》《山清水秀》,導演甘小二,劇情片,片長102分鐘。在廣東省一個風景如畫的鄉村,青山綠水之間發生著一個辛酸的故事。
這部作品已經擺脫了“DV”這個詞在當下所具有的個人、實驗、倉促和浮躁的氣息,而事實上根本就是構思細密風格強烈的一部劇情長片。
首先,就直接的視覺經而言,畫面間滿是生動的充滿活力的綠色。以DV設備拍攝出這樣的美麗的景色已經難能可貴。青山、小溪、瀑布、農居……城市裡沒心沒肺的小資們能夠想像到的田園風景這裡一應俱全。可是,就是在這“詩情畫意”的空間裡,人生的苦難卻真實的呈現在眼前。故事發生的空間特徵和故事本身的沉重內容之間形成的反差,造成了強烈的反諷和戲劇效果。相信這是導演的安排:他一定要讓畫面儘可能的美麗,讓我們的心靈在視覺的迷醉中漸漸收縮、抽搐,這才是最尖銳的創痛。
敘事的風格接近侯孝賢。鏡頭幾乎不移動(除頭尾兩處在船上),就是在那裡一動不動地注視著。當然這也許和設備的局限有關係,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證明創作者的美學傾向。鏡頭的紀實功能被充分表現出來,而不是利用蒙太奇的畫面組合來完成表達。這裡要突出強調的是,本片的作者在一些重要段落的處理上,尤其具有個人的理解。
在一些描述主人公家破人亡的關鍵段落,越是需要感情強烈起伏的地方,作者的描寫越簡單,鏡頭也離的越遠。當孩子被抱走的時候,爹娘跟著買主走出門,一個很遠的大全景,就好象是最普通的送客出門;母親沒有哭,也沒有劇烈的動作,甚至她悲傷的臉只在樹叢後面出現了一下,就再也不見;當知道丈夫身患了絕症,妻子一言不發地躺在他身邊,摟住丈夫的身體;還有就是她最後的隕落,看上去只是對景色的描畫,但是巨大的流水聲中包含著震撼人心的殘酷……沒有更多的渲染,沒有鏡頭的推拉搖移,甚至連音樂都沒有,一片平靜之中,淡淡地勾勒著人物的行動。
難以抗拒那青山翠谷之間幽幽地傳達著的悲憫情懷,接近於宗教,事實上就是宗教。開畫的第一個鏡頭中就矗立著一個十字架,以及後來劇情中反覆出現的牧師與十字架的情節,包括那個哺育孩子的牧師妻子,都向我們昭示了導演本人的宗教傾向。他是在講述故事,幾乎不帶感情。但是我們知道他是有感情的,苦難只是現世的宿命,他在想像上帝從雲端望向世人的眼神,期待著人間獲得拯救。雖然一直對中國人信奉基督教這一現象中是否存在文化的誤讀表示懷疑,但是本片中的宗教情懷卻真誠地打動了人。
 《山清水秀》
《山清水秀》就美學特徵而言,本片難能可貴地把握了東方美學的含蓄內斂。不僅僅是畫面、鏡頭、節奏,故事中的人物性格也體現出來。雖然著墨最多的是男主人公阿水,但是我以為最成功的角色恰是妻子阿月。她承受了同樣的艱難,還有十月懷胎的辛苦,而她從來沒有一絲抱怨的神情。隱忍、從一而終,這些未必都是至善的行為,可是對家庭的責任和忠誠、同甘共苦……這些內容卻是在今天的社會中日益淡漠。我們無須為了人物的選擇進行爭論,所謂“值不值得”的無聊問題,我們只要問自己,換了是我,我能做到嗎?
全部的演員是非職業演員。當然的在表演上有生硬和不自然;有些場景的戲覺得力度不夠,還沒有到位——但是女主角的表演卻是令人驚艷的,細緻而又準確。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本片除頭尾出字幕時幾乎沒有任何音樂,無論戲份如何重要、情感如何洶湧,始終是一片寂靜——哪怕觀眾的心裡已經千呼萬喚。
誠然,仔細分析,本片依然採用了戴錦華所謂“苦情戲”的敘事策略。雖然作為獨立製片的作品,意識形態的教化色彩在此片中較為淡漠,更多的表現為獨立的知識分子對社會生活的記錄和表達;但是,這種通過講述偏遠農村/社會弱勢群體的生活而刺激城市知識階層/主流的獨立電影觀眾的最終結果,一方面在事實上對生存於苦難中的人們的現實生活於事無補,另一方面在主觀上也或多或少地以一種“奇觀化”的效果滿足了城市中產的某種快感。
但是這些都是無可厚非的事情。批評從來就象野草一樣,在作品的縫隙里隨處生長,任何作品都難逃“厄運”。拋開文化分析不談,就這部作品本身的藝術質量而言,令人心悅誠服。
任何作品,無論形式上怎樣實驗,內容上怎樣不羈,精神上怎樣叛逆,但是,有一點是不能馬虎的:它必須觸及人的靈魂或者性情,自己的或是他人的。如果不能讓人感動,讓人思考,哪怕讓人笑或者鬧,它存在的價值何在?
所以我們要感謝《山清水秀》這樣的作品。它不僅儘可能嚴肅地表達了自己的聲音,也讓我們看見了獨立製片群體的光亮:還是有人在認真地做,認真的思索。
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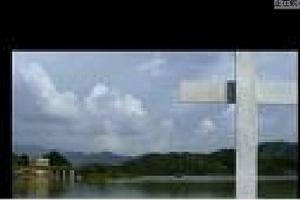 《山清水秀》
《山清水秀》《山清水秀》是一部努力尋找新的言說空間的電影,為自己尋找,在另一個意義上,也是為中國電影尋找。自新時期以來的中國電影呈現本土文化空間(尤其是傳統文化)的方式,經過第五代導演在國際電影節上十數年的打摸滾爬,已經大體上形成了相對固定的作品形態。應該說,這種形態是西方與東方,看者與製作被看之物者相互交合的結果。
這些作品中許多在形態(包括內容與形式)上明顯是一種西方視野下的東方,或者說,它是明顯地帶有文明中心地區視野下的文明邊緣地區的文化生態的痕跡。范此種種,當然它們中肯定也有許多作品並不盡然是為“友邦人士”之類的看客的戲子心態,應該說在某些時候,某些作品確實是有著真切的反省精神,然而歷史的玩笑在於,這種反省的潛在參照系恰恰又是西方體系下的。
這是我們當前這一類的作品的一種真實。我們不否認在一些時候,這種對西方認可的渴求、對東西方文明交合的渴求曾經為歷史、為中國文化(尤其是五四時期)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在當前的中國電影現實中,乃至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它會是一股巨大的力量,為中國電影尋找新的呈現本土空間的形式形成了某種阻礙(當然這不是唯一的原因)。然而對於新的一代,這種沉積是無法不去面對的。
我們可能在甘小二的長片處女作《山清水秀》中沒有看到令人倒吸一口涼氣的嶄新的空間,沒有看到通達於作品表里的全新的氣韻,但是我們看到了某種擺脫這種力量的嘗試。這種嘗試不應該被忘記。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新”的出現,而在於太多的東西太過於輕易地被忘記,以至於更新一輪的“新”往往陳舊而混亂。假設我們對於中國電影的明天從未失去應該有的信心,那么我們應該銘記。
片首悠長的笛聲吹的是一首宗教歌曲,用竹笛來施領聖恩,這給全片定下了一個奇異的氛圍。中國向來少有終極意義上的宗教,大都是世俗而現世,然而這部影片說的卻是宗教對一個社會邊緣的農民的終極穿透。這種穿透和現實甚少必然的聯繫(就作品表現出來的現實而言),而更多地與導演的信念有關。影片盡力揭示命運的車輪對個人無情的輾壓,但整個人物的發展似乎更多地出於導演個人想像的發酵,而不象是從現實的土壤里自然地生長出來的。這種情況在學院式的作品中屢見不鮮,在作者的風格沒有進一步地發展成熟之前,很難說是優點還是缺點,關健是看作者是否自覺地意識到這種距離感,並且適應和利用這種與現實的距離關係。
 《山清水秀》
《山清水秀》這部電影的英文片名與影片的敘事原點有關。影片中用了數個兒子的線索,有來自於聖經的典故,也有來自於影片內部。第一個是傳教士在鄉村宣道講到的亞伯拉罕和以撒。亞伯拉罕被稱為信心之父,神要亞伯拉罕把他的兒子以撒獻給神,做人肉燔祭。亞伯拉罕毫不猶豫就拉著兒子上山了,要在山上把兒子殺了,獻給神。結果神賜下替罪的羔羊代替以撒。亞伯拉罕之所以成為人類的祖先,主要是因為他對神有信心。第二個,傳教士說,上帝把它唯一的兒子耶穌賜給人類,耶穌本身是沒有罪的,因為人的罪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其實,就是被我們的人性中的罪和缺陷釘死的。第三,就是阿水和他的兒子高升的父子關係。這裡有三個獨生子,三種父子關係。
按照聖經里的說法,人應該具有亞伯拉罕那樣的信心,來作為對神的救恩的呼應。另外阿水的兒子高升與傳教士帶著的小孩(我們並不清楚是否是他的親生骨肉)用的是同一個演員,但不知為何導演沒有強化這一點,以至於幾乎每一個觀眾都無法意識到這一點。我們並不清楚是否出於導演個人經歷的原因,影片竭力在偏遠地區的農民和十字架之間產生某種關聯,而沒有更多更細緻地深入到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可以確定的是,整個影片的動力在於此。這導致了整個影片的格局,導演更感興趣的是主人公的命運與十字架相交和的宿命效果,而不是他們的現實層面或者精神世界。
這是一部充滿著矛盾的,但不是一部複雜的影片。故事背景是一個封閉的山村。基督教意識滲透著原始文化生態(導演沒有把它們當作同等的滲透、改變著本土原始文化生態的外來威脅,他在處理時是有褒貶高下之分的)。電影一開始,阿水已經被這個無形的大網所籠罩,接下來是收網的過程展示,無可逃遁,沒有掙扎,一切連同希望都深入水底。但所有這一切又被那異質的、或者說“更寬廣”的基督意識包容著(在導演的處理中,基督教與原始的形態也是不對等的,是包容與被包容的關係,而不是我們所知道的平等的關係,這也許和導演的信仰有關)。當被拯救的光芒所照耀,阿水死寂的內心也是波瀾蕩漾的。
這是一部沉默的影片,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部無言的影片。在某種時刻,我們確實感受到了沉默所應該具有的力量。但更多的時刻,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無言更多的是出於無奈,是一種被動的結果。它的底下並沒有奔流不止、灼熱似火的岩漿,也就沒有足以衝破冰冷堅硬地殼的強大力量。我們並不是在所有偉大的作品中都能看到火山爆發的壯麗,但涌動不息的岩漿卻無論哪裡都是始終在場的,儘管可能是在地表以下。沒有因為它們,沒有生命氣息的注入,地球是一塊沒有生命的石頭。
這也是當前中國大量藝術作品的一個無法擺脫的咒語。它們在形成之前就已經是一個欣賞對象。它們對於此在是冷漠的,而最終這種冰冷本身被置於冰冷的、無物的宇宙。或者說,作者的冰冷從一開始就決定了此在不再對作品敞開。最終此在對於作品也是冰冷的,遮蔽的。我們寧願把這種被迫的無言歸咎於作者的成長環境、教育機制,創作觀念,創作環境等諸多因素,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電影前面漫長的道路。
甘小二也說了這樣的一個例子。在他第一部長片《山清水秀》創作時,曾有人想給他投資,但出於謹慎,投資人找來了一些出版社編輯幫忙看看這部作品的投資前景,“一位女編輯在看了我的劇本後對我說:‘要揭中國人的瘡疤,你慢了。’她的意思是早有張藝謀等大導演走在前面了,這話當時對我刺激非常大,你知道一個創作者的創作信心是很容易受挫的,你不知道自己的東西是否真的有價值。但後來我的朋友李輝對我說:‘電影是給觀眾看的,不是給洋人看的’,是他信任了我也支持了我,我想說我們這些把片子送去國外參展的導演,在愛國這點上是毫不遜色的。”
獲獎情況
 甘小二長片處女作《山清水秀》
甘小二長片處女作《山清水秀》2003,第22屆溫哥華國際電影節“龍虎獎”競賽單元,評審團特別獎;
2003,第8屆釜山國際電影節“新浪潮”競賽單元,入圍;
2003,“我是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北京,展映;
2004,第33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主打故事片”單元,展映;
2004,第4屆新加坡亞洲電影論壇,開幕電影;
2004,第6屆台北電影節“華語電影”單元,展映;
2004,香港亞洲影展,展映;
2005,第2屆廣州三年展“珠三角電影回顧展“1998-2005”,展映;
大陸獨立電影之劇情片
| 在中國大陸,由於現階段審查的存在,那些不經審查而拍攝的電影,被這些電影製作者自稱為“獨立電影”,而更貼切的稱謂則是“地下電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