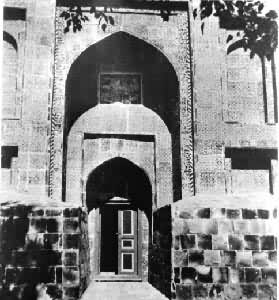維吾爾族文學
正文
維吾爾族人口約 595萬餘人(1982),主要聚居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其語言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從 6、7 世紀起,先後採用過突厥魯尼文(亦稱“鄂爾渾—葉尼塞”文)、回鶻文,10到11世紀後,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的維吾爾文逐步取代了以粟特字母為基礎的回鶻文,20世紀70年代,曾推行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新維吾爾文。維吾爾族文學淵遠流長。民間文學及作家文學都有悠久的歷史及鮮明的特色。民間文學 民間文學是維吾爾文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英雄史詩、民間敘事詩、民歌、民間故事、寓言、諺語、民間彈唱等多種體裁和形式,對維吾爾族作家文學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
維吾爾族史詩中,代表性作品首推《烏古斯傳》(亦稱《烏古斯可汗的傳說》)。它是迄今發現的保存得比較完整的一部古老的散文體史詩。反映了尚處於遊牧氏族部落社會階段時期的維吾爾族先民信奉薩滿教的原始風習,對蒼狼的圖騰崇拜,及對周圍其他古老部落名稱的民俗學解釋。史詩通過關於烏古斯可汗南征北戰的有聲有色的描述,表現了烏古斯可汗的英雄氣概和赫赫戰功,表達了各突厥遊牧部落要求聯合統一的願望。結構嚴謹,層次清晰,語言古樸生動。此外,成書於11世紀的《突厥語辭典》中,也採擷了若干英雄史詩的片斷,如關於英雄阿里甫·艾爾·童阿的輓歌、關於與非伊斯蘭回鶻人、唐古特人之間征戰的史詩片斷等等。這些作品不僅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而且為研究維吾爾族及其他操突厥語民族的古代歷史、宗教、民俗、語言等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
維吾爾族的民間敘事詩以反抗封建婚姻、謳歌婚姻自主的愛情長詩居多。如《艾里甫和賽乃姆》、《塔伊爾與祖赫拉》等等。這些流傳於民間的愛情故事往往成為歷代詩人、作家進行創作的傳統題材,許多作家的作品也回到民間流傳開來,循環往復,形成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水乳交融的狀況,這也是維吾爾族文學的一個特點。《賽依特好漢》等敘事詩則以對抗封建王朝的反動統治,反對壓迫剝削為內容,歌頌了維吾爾族勞動人民的勇敢、機智和大無畏的鬥爭精神。
維吾爾族民歌十分豐富。按其內容大體可分為勞動歌、生活歌、歷史歌、習俗歌、情歌及新民歌等。
勞動歌既有產生於遊獵時代的古老獵歌,也有定居從事農業生產之後的刈麥歌、打場歌等,大多表現了人們對於勞動的熱愛及收穫時的喜悅。生活歌有訴說長工、礦工、趕車人苦情的歌,有傾吐婦女哀怨,描述孤兒淒楚的歌等等,它生動真實地反映了舊社會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活。歷史歌主要是關於維吾爾族歷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歌謠,有的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及農民的英勇反抗和暴動起義,有的反映了維吾爾族人民反抗外來侵略,保衛家鄉、保衛邊疆、維護祖國統一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其中流傳較廣的有北疆伊犁地區的《諾孜古姆》、《築城歌》、《英雄沙迪爾的歌》、反對沙皇的《迫遷歌》,南疆喀什地區的《關於馬提台的歌》等等。習俗歌多在婚喪嫁娶、節日慶典時吟唱,有酒歌、婚禮歌、哀悼歌等。它與維吾爾族的傳統習俗緊密相連,富於民族特色,是民俗學研究的重要材料。情歌在維吾爾族民歌中占有很大比重,青年男女間熾熱的戀情往往通過富有維吾爾民族心理特徵和地域特色的比興手法來加以表達,因此具有一種獨特的藝術魅力。新民歌則是維吾爾族人民對於社會主義新生活的熱烈頌歌,表現了人民對黨、對領袖、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熱愛。
維吾爾族民間故事,內容廣泛,風格多樣,有的清幽淡雅;有的瑰麗神奇;有的機智幽默;有的寄寓遙深,大多表現了勞動人民鮮明的愛憎是非觀念和頑強、樂觀、風趣的民族性格特徵。如描述一個吝嗇刁鑽的巴依不許長工們在他門前樹蔭下歇涼,長工們集資買得蔭影后,隨著蔭影的移動,跑到巴依院子裡、屋頂上開懷作樂,使得巴依叫苦不迭的《桑樹蔭影的故事》;流傳極廣的《阿凡提的故事》,以及與之相類似的《毛拉則丁的故事》、《賽萊依·恰坎的故事》等,都顯示了維吾爾族民間文學詼諧幽默的情趣。《三條遺囑》之類的故事則具有較濃厚的諷喻色彩,它教育人們要依靠自己的雙手,通過辛勤的勞動去謀求幸福。在維吾爾族民間流傳的故事中,還有一類連環故事,如流傳於南疆喀什、和田一帶的、包括36則故事的《鸚鵡的故事》、包括10則故事的《國王阿扎旦和巴哈提亞爾》等。它們在結構上、情節內容上,都明顯反映出印度文學、阿拉伯—波斯文學的影響,這是由於新疆曾經處於絲綢之路的樞紐,維吾爾族汲取了各種文化精粹的結果。維吾爾族民間故事中還有包括動物故事在內的相當數量的寓言故事,它深刻而生動地反映了維吾爾族人民的道德觀念和生活哲理,言簡意賅,耐人尋味。
維吾爾族的諺語,11世紀的《突厥語辭典》中就輯有不少,其後又不斷豐富發展,不少諺語表現了尊重知識、慷慨好客、注重團結、講求實效等傳統的民族風尚。
維吾爾族的民間彈唱是一種表演性很強的綜合藝術。吟唱內容有神話傳說、英雄史詩、愛情敘事詩、民歌等,亦有演唱大型套曲《十二木卡姆》者。《十二木卡姆》中的歌詞除古典作家的詩章片斷外,亦有傳統的民歌及情歌。
此外,維吾爾族還有許多獨特的民間文藝活動,如“麥西萊甫”、“巴赫賽依萊”、“努魯孜”、“白雪節”等,在這些活動中,除了歌唱、舞蹈、遊戲外,還有講故事、說笑話、對詩聯句等文學內容,深受民眾喜愛,也是民間文學一代代流傳普及的一條重要渠道。
作家文學 維吾爾族的作家文學,根據迄今為止的出土文物及考古資料表明,至遲發軔於公元7、8世紀,它大體可分為突厥汗國—回紇汗國文學、高昌回鶻汗國—喀拉汗王朝文學、察合台文學、近代文學、現當代文學等幾個歷史時期。
突厥汗國(552~744年)與回紇汗國(744~840年)文學 這一時期(6世紀中葉至9世紀中葉)的文學作品,保存下來的主要是鄂爾渾碑銘文獻。這些碑銘中有一部分是具有濃郁的文學色彩和史詩性質的碑文。如《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可認作維吾爾人的第一批書面文學作品。碑銘採用了散韻相間的敘事詩體裁,以排比、反覆等手法構成了詩的節奏。語言生動,內容凝鍊,具有英雄史詩剛健雄渾的風格。這些碑銘儘管反映的歷史事件不同,但在語言及思想傾向、藝術風格、表現手法上具有共性。幾乎都以結束內部紛爭及戰亂,建立統一團結的汗國,俾使人畜興旺發達為主題,歌頌了為實現這一願望而鬥爭的英雄的功績。這些碑銘文獻除具有文學價值外,還提供了有關古代突厥—回紇部落的歷史、人文、民俗資料及古回鶻語言文字的第一手資料,不僅對研究古代維吾爾,而且對研究當時共同生活在漠北草原的其他突厥語系諸民族也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它們為後來的抒情長詩和敘事長詩的發展奠定了基石。
高昌回鶻汗國與喀拉汗王朝時期文學 9 世紀中葉,維吾爾族歷史上的大遷徙,開創了文學史上的一個新時期。從蒙古高原西遷到新疆的維吾爾人與先前的居民一道建立了兩個各自獨立的汗國。由於這兩個汗國所處的歷史、地理、宗教等社會條件的不同,因而在文學上呈現了雙峰對峙、二水分流的局面。一為摩尼教、佛教及漢族文化影響下的高昌回鶻汗國文學;一為伊斯蘭教及阿拉伯、波斯文化影響下的喀拉汗王朝文學。
高昌回鶻汗國文學 9世紀中葉,西遷的回鶻人中的一支與原先在北庭一帶遊牧的回鶻部落聯合起來,建立了以吐魯番為中心,東接河西走廊,西至拜城,包括焉耆、庫車、拜城、鄯善、哈密及敦煌以東一部分地區的高昌回鶻汗國,轉入了農業定居,當地的古代焉耆人、龜茲人、高昌人、漢人等也逐步融合了進去。城市與貿易進一步得到發展,回鶻書面語隨之在新疆及中亞成為通行的語文。高昌地處絲綢之路的要衝,早就是中原文化和東羅馬文化、古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的交流薈萃之所。兼之高昌汗國境內,佛教、摩尼教、景教同時並存,因此這一時期的維吾爾文學呈現出兼收並蓄,異彩紛呈的繁榮景象。不僅從漢文、梵文、吐火羅文、藏文翻譯了大量佛經以及摩尼教、景教典籍,而且還翻譯或改寫了許多源出佛教傳說、本生故事的文學作品:如《恰希塔尼·伊力克伯克》、《哈勒亞木哈拉和帕帕木哈拉》、《兩王子的故事》、《神猴與帕德摩瓦提姑娘》、《達尼提·帕拉》等。此外還有《伊索寓言》、《聖喬治殉難記》以及《三個波斯僧朝拜伯利恆》等與景教流傳有關的故事。詩歌有《吐魯番民歌集》、《佛教詩歌集》、《摩尼教讚美詩》等等。這一時期詩歌的特點是押頭韻,與其後的維吾爾詩歌明顯不同。過去世代口頭流傳的英雄史詩,如《烏古斯傳》等,此時有了寫本或抄本傳世。戲劇文學及舞台藝術也開始進入了維吾爾人民的社會生活,多幕劇《彌勒會見記》的幾個抄本的發現可為例證,宋人王延德所撰《使高昌記》對此亦有所記載。13世紀後,伊斯蘭教開始在新疆全境取得統治地位,高昌汗國時期及其以前創造的大量非伊斯蘭文化典籍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因此迄今發現的這些文獻不僅只是當時大量文學作品中為數寥寥的一部分,而且多屬斷簡殘篇,原著譯者已無從查考。現僅從少數倖存作者姓氏的殘卷中得悉當時的作家、詩人和翻譯家有迦魯納答思、齊齊、阿普林啜特勤、僧古薩利、齊速亞都統、伽琳·凱什、闕達乾、阿思黑都統等人。
阿普林啜特勤的愛情詩語言質樸清新,感情誠摯深沉。摩尼教讚美詩對黎明之神的讚頌,反映了人民對於光明和幸福的追求和嚮往。僧古薩里所譯《金光明經》及《玄奘傳》,不僅表明了翻譯家漢文、回鶻文造詣之深、翻譯技巧之高,而且顯示了當時維吾爾書面文學發達的程度。源於佛教本生故事的《恰希塔尼·伊立克伯克》,通過對菩薩轉世的恰希塔尼·伊立克伯克翦除兇惡的妖魔、瘟神,解救人民的英勇無畏精神的描繪歌頌,反映出當時勞動人民戰勝社會和自然邪惡勢力的強烈願望。作者採用對反面人物猙獰面目的誇張描寫,成功地反襯出主人公的英雄形象,這種對比陪襯手法成為後代維吾爾文學創作經常採用的藝術手段之一。
喀拉汗王朝文學 從漠北西遷的另一支回鶻人與葛邏祿等突厥部族匯合,建立起囊括新疆南部、七河流域及中亞細亞大部分地區的喀拉汗王朝(亦稱黑汗王朝或哈喇汗國)。隨著生產的發展,城市手工藝及貿易的繁榮,巴拉薩袞、喀什噶爾成為喀拉汗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維吾爾文化和文學也相應地出現了繁榮高漲的局面。喀拉汗王朝以伊斯蘭教為國教,整個社會生活,包括文學藝術被置於伊斯蘭教義及伊斯蘭哲學的影響之下,因此喀拉汗王朝的維吾爾文學,與同出一源的高昌汗國維吾爾文學相比,更多地吸收了阿拉伯—波斯文學的影響,無論在內容、形式、體裁、風格上都別具特色。
喀拉汗王朝遺留下來的重要文學遺產有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語辭典》、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樂智慧》、艾哈買提·尤格納克的《真理的入門》、艾哈買提·雅薩惟的《箴言集》等。
《突厥語辭典》系作者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蒐集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於1072至1074年編纂而成。它介紹了維吾爾族及其他突厥語部族的源流及分布地域、典章制度、人文風尚、文化成就等多方面的情況,被世界突厥學界公認為11世紀突厥人的百科全書,具有多學科的重大學術研究價值。在該書詞條的注釋中收錄格言、諺語300多條,詩歌及史詩片斷約240餘段,按其內容、形式、韻律歸納分類,除有英雄史詩的片斷外,還有勞動狩獵歌、征戰詩歌、描繪大自然的季節歌、習俗歌、愛情詩歌以及關於道德風尚、民族傳統方面的訓誡性詩作片斷等等,從中可以窺見古代維吾爾文學反映歷史和現實的廣度、深度及其藝術成就,是極為珍貴的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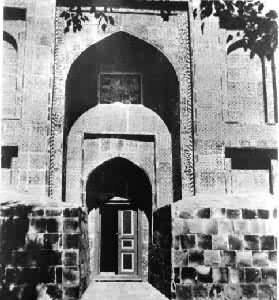 維吾爾族文學
維吾爾族文學 維吾爾族文學
維吾爾族文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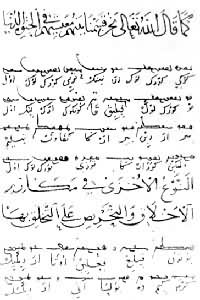 維吾爾族文學
維吾爾族文學《真理的入門》是喀拉汗王朝末期的代表性作品,在《福樂智慧》的影響下寫成,但語言已採用較多的阿拉伯、波斯語借詞。這部哲理訓誡性長詩強調了知識文化的重要,稱頌了慷慨、正直、謙遜、大度等美德,譴責了無知、昏庸、貪婪、驕傲等惡習,具有進步意義,但同時也和《福樂智慧》一樣,宣揚了伊斯蘭教義及封建道德規範。
喀拉汗王朝的維吾爾文學,受到伊斯蘭教的深刻影響,許多作品都滲透著伊斯蘭教義及蘇菲主義思潮,生活於12世紀初期的艾哈買提·雅薩惟就是蘇菲教派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其主要作品為《箴言集》,這部詩集規勸人們摒棄世俗慾念、宣揚返樸歸真、聽天由命的遁世哲學。喀拉汗王朝後期內憂外患的處境,以及作品語言與口語相近,使其在民眾中流傳甚廣,對後世維吾爾族文學創作也有不容忽視的影響。
察合台文學 13世紀成吉斯汗的進軍和蒙古帝國的建立,給生活於新疆及中亞地區的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語民族的社會生活,帶來了重大變化和新的因素。從蒙古草原到裏海之濱的遼闊地域連成了一片,各突厥語民族人民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繫進一步密切,從而導致了打破方言地域界限、統一的書面文學語言的形成。這一文學語言是在喀拉汗王朝的突厥──維吾爾語及高昌汗國的回鶻語基礎上,吸收阿拉伯、波斯文學語言的影響發展形成的,它通行於察合台汗國的廣袤疆域,並在察合台汗國分崩離析後仍流行於故地,故習稱“察合台語”。高昌汗國併入察合台汗國版圖後亦逐步伊斯蘭化,至此維吾爾文學複合二為一,逐步進入了使用共同書面語──察合台語的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即察合台文學時期(13~18世紀)。
這一時期前期的傑出代表作家有拉布烏孜、阿塔依、賽喀克、魯提菲和納瓦依等,他們的作品為維吾爾古典文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納斯爾丁·拉布烏孜的《先知傳》(又稱《拉布烏孜故事集》),屬察合台文學早期,它取材於伊斯蘭世界廣為流傳的先知故事和宗教傳說,以散文體寫成,其中某些抒情寫景及闡述哲理的部分穿插詩歌韻文,代表了當時的一種特殊風格。精闢的箴言在短小精練的故事中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極富藝術特色。
這一時期,反映在文學領域中的鬥爭,就創作思想而言,是為中世紀封建專制主義歌功頌德的宮廷文學及其同盟者宣揚宗教蒙昧主義、苦行主義、遁世哲學的蘇菲派文學與反對封建及宗教桎梏、主張正義、自由、熱愛生活、歌頌純真愛情和理想的人文主義文學之間的鬥爭;就書面語言而言,則是風靡一時的以阿拉伯、波斯語創作的傾向與抵制這一潮流,堅持用本民族語言進行創作之間的鬥爭。這一鬥爭促進了維吾爾文學的發展,培養和造就出一大批站在時代前列的作家和詩人,如阿塔依、賽喀克、魯提菲以及後來代表整個察合台文學高峰的納瓦依等。同時這一時期由於某些歷史的原因,中亞的文化中心已由喀什噶爾遷往河中地。許多維吾爾作家、詩人往往聚集在河中地進行創作甚或度過自己的一生。阿塔依和賽喀克這兩位同時代的詩人儘管有各自不同的創作經歷和風格特色,但在創作題材及思想內容上有著許多共同之點。他們都揶揄嘲笑寄希望於天堂的苦行主義、遁世哲學,主張熱愛世俗生活,頌揚忠貞純潔的愛情,歌頌現實生活之美,歌頌對光明和幸福的追求,痛斥矯揉造作的偽善。他們創作了大量感情真摯,藝術高超的“格則勒”,為這一抒情詩體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繼阿塔依、賽喀克之後,在抒情詩創作上,魯提菲的成就尤為突出。魯提菲被納瓦依譽為“維吾爾語言的泰斗”,他的傳世之作,一為抒情詩集《魯提菲集》,一為敘事長詩《古麗與諾魯茲》。他通過自己的作品將真善美形象化,激發人們對美好事物、對理想和光明的信念,摒棄對來世的虛無飄渺的幻想,勇敢地為追求正義和幸福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詩人的美學思想和對人生的積極態度,對後世維吾爾、烏孜別克、阿塞爾拜疆文學的發展都有較大影響。
新疆及中亞許多突厥語民族(包括近代才分化形成的某些民族),歷史上曾處於同一封建王朝的統轄之下,加之語言、文化傳統及其他人文方面的共同因素,在文學上長期存在著互相滲透、互相交錯的複雜情況。正是由於這一歷史現象,造就了納瓦依在維吾爾及其他突厥語民族文學中的巨大影響和突出地位,使其創作成果成為維吾爾及突厥語系某些民族文學史上的共同的豐碑。
納瓦依著述甚豐,代表作有包括 16種詩體 3130首44803 行的四卷集抒情詩《精義寶庫》和包括五部長篇敘事詩的《五部詩集》。納瓦依的這些作品突破了中世紀窒息人類自由的封建專制主義和宗教蒙昧主義的思想樊籠,強調了人的尊嚴,斥責了對婦女的歧視,充滿著對暴政的憤怒抨擊,閃爍著人文主義的思想光輝。他的敘事詩更充分展現了這種進步思潮與封建宗法統治之間的深刻的社會衝突。此外,集中反映了作者哲學思想的《鳥語》、頌揚各種行業分工的《情之所鍾》、闡述詩歌韻律的《詩律準繩》、評介當代及前輩詩人的《群芳雅會》及闡述突厥語優越性的《兩種語言之爭辯》等等,都對維吾爾古典文學乃至現代文學有著深遠的影響。
察合台文學後期,繼承了魯提菲、納瓦依的優秀詩歌傳統的代表人物當推赫爾克提、翟黎里和諾比提。赫爾克提的《愛情與苦惱》充滿浪漫主義的色彩,格調清新,想像奇特,在敘事詩中別開生面。翟黎里的《漫遊記》等詩集,滿挹憂國憂民之思,感情深沉激越。諾比提的抒情詩風格細膩,寄寓遙深,香草美人,別有懷抱。此外,在他們之前和以後,輝映維吾爾文壇的還有阿曼尼莎汗的《納菲賽詩集》、哈依勒·西凱斯特的《照世鏡》、毛拉·艾萊姆·沙赫亞爾的《玫瑰與夜鶯》、毛拉·熱依木的《情緣錄》和卓加罕·艾爾西的《艾爾西詩集》、毛拉·哈西木的《諸王書》、奧麥爾巴克的散文體《法爾哈德與希琳》、《萊麗與麥吉儂》等等。
近代文學 1759年清政府平定了準噶爾叛亂及和卓們的騷亂,恢復了新疆與祖國大家庭的統一。新疆與內地的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聯繫更加密切,不少維吾爾族學者應邀到北京參加《五體清文鑒》的編纂工作。但是隨著清王朝的日益走向腐朽沒落,清政府派往新疆的官吏與維吾爾族上層勾結在一起肆無忌憚地魚肉人民,激起了不斷的反抗和起義,這一形勢推動了文學進一步與社會現實生活的結合,使維吾爾文學進入了一個直面人生、針砭時弊的批判現實主義的階段,察合台文學末期初露頭角的諷刺藝術到這一時期表現得更為犀利尖銳,成為這一時期(18世紀下半葉~19世紀末)文學創作上的基本特色之一。
這一時期中,作出了卓越貢獻的作家、詩人有尼扎里、古穆納木、凱蘭代爾、薩布里、艾里畢·吐爾都西阿洪、毛拉·畢拉勒、毛拉·玉素甫、毛拉·夏克爾和泰介里等。
尼扎里流傳至今的作品有愛情長詩《法爾哈德與希琳》、《萊麗與麥吉儂》、《麥赫宗與古麗尼莎》、《熱碧亞與賽丁》等12部敘事詩。哲理長詩《濟世寶珠》和抒情詩集《穆罕默斯集》。愛情長詩中,特別是《熱碧亞與賽丁》取材於當時的真人真事,通過這一悲劇把矛頭直接指向了扼殺純真愛情的封建等級制度和傳統觀念,亟富現實意義。古穆納木與凱蘭代爾都是優秀的抒情詩人,薩布里與艾合買提夏·哈里哈西則擅於辛竦的諷刺。艾里畢·吐爾都西阿洪把最底層的工匠們的生活納入自己的創作題材。毛拉·畢拉勒則更有進一步的突破,在其長詩《中國土地上的聖戰》中直接描述了伊犁農民暴動及竊取了起義領導權的封建上層與宗教上層內部勾心鬥角的鬥爭;在《諾孜古姆》中塑造了一個被清軍流放的英勇不屈的女英雄形象;在《長毛子玉素甫汗》中揭露了一個來自浩罕、自稱聖裔、披著宗教外衣、招搖撞騙的無賴典型。這些作品為維吾爾文學進一步走向現實主義奠定了堅實基礎。毛拉·夏克爾繼其後以《凱鏇記》反映了1863年的庫車農民起義,而泰介里的《電光的顯露和消失》,則滲透著樸素的辯證思想和對光明未來的信念,在維吾爾族的古典文學與現代民主主義文學之間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
現當代文學(1919~ ) 進入20世紀以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銳,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疆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內憂外患的處境和抗日戰爭的烽火,促使這一時期的維吾爾族文學呈現出一個嶄新的局面。時代風雲和歷史潮流賦予這一時期的文學以一種慷慨激昂、悲憤激越的色彩。文學與人民民眾、與進步思潮、與革命鬥爭的聯繫、結合大大加強,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現代民主主義思想已成為創作思想的主流,不少作品還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許多作家和詩人直接投身於革命鬥爭,有的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如果說阿拉伯、波斯文學曾對維吾爾族古典文學有過較大的影響,那么這一時期的維吾爾文學則是從五·四新文學和俄國民主主義的優秀作品和蘇聯文學中吸取了豐富的滋養。祖國的命運、人民的解放,已成為文學創作首先注目的中心。作為整箇中華民族組成部分的維吾爾族誓與祖國共存亡的堅定決心,祖國高於一切、祖國重於生命的熾烈感情在許多作品中得到了明確的體現。古典作品中那種對自己家鄉故土的深摯愛戀已升華為對整個祖國的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和神聖的歷史責任感。在體裁上也出現了歌劇、話劇、散文、小說、文藝評論等現代文學形式。所有這一切特徵,標誌著維吾爾族文學與現代漢族文學潮流相一致。
阿不都哈勒克·維吾爾、黎·穆塔里甫、尼米希依提、艾里坎木·艾合坦木、祖農·哈迪爾、鐵依甫江等,是這一時期引人注目的代表。其中,尤以維吾爾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旗手黎·穆塔里甫的成就和影響最為突出。黎·穆塔里甫(1922~1945)曾經受到陳潭秋、林基路等中國共產黨人和文學大師茅盾的深刻影響,他既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優秀作家、詩人,又是一位英勇無畏的堅強戰士。他在《五月之歌》、《中國》、《我青春的花朵就會開放》、《中國游擊隊員》、《對歲月的答覆》等名篇中,以犀利的筆鋒,猛烈抨擊日寇的野蠻侵略和反動當局對革命者的迫害,激勵人民奮起與一切反動勢力作殊死的拼搏,為爭取光明、自由、解放的新中國而鬥爭。詩風豪邁雄渾,氣勢磅礴。除詩歌外,他還寫劇本、小說、散文、文藝論文。這位堅貞不屈的詩人1945年被國民黨反動當局殺害於阿克蘇獄中,犧牲時年僅23歲。阿不都哈勒克·維吾爾(1904~1932)也是維吾爾族新文學的開拓者之一,寫有不少反對壓迫剝削、爭取自由解放的充滿戰鬥激情的詩章,1932年在組織吐魯番農民起義時被盛世才所殺害,其作品亦多散佚。尼米希依提、艾里坎木·艾合坦木、祖農·哈迪爾等都直接參加了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新疆三區革命,他們或以激情洋溢的詩篇,或以催人淚下的小說、劇作,喚起人們對舊世界的憎恨,對光明未來的信念,激勵人們為推翻三座大山而英勇鬥爭。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新疆獲得和平解放。從此,維吾爾族文學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尼米希依提、艾里坎木、鐵依甫江、克里木·霍加等,以他們絢麗的彩筆,描繪了一幅幅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圖景,鼓舞著人們為建設美好的新中國而忘我勞動,許多富有民族特色和時代精神的作品相繼問世,為中國多民族的文學畫廊增添了風姿。尼米希依提的《思念》、《告別了,但永遠告別不了》、《在時代的講壇上》,鐵依甫江的《祖國,我生命的土壤》、《一位老戰士的囑咐》等,都以恢宏磅礴的氣勢,深沉激越的感情而膾炙人口。克里木·霍加的許多“柔巴依”,短小精悍,深寓哲理。祖農·哈迪爾的小說《鍛鍊》、劇本《喜事》,則是老作家對新生活的熱情禮讚,艾里坎木·艾合坦木用他樸實清新的詩筆在創作抒情詩之餘,還寫出了長詩《沙婀黛蒂汗》,深刻地揭示了維吾爾人民在封建王公伯克制度下的苦難歷史。社會主義時期的維吾爾族當代文學正在蓬勃發展的時候,由於歷史出現了曲折,歷次左的干擾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嚴重地阻礙和破壞了維吾爾族文學的繁榮。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維吾爾族當代文學才開始復甦並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重新邁開步伐。近年來,在擺脫了思想和文化的禁錮之後,維吾爾族文學的現代化和民族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長篇小說、中篇小說、電影文學劇本這些新文學體裁的作品相繼問世,許多老作家、老詩人重新煥發了青春,而更多的中、青年作家不斷湧現於文壇。柯尤慕·圖爾迪、祖爾東·薩比爾等在小說創作中已獲得令人喜悅的成就。對於古典文學遺產的整理、研究;對於中外名著的翻譯介紹,也都已重新蓬勃開展起來,這一切預示著當代維吾爾族文學正在一個更為堅實的基礎上向前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