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揚之水,不流束薪。 《王風·揚之水》
《王風·揚之水》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譯文
激揚之水,飄不動被捆束的薪柴。
 《王風·揚之水》
《王風·揚之水》留在家鄉的妻子呀,不來與我守申地。
我懷念你呀懷念你,何月才能來到我身邊。
激揚之水,飄不動被捆束的牡荊。
留在家鄉的妻子呀,不來與我守甫地。
我懷念你呀懷念你,何月才能來到我身邊。
激揚之水,飄不動被捆束的菖蒲。
留在家鄉的妻子呀,不來與我守許地。
我懷念你呀懷念你,何月才能來到我身邊。
注釋
1.束:《易·隨·上六》:“拘束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論語·述而》:“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莊子·秋水》:“曲士不可以語於吾道者,束於教也。”《荀子·勸學》:“強自取柱,柔自取束。”《玉篇·木部》:“束,約束。”《集韻·遇韻》:“束,約也。”這裡用為約束、限制之意。
2.薪:《周南·漢廣》:“翹翹錯薪。”《詩·小雅·無羊》:“以薪以蒸。”《周禮·委人》:“薪蒸材木。”《禮記·月令》:“收秩薪柴。”《禮記·曲禮》:“某有負薪之憂。”《管子·輕重甲》:“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說文》:“薪,蕘也。”這裡用為燒火的木柴之意。
 《王風·揚之水》
《王風·揚之水》3.曷:(he和)《易·損·辭》:“損,有孚,元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書·盤庚上》:“汝曷弗告朕。”孔傳:“曷,何也。”孔穎達疏:“曷何同音,故曷為何也。”《詩·召南·何彼襛矣》:“曷不肅雝?王姬之車。”《邶風·雄雉》:“道之雲遠,曷雲能來?”《王風·君子於役》:“君子於役,不知其期,曷至哉?”《詩•小雅•四月》:“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雲能穀?”《說文·曰部》:“曷,何也。”這裡用為代詞,相當於“何”,表示疑問之意。
4.楚:植物名。《詩·鄭風·揚之水》:“揚之水,不流束楚。”《秦風·黃鳥》:“交交黃鳥,止於楚。”《禮記·學記》:“夏楚二物。”《儀禮·鄉射禮》:“楚撲長如笴。”《說文》:“楚,叢木也。一名荊。”《漢書·漢延壽傳》:“民無箠楚之憂。”這裡用為牡荊之意。
5.蒲:植物名。《陳風·澤陂》:“有蒲與荷。”《詩·小雅·魚藻》:“魚在在藻,依於其蒲。”《周禮·澤虞》:“共其葦蒲之事。”《周禮·大宗伯》:“男執蒲璧。”《禮記·中庸》:“夫政也者,蒲盧也。”《說文》:“蒲,水草也。可以作席。”這裡指為植物菖蒲或是香蒲之意。
研究
這是一首將士久役思歸的抒情詩。此詩與《詩經》中的其他大多數抒情詩篇的不同之處在於:在抒情的同時為讀者提示了重要的歷史信息——戍守及其地點:申、甫、許。戍守與懷念因為“彼其之子”被聯繫在一起,構成文本的結構主體,貫穿全詩。那么,抒情主人公為何離家遠戍,不能與家人團聚?其戍守之地在當時社會有著何重要地位?本著這樣的疑問,在檢討歷代學者對此詩本事的探尋基礎上,補充相關的歷史敘述材料,進而確認此詩本事。
一、前人的詩本事研究:周衰時的被動防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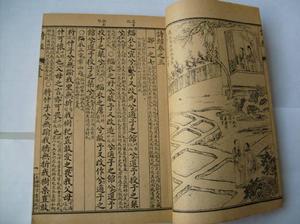 詩經
詩經對於《王風·揚之水》本事的討論,前人主要有兩種意見:第一種觀點認為:為抵禦楚國侵擾,周平王派兵戍守以申為主的南方各國。代表人物主要有鄭玄和崔述:鄭玄: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強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崔述《讀風偶識》:申與甫、許皆楚北出之沖,而申倚山據險,尤為要地。楚不得申,則不能以憑陵中原,侵擾畿甸。是以城濮還師,楚子入居於申;鄢陵救鄭,子反帥師過申。申之於楚,猶函谷之於秦也。宣王之世,荊楚漸強,故封中伯於中以塞其沖。平王之世,楚益強而漸弱,不能自固,故發王師以戍之耳。
第二種觀點認為:楚國在周桓王九年(公元前711年)時開始對周王朝構成威脅,於是,周王朝派兵戍守申等南方諸國。代表人物有季本。季本《詩說解頤》:今觀《采芑》詩,宣王時楚已強盛,但命方叔徂征而蠻荊來威,迄於平王楚猶未敢為患,直至桓王十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而始懼楚事。在《左傳》桓公二年,則此時楚始為患,而申與甫、許皆與鄧相鄰之國,且近於周,遣兵往戍,理宜有之。但不當為平王事耳。至謂申為平王母家而戍之,則尤臆說矣。《集傳》序申侯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之事,而責平王忘親釋怨之罪。此信舊說之過也。
第一種觀點是自《毛詩序》以來流傳最廣的觀點。大家爭論的焦點在於周平王出兵的動機。大多數經學家認為周平王出兵的主要原因是為了保護母家申國;並著力批評周平王不顧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殺幽王,並迫使周王室東遷的家仇國恨,而只考慮母家申國的安危。以崔述為代表的疑古派則認為,周平王戍守申國的主要原因是荊楚逐漸強大並威脅到了周王朝的安全。第二種觀點將周王可能戍守的時間認定為周桓王時期,主要理由是“此時楚始為患”,亦有一定的道理。
上面兩種觀點雖在具體戍守時間上有差異,但亦有相同之處,即:它們首先假定只有在周王朝衰弱、並且荊楚強大之後,周人才會出兵戍守申、甫、許等南方諸侯國;它們把主要的敵人預設為楚國。傳世文獻也支持這個假設。《今本竹書紀年》記載在周平王時期,周人戍申。但這種假設並不能排除周人在其強盛時期戍守這些國家的可能性。
二、詩本事新考:周人經營漢淮平原的進攻與防禦。
周人無疑是為防禦南夷而戍守申、甫、許。但對《王風·揚之水》本事的考證還應該考慮兩個問題:一是申、甫、許等國於哪一年始封於南方,成為周王朝的屏障,周人又是在什麼時期對其進行戍守的;二是申、甫、許等國在哪個時期衰亡。在此基礎上,再討論周人派兵戍守的問題。本文首先就第一個問題進行考察。
前人通過周代封國的溯源研究,為我們提供了這些諸侯國的姓氏、始封、遷移的歷史描述。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和楊伯峻的《春秋左傳注》,從周武王開始,周人便在南方分封諸侯。如周穆王時已有呂侯,宣王時封申叔於謝。但這種封國的溯源研究並不能明確說明這些諸侯國的始封與遷徙的具體地點,更不能以此說明周人對這些諸侯的戍守情況。
與傳世文獻不同,金文則對當時社會個別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有著詳細而確切的記載。根據金文中的記載,康王時期,申、甫、許等南方諸侯國已經出現在漢淮平原,還有周人戍守和巡省這些諸侯國的記載:關於甫國(即呂):班簋記載成王時期的毛公執掌江淮之間的鯀、蜀、巢諸國,周王令其率本族士兵平定東方,同時派呂伯與吳伯出城護衛毛公。因此,呂國於成王時就已出現在江淮之間。關於周人戍守申、甫和許國:與相關的十器記錄了周康王時期周人派兵巡省和戍守申、甫、許等南方諸國的具體情況。此銘文所提到四個專名詞:作器者、作器者的上司師雍父、作器者所使之國——甫、作器者及其上司所戍之地——古自,陳夢家先生將與此四名之一相聯繫的十器綜合起來研究,指出師雍父6月戍在許,並派遇使於甫(此銘中的“寘”即是“甫”)。在11月的時候,師雍父巡省道國,並至於甫。
綜上所述,在周成王時,呂已在周人平定江淮平原的戰役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康王時期,周王朝即派兵戍於許,並派“使”巡省道、申等南方各諸侯國。這些行動說明這些國家在軍事上能夠相互支持,遣使派兵往來十分便利。從地理上看,申、甫、道、許等國成品字陣地,互為犄角,在當時戰略要地管和成周洛陽的南方形成重要的防禦地帶。可以看出,它們從西周初年起就是周王朝在南方的重要軍事要塞。周王朝通過不斷地對這些諸侯國進行戍守、巡省和封賞,以強化這些南方諸國的軍事地位。傳世文獻與金文的記載可能只是其中的幾次,但這種不一致的記載正說明了周王朝持續派兵戍守的可能。
現在回答第二個問題。公元前770年,諸侯立平王於申,申侯和許文公都曾參與。因此,在東周初年,申和許是周王朝比較倚重的諸侯。這種情況說明此時申、許國力自然不弱。周王室雖然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但仍然為天下共主。因此,周平王也有能力會對這些南方諸侯國進行戍守。比如,《竹書紀年》記載在公元前735~前731年間,周平王鑑於楚國對申國的入侵,派兵戍申。但隨著東周與申、許等國的衰弱而其他諸侯國的強大,這種局面就被打破了。公元前712年,魯公、齊侯與鄭伯侵入許國。諸侯入侵許國意味著東周王室與申、許的關係徹底被瓦解。在齊楚爭勝的情況之下,周王室已經無力戍守這些國家。
關於周平王派兵戍守申國,抵禦楚國入侵的問題。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首先,楚國並不是周人長期戍守南方各諸侯的主要原因。周人派兵的出發點是與漢淮平原的異族爭奪資源。正是中原諸侯之間的爭鬥使楚國能夠逐漸強大,並向北擴張。其次,軍事進攻與戰略防禦並不矛盾。周人並不是只有在處於劣勢才開始戍守申等諸侯國,在其處於攻勢時,就不派兵戍守。周人與南方異族對資源的持續爭奪沒有取得絕對的勝利,這種長期的你爭我奪正是《揚之水》出現的主要原因。
 shij
shij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周人建國之初便控制了南方的若干重要據點,周成王時呂國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個。至少在周康王時,周人即派兵戍守申等南方諸侯國。相關傳世文獻和相關金文材料說明從周文王經營漢淮平原開始,周人就有可能在南方封建諸侯並派兵戍守。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東周初年,並不晚於公元前712年。這就是《王風·揚之水》創作的本事。
三、戍守與戰爭的深層原因:周人與南方族群對資源的爭奪。
但問題並沒有結束。眾所周知,在周幽王時期,周王想通過改變王位繼承人的手段削弱以申國為首的姜姓諸侯國,從而引起了姜姓諸侯國的不滿。他們聯合渭水的其他姜姓族群攻入宗周,迫使周平王遷都洛陽。那么,周人與申、許等南方諸侯國之間是什麼關係?為什麼必須不斷與其修好、不斷封賞與派兵戍素?而這樣的軍事行動又為何讓周人如此難以釋懷?除了防禦南夷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更為重要的原因?周人與南方異族對資源的爭奪正是回答這些問題的關鍵。
西周時期是中國青銅時代的重要發展階段,此期青銅器數量之大,遠遠超過前代。現代科學史研究表明,商周中原、長江中下游和巴蜀地區的青銅器所使用的礦料都屬於同一來源。考古資料表明,周人與南夷的戰爭與當地盛產銅礦有關。申、呂的東方和南方,楚國的東方,淮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的兩岸,皆有銅礦采冶遺址留存。這些地區的銅礦開採從西周一直持續到漢代。從西周初年開始,周王朝為了保障國內對銅的需求,不斷征討南夷,向其索要貢賦。1974年在陝西武功出土的駒父簋蓋,生動地說明了周宣王向南夷索取貢賦的情形。
據記載,周王十八年正月,“南仲邦父命駒父簋南諸侯率高父,見南淮夷”,淮上大小族群無敢不奉王命,“不敢不敬畏王命”,“厥獻厥服”。從西周建國到西周晚期,為了保障銅礦的充足供應,周人必然會與南方異族發生爭鬥。與此同時,周人也必須派兵戍守申等南方諸侯國。
從建國之初至東周初年(不晚於公元前712年),周人為了爭奪資源,與南方異族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在這個過程中,周人不斷向南方派兵與其發生戰爭,並對軍事要塞進行戍守。申、甫、許等諸侯國與南方異族的鄰近,是周王朝爭奪銅礦的前沿戰略據點。對申、甫、許等軍事要地的長年戍守只是周人向南的軍事行動之中很小的一部分。上述這一時段的軍事行動也催生了《王風·揚之水》這樣的動人而哀怨的詩歌。當然,對此詩創作年代的進一步推定還需要結合辭彙、體裁、禮制、音樂等制約條件進行綜合考察,限於篇幅與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此暫時只將《王風·揚之水》繫於上述這一段時間之內。
鑑賞
朱熹曰:“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
范處義曰:“楚輕於薪,蒲輕於楚,以喻王益微弱,不特不能令大國,亦不能令小國矣。申,平王之母申後之家,在陳、鄭之南,迫切於楚,故戍守之也。”“甫也,許也,與申同為姜氏,亦平王之母黨也。‘彼其之子’,指諸侯而言,謂當戍而不往者。”王應麟引《大雅·崧高》“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曰“申、甫之地,為形勢控扼之要”。又引《左傳·成公七年》楚子請申、呂以為賞田事,曰“楚得申、呂而始強,茲所以為周室之屏翰歟”。按甫即呂。又,蒲,毛傳曰“草也”,鄭箋則曰蒲為蒲柳。當以毛說為是。“不流束蒲”,是極言其微也。又“束薪”云云,《詩》多用來擬喻婚姻,而婚姻也常常是政治力量的結緣,用在“揚之水”之喻中似乎也有這樣的含義。
可以引來與這一首詩作對比的,有《秦風·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於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此詩很能夠代表秦地風氣。班固講漢事,猶引《無衣》,曰“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許謙說此詩云:“平居暇日,情意之孚,恩愛之接,固已彼此交得歡心,一旦同在戰陣,晝識面貌,夜記聲音,而左提右挈,協心力戰,可以揚威而制勝,不幸而敗,亦爭取為死,此王者之兵所以無敵也。”《無衣》固奉王命而出征,但彼時秦乃將興將盛之邦,本當有如此義勇之氣,若《王風·揚之水》,則是一個國事日壞的局面,雖王命,而無力已如“揚之水”。
 詩經鑑賞
詩經鑑賞詩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此說大抵可據。姜炳璋曰:“申、許為中國門戶,楚不得申、許,北方未可窺也。今用重兵扼之,未始非東遷後之要務,然申於晉、鄭諸國為近,而於周差遠,平王既不能正申侯之罪,號令四方,復遣京旅遠戍仇國,只覺侯國之民安堵如故,而王畿之民奔走不逞,更代無期,歸期莫卜,戍者所以怨也。”戍申、戍甫、戍許,本是固邊之策,或曰王畿之民不當遠戍,也不是沒有道理,但怨聲之出,關鍵似乎仍不在此,是國人對國事失望,對國君失掉信心,乃所以有從軍之怨也。秉國者失去國人的信任,又如何可以號令天下。故也可以說,有《揚之水》之怨,而王室不能不微了。
“揚之水,不流束薪”,比也。歐陽修以為:“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於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國人遠戍,久而不得代爾。”鄧翔曰:“王者下令如流水之源,所以裕其源者,蓋有道矣,故勢盛而無所不屆。今悠揚之水至不能流束薪,何足以用其民哉。”如此解釋,不惟說此詩通,用以說同題的《鄭風》和《唐風》,也大抵合於詩意,即它是用來擬喻勢力微弱。至於“揚之水”之揚,曰“激揚”,曰“悠揚”,似乎都不錯,但是就詩意而推敲,則仍以“悠揚”之釋為切。
當然這裡很可能還有音調相同的一面。劉玉汝曰:“《詩》有《揚之水》,凡三篇。其辭雖有同異,而皆以此起詞。竊意詩為樂篇章,《國風》用其詩之篇名,亦必用其樂之音調,而乃一其篇名者,所以標其篇名音調之同,使歌是篇者即知其為此音調也。後來歷代樂府,其詞事不同,而猶有用舊篇名或亦用其首句者,雖或悉改,而亦必曰即某代之某曲也。其所以然者,欲原篇章之目以明音調之一也。”“以此而推,則《詩》之《揚之水》其篇名既同,豈非音調之亦同乎。”
藝術
“王風”是東周王國境內的歌謠。公元前771年,西周西北部的犬戎(古族名,戰國以後稱為匈奴)殺死周幽王(姬宮理),滅了西周。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姬宜臼)東遷洛邑(在今河南洛陽市洛水北岸),史稱東周,疆域在今洛陽市一帶。東周雖已不能統轄諸侯,但名義上還是中國的王。故其境內之歌謠稱為“王風”。
從本詩表層語意上看,《揚之水》是一首戍卒思婦的情詩,表達了不堪征戰、戍邊之苦的戰士對妻子的刻骨相思。從深層意蘊上看,它又是一首政治抒情詩,蘊涵著人民對連年征伐、不得和平安定生活的怨恨。
詩的第一章開頭兩句說:大河流水盪悠悠,難載束薪我心愁。揚:形容水流激盪的樣子。朱熹曰:“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束薪:成捆的荊條。在詩經中,束薪多比喻牢固的夫妻關係,後引申指婚姻。聞一多《詩經通義》“邶風”條中說:“析薪、束薪,蓋上古婚禮中實有之儀式,非泛泛舉譬也。”當代著名的《詩經》研究專家蔣立甫先生則認為:“風詩中‘薪’常連及男女婚事,如《漢廣》:‘翹翹錯薪’;《南山》:‘析薪如之何’;《東山》:‘烝在栗薪’等。這大約與當時婚禮的風俗習慣有關。下二章‘束芻’、‘束楚’同此。”據說,過去有的地方,嫁娶的時候,男家把柴用紅絨纏繞著送到女家;女家則把炭用紅絨纏繞著回贈男家。先秦時代,民間男女合婚時,男家送到女家的聘禮,除羔、雁之外,定有薪柴之類的象徵物品。漢代婚禮中,用蒲、葦、卷柏、女貞等。卷柏、女貞固然屬於“薪”類,無可懷疑;蒲、葦亦歸於先秦時代的“薪”的範疇,故《王風·揚之水》首章雲“揚之水,不流束薪”,次章則言“揚之水,不流束楚”,而末章說“揚之水,不流束蒲”,以“薪”、“楚”和“蒲”對舉,可見它們都可以稱為薪類。以蒲與葦為聘禮,是取其滋生快速且多的特點,以喻子孫繁衍,家道昌盛;蒲、葦二物堅韌耐久,以祝願夫妻二人白頭到老,永不分離。在這個意義上講,詩歌開篇用“束薪”這一意象表達了愛的忠貞。若從社會學角度看,這兩句又有另外的闡釋,恰如歐陽修所認為的,“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於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國人遠戍,久而不得代爾”,這兩句是委婉地表明:周天子政令煩急,王畿之民疲於奔命;君王不能流惠於民,國人怨聲載道,這是對周的衰政的指斥。
 《王風·揚之水》
《王風·揚之水》接下來的兩句直抒胸臆:可憐家中的妻子,不能相聚在邊關。“彼其之子”,即那個人,指妻子;“申”,地名;“不與我戍申”,就是說不能和我一起在邊關。鄭玄《毛詩正義》曰:“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強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竹書紀年》載有周平王三十三年(前七三八)“楚人侵申”和三十六年“王人戍申”的事。周平王母家申國鄰楚,數被侵伐,因遣戍守申,使人民家室離散,國人作詩諷之。這兩句是從戍卒的心理角度來寫。
尾二句說:懷念妻子情綿綿,何日才能聚相守!反覆疊用“懷哉”一詞,極言思念之切,憂痛之深。結句用“曷……哉”的設問句式表達了戍卒內心的怨懟。
詩的二、三兩章只變換了4個字:“楚”、“甫”、“蒲”、“許”。這是重章疊唱手法的運用,反覆渲染“我”的惆悵與傷感。“甫”、“許”與“申”一樣都是地名,甫、許,與申,同為姜氏,是平王之母黨。戍申、戍甫、戍許,是固邊之策,本是侯國之責,王畿之民不當遠戍,而周天子國勢日頹,號令四方已捉襟見肘,此種情形下,王畿之民奔走戍邊,更代無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束楚”、“束蒲”與“束薪”一樣都是代指荊條,鄭箋則曰蒲為蒲柳。另外一種觀點,蒲是一種草,如,毛傳曰:“蒲,草也”。《詩經》的重章疊句,大都並非簡單重複,而是在語意上有遞進或加深。從“不流束薪”至“不流束蒲”,其實是暗示了周天子國勢的式微。范處義《詩補傳》曰:“楚輕於薪,蒲輕於楚,以喻王益微弱,不特不能令大國,亦不能令小國矣。”這是一種政治學的解讀。“束薪”、“束楚”、“束蒲”等植物,在《詩經》多用來擬喻婚姻,而婚姻也常常是政治力量的結緣。
“懷哉懷哉,曷月乎還歸哉”一句反覆出現三次,既有戍卒對家人的焦灼相思,又有不能及早與家人團聚的怨憤。
此詩三章句式完全相同,每章都在同一個地方換用兩個韻,結構整齊,音韻和諧,節奏緩慢,適合抒發憂鬱、沉重的心情,以水喻愁緒,每章的一、三句與尾二句的句式完全相同,能收到一唱三嘆的效果,將戍卒的念妻盼歸之情表達得更深厚更強烈。
《詩經》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詩”,有目無辭,不計在內),所以又稱《詩三百》。匯集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詩歌總集,與《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合稱為五經。古者《詩》三百餘篇,及於孔子,去其重……”(《史記·孔子世家》),據傳為孔子編定。《“最初稱《詩》,被漢代儒者奉為經典,乃稱《詩經》,也稱《詩三百》。他開創了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的優秀傳統。《詩經》里的內容,就其原來性質而言,是歌曲的歌詞。《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意謂《詩》三百餘篇,均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些說法雖或尚可探究,但《詩經》在古代與音樂和舞蹈關係密切,是無疑的。
 詩經
詩經《詩經》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十分豐富,它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經濟,祭祀典禮,戰爭徭役,定都建國,燕饗歡聚,狩獵耕耘,採摘漁牧,君王貴族,將軍大夫,君子淑女,農夫商賈,思婦棄婦,遊子隱逸,初戀思慕,閨怨春情,幽期密會,洞房花燭,迎親送葬,懷人悼亡,草木魚蟲,飛禽走獸,鶯啼馬鳴,風蕭雨晦,波光山影,火山地震,祈禱祝願,占卦圓夢等等,其信息量之大,文獻價值之高,令人驚嘆。可以說,一部《詩經》立體地再現了生存環境、事態人情,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反映,其內容在世界古代詩歌作品中是獨一無二的,遠比印度的《吠陀》與基督教《聖經》中的詩篇要廣泛得多。它的主題已不限於宗教性的,或僅僅表達一種虔誠的感情,它也不像荷馬史詩只談論戰爭與冒險,它歌唱的是人的生活,人的感情,用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詩說:“卑俗的山歌俚曲,現今日常熟悉的事情,天然的悲苦和傷逝,過去有過,以後還會有。”(選自《孤獨的割麥女》)在如此自然,如此樸素,如此親切地表現普通人民的心聲和感情方面,很少有別的詩集堪與《詩經》相提並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