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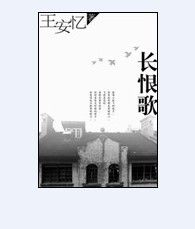 長恨歌
長恨歌一個女人四十年的情與愛,被一枝細膩而絢爛的筆寫得哀婉動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還是中學生的王琦瑤被選為“上海小姐”,從此開始命運多舛的一生。做了李主任的“金絲雀”從少女變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李主任遇難,王琦瑤成了普通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內心的情感潮水卻從未平息。與幾個男人的複雜關係,想來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瑤難逃劫數,女兒同學的男朋友為了金錢,把王琦瑤殺死,使其命喪黃泉。
作者簡介
 王安憶
王安憶王安憶,1954年3月生於南京,次年隨母親茹志鵑遷至上海讀國小,國中畢業後1970年赴安徽淮北農村插隊,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工作,1978年回上海,任《兒童時代》編輯。1978年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平原上》,1986年應邀訪美。1987年進上海作家協會專業創作至今。現為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
王安憶的主要著作有:《雨,沙沙沙》、《王安憶中短篇小說集》、《流逝》、《小鮑莊》、《小城之戀》、《錦銹谷之戀》、《米妮》等小說集,及長篇小說《69屆國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紀實和虛構》、《長恨歌》、《富萍》、《上種紅菱下種藕》、《桃之夭夭》、《遍地梟雄》等,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遊美利堅》(與茹志鵑合著)等,兒童文學作品集《黑黑白白》等,論著《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等。
王安憶多次獲得全國優秀短篇、中篇小說獎,《長恨歌》獲得了“第五屆茅盾文學獎”。1998年並獲得首屆當代中國女性創作獎。2001年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最傑出的華文作家”稱號等。
作品評論
王安憶長篇小說《長恨歌》的題名顯然襲自白居易與陳鴻撰《長恨歌傳》。未諳王著《長恨歌》者,有可能誤會它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李楊愛情故事現代詮釋版。事實上,王著《長恨歌》敘述了一個現代中國大都市中女性個體生命——海上淑媛王琦瑤的生存和死亡傳奇,傳達了作者對現世個體生命意義的感覺。我無法斷言,王著能否像白樂天之長恨歌“歷千歲之久至於今日,仍熟誦於赤縣神州及雞林海外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陳寅恪語)。我只知道,王著《長恨歌》的出版,說是“洛陽紙貴”未免誇張,說是“好評如潮”大概不虛,無論如何,得了以弘揚主鏇律為宗旨的茅盾文學獎總是事實。
《長恨歌》稱得上是女性主義(有別於女權主義)小說的範本。上海的弄堂世界在作者的筆下成了女性世界,幾乎所有的男性都被放逐了。王琦瑤的父親是男人,被作者放逐到虛無之中,連露面的機會都沒有,更談不上對女兒的人生提供看法了。蔣麗莉的父親是男人,被作者放逐到內地辦廠,騰出空間讓王琦瑤在蔣家作張作致。與王琦瑤同住一條弄堂的熟客——嚴師母,她家先生是男人,“一爿燈泡廠的廠主,公私合營後做副廠長”,被作者放逐到上下班的自備車裡,鄰人多年來連他的面目都沒看真切過。上海的多數男人固然和女人一樣離不開弄堂世界,但他們更離不開弄堂外面的世界,他們必須在後一個世界裡為自己、也為妻子兒女的衣食奔波,說不定還會對時局發表一點看法,因此,男人命中注定是屬於歷史時間的,不得不被逐出作者筆下的弄堂世界。剩下為數不多的有資格在王琦瑤裙邊廝磨時光的男人,如程先生、康明遜、薩沙、老克臘、長腳、她女兒薇薇的男朋友,全都女性化了。只有李主任是個例外,他是偶然到這個女性弄堂世界來客串的票友,因為捨不得離棄弄堂外面的權勢世界,一場空難成了他最好的結局。小說作者借王琦瑤外婆的嘴說出做女人的種種好處:“外婆喜歡女人的美,那是什麼樣的花都比不上,有時看著鏡子裡的自己,心裡不由想:她投胎真是投得好,投得個女人身。外婆還喜歡女人的幽靜,不必像男人,鬧轟轟地闖世界,闖得個刀槍相向,你死我活。男人肩上的擔子太沉,又是家又是業,弄得不好,便是家敗業敗,真是鋼絲繩上走路,又艱又險。女人是無事一身輕,隨著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便成了。外婆又喜歡女人的生兒育女,那苦和痛都是一時,身上掉下的血肉,卻是心連心的親,做男人的哪裡會懂得?”
女人的自然人生與男人的歷史時間的唯一聯結是婚姻,這是具有法律軀殼的男女關係,這軀殼本身是屬於歷史時間的。嚴家師母說:“你曉得我最擁護共產黨是哪一條?”“那就是共產黨不讓討小老婆。”共產黨是屬於歷史時間的 ,“不許討小老婆”也是屬於歷史時間的。婚姻是恩和義,“恩和義就是受苦受罪,情和愛才是快活;恩和義是共患難的,情和愛是同享福的。”恩和義是屬於歷史的,情和愛是屬於自然的。於是王琦瑤和康明遜的關係,只剩下了近於肉慾的情和愛。“夫妻名分說到底是為了別人,他們卻都是為自己。他們愛的是自己,怨的是自己,別人是插不進嘴去的。是真正的兩個人的世界,小雖小了些,孤單是孤單了些,可卻是自由。愛是自由,怨是自由,別人主宰不了。這也是大有大的好處,小有小的好處。大固然周轉得開,但難免摻進旁務和雜念,會產生假象,不如小來得純和真。”程先生在王琦瑤有媽無爹的女兒出生前後付出的恩和義,因為沒有婚姻做面子,也沒有愛情做芯子,未免有些不尷不尬,以至終於恩斷義絕。但程先生究竟是這女人世界的一員,這恩斷有點像抽刀斷水,這義絕也有點像不絕如縷。
作品對比
 《長恨歌》
《長恨歌》1995年,上海女作家王安憶的長篇小說《長恨歌》,榮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受到廣泛讚譽:“一部堪稱近年來罕見的作品:一個女人四十年的情與愛,被一枝細膩而絢爛的筆寫得哀婉動人,跌宕起伏。” 《長恨歌》問世10年,先是被改編成話劇,這個話劇還先後改版三次;稍後,再改編成為電影;最後,再不屈不撓地改編成35集電視劇。
電影《長恨歌》是關錦鵬導演所拍攝的,關錦鵬是華語影壇極具女性氣質的導演之一,也是最為關注女性命運的導演之一。《長恨歌》在關錦鵬的鏡頭下則顯得異常的唯美。在對生活細節的描繪中,以光影的形式表達了對社會人的本性慾望和情感選擇的思考。但關錦鵬的鏡頭下的《長恨歌》非王安憶的筆下的《長恨歌》,關錦鵬幾乎把《長恨歌》打成了一盤散沙,再在這片廢墟上重建關氏風格的《長恨歌》。
小說是這樣開頭的:“站一個制高點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它是這城市背景一樣的東西。”用大量的篇幅介紹了上海的弄堂的各種情趣。而在電影版里的《長恨歌》不見了上海弄堂,只見侷促的室內,貼面舞般人頭攢動,一頭扎進人堆里就再也爬不出來。
王安憶那細緻的,帶有女性特點的觀察被關錦鵬的男性氣質所淹沒。《長恨歌》中故事開始之前大段大段的描寫,弄堂,流言,閨閣,鴿子,沒有耐心的人恐怕是會跳過去的。可其實呢,這也是王安憶才氣的流露,小說前面對弄堂、流言、閨閣、及鴿子的描寫只有女性才有那么細緻的心。
王安憶對《長恨歌》中精緻描寫的還有服裝。也表現出了女性特有的心思。王琦瑤學生時代的旗袍不考究面料,比較松垮,色系都很清淡,符合弄堂里女學生的身份,旗袍的長度大都比較短,突出了少女的青春與清純。做了李主任的金絲雀後,王琦瑤的旗袍開始考究質地了,明顯和學生時代的不同,長度變長,剪裁更合身,顏色變濃,彰顯的是女人的嫵媚。後來還教女兒的朋友張永紅怎么進行服飾搭配、選擇布料等。而電影中有關服飾的鏡頭可謂少之有少。女性對生活中瑣事不厭其煩的敘述,在關錦鵬的策劃下也消失的無影無蹤。
蔣麗莉不管在小說還是電影中都是比較重要的人物,但她去有著不同的命運,在王安憶的原著中,蔣麗莉是談不上美的,她戴著厚厚的瓶底眼鏡,胖胖的臉,性格內向甚至有些古怪,她的出現是為了王琦瑤,使得王顯得更加優秀。這也是很多的作者都喜歡套用的烘雲托月的手法。最後因病死於上海。但也許是關錦鵬一向喜歡唯美的風格,為了讓片中的角色都給人一種舒服的感覺,他對蔣麗莉這個人物作了較大改動。改動後的蔣麗莉外形也很清秀,在教會學校上學,家教好,很有修養,言談舉止是典型的大家閨秀的做派卻讓蔣麗莉在台北與人間永別。可以說,是關錦鵬對蔣麗莉一角的大手術,讓角色鮮活可愛了起來。
程仕路是最早邂逅王琦瑤的人,一生以朋友的身份深愛著、照顧著王琦瑤。梁家輝在片中充滿著一種寂寥.無奈、冷靜的氣質,把自己隱忍、欲罷不能的感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影片結尾時,他對著王琦瑤的屍體老淚縱橫的一幕,是影片最為動人的瞬間,其中閃耀著關錦鵬影像的光芒。小說沒有寫程仕路看到王琦瑤的屍體的情形,王安憶沒有寫可能是想給讀者留想像的空間,起到一種無聲勝有聲的效果吧。我們也是可能說,這與女性有著在豐富的想像力是分不開的。
在電影中,較強地突出了時代的特徵,其中也有很多的政治內容。電影中李主任離開上海時的緊張局勢,及其鬥爭。還有在知青上山下鄉時期,程先生也是到了鄉間參加體力勞動。在廣播之中不時的出現具有時代特徵的新聞:“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世界是我們的世界……。”小說與電影相比,政治性是很弱的,李主任離開上海只是輕描淡寫的帶過原因,小說關注的只是王琦瑤的感情波折。而電影,是兼顧了時代與社會大背景的。這也許是與女性對社會政治不太感興趣的原因的吧。在政治上,可以說女性是相對要遲鈍的,這主要與大多數的女性性格軟弱有關,但也不排除有少數的女強人。
總得說來,當王安憶的《長恨歌》被濃縮成關錦鵬的“短歌行”,原著中大段大段的環境描寫被代之以富有時代氣息的歌曲來提示歲月的變遷,從舊上海的靡靡之音到革命歌曲,缺少足夠的戲劇衝突。電影《長恨歌》不能令人滿意地方也在於敘事表達手法和人物入戲出戲上顯得非常突兀,跳躍性很強,程仕路在公寓見面時還需要相互引見,李忠德出事後,程仕路成了唯一到秘密住所探望的人,期間因由沒有任何的鋪墊;康明遜與王琦瑤在醫院第一次見面的鏡頭過後,進入觀眾眼瞼的已是兩人熱烈的親吻……。我之所以能看懂電影,主要是因為,我看了小說,我相信沒有看過小說人的,第一次看《長恨歌》電影,肯定是有些找不著北的。小說中王琦瑤機警的對白,謹慎的動作,或許是堅強果敢、敢愛敢恨的她給了我很深的印象。而正是對小說中王琦瑤的喜歡,才導致我對電影中的王琦瑤的失望。
作者小說的“常”與“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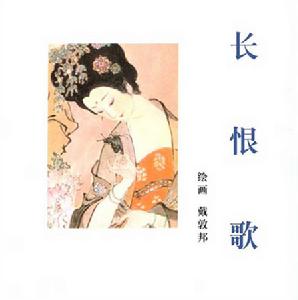 長恨歌
長恨歌一
王安憶在二000年接受《收穫》編輯鍾紅明採訪時說:“寫作資源就意味著生存札記。寫作中材料的緊張緊缺對我真是一個問題。我個人經歷比較簡單,生活環境比較簡單,個人也比較喜歡安靜的生活,不喜歡變動的生活,所以我始終感到我的磚頭很少。”[1]縱觀王安憶的生活經歷,主要由學生、知青、文工團員、編輯、作家等五種社會角色相續構成。王安憶將這生活饋贈的“磚頭”分別寫進《69屆國中生》《本次列車終點》《小鮑莊》《舞台小世界》《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叔叔的故事》等文本中,由此可見王安憶是一位很善於從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發現創作材料,並以藝術的眼光發掘其底蘊,抉微勾沉,使其纖毫畢現的作家。
二
縱觀王安憶二十多年的創作,其作品有三個顯著的特徵:即歷史的真實、生活的真實、人性的真實,而我們如果挖掘其隱含的創作心態,則可以找到作家的兩種情結:“鄉土情結”和“舞台情結”,我將這“三個真實”和“兩種情結”看作王安憶小說的“常量”。
王安憶的小說歷史底蘊深厚,她不像上世紀80年代後期“新歷史主義”粗野而陰冷地敘說任何人都無法考證的歷史,王安憶的歷史敘說(解放前的上海、知青時代、文革)返歸我們一個真實的歷史文本,既沒有意識形態束縛下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又不效仿消解“紅色經典”後的世俗化與粗鄙化,她的小說在歷史背景映襯下凸顯著人性溫馨的閃光,讓讀者在樸素、溫暖和豁達中從容地見證歷史的年輪,當然,王安憶小說歷史的真實離不開對風俗、民情、地域細緻而精當的描繪,無論是實指的上海的蘇州河、弄堂、租界、洋房,還是虛指的大劉莊、小鮑莊,王安憶都將其丰韻神貌刻畫得栩栩如聲,頗有歷史深度。
生活的真實是指王安憶小說中生活體驗和內心世界的真實,王安憶認為“小說是以和日常生活極其相似的面目表現出來的另外一種日常生活”,[2]當然,這種理想化精神化的“日常生活”與我們真實經歷的日常生活是有區別的,但王安憶注重兩者間的相似與橋樑作用,其創作風格表現在情節和語言都非常日常生活化,敘述冷靜,注重細節,不關注浮光掠影的喧囂泡沫,而是將目光聚焦在扎紮實實,非常瑣細的日常人生上,這種創作一方面導致了王安憶小說情節的緩慢與瑣細,另一方面這種關注生活本身不誇大不偽飾不拔高的創作讓讀者讀來親切感人,從中能悟出生活本身的甜鹹苦辣複雜滋味。
人性的真實是王安憶小說中最為本質的真實,無論哪一部作品,王安憶都是憑藉其飽滿淋漓的人性徵服著讀者,這突出表現在王安憶對內心活動細緻入微地刻畫和對道德“合適性”的妥當處理。
擅長內心刻畫是王安憶的顯著特色,在《逃之夭夭》中有一段關於十五六歲男孩郁子涵單戀滑稽戲演員笑明明微妙心理的描寫,煞是精彩:
第二次看見他,他站在了院子裡,與他小妹妹玩挑繃的遊戲,就是用根線繩,兩頭系個結,兩手撐開,和對方互相挑,挑出花樣,卻不能亂和散。這是小姑娘的玩意兒,可這少年,穿了洗白的毛藍布長衫,藏在梨樹的花影里,真像一個秀美的姑娘。回眸間,看見笑明明,無端地紅了臉。笑明明不由心裡又是一陣好笑。第三次,笑明明就與他說話了,問他要不要看戲,她可以帶他進戲院。他兩手在身後交疊,靠在門框上,羞紅了臉。
本是日夜都想靠近自己喜歡的女孩,但在現實中卻處處退縮,這種“以退為進”的敘說主要通過動作、神態表現出來,真切細膩地再現了少年羞澀懵懂而又無一絲瑕疵的初戀。諸如此類浸潤著生活汁液的妙筆在王安憶作品中比比皆是,讀者在她溫馨的充滿人情味的敘說中很容易產生共鳴,悟出生活的哲理。
王安憶的小說與當今時尚的“女性寫作”“身體寫作”“美女寫作”是相迥異的,這凸顯在王安憶對道德“適當性”的妥當處理上。按西方新人文主義白璧德的觀點:文學藝術要力圖使基於莊重人性的道德觀念與審美的藝術感覺結合,文學作品的真正價值在於它所表現的道德方面的“適當性”。王安憶的小說很符合這個理念,即王安憶在創作中考慮到小說的社會效果,兼顧社會道德與作家責任:小說應該使讀者的精神境界有所提高,使人想活得高尚一點,這就是為什麼郁曉秋雖然生活在社會底層,歷經歲月洗禮而並不走向“墮落”(儘管文中多處介紹“貓眼”、“工場間西施”、她母親的傳奇梨園經歷、自己曖昧的身世)?這就是為什麼同樣是描寫“性”的題材,王安憶的“三戀”能折射出晶瑩的人性關愛光芒,其超越生理欲望後留下的審美空間與衛慧、綿綿那種僅滿足讀者純感官的生理刺激的文本是何等的涇渭分明!
王安憶的三個真實是其風格外化的重要表現,而隱含之中的兩種情結也是不容忽視的。
十六歲時,王安憶到安徽五河插隊落,儘管王安憶聲稱:“我始終不能適應農村,不能和農村水乳交融,心境總是很抑鬱。”[3]但縱觀王安憶的作品,無論是《大劉莊》《崗上的世紀》《小鮑莊》“三戀”等鄉村題材的小說,還是《叔叔的故事》《逃之夭夭》《我愛比爾》等城市題材的文本,都有著對鄉土揮之不去的追憶,王安憶的鄉村生活經驗只有兩年半,但它對王安憶的創作卻產生了非同尋常的影響,王安憶一再地在她的文學境界裡重溫她的鄉村生活的經驗與感受,對自己短暫的鄉村經歷進行分析、體驗、回味,她說:“現代化的都市生活太制度化與格式化,人變得概念而抽象,而農村的生活是感性的,更富有人性,更具審美的性質,就這么簡單,是農村影響了我的審美方式。”[4]正因為對土地的親近和對鄉村生活的悉心體悟,王安憶寫出大量被泥土滋潤得壯實飽滿的文字,這就是王安憶的“鄉土情結”。
與在農村待了兩年半相比,王安憶認為:“六年大提琴手生涯對我的影響更大。”[5]這在王安憶的創作中突出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王安憶的作品中有相當部分以此為題材,如中短篇《文工團》《舞台小世界》等,長篇小說《富萍》《逃之夭夭》中均有相當篇幅介紹與舞台演出有關的劇場、戲院、劇種、演員觀眾等;另一方面是王安憶小說中的人物塑造往往以“舞台”意象為借鑑,即她喜歡將人物設定在一個生活的舞台上,操縱著四周的光、影、背景來造型,由此烘托出人物的細膩心理變化,如《逃之夭夭》中郁曉秋在外界流言蜚語中孤獨徘徊的一段:
……她在浴室里,將水管當扶把,練功,鏇轉,大跳,地磚長久乾涸,很粗糙,磨著鞋底。她跳累了,就停下,不多會兒卻覺著冷,站起來再跳。這裡,白天也需開燈的,但從浴室高處的氣窗上,看得出天色轉暗,最後變成漆黑,甚至還可看見一顆寒星。
這是一個典型的用舞台造型(包括動作、背景、光影)來傳達人物心理變化的例子,類似的表達在王安憶小說中屢見不鮮,除了人物塑造外,王安憶在場景描寫、情節發展中也往往借鑑舞台的布局與烘托效果,營構出精巧的藝術世界。這就是王安憶小說中的“舞台情結”。
三
文學藝術作為意識形態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的變化時代的變化決定了作家創作題材、手法的諸多變化。王安憶在時代的潮流中總是不斷超越,不斷否定,她不願意自己局限在某一種敘事方式、某一種小說模式、某一種特定題材的範圍之內,她是一個在變動中超越自身的作家。王安憶小說中的“變數”突出表現在兩方面:語言的變化;敘述方式的變化。
王安憶早期作品中的語言往往很簡約,這在《流逝》《本次列車終點》中表現得很鮮明,這和上世紀80年代初處於時代共名狀態下的文學注重較為單一的教化功能是一致的,那個時期的作品往往意識形態色彩較濃,情節和人物塑造都較為傳統。到了上世紀90年代後,時代進入比較穩定、開放、多元的社會時期,人們的精神生活日益變得豐富,王安憶小說的語言也變得豐繁起來,這適應著時代價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發展趨勢,人們可以從不同的層面來理解王安憶的作品,其文本的多重闡釋性提供讀者多樣的審美空間。
在敘述方式上,王安憶也從平面走向立體,王安憶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和情節發展都較為平直,雖有波折起伏,但大多屬於單線條的流浪漢結構。到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小鮑莊》《叔叔的故事》開始,王安憶採用多重線條,多種講述故事的“複合”方式進行創作,這種敘述雖然增加了讀者閱讀的難度,但大大加強了文本的深度與多重闡釋的可能。
詩歌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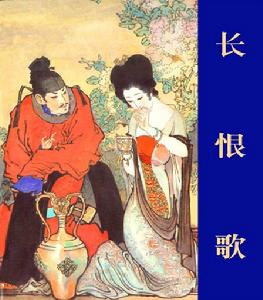 長恨歌
長恨歌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
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
天鏇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
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
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為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
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
聞到漢家天子使,九華帳里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回,珠箔銀屏邐迤開。
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搖舉,猶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淚闌乾,梨花一枝春帶雨。
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里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
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唯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電影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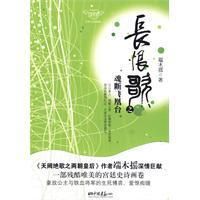 長恨歌
長恨歌由關錦鵬執導鄭秀文、梁家輝、胡軍、吳彥祖主演的《長恨歌》正式入選威尼斯電影節。關錦鵬導演屆時將率領大隊出席電影節。
《長恨歌》改編自王安憶同名獲獎小說,描述傳奇女子王琦瑤從璀璨走向平淡的一生,見證上海四七至八一年種種變遷,締造了人與城市一脈相連的神話。揮不掉上海情意結的關錦鵬與張叔平,在鄭秀文身上看到他們的下一個女神。
劇情:
王琦瑤這一飛,竟然鳥瞰了上海這座城市如何被時間洗刷的過程。
1948年,掌握軍政大權的李主任義無返顧地以愛囚禁了她,使她遊走過充斥著靡靡之音的百樂門舞廳,陪伴李主任出入於槍林彈雨,而她亦心甘情願地以他為終身伴侶。她樂意相信這第一個男人會是最後一個男人!李主任為什麼再沒有出現,王琦瑤只知道他生死未卜,這種事在那段日子的上海不是不經常發生的!
1956年,王琦瑤蛻了層皮,過著小戶人家的生活。她回響那個時代人人節約的意識形態,甚至精神上也只限於跟已婚的程先生作適可而止的交往。這段風平浪靜不久被富家子康明遜攪亂了。
康明遜在她眼中就是缺乏了那么一點軒昂、一點氣概,到王琦瑤心甘情願跟他過一輩子,他卻要跟家裡去香港繼續做他們的生意了。
王琦瑤懷著孩子繼續留在上海,她拿著積蓄換了一段名正言順的婚姻,跟一個身患絕症的人辦了結婚手續,這事情只有程先生明白她是為了要挽回自尊。
1970年,王琦瑤最渴望與離了婚的程先生邁進一步,是在文革期間,她無聲地感激他多年不渝的等待,只是程先生因應社會的風向,要去雲南一個小鎮支援邊疆。二人不知不覺已走過了漫長的日子,這次暫別總應是轉眼便又重逢。
這一別卻是十年,十年過後,王琦瑤再遇程先生,程先生介紹了一位跟琦瑤女兒年齡相仿的男孩,老克臘。
程先生沒想過,王琦瑤居然會因為老克臘的衝動之情而陷入一段矚目驚心的忘年戀……
王琦瑤孤注一擲地愛老克臘,甚至顧不上這個男孩到底是迷惑於自己身上殘餘的舊日上海風情,還是有不可測知的理由。王琦瑤猛然崩潰的剎那,是這個八十年代的年青人跟她說要出國了,原來沒有人象她那么堅守上海城市,這個成就了她一生的城市……
以民國為背景的小說
| 民國是一個很傳奇的年代,不僅出傳奇的事,更多傳奇的人,當前許多熱播劇都是以民國為背景。大家都來聊聊都有哪些以民國為背景的小說,哪些比較好看——不論是名家的還是當前流行的網路小說,請各位把小說的大概內容、主要人物關係、看點等所有東西都列出來。 |
茅盾文學獎歷屆獲獎作品
| 第一屆(1982年 六部長篇小說) |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周克芹 | 《東方》 魏巍 | 《李自成》(第二卷) 姚雪垠 | 《將軍吟》 莫應豐 | 《冬天裡的春天》 李國文 | 《芙蓉鎮》 古華 |
| 第二屆(1985年 三部長篇小說) | 《黃河東流去》(上下集) 李準 | 《沉重的翅膀》 張潔 | 《鐘鼓樓》 劉心武 |
| 第三屆(1988年 五部長篇小說) | 《平凡的世界》 路遙 | 《少年天子》 凌力 | 《都市風流》 孫力、余小惠 | 《第二個太陽》 劉白羽 | 《穆斯林的葬禮》 霍達 (榮譽獎二部) 《浴血羅霄》 蕭克 | 《金甌缺》 徐興業 |
| 第四屆(1989-1994年 四部長篇小說) | 《戰爭和人》 王火 | 《白鹿原》(修訂本) 陳忠實 | 《白門柳》(一二部) 劉斯奮 | 《騷動之秋》 劉玉民 |
| 第五屆(2000年 四部長篇小說) | 《抉擇》 張平 | 《塵埃落定》 阿來(藏) | 《長恨歌》 王安憶 | 《茶人三部曲》(1、2)王旭烽 |
| 第六屆(2005年 五部長篇小說) | 《張居正》 熊召政 | 《無字》 張潔 | 《歷史的天空》 徐貴祥 | 《英雄時代》 柳建偉 | 《東藏記》 宗璞 |
| 第七屆(2008年 四部長篇小說) | 《秦腔》 賈平凹 | 《額爾古納河右岸》 遲子建 | 《暗算》 麥家 | 《湖光山色》 周大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