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書名:《紀實和虛構》作者:王安憶著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第1版
出版時間:1993年6月1日
叢書名:新中國60年長篇小說典藏
精裝:46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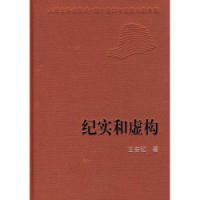 |
| 《紀實和虛構》 |
正文語種:漢語
開本:32
ISBN:7020074642,9787020074648
定價:34.00
內容簡介
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之際,我們從業已出版的長篇小說中遴選出部分優秀作品,匯集成“人民文學出版社”一次性推出。這些書目的選擇,兼顧歷史評價、專家意見、讀者喜好,以及題材和思想藝術風格的豐富性,它們集中展示了新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偉大成就和發展變化,從文學的角度折射出中國特別是新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風貌。入選作品大都經過了時間淘洗,是可以流傳的上乘之作。閱讀或收藏,均富有價值。編輯推薦
《紀實和虛構》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新中國60年長篇小說典藏”之一,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新中國文學出版事業從這裡開始。序言
很久以來,我們在上海這城市裡,都像是個外來戶。我們沒有親眷,在春節這樣以親眷團聚為主的假日裡,我們只能到一些“同志”家中去串門。我們家的小孩子和這些“同志”家的小孩子在一起玩,我們使用的語言不是上海話,而是一種南腔北調的國語。這樣的語言使我們在各自的學校和里弄里變得很孤獨,就像是鄉巴佬似的。當然,假如是在上海的徐匯區,事情就又是一番面目。徐匯區是“同志”們比較集中的區域,許多重要的學校里,是“同志”的孩子們的天下,國語是他們的日常語言,假如有誰說上海話,就會歸於“小市民”之流。“小市民”在那裡受到普遍的歧視。在上海城市邊緣的有些區域,比如楊浦、普陀,則又是以蘇北話為主,紀念著他們在戰亂與饑荒中離開的故鄉。他們是撐著船沿了蘇州河進上海的一群,在上海的郊野安營紮寨,形成部落似的區域。在那裡的學校,倘若不說蘇北話,便將遭到排斥。這就是上海這城市的語言情況。我們是屬於那一類打散在民眾中間的“同志”,我們居住在最典型的上海的區域:盧灣區。這使得我們必須學習說上海話,不會說上海話使我們很自卑。從整體上說,像我們這些“同志”是打著腰鼓扭著秧歌進入上海的。腰鼓和秧歌來源於我們中央政權戰鬥與勝利的所在地延安,延安這山溝溝里的小東西後來成為上海最主要的一條東西大道的命名。文摘
我們在上海這城市裡,就像是個外來戶。母親總是堅持說國語,雖然她明明會說上海話,且還比國語更標準。國語是我們家中的語言,這使我與人交往有了困難。我常常閉口無言,人們就以為我是個沉默孤僻的孩子。等我將上海話越說越流利,不再憚於開口的時候,人們反以為我變得聒噪了。母親還不準我和鄰家的孩子往來,認為他們會帶給我不好的影響,至於這不好的影響是什麼,我在很長的時間內一直沒有弄清楚。因此我和他們在一起時,內心就處在一種緊張的狀態,我時時警惕著,卻不知應當警惕什麼。可是偶爾的,我的某一個表現,便會遭到母親嚴厲的批評。母親批評我們從不以激烈的態度,她只是使我們感到強烈的羞慚,這羞慚將伴隨我們一生。母親批評我們的標準,我很久以來難下判斷,不知該往哪一類型歸納,這其實反映了母親的經過了嫁接的價值觀念,這是我後來才弄明白的。母親從不帶我們去看越劇這樣帶有村俗氣的劇種,可是要抵制越劇的誘惑在我們所住的那幢房子裡幾乎不可能。越劇里後花園私定終身的故事是各家保姆奶媽們熱心的話題。保姆偷偷帶我們去看了一場《梁祝》,那絢麗的服飾和婀娜的身姿使我們頓時傾倒。從此,我們的遊戲便是站在床上,披了毛巾毯作水袖,演出後花園裡的悲喜故事。心裡則充滿了犯罪的感覺,生怕被母親發現,便做賊似的躡著手腳。有一回,母親到我學校去開家長會,出於向母親表現的動機,這晚上我便分外活躍,走進走出,喊這喊那,情緒亢奮。回家的路上便被指責為:行動瑣碎。和同學胳膊挽胳膊走路也是不允許的,這是俗氣的姿態。母親還經常檢點我們誠實、勇敢、勤勞、儉樸的品格。匯總起來看,母親對我們的要求是,具有大家閨秀的風範,屏除市民習氣,再具有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品質和理想。作家王安憶
鄰居們稱呼父親母親為“同志”,態度恭敬,這使我覺出我們與他們的區別。這種稱呼延續了許多年,後來的改變是由於我們家新來的保姆。她進門就稱父親為“先生”,母親為“師母”,無論母親怎樣糾正,請她叫“同志”,她只說:我不會叫。她是那種生來就為保姆的人,一看見她,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隨她去米店買米,一見如故的心情油然而生。她十七歲就來上海幫傭,那時已是四十歲,懂得一切僱傭和受僱的規矩。在這點上,她對母親起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開頭就是關於稱呼這一件事。我覺得,對於我們進入上海城市生活這一樁事,她是有著不可抹殺的功勞。她還喜歡帶我們到她昔日的東家家中去,讓我和那些人家的孩子結成朋友。在她離開我們家後,同樣也帶了她新東家的孩子來玩。這拓展了我們家的單一的“同志”式的社會關係,對於我們家契入上海社會,也是一個有力的推動。她幫傭過的人家形形色色,她對各家的底細,也都一清二楚。有時候,我們被引進寬闊的客廳,她和她昔日的師母娓娓而談,我則流連於一排玻璃櫥前,櫥內滿是擼甲大小的玉做的飛禽走獸,一層又一層,這給我的童年印象抹下了深刻的一筆。我們有時候只能坐在黑暗的灶披間裡,小孩子在後弄里衝來殺去。她不時出去拖進一個,喝斥著擤掉他的鼻涕,拉直他的衣領,再放他回去。我跟隨她走過上海許多明亮的客廳和黑暗的灶披間,那裡的生活與我的都是大相逕庭。保姆她還在外國人住的公寓裡幫過傭,所以她會說幾句英語:早安,晚安,去,來什麼的。她稱外國人為長毛,極其蔑視,說那長毛只穿了三角褲在陽台上曬太陽觀街景,恨得她立即辭了生意,掉頭就走。她
 |
| 作家王安憶 |
總之,保姆是上海這城市裡信使一般的人物,又有些像奸細。她們可以深入到主人的內房,以她們獨特的靈敏的嗅覺,從一切蛛絲馬跡上組織情節,然後她們再將這情節穿針引線似的傳到這家又傳到那家,使這裡的不相往來的家庭在精神上有了溝通。我想,我們對自己所居住環境的了解,是從她走進我們家之後開始的。在這之前,串門走戶,被母親嚴格禁止,而她視我母親的法律為糞土,母親說母親的,她行她的。於是,自她來後,我開始走進了我們鄰居家的門。再由於保姆她的帶領,人們也相繼以“先生”和“師母”這樣的稱謂稱呼我的父母,這使我欣喜若狂,我認為這是我們一家真正走進這個城市的第一個信號。我從小就這樣熱衷於進入這個城市,這樣生怕落伍,是母親對我最感失望的地方。有一次,我和母親路過一幢樓房,我告訴母親這是我們區的少年宮。母親先不作聲,只是駐步仰望了一下那樓房的尖頂,紅瓦頂上正飄揚了一面少年先鋒隊的隊旗,背景是藍天白雲,似乎還飄蕩著悠揚的鴿哨。我注意到母親的眼睛有一種微妙的表情,她望了一下樓頂,然後說:這是我的姨母家。這話使我大受震動,後來每當我心感寂寞的時候,我就會走到這座樓房前,樓房裡總是喧聲震天,孩子們的腳步幾乎將樓板踏穿。目睹他們的熱鬧,我心裡想著:雖然你們中間我一個人都不認識,可是這座房子是我母親的姨母的。想罷我便驕傲地轉過身子,向回走去。有了這幢房子作背景,我在這城市裡就不再是孤獨的了。而我根本弄不清我母親的姨母是什麼人物,現在去了哪裡,和我母親的關係又如何。我有一回試圖向母親提出這些問題,母親卻不快地反問道:這對你有什麼重要呢?從此我就不敢再提這問題,母親也閉口不談這話題。但是,我卻從此堅信,我們在這城市裡不再是無親無故。在我童年的時候,這座房子對我的作用就是這樣重要。除了這幢房子以外,還應當提到一位母親稱之為“三娘娘”的女客。她所以在我幼年時代深入記憶,是因為她是我們家惟一的一位說上海話,並且不屬“同志”隊伍的一位客人。她的裝束也與“同志”大不相同,她描眉,塗唇膏,指甲上染有蔻丹,她穿一件翠綠的旗袍,她很漂亮,又很傷心,她一坐下來,總是淚水漣漣。母親對她很客套且很冷淡。記得有一回她給母親看她腕上的青紫傷痕,母親正在削一個梨,削下的梨皮完整地包在梨身上,也許是削得過於專心沒有聽見,母親連眼皮都不曾抬一下。她只得把她的手腕給我看,我由衷地唏噓了一下,她臉上露出了安慰的笑容。她走的時候,母親送她到門前的台階上,總是由我積極地跑出去為她開天井的門,那月光如洗,她身穿翠綠旗袍,裊裊婷婷走過天井的景象實在難忘。她每回來去總是走前門,這也是一個特徵,母親站在台階上迎送的情形,使我們家有一種高門大戶的威勢。她身上有一種“舊社會”的氣息,而我們家卻是一個完整的新社會,這體現在我們都說國語,還有,我們來往的都是“同志”。三娘娘在我們家有點畢恭畢敬,母親則有點傲然,這在我們家中顯現出來的等級關係,令我陌生、不舒服,卻又異常興奮。有時候當她在的時候,家中又來了一位客人,母親並不與他們作介紹,只是著重地說一句:這是一位同志。“同志”的意義這時大放異彩,連我都有些驕傲。三娘娘立即起身告辭,走過天井時,就有些灰溜溜的。這便是我們家與上海這城市所有的關係了。在我父親那邊,是別指望有什麼線索的,他來自很遙遠的地方,為我與這城市的認同,幫不上一點忙,希望就寄托在我母親身上了。這些關係雖然不多,而且為母親有意緘默,但是卻多少減輕了我在上海這城市裡的孤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