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小說
正文
現代的中國小說。其主體是“五四”文學革命聲中誕生的一種用白話文寫作的新體小說。它取法歐洲近代小說,卻植根於現實生活的土壤,既不同於中國歷來的文言小說,也迥異於傳統的白話小說。和中國封建時代許多小說表現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內容相對立,現代小說以日常生活中普通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和市民為重要描寫對象,具有現代民主主義的思想色彩,不少作品還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在藝術表現上,性格小說大量出現,心理刻畫趨於細密,“全知”式敘述角度有所突破,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得到遵循,這些也都構成了“五四”以後新小說與實際生活大為接近的顯著特點。儘管章回體小說在現代依然存在,但這些作品也程度不同地吸收了新小說的思想藝術營養,並逐步朝新小說方面轉化。中國小說從“五四”時期起,跨進了一個與世界現代小說有共同“語言”的嶄新階段。 現代小說
現代小說20、30年代小說創作的發展和繁榮
現代小說一開始就密切關心現實人生問題。提倡“文學革命”的《新青年》和最早成立的新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既反對封建的“載道”文學,也反對鴛鴦蝴蝶派的遊戲文學,他們主張文學“為人生”。“問題小說”在“五四”時期的風行,便是這種潮流的一個突出標誌。倡導者從啟蒙主義的思想立場出發,認為“問題小說,是近代平民文學的產物”(周作人《中國小說里的男女問題》)。現代小說的第一篇作品──魯迅的《狂人日記》,就提出了家族制度和封建禮教“吃人”這個重大問題。葉紹鈞的《這也是一個人?》,汪敬熙的《誰使為之?》,羅家倫的《是愛情還是苦痛?》,冰心的《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朴園的《兩孝子》,以及廬隱、王統照、孫俍工等的一些小說,或提出人生目的意義問題,或提出青年戀愛婚姻問題,或提出婦女人格獨立和教育問題,或提出父與子兩代人衝突問題,或提出破除封建舊道德束縛問題。此外,也有作品涉及勞工問題、兒童問題等等。這類小說對社會問題的答案並不一致,不少作品用“美”和“愛”的浪漫主義空想當作解決現實問題的鑰匙(冰心和葉紹鈞、王統照最初的小說都有這種傾向,許地山則還有宗教哲理色彩);有的連答案都沒有,屬於所謂“只問病源,不開藥方”;但“不開藥方”本身,也正是“問題小說”的特點之一。真正顯示了“五四”到大革命時期小說創作的現實主義特色的,是魯迅以及在魯迅影響下的文學研究會、語絲社、未名社一部分青年作家。他們的短篇小說,描繪了各地頗具鄉土色彩的落後、閉塞的村鎮生活,提供了中國農村宗法形態和半殖民地形態的寬廣而真實的圖畫,獲得了顯著的成就。其中魯迅的《吶喊》、《徬徨》,更以圓熟單純而又豐富多樣的手法,通過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異常深廣的時代歷史內容,真實地再現了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在獲得無產階級領導前的極度痛苦,展示了鄉土氣息與地方色彩頗為濃郁的風俗畫,代表了“五四”現實主義的高度水平。很早就有評論者指出:“他的作品滿薰著中國的土氣,他可以說是眼前我們唯一的鄉土藝術家”(張定璜《魯迅先生》)。正是在魯訊的開拓與帶動下,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的後期出現了一批鄉土文學作者,如潘訓、葉紹鈞、蹇先艾、許傑、魯彥、彭家煌、廢名、許欽文、臺靜農、王任叔等,使這類小說獲得很大的發展。新體小說從最初比較單純地提出問題到出現大批真實再現村鎮生活的鄉土文學作品,標誌著小說領域裡現實主義的逐步成熟。
但“五四”是一個開放的時代,現實主義之外,浪漫主義、象徵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新浪漫主義以及總稱為現代主義的表現主義、未來主義、達達主義等文藝思潮連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也同時介紹到中國。創造社主要作家的小說創作,便兼有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的特徵。他們之所以被稱為“異軍突起”,主要因為創作上與倡導寫實主義的《新青年》、文學研究會的作家顯示了很大的不同。由郁達夫、郭沫若、陶晶孫、倪貽德、葉鼎洛、滕固、王以仁、淦女士等所代表的創造社這個流派的小說,基本上是一些覺醒而憤激不得意的新型知識青年的自我表現,帶有濃重的主觀抒情色彩和自我寄託成分(稍有不同的是張資平,他最早的一些小說還是自然主義或現實主義居多)。從郁達夫的《沉淪》起,坦率的自我暴露,熱烈的直抒胸臆,大膽的詛咒呼喊,誇張的陳述詠嘆,便構成了創造社小說的浪漫主義基調,與葉紹鈞、許傑、彭家煌以及稍後的魯彥等作家對現實本身所作的冷靜描寫和細密剖析迥然相異。此外,創造社一部分作家的小說還具有現代主義成分。郭沫若、郁達夫都在不同程度上受過德國表現派文學的影響 (這從郭沫若的《喀爾美蘿姑娘》、郁達夫的《青煙》都可以看出來)。郭沫若的《Lobenicht的塔》、《殘春》,陶晶孫的《木犀》等小說,則按弗洛伊德學說分析心理,描寫“潛在意識的一種流動”;有的作品還運用了意識流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為後來的現代派小說開了先河。創造社的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傾向,曾使淺草──沉鍾等社團受到影響。但隨著作家接觸社會生活的增多和世界觀的變化,郭沫若不久就批判了弗洛伊德學說並否定了浪漫主義,郁達夫的小說自《薄奠》以後,也逐漸增多了現實主義成分,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的一些重要作家後來終於殊途而同歸了。
 現代小說
現代小說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促進了小說創作的發展。這個時期的作品,無論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廣度與藝術本身的成熟程度上都有新的進展,中長篇小說尤其獲得豐收。代替“五四”以後男女平等、父子衝突、人格獨立、婚姻自由等反封建題材與主題的,是城市階級鬥爭與農村革命運動的描畫。不少作者力圖套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來指導創作實踐,既克服“革命的浪漫蒂克”、“用小說體裁演繹政治綱領”等不正確傾向,也注意防止單純“寫身邊瑣事”的偏向。丁玲、張天翼、柔石、胡也頻、魏金枝等給文壇帶來了新鮮氣息的作者,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受到了重視。左翼作家參預或親歷實際革命鬥爭,使創作面貌繼續有所變化;再現生活時的歷史性具體性既有增進(包括《咆哮了的土地》這類小說),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有些青年作家(如葉紫、東平)的作品中也得到發揚。茅盾的《子夜》以民族資本家吳蓀甫形象為中心,在較大規模上真實地描畫出30年代初期上海的社會面貌,準確地剖析了中國社會的性質,這是作者運用革命現實主義方法再現生活的出色成果。《子夜》的成功,開闢了用科學世界觀剖析社會現實的新的創作道路,對吳組緗、沙汀、艾蕪等創作的發展和一個新的小說流派──社會剖析派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共產主義者魯迅也在《理水》、《非攻》等作品中,用新的方法塑造了“中國的脊樑”式的英雄形象,顯示了對革命前途的樂觀與信念。在“左聯”的關懷、幫助下,湧現了蔣牧良、周文、蕭軍、蕭紅、舒群、端木蕻良、歐陽山、草明、蘆焚、黑丁、荒煤、奚如、彭柏山等一大批新的小說作者。儘管左翼小說創作也還羼雜著某些舊現實主義乃至自然主義的因素,塑造革命者和工農形象時較普遍地存在蒼白、不夠真實等缺點,總的說來,卻還是向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前進了一大步。“左聯”以外的進步作家,也因為堅持現實主義道路,在小說創作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巴金的《家》通過封建大家庭的沒落崩潰與青年一代的覺醒成長,在相當寬廣的背景上表現了“五四”以後時代潮流的激盪;老舍的《駱駝祥子》描述了勤勞本分的人力車夫祥子從奮鬥、掙扎到毀滅的悲劇性一生,對舊社會、舊制度作出深沉有力的控訴;它們與《子夜》等左翼作品一起,將中國長篇小說藝術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此外,還出現了象葉紹鈞的《倪煥之》,李劼人的《死水微瀾》、《暴風雨前》,王統照的《山雨》,魯彥的《憤怒的鄉村》以及羅淑的《生人妻》等一批相當重要的長短篇作品。30年代的“京派”作家如沈從文、廢名、凌叔華、蕭乾等,也寫出了一些內容恬淡、各具特色的小說,象沈從文的中篇《邊城》、長篇《長河》,則是藝術上相當圓熟的作品。在上海,以施蟄存主編的《現代》雜誌為中心,還聚集著杜衡、穆時英、劉吶鷗、葉靈鳳等一批作家;他們中,有的從事著現實主義的小說創作,有的則以日本新感覺派或歐美其他現代派小說為楷模,嘗試著現代主義的創作道路,其中一部分作品在運用快速的節奏以表現現代都市生活,探索現代心理分析方法,吸取意識流手法以豐富小說技巧等方面,盡了一定的開拓作用。
 現代小說
現代小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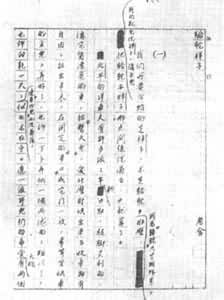 現代小說
現代小說抗戰爆發後小說創作的面貌
抗戰的炮火激發了廣大作家的創作熱情。許多作品迅速反映生活,歌頌前線和後方的新人新事。小說創作在現實主義基礎上明顯地增長了浪漫主義的成分;形式上則趨於通俗,趨於大眾化。姚雪垠就是這方面有成就的代表。他的短篇《差半車麥秸》、中篇《牛全德和紅蘿蔔》,都以生動地刻畫農民戰士的性格和成功地運動民眾口語而為人稱道。長篇如吳組緗的《鴨嘴嶗》,齊同的《新生代》,也都寫出了新的性格在民族危難關頭突破重重阻力而成長。但抗戰初期小說創作的普遍弱點,是對生活的反映比較表面,流於浮泛。正是在這種情勢下,《七月》雜誌上丘東平的《一個連長的戰鬥遭遇》等小說,就以有血有肉的戰鬥生活,熱情而深沉的藝術風格,顯示出可貴的特色。稍後出現的路翎,也是“七月派”的小說作家。從《飢餓的郭素娥》到《財主的兒女們》,同樣表現了他對現實主義藝術的獨到的追求。這些作品有內在的熱情,有心理現實主義的某些特點,在表現倔強的人物性格、真實的生活邏輯方面都有頗為深刻之處。但“七月派”小說家筆下的人物,常常倔強而近於瘋狂和痙攣,具有某種歇斯底里的成分。這和他們對生活的觀察、體驗帶有過多的主觀色彩有關。“七月派”作家是既強調現實主義,又強調主觀戰鬥精神的,他們的小說創作的長處和弱點,似乎都可以從這方面去尋找原因,作出解釋。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統治的黑暗、腐朽、反動逐漸暴露得愈益充分,國民黨統治區的小說也愈益向著深入揭露陰暗面方面發展。從張天翼的《華威先生》到沙汀的《淘金記》、茅盾的《腐蝕》、巴金的《寒夜》,便是這類作品中的傑出代表。由“皖南事變”以後環境黑暗所帶來的沉重氣氛,卻也在一部分小說中留下了較深的烙印(如夏衍的《春寒》、沙汀的《困獸記》等)。到1944年民主運動高漲後國民黨統治區產生的一些作品,象張恨水的《八十一夢》、沙汀的《還鄉記》、艾蕪的《山野》、黃谷柳的《蝦球傳》,在暴露諷刺方面則已具有直捷痛快、淋漓盡致的特點,有的並顯示著人民鬥爭終將勝利的曙光。戰後出版的長篇,如錢鍾書的《圍城》,姚雪垠的《長夜》,或寫抗戰以來的現實,或寫20年代的歷史,都以獨特的藝術成就,贏得了讀者的喜愛。老舍的《四世同堂》,則以百萬字篇幅的宏大規模,反映了淪陷後北平市民的苦難和抗爭,不僅成為以藝術方式記載的日寇、漢奸的罪行錄,而且也是中華民族不屈鬥爭的正氣歌。短篇小說方面,沙汀、艾蕪的一些作品,無論思想與藝術,都達到了很高的成就,標誌著國民黨統治區革命現實主義小說的進一步成熟。此外,國民黨統治區和上海淪陷區這個時期也曾出現過一些新的小說作者,如駱賓基、於逢、王西彥、碧野、郁茹、張愛玲、汪曾祺等,他們的一些有特色的作品,也都曾引起文藝界的注意。這時的國民黨統治區也存在過另一種創作傾向,代表作家是《鬼戀》、《風蕭蕭》的作者徐,《北極風情畫》、《野獸、野獸、野獸》的作者無名氏。他們的小說並無充實的生活基礎,卻以編織浪漫故事、抒發人生哲理見其特色,具有較重的感傷情調。政治傾向並不好,藝術上則有某些可取之處。
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和後來的解放區,由於作家同人民民眾的逐步結合,小說創作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思想感情到語言形式都大大民眾化了,工農兵民眾特別是他們中間成長起來的新人,開始成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並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實程度,根本扭轉了過去那種“衣服是勞動人民,面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狀況。還出現了一批用傳統的章回體寫法表現新生活內容的比較成功的長篇(如《呂梁英雄傳》、《新兒女英雄傳》等)。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短短七、八年內,不僅有柳青、孫犁、康濯、秦兆陽、馬烽、西戎、束為、馬加、王希堅等一批新的小說作者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而且還湧現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高幹大》、《種穀記》、《原動力》等一批優秀或比較優秀的長篇。趙樹理更是解放區小說作家的突出代表。他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作品,不僅語言形式民眾化,而且感情內容也浸透著來自農民的樸實、親切、幽默、樂觀的氣息,讀後使人耳目為之一新。孫犁、康濯等人的短篇小說,則洋溢著真正從民眾生活和鬥爭中得來的詩情畫意。他們的小說為後來的一些創作流派開了先河。在反映革命部隊的戰鬥生活方面,劉白羽等的中短篇小說,也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某種意義上說,延安文藝座談會後解放區文學的實踐,確實可以稱得上是繼“五四”文學革命之後的又一次深刻的變革,為小說創作的民族化、民眾化開闢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解放區文學主要是在農村環境中發展起來的。在強調向農民學習,與農民結合,因而取得出色的成就的同時,卻也產生了對小生產思想的落後消極方面放鬆警惕的缺點。對丁玲小說《在醫院中》的不正確批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解放區一些小說的另一個弱點,是對外國文學借鑑得少。作家在民眾中紮根深了,但來不及從更廣闊的範圍吸取豐富的營養。這種局限同延安文藝座談會後時間很短,又處於緊迫的戰爭環境,很多作者原有的文化程度不高等客觀因素都有關係,但同主觀認識上的某些偏差也有一定聯繫。正是主觀認識上的某些片面性,使我們的文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逐漸突破上述局限時,仍不免走著曲折的道路。
 現代小說
現代小說50年代小說創作的進展與豐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結束和社會主義時期開始。這個重大的歷史性轉變,使現代小說獲得了新的生活土壤與發展條件。新中國的小說作者,大多經歷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生活的冶煉,他們是帶著深厚的生活根基、與革命潮流的緊密聯繫以及對現實變化的敏銳感應跨進共和國的文壇的。這就使建國後的小說創作從一開始就與“五四”以來、特別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革命文學的戰鬥傳統保持著血緣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首先出現的是一批創作在歷史的黑夜與黎明交替時刻的作品。劉白羽的中篇《火光在前》,馬加的中篇《開不敗的花朵》,柳青的長篇《銅牆鐵壁》,都真實記錄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隊伍和人民民眾最後摧毀舊制度、迎接新制度的鬥爭。楊朔的長篇《三千里江山》,則迅速反映了中國人民在獲得政權以後,為保家衛國而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表現革命戰爭題材而更能顯示特色的,是稍後出現的一批長短篇小說。峻青的《黎明的河邊》,王願堅的《黨費》,通過艱苦年代嚴酷鬥爭的真實描寫,異常感人地讚頌了革命根據地人民的英雄氣概和獻身精神。杜鵬程的長篇《保衛延安》以宏大的藝術規模再現了延安保衛戰威武雄壯的歷史場面,成功地塑造了從連長周大勇、團政委李誠到高級指揮員彭德懷的形象,成為建國後長篇創作的第一個重要收穫。這些作品都以悲壯激越的基調,激動著許多讀者。反映抗美援朝的一些短篇,如巴金的《黃文元同志》,和谷岩的《楓》,路翎的《初雪》、《窪地上的“戰役”》等,或熱情奔放,或筆觸細膩,也都顯示了各自不同的風格特色。
描繪農村現實生活的短篇小說,也給建國初期的文壇帶來了新鮮氣息。趙樹理的《登記》,谷峪的《新事新辦》,都表現了農民民眾在砸碎封建政治枷鎖以後進一步掙脫封建主義精神束縛的鬥爭;馬烽的《結婚》等短篇,則反映了農村新人新品質的成長。這些作品藝術筆調明朗,生活氣息濃郁,凝聚著作者長期與農民共命運所獲得的珍貴情感。隨著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逐步展開,反映農村生活的巨變,成為小說創作的重要主題。青年作家李準的短篇《不能走那條路》,便是敏銳地觸及土改后土地私有制尚未根除而產生的新矛盾的第一篇作品。趙樹理的長篇《三里灣》,通過更為複雜的生活內容,展示了這種矛盾的各個側面。孫犁的中篇《鐵木前傳》,藝術觸角伸延到解放前後兩個時代,以兩戶農家關係的演變,透露了土改後農民出現分化的信息。秦兆陽的《農村散記》、康濯的《春種秋收》兩集中的短篇小說,則以清新的筆調和精美的構思著重反映農村變革中農民民眾的思想波瀾和生活變化。在這股創作潮流中貢獻了有特色的作品的,還有陳登科、劉澍德、駱賓基、王希堅、吉學霈、劉紹棠等一大批作家,他們忠於革命現實主義原則,從各自的生活視角真實描畫了50年代前期中國農村社會的種種風貌。瑪拉沁夫、李喬、明斯克、阿·敖德斯爾等少數民族第一代小說家,或描繪內蒙草原上驚心動魄的鬥爭,或抒寫西南彝區人民的苦難與歡樂,也都獲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
 現代小說
現代小說從50年代初期到中期,小說創作獲得了穩步的發展。這段時間,國家經濟、政治生活日趨穩定,文藝界藝術民主氣氛比較正常,特別是中國第二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後,總結了前階段文藝工作的經驗教訓,探討了創作上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的因由,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一些原則問題,取得了較為辯證的全面的認識。當時蘇聯文藝界對“無衝突論”、對典型問題上教條主義觀點的衝擊,也直接促進了中國小說創作隊伍思想的活躍。作家對新生活的觀察和認識逐漸深化,過去的生活積累也有了較長時間的消化過程,對中外作品的借鑑又從藝術修養上為創作做了較多的準備,在此基礎上,許多作家開始醞釀長篇巨製。到50年代後期,中國文壇終於迎來了建國以來長篇小說的第一次豐收。
這次豐收所湧現的一大批長篇作品,在現代小說發展過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顯示建國後整個文學水平的重要標誌。
追求概括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是這批長篇創作的一個顯著特點。這在革命歷史題材的創作中尤其得到了集中的體現。梁斌的《紅旗譜》,歐陽山的《三家巷》,楊沫的《青春之歌》,高雲覽的《小城春秋》,馮德英的《苦菜花》,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岩》等,組成了一幅幅巨大的歷史畫卷,鮮明生動地展現了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這批作品在深刻表現歷史內容、展示鬥爭複雜過程方面,較之過去創作有重大突破,而在現實基礎上升華起來的革命理想激情,也給作品增添了明朗、熱烈的色彩,為豐富中國小說的革命現實主義傳統提供了新鮮經驗。李劼人的《大波》(修改本),李六如的《六十年的變遷》,用精細而又恢宏的現實主義筆法,真實地再現了清末以來的社會面貌;它們的出現,使長篇小說展現的歷史畫卷向上延伸到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些小說的作者,幾乎都是當年革命鬥爭的親身經歷者或目擊者,他們筆端留下的歷史生活圖畫,在小說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以社會主義時期現實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在表現生活的廣闊性和縱深感方面,也有長足進展。柳青的《創業史》和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是描寫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的著名長篇。前者通過梁三老漢、梁生寶兩代農民不同的創業命運,揭示出中國農民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是歷史的必然;後者側重於剖析農村生產關係變革過程中人們精神世界的細微而深刻的變化。反映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命運和生活動向的《上海的早晨》,是作家周而復的一部長篇巨著。它對具有中國特色的都市生活所作的藝術概括,曾引起國內外讀者的興趣。
這個時期,許多小說家經過較長時間的藝術實踐,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發展著自己的獨特風格,並形成若干新的創作流派。趙樹理嫻熟地運用中國古典小說和民間文藝的傳統手法,生動樸素、維妙維肖地表現了山西一帶新農村的社會情緒和農民心理,早已在小說領域中獨樹一幟。在他的藝術作風影響下,產生了馬烽、西戎、孫謙等思想傾向、藝術見解、創作風格相近的作家群,被人稱作“山西派”或“山藥蛋派”。孫犁那意境悠遠、韻味無窮的“荷花澱”風格,給他筆下的現實生活圖畫,添上淡淡的浪漫主義氣息,這種獨具特色的藝術經驗,也為一些青年作者所效法。柳青在對現實冷靜、客觀的描繪中,糅進了哲理的議論和感情的抒發,使精確的畫面透露出渾厚激越的氣勢。他對於廣闊的社會場景的多方面的概括,對於生活內涵的深入發掘,一直到他的夾敘夾議的語言,都在隨後出現的若干青年作家的小說中,留下鮮明的投影。周立波追求的則是一種秀朴而明麗的風格,他常常把自己的感情傾向熔鑄到山鄉風情和自然景色的細膩而又酣暢的表現中,讓人們在詩情畫意的藝術氛圍里領略新生活的美;從他的短篇《山那面人家》、《禾場上》到謝璞的短篇《二月蘭》等,可以感受到湖南一些作家的共同藝術追求。一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成長起來的小說家,如杜鵬程、李準以及寫了《高高的白楊樹》、《百合花》、《靜靜的產院裡》的茹志鵑,寫了《大木匠》、《沙灘上》的王汶石等,都在追求著自己鮮明的藝術個性。所有這些,都標誌著建國後小說藝術的逐漸趨於成熟。
50年代末到80年代小說創作的曲折道路
由於社會政治思潮的影響,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中期,小說的發展有過較大的曲折。1956年前後,小說領域曾出現過以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為代表的一批“干預生活”的短篇,它們大膽觸及現實的各種矛盾,尖銳揭露社會生活的一些弊端,這批作品既是當時國內外文藝界反對“無衝突論”創作思潮的直接產物,也是當代小說家希冀於小說的社會功能獲得更大發揮的一次勇敢嘗試。但因當時環境所囿,這個創作潮流剛露端倪就被人為地宣告結束。隨著對“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實主義深化”論、“寫中間人物”論的責難,代之而起的是一股粉飾現實、以虛假現實主義昌充革命現實主義的創作浪潮。不過,在這股思潮泛濫時,不少有膽識的小說家仍有好作品問世。趙樹理的《鍛鍊鍛鍊》、《套不住的手》,馬烽的《三年早知道》,劉澍德的《甸海春秋》,西戎的《賴大嫂》等短篇,都是堅持革命現實主義精神、真實揭示生活矛盾的好作品。一些作家把筆鋒轉向歷史,寫出《陶淵明寫輓歌》(陳翔鶴)、《杜子美還家》(黃秋耘)等短篇,以歷史的鏡子映照現實,這是小說家們在特殊環境中堅持現實主義精神的曲折表現。李準的《李雙雙小傳》,王汶石的《新結識的夥伴》,雖以“大躍進”為背景,但立意不在歌頌浮誇作風,而著力於塑造農村新人富有鮮明個性特徵的性格,至今仍保持一定的藝術魅力;至於真實刻畫了土生土長的好乾部形象的《延安人》(杜鵬程)、《我的第一個上級》(馬烽)等短篇,更是具有較大感染力量的優秀作品。1962年以後,小說創作的興旺局面開始冷落,其間雖有姚雪垠的優秀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第 1卷問世,但其他好作品不多。浩然的《艷陽天》和陳登科的《風雷》反映農村生活,藝術上有可取之處,內容上卻明顯留下階級鬥爭擴大化思潮的痕跡。
“文化大革命”中,小說的正常創作活動受到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壓制,而一批反現實主義作品則在唯心主義思潮下應運而生。以《序曲》為結集的一批短篇,就是突出代表。
1976年10月,中國歷史出現了新的轉折,社會政治動亂開始平復,隨著思想路線逐步端正,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文學事業又呈現出生機勃勃的趨勢,小說創作更是盛況空前。作為中國社會由大動盪走向大整治、大改革的歷史過程的生動反映,這時期的小說創作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特點:
一是恢復和發展了“五四”以來的革命現實主義傳統,並不斷走向深化。社會政治生活中唯物主義路線的恢復,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使小說家們精神上獲得一次大解放,他們敢於面對現實的人生,正視生活中普遍關心的矛盾,提出自己積極的思考。進入新時期的頭兩三年,從劉心武的《班主任》開始,出現了一批曾被稱為“傷痕文學”的短篇小說,它們第一次把林彪、“四人幫”倒行逆施所造成的慘痛展現在讀者面前,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反響。還有一批作品,如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魯彥周的《天雲山傳奇》、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等,則是從歷史和現實的交錯表現中,著重探索建國30年來國家所走過的曲折道路和深刻教訓,進行歷史的“反思”。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莫應豐的《將軍吟》,是反映十年動亂生活最有影響的長篇,它們不僅深刻地揭示了這場動亂所造成的歷史倒退,更著力於表現人民民眾對社會主義光明的強烈渴求。這幾年繼姚雪垠《李自成》第 2卷後所湧現的《星星草》、《金甌缺》、《風蕭蕭》等一大批歷史小說,也有一個共同的鮮明特徵:從歷史的真實發展中探求深刻的生活哲理,以喚起當代讀者感情的共鳴。進入80年代以來,作家的筆鋒逐漸轉向了正在發展中的當前現實。從各個不同角度反映朝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前進的生活巨流,有力揭示社會大變革時期的各種矛盾,塑造“改革者”或當代新人的形象。蔣子龍的短篇《喬廠長上任記》是引起社會矚目的第一篇作品。陸續出現的還有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水運憲的《禍起蕭牆》、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等。一批以70年代末期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和當前軍隊生活為題材的中短篇小說,在揭示部隊生活矛盾、塑造當代軍人形象方面也有明顯突破,象徐懷中的《西線軼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就是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佳作。
 現代小說
現代小說從對普通人的命運的真實描寫到對人生意義的深沉思索,是這類題材創作的一個重要進展。韋君宜的中篇《洗禮》、路遙的中篇《人生》等,都凝聚著小說家們對人的社會價值和人生意義的深刻思考。在表現這類生活內容的創作中,也有曲折。一些青年作者由於思想功力的欠缺,在複雜生活面前感到迷惘,無法正確把握社會矛盾的本質所在和它的必然趨向,因而產生了一些藝術上雖有特色而思想傾向上有明顯失誤的作品。這也是除舊布新年代的一種值得注意的創作現象。
三是創作樣式的交疊變化和藝術手法的大膽革新。從小說樣式方面來看,新時期的頭幾年,短篇小說非常活躍。到80年代,中篇小說異軍突起,以大批優秀作品占領文壇,僅1981至1982年就湧現了1100多部作品,這是現代小說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長篇小說自1977至1982年6年時間湧現了500多部作品,數量可觀,但從創作勢頭看,尚處於方興未艾的狀態。
這時期小說的藝術風格與表現手法,顯得異常豐富多彩,探索的道路也更加寬闊。一些致力於小說民族化的作家,在對傳統小說藝術經驗吸取的同時,更注重於民族感情的熔鑄。李準的長篇《黃河東流去》、葉蔚林的中篇《在沒有航標的河道上》、劉紹棠的中篇《蒲柳人家》是這方面較早出現的佳作。對西方現代派小說藝術手法的吸取,是這時期小說形式革新的一個突出方面。以意識流作為結構作品的手法,多視點、多角度、多層次揭示人物精神生活的手法,在創作中得到比較廣泛的運用。走在這種探索前面的作家是王蒙,他的中篇《蝴蝶》、短篇《春之聲》,獲得社會首肯。李國文在長篇革新方面也邁開了第一步,《冬天裡的春天》是一個可喜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