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基礎
 信託公示
信託公示公示本是物權法中的一項基本制度。由於物權為絕對權,其義務主體是不特定的任何人,物權人與任何人都存在物權關係。因此,物權的得、喪、變更,不僅僅是權利人個人的事,對不特定的任何義務人(即社會公眾)亦發生權利義務變動的效果。權利人變動權利,雖不需要義務人同意,但應將變動的事實告知義務人,否則對義務人無拘束力。在債權,由於其義務主體是特定的,因而債權人只須將債權變動的事實通知債務人即可,無須公示。而對於具有絕對權性質的物權來說,由於其義務主體為不特定的任何人,權利變動的事實就無法一一通知義務人,因而告知義務的履行就只能以公示的方式進行。只有將物權變動的事實告知社會公眾,才能使他人知道自己對何人負有法律上的不作為義務,權利人才能對任何義務人主張權利。正如德國學者曼弗雷德.沃爾夫所言,物權的絕對對世效力不僅要求對物權種類進行界定,同時也要求物權的具體種類具有可識別性。為了實現物權的可識別性,公示原則發揮了作用。在設立或者轉讓物權時,法律要求履行不同形式的公示方式。動產物權的公示方式就是占有,不動產物權的公示方式則是不動產登記。
(二)交易安全
安全是法律所追求的重要價值之一。法律上的安全有“動”的安全和“靜”的安全之分。“靜”的安全是享有的安全,“動”的安全是交易的安全。[4]在一般情況下,法律始終必須兼顧“靜”的安全與“動”的安全的一體保護和周到保護。但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動”的安全與“靜”的安全會發生衝突,法律無法兼顧。這時,法律就必須根據“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選擇其中一種價值,予以優先保護。
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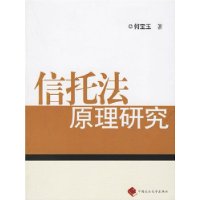 信託公示
信託公示中國《信託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信託,是指委託人基於對受託人的信任,將其財產權委託給受託人,由受託人按委託人的意願以自己的名義,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進行管理或者處分的行為。”由此規定可知,信託行為是由兩種行為組合而成的,一是“將財產權委託給受託人”的行為,此所謂“委託給受託人”,是指將財產權移轉(或者為其他處分)給受託人。根據民法的一般原理,財產權的移轉或者其他處分行為,是使財產權直接發生變動的行為,在性質上屬於處分行為(包括物權行為和準物權行為)。二是委託人“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而實施的對信託財產“管理和處分行為”,這在法律性質上也是一種處分行為。前者屬於信託行為成立的條件,後者屬於信託行為成立的效果。信託行為就是這兩種行為的複合體。
(二)信託公示的複合性
信託的公示方式由信託財產的性質決定,信託財產的性質不同,信託的公示方式也不一樣。如前所述,信託財產是一項複合財產。根據在國《信託法》的規定,信託財產可以包括物權、債權、股權和智慧財產權。在物權中又包括動產、不動產和證券化的物權,在債權中包括普通債權和證券化的債權,股權包括有限責任公司的股份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智慧財產權又包括著作權、專利權和商標權以及其他智慧財產權。信託財產的複合性決定了信託公示的複合性。
(三)信託公示的具體方式
如前所述,信託行為的複合性和信託財產的複合性決定了信託公示的二重性和複雜性。前者意味著,在對信託進行公示時必須分兩步走,首先是對設立信託的條件行為——委託人通過轉移或者其他處分行為將自己的合法財產委託給受託人的行為進行公示,這是對財產權一般變動的公示;在這個公示之外,還必須進行第二次公示,即表彰信託設立的信託公示。正如台灣學者賴源河所指出的:“所謂信託公示,系指於一般財產權變動等的一般公示外,再規定一套足以表明其為信託的特別公示而言。質言之,在制度構造上,可謂其系在一般財產權變動等的公示方法以外,再予以加重其公示的表征。”[8]可見,信託的公示,一方面必須遵循財產權變動的一般公示原則,另一方面又必須在公示方式中體現出設立信託的表征。後者意味著,對於性質不同的信託財產,應當採用不同的公示方式。具體而言,信託的公示可分為以下三種情形:
1、以應登記的財產權設立信託的
2、以有價證券設立信託的
效力
 信託公示
信託公示對於信託公示的效力問題,不同國家的信託法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在英美法系國家,由於對所謂的秘密信託和半秘密信託的承認,[10]因而信託的設立不僅不需要公示,甚至還可以秘密設立。信託對抗第三人的效力也不需要通過公示來實現。[11]英國牛津大學的比較法學家F.H.勞森和B.拉登在其所著的《財產法》一書中指出:“受益人可以追蹤或追溯違背信託所轉讓給任何其他人的信託財產,但是沒有注意到違背信託的善意有償買受人或者即使他注意到先前對信託的違背,但他卻是從善意受讓人那裡或者通過善意受讓人而取得財產的人例外。”[12]可見,在英美信託法中,信託對抗第三人的效力不是取決於信託的設立是否進行了公示,而是取決於該第三人在受讓信託財產時主觀上是否善意。如果該第三人是善意的或者從善意受讓人手中獲得,則委託人和受益人均不得以信託對抗該第三人;反之,如果第三人在受讓信託財產時主觀上是惡意的(即明知或者應知受託人違背信託處分信託財產),則委託人和受益人可以以信託對抗該第三人。
簡要評析
 信託公示
信託公示首先,在信託的公示方式方面,只規定登記一種,不僅在理論上存在邏輯不周延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上必然給交易的安全帶來嚴重的威脅。如前所述,信託財產是一項複合財產,在這項複合的財產中,不僅包括應當辦理登記手續的不動產、準不動產(汽車、輪船、火車、飛機、航空器等)、有限責任公司的股份、專利權、商標權、積體電路布圖設計權和植物新品種權等財產,也包括依法不需要辦理登記手續的有價證券(以及動產、金錢、普通債權和著作財產權等財產)。
其次,在信託公示的效力方面,我國《信託法(草案)》 (2000年4月稿)曾經採行對抗主義。該草案第18條規定:“委託人以法律規定應登記的財產進行信託的,應向有關登記機關辦理信託登記。未登記的,信託不得對抗第三人。”[15]但後來正式頒布實施的《信託法》又改採生效要件主義。
現行《信託法》對信託公示的效力的規定,雖“獨闢蹊徑”,但未必是最佳選擇。因為信託公示不同於一般財產權變動的公示。在一般的財產權公示中,無論采對抗要件主義還是生效要件主義,只要相關的制度配套、完善,在實踐中的效果並沒有太大差別。
結論
 信託公示
信託公示本文的分析表明,我國的《信託法》第10條關於信託公示的規定,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看,都存在明顯的缺陷,在將來修改《信託法》時,應當加以修改、完善。筆者認為,應當參照日本、韓國和我國台灣地區的《信託法》關於信託公示的規定,將我國《信託法》第10條修改為如下兩款。第1款規定:“設立信託,對於信託財產,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登記手續的,應當依法辦理信託登記。未辦理信託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第2款規定:“以有價證券為信託財產設立信託的,必需根據有關主管機關的規定,在證券上或其他表彰權利的檔案上載明為信託財產,否則不得對抗第三人。”
法律術語(九)
| 人類在社會層次的規則,社會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規範,以正義為其存在的基礎,以國家的強制力為其實施的手段者。法治和法律要逐漸變得適當寬容以利於社會和諧.法一般限於憲法、法律。法屬於上層建築範疇,決定於經濟基礎,並為經濟基礎服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