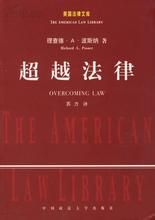作 者
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1939年元月11日出生在紐約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律師,母親是一位“非常左
 理察·波斯納
理察·波斯納傾”(波斯納語)的公立學校教師。他1959年以最優生畢業於耶魯大學英文系,1962年以全年級第一名畢業於哈佛法學院。在法學院期間,他擔任過《哈佛法學評論》主編(president)。他沒有拿過Ph.D,但他曾獲得過包括耶魯、喬治城等國內外大學的榮譽法學博士。1962年畢業後,一直到1967年,他曾先後在聯邦最高法院擔任大法官布冉能法律助手一年,並先後在其他政府機關任職,同時開始接觸並自學經濟學,形成了他的學術思想。1968年,他加入史丹福大學法學院,成為副教授;次年,他來到了芝加哥大學,擔任教授;1973年一部《法律經濟學分析》,給整個法律界帶來了一場“革命”(《紐約書評》語);1978年以後又成為法學院講座教授。1981年,里根總統提名他出任聯邦第七抗訴法院(在芝加哥)法官至今,並在1993年到2000年間因為資深擔任首席法官(院長),兼管該法院的一些行政事務。
內容簡介
但凡讀過波斯納著作的讀者莫不為其敏銳的思想、獨到的眼光、研究的廣度及對美國法律制度與司法體系深刻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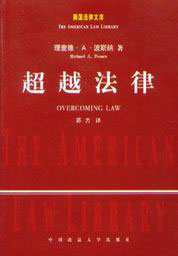 超越法律
超越法律所折服。《超越法律》是波斯納的又一部重要的法理學著作,作者本人把該書連同他1990年的《法理學問題》以及1999年的《道德與法理學理論的疑問》一起稱為自己的法理學三部曲,而《超越法律》更是進入了1995年紐約書評的學術暢銷書之列。 “這本書中不但有波斯納到目前為止對自己的法律、特別是司法哲學以及思想來源的最系統闡述,而且就其所涉獵的學術範圍和學術題目來看,也足以作為波斯納的代表作”。誠然,對於已經習慣了教科書式法理學著作或典型“專著之範式”的讀者而言,該書可能“有些奇怪和難讀”,但破解之法在於讀者要努力置身於作者的語境以及讀者需要對西方與美國法理學和哲學傳統有初步的了解。這樣,或許在“某個不特定的時刻,你會猛然間把作者的關係同自己的關心連線起來”而實現所謂的“視野的融合”並恍然悟出無論是法律抑或學術的某些道理“甚至會對人生和社會有某種感悟”。因為,這不是一本工具性的法律書,“而是一本從法律問題切入的視野廣泛的”著作,“正如其書名,是“超越法律的”。 該書的譯者認為法理學在中國法學界“面臨著某種困境”。其實在實務界何嘗不是如此。一旦涉及法理學問題,不少人言必稱“法治、憲政、正義、公平”等等“高級理論”與“大詞法學”。而法理學的深意於法官而言遠非止於此,法官要褪去工匠的“俗套”而涅盤成為學者乃至“學家”,“必須開拓理論法學的研究視野”。
評價
《超越法律》“既是一本法律理論的書也是一本關於法律理論的書”,延續了作者在他的第一部曲《法理學問題》中對法律理論的理解。由此出發,本書從一開始就向讀者表明了如下問題:超越什麼“法律”?為什麼要“超越”法律?如何“超越法律”?而作者對這些問題的闡釋無疑向我們提供了理解本書的鑰匙。
言論
波斯納要“超越”的法律到底是所指為何呢?如果我們意識到這本書與《法理學問題》的淵源,也就不難找到答案。而且在本書中,作者清楚地指出,“書名中所提到的這個‘法律’是一個職業圖騰,它指的是法律傳統中一切有爭議的、封閉的、有偏見的和不合邏輯的東西。”而在這一“職業圖騰”所象徵的事物中,首當其衝的便是從19世紀後期就開始充斥法學傳統的以形式主義法學為代表的概念主義,是那些“支配一切的正義觀”。
因此,“為什麼要超越法律?”這一問題也就不言而喻。實際上,波斯納在《法理學問題》一書中就已經給予了論述。令作者十分不滿的是,那些流行的所謂法學理論都無視法律實踐,都遠離實際的法律生活、迷失於意識形態爭論之中。這些法理學大多“與法律實務者的日常關係相距甚遠”,“它所設計的問題無法參照或根據常規的法律檔案推理而加以解決,它所運用的視角也無法演繹出法律原理和法律推理。”(《法理學問題》,“序言”,中譯本第1頁。)而這正是法律形式主義的流毒。而且,波斯納在他的最新力作《法律理論前沿》中還進一步指出了法律教育的不足:“傳統法律教育的焦點是實踐,是探討如何成為一個很棒的律師。其重點在於……職業價值,並且,越來越多地放在了獲得訴訟和談判技巧之上。這樣一種教育……可以塑造具有很高技巧的專業人士,……但是卻不能夠提供一個理解和改進這一系統的基本工具,因為它並不能培育必要的外在洞察力。”(“導言”,第1頁。)因此,必須超越“法律”,超越傳統的法學研究和法律教育。
不過,本書的書名以及作者對法律形式主義的抨擊並不表明作者反對法治,或者說,想用“經治”或其他專家治理來替代“法治”,波斯納從一開始就表明,他的目的在於以司法實踐為著眼點來重新理解法律,而不是灌輸某一種或幾種理論(比如經濟學)或者用理論來取代實踐。波斯納一直以來所作的工作正是要“推翻那些雄心勃勃的法律理論”;他在他的“法理學第三部曲”《道德和法律理論的難題》中更是全力以赴。
那么,究竟該如何“超越法律”呢?這正是本書的核心所在。波斯納指出,起初作為法律形式主義反動的現實主義法學除了粗略地延展了的霍姆斯和卡多佐的思想外並無建樹,也同樣是必須加以超越的對象。而且,“僅僅是一種批評的進路缺乏持久的力量;並且,即使是摧毀性的批評也不能摧毀,如果批評者沒有什麼可以取代他希望摧毀的廢墟。”所以,波斯納在批評的同時也注意了建構性的方面,指出了“通向替代性進路的途徑”。單就這一點而言,《超越法律》的思考比他的第一部曲《法理學問題》更為深入。
波斯納給出了把握法律理論問題的三柄鑰匙:實用主義、經濟學和古典自由主義。當這三柄鑰匙一起使用時,大門就會開啟,——用波斯納的話來說,就“可以使法律理論成為一個有效的工具,理解和改進法律以及一般的社會制度的工具,例證現存法律思想之不足的工具並以更好的東西予以取代的工具。”
首先,必須清除法律形式主義的流毒。法律形式主義的背後是“一種唯理主義,它對那些有爭議的形上學主張和倫理主張,要用純粹的分析手段來推導出有關的真理”。這也是波斯納對法律形式主義病因的診斷。要根治這一惡疾,必須“超越”教條與僵化,否則就會像現實主義法學那樣表面上反對但最終陷入另外一種概念主義。波斯納認為美國本土出產的實用主義哲學是最好的解毒劑。而波斯納理解的實用主義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實用主義,而是康奈爾·韋斯特在描述實用主義的“公分母”時抓住的那種意義,“一種努力以思想為武器、使更有成效的活動成為可能、以未來為導向的工具主義”。在概括這種實用主義的特點時,作者所用的形容詞是“實踐的”、“工具性的”、“向前看的”、“能動的”、“經驗的”、“懷疑的”、“反教義的”、“重視實驗的”,等等。只有這種實用主義作為一種實踐的方式、處世的態度、行動的工具,而不是某種描述、結論、看法、概念、標籤,才可能擺脫概念主義的厄運。
如果說實用主義進路能有助於瓦解作為那種圖騰意義的法律,那么,法律經濟學分析則是有助於用一些更好的東西來取代它。作為一個法學家兼經濟學家,波斯納強調“法律經濟學分析”絕不是許多人認為的,是用經濟概念取代法律概念,相反,“法律經濟學集中體現了實用主義意義上的科學研究倫理在法律中的運用。”經濟學作為最典型的工具性科學,它想像的理論個體正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現代經濟學可以很自然地“為法律迫切需要的經驗性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理論框架。”
不過,作者清楚地意識到,經濟學雖然好用,但絕不是萬能鑰匙。很顯然,“並非法律遇到的所有問題都能不費吹灰之力地轉化為經濟學的問題”,許多問題也根本“無法在經濟學內部給出答案”,甚至,“典型的功利主義和經濟學思考中還有不自由的隱含義”,我們又無法“通過配置權利來消解這些不自由的隱含義”。因此,波斯納承認,“在某些問題上,哪怕你非常信奉法律經濟學方法的人,也還是不得不在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問題上表明立場。”波斯納毫不掩飾地言明,古典自由主義是他的政治信念。
“喜好事實,尊重社會科學,折衷的好奇心、渴求實用,相信個人主義、以及對於新視角的開放,這是某種類型的實用主義、另一種類型的經濟學以及另一種類型的自由主義的全部的相互聯繫的特點”,“它們共同聯手構成了一個強有力的光束,可以闡明法律中的理論問題。”這就是“波斯納法理學”的要義,這就是“超越法律”的核心意涵。
通過這條波斯納所給出的“通向替代性進路的途徑”,我們可以進入這部60多萬字的著作之中,在走過那些被摧毀的“法律帝國”(羅納德·德沃金正是波斯納一再攻擊的對象)的廢墟的同時,也可以看到波斯納重新建立起的一座座現代法律大廈。
波斯納把本書分為建構性方面和批判性方面。引論和第一編以及第六編的各章主要是構建的,這些章節表明了和例證了作者認為法律理論應當如何研究。中間的各編主要是批判性的,這些章節表明和例證的是作者認為法律理論、包括某些形式的實用主義法律理論,不應當如何做。儘管本書許多部分最初都是一些論文或書評,但作者在成書時都作了許多細緻的修改,並在整體上進行了精心安排,“本書不是一個大雜燴或一本百科全書,它準備人們按順序連貫的閱讀。”
在第一編波斯納用了占本書四分之一的篇幅深入考察了“法律職業”問題,特別是法律職業的特點、法律職業的結構對法律思想的影響(第一章、第四章)、學術界與職業界的關聯(第二章)、法官的行為與效用(第三章)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其中許多見解頗為獨到和深刻。
其後第二編到第四編中,波斯納考察和批判了從所有意識形態範圍和方法論範圍內抽取的代表人物和相關法律理論,包括憲法理論(第二編)、法律理論中的多樣性和意識形態(第三編)性別與種族的問題(第四編)等許多內容。
作者對法律理論的理解是寬泛的,本書中涉及的許多廣泛的問題此前多被認為屬於政治理論或社會理論,而不屬於法律理論。而這種寬泛所反映出興趣的拓展,恰恰是當代法律學術的特點;本書的第五編“哲學視角與經濟學視角”和第六編“法學的邊陲”是作者的這種廣泛興趣的集中體現。第五編由四組文章組成,包括對實用主義(第十九章)、羅納德·科斯的方法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和當代哲學(第二十二章)等外在視角的討論;第六編由四組文章構成,包括對法律與文學(第二十三章)修辭與法律推理(第二十四章)、外在形象的法律保護(第二十五章)和經濟學與性態(第二十六章)等法學前沿問題的集中討論。
因此,作者說,本書的讀者將會發現,除了有關法官、法律職業、法學文獻、美國憲法以及規制就業契約的各章外,本書還有許多章處理的是性態、社會構建主義、女權主義、修辭、制度經濟學、政治理論以及文學中的法律描寫。作者甚至跑到了遠離常規法律理論的領域,涉獵了諸如貝多芬的祖先、中世紀冰島的血族復仇、古希臘的兒童養育以及聾啞兒童的教育這樣的題目。波斯納說,“這都是從我作為一個法官和一個法律學者的職業興趣中成長出來的。”這也是波斯納法理學一貫的特點。
經濟法學及相關著作
| 經濟法學是研究經濟法及其發展規律的法學學科,它與法理學、憲法學、行政法學、民法學、刑法學等同屬於法學體系的其他學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