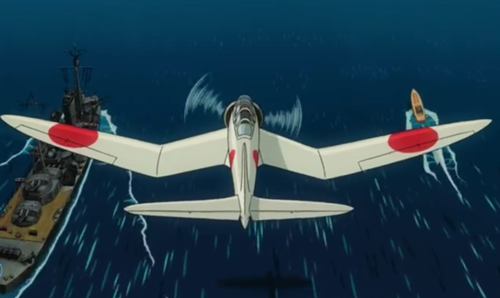安樂死,一個一直以來都備受爭議的話題。通常被用來指患不治之症,長期飽受精神和軀體極端痛苦生命垂危的病人,在病人及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過程。據了解,斯巴達人為了保持健康與活力,會處死生來就處在病態的兒童。然而16世紀起,人本主義思想興起,人們主張天賦人權,因此“安樂死”一說也沉寂一時。直到20世紀30年代,納粹德國崛起,“安樂死”被再次提出,並得到了大力的宣傳與推廣,不少鮮活的生命命喪納粹刀下,其中就包括一個特殊的群體——自閉症兒童。 自閉症兒童
自閉症兒童
奧地利兒科專家漢斯·亞斯伯格(Hans Asperger)一直被視為自閉症研究的先驅,也曾被當成英雄,因為他強調自閉症兒童具有高智商,使眾多患病兒童倖免於納粹清洗計畫。但是,在納粹德國時期,亞斯伯格參與謀殺殘疾兒童已是無可非議的事實。 圖1:20世紀40年代維也納Am Spiegelgrund診所的一個病房。
圖1:20世紀40年代維也納Am Spiegelgrund診所的一個病房。
歷史學家Herwig Czech在《分子自閉症》(Molecular Autism)的2018年4月刊上完整地記錄了這件事情。現在,歷史學家Edith Sheffer根據Czech的研究成果,再結合自己獨到的學術見解,寫成了一本偉大的書籍——《亞斯伯格的孩子》。她在書中強有力地指出,自閉症的基本概念源於一個竭力反對神經多樣性的社會。
如何保障診斷準確性,如何保障社會對自閉症患者的接受和支持,是自閉症患者長期以來所面臨的困境,而以上發現給自閉症的歷史又進一步蒙上了一層陰影。揭露出來的真相在自閉症患者及其家人、研究人員和臨床醫生中也引起了爭議,他們在討論是否應該廢除“亞斯伯格症候群”的診斷標籤。
1981年,精神病學家Lorna Wing在《心理醫學》(Psychological Medicine)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首次將亞斯伯格的臨床觀察記錄介紹給英語醫學界,並創造了“亞斯伯格症候群”一詞。十年後,發育心理學家Uta Frith在《自閉症與亞斯伯格症候群》(Autism and Asperger Syndrome)(1991)一書中,將亞斯伯格在1944年撰寫的聲稱發現了自閉症的論文翻譯成英文。
及至1994年,美國精神病學會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第四版中承認了亞斯伯格症候群。亞斯伯格症候群的症狀表現為興趣範圍狹窄,但是對興趣異常投入,在社會交往和溝通方面存在困難,同時具有正常或超常的智商,且語言發展並不遲緩。(在2013年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修訂版中,美國精神病學會刪除了亞斯伯格症候群條目,而採用了單一條目——自閉症譜系障礙。) 圖2:1940年左右,漢斯·亞斯伯格和一些兒童在維也納大學兒童醫院。
圖2:1940年左右,漢斯·亞斯伯格和一些兒童在維也納大學兒童醫院。
在對亞斯伯格的研究進行歷史鉤沉的過程中,Sheffer補充了John Donvan 和 Caren Zucker所著的《另一種音調:自閉症的故事》(In a Different Key)一書對亞斯伯格的推測。該書引用了Czech之前的發現。據Sheffer揭露,納粹企圖通過殺死他們認為不值得活的人,創造一個“純潔”的社會,而這直接導致了大屠殺。
通過深入細緻地挖掘史料,Sheffer揭示了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原本基於慈悲和同理心的精神醫學淪為納粹的作惡工具,被用於將德國、奧地利和其他國家的國民分成“基因”健康的和“基因”不健康的兩類人。在偽裝成“安樂死”的屠殺計畫下,精神病醫生和其他醫生需要決定哪些人能活,哪些人得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出現了“自閉性精神病”(亞斯伯格所創)一類的診斷標籤。
Sheffer將證據一一鋪開,包括醫療記錄和轉診信等,它們全都表明亞斯伯格是納粹殺人機器的同謀。他的確保護了他認為聰明的孩子,但是他也把一些孩子送入了維也納的Am Spiegelgrund診所。他當然知道這個診所是一個“兒童安樂死”中心,這箇中心後來被納為T-4行動的一部分。 納粹醫生人體醫學實驗
納粹醫生人體醫學實驗
就是在這裡,納粹將那些被他們認定為“基因低劣”的兒童殺害,納粹認為這些孩子無法遵從社會規範,或者帶有他們認為是不良的生理或心理缺陷。一些孩子被餓死了,另一些則被注射死,但是卻被記錄為死於肺炎等。Sheffer提出,亞斯伯格支持納粹清洗那些被認為與“人民”(Volk)格格不入的兒童。Volk指全為雅利安人的法西斯理念。
Czech 和 Sheffer都詳細敘述了兩個無血緣關係的孩子的故事以及由亞斯伯格親筆簽名的轉診信。這兩個孩子分別叫Herta Schreiber 和Elisabeth Schreiber。在轉診信中,亞斯伯格解釋Herta 應該被送到Am Spiegelgrund的理由是:“她對她的母親來說一定是一個無法承受的負擔。”Elisabeth的理由是:“毫無疑問,這個孩子是她的家人難以承受的一個負擔。”這些證據都表明亞斯伯格等於是簽下了這兩個孩子的死亡判決書。近800名兒童在Am Spiegelgrund被殺害,而亞斯伯格卻成為學術界的“常青樹”,直到1980年去世。
《亞斯伯格的孩子》一書和Czech的論文都指向了同一個結論。就我個人而言,我現在再也無法接受以亞斯伯格來命名這個疾病。無論如何,亞斯伯格症候群已經從美國通行的最新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刪去了。2019年歐洲國家也會在《國際疾病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的第11版中效仿美國的做法。
當然,未來在討論這個詞的使用時,必須考慮自閉症人群的觀點。許多人把亞斯伯格症候群當作其身份標示的一部分而感到自豪,他們認為這個病名表明了他們的個性和認知風格,而這顯然不會因為歷史真相而輕易發生改變。這些人可能不想要換病名,不過也有一些人要求把病名改成“自閉症”(或自閉症譜系障礙)。
為簡明和中立起見,我支持用“自閉症”這個詞。但是,由於自閉症人群異質性很高,我認為他們應該和家屬、自閉症研究者、臨床醫生以及其它相關專業人員共同討論是否應該引入自閉症亞型。
在Wing創造出“亞斯伯格症候群”這個詞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亞斯伯格是納粹的積極支持者。根據Sheffer 和 Czech的歷史研究結果,我們現在是時候改變對他這個人的看法了,說不定還包括對某些用詞的看法。心理學、精神病學和醫學生都應該讀一讀《亞斯伯格的孩子》這本書,這樣我們才能以史為鑑,避免重蹈覆轍。這本書揭露的殘酷事實提醒我們,慈悲應該被擺在臨床研究和實踐的首要位置。
納粹 自閉症 科技生活 安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