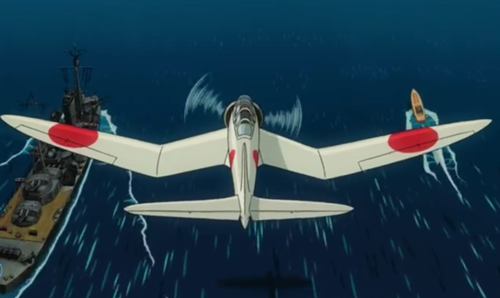自18世紀,奧地利著名物理學家薛丁格提出了一個關於貓的思想實驗之後,薛丁格貓到底死了還是活著始終是困擾人們的一大難題。然而,一群科學家正嘗試通過雙縫干涉實驗,讓觀測者用肉眼驗證量子疊加態。更令人激動的是,他們的實驗還可能為量子力學的一個核心問題——測量問題找出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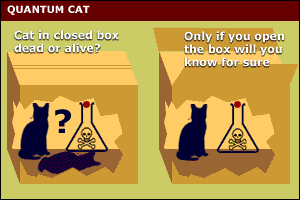 薛丁格貓
薛丁格貓Paul Kwiat要求志願者們坐在一間黑暗的小屋裡。在他們的眼睛逐漸適應黑暗環境時,每一位志願者就像驗光時一樣,將頭支撐在一個支架上,用一隻眼睛盯著一個很暗的紅十字看。在十字的兩邊各有一根光纖,可以將單個光子從十字左邊或右邊射入志願者的眼中。
Kwiat是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的實驗量子物理學家,在驗證了人眼探測單個光子的能力後,他和同事有著更高的目標:根據他們上個月在預印本網站arXiv上提交的論文,他們想要用人眼去驗證量子力學的基本假設。
他們並不是簡單地將一個光子通過左邊或者右邊的光纖送入志願者眼中,而是輸送一個同時處於左邊和右邊的量子疊加態的光子。人們會看到什麼不一樣的現象嗎?根據標準量子力學,答案應該是“不能”。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人做過這類測試。如果Kwiat團隊的最終結果和理論預言不同,就會動搖我們對量子世界的現有理解,人們也將嘗試通過一些其他理論來解釋量子力學。這些理論對自然的看法與現有的完全不同,它們預言現實的存在與觀測行為和觀測者無關。如果成立,我們對量子力學的現有解釋將被徹底推翻。Rebecca Holmes是Kwiat以前的學生,現在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他設計了這套實驗裝置。他說:“這可能成為超出標準量子力學的現象存在的證據。”
肉眼觀測單個光子
為了探究人眼是否能直接觀測到單個光子,近一個世紀的物理學家做了大量努力。1941年,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人員在Science上發文稱,即使一束光中只有五個光子落在視網膜上,人眼也能看到。30多年後,當時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生物物理學家Barbara Sakitt通過實驗似乎驗證了人眼可以看見單個光子。不過,這些實驗遠遠不能給出確定的結果。Holmes說:“這些實驗的問題在於它們都試圖使用‘經典’光源”,但我們無法確定經典光源發出的到底是不是單個光子。也就是說,我們甚至不能保證那些早期實驗都只用了單個光子。
直到2012年,人們有了確鑿的證據,發現青蛙眼中的光感受器,或稱視桿細胞,可以探測到單個光子。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的Leonid Krivitsky和同事從成年青蛙的眼中提取了視桿細胞,隨後通過實驗證實這些細胞對單個光子有反應。Kwiat說,現在“毫無疑問單個光感受器是可以對單個光子有反應的。”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視桿細胞在活體青蛙或者人體中有著相同的效果。因此,Kwiat和他在伊利諾伊的同事Anthony Leggett等人開始計畫用單光子光源測試人類的視覺。很快,Kwiat團隊開始了實驗。現在,Holmes也加入了團隊,負責實驗操控。但是“我們當時失敗了。”Holmes說。
2016年,當時在維也納大學的生物物理學家Alipasha Vaziri領導的研究團隊報告稱,他們用單光子光源證實了“人眼可以探測到單光子事件,而且探測到的機率很高,這顯然不是巧合。”
雙縫實驗解決測量問題?
Kwiat團隊對這個結果有些懷疑,他們想要用更多志願者、做更多實驗以提高數據的確信度。他們擔心的核心問題是眼睛探測光子時的低效。入射光子必須首先經過眼球最外面一層透明的角膜,這會反射掉一部分光。接下來光子進入晶狀體,晶狀體和角膜共同將光匯聚在眼球後部的視網膜上。而在視網膜和晶狀體之間,凝膠狀的玻璃體也會吸收或散射光子。最終,抵達角膜的光子中,只有不到10%能出現在視網膜上的視桿細胞中,進而產生神經信號,神經信號傳送到大腦就形成了視覺。所以,得到可以在統計學上排除偶然性的顯著性差異,是一項令人生畏的挑戰。Kwiat說:“我們希望在未來六個月得到確定的答案。”
這並沒有使他們停止設計新的實驗。在標準設計中,一面半塗銀面鏡會讓光子進入左邊或右邊的光纖,然後落在左眼或右眼的視網膜上,志願者就會敲擊鍵盤來表示他們看到的方向。但是,研究者也可以很容易地利用量子光學技術製造出疊加態的光子,使其同時進入兩條光纖,然後同時出現在左右雙眼的視網膜上。接下來光子到底發生了什麼,取決於你相信光子發生了什麼。
物理學家用一種叫做波函式的數學抽象概念來描述光子的量子態。在疊加態的光子打在視網膜上之前,波函式會彌散出去,這時光子在左邊和右邊被發現的機率相同。光子和視覺系統的作用是一種觀測,而人們認為觀測會使波函式“坍縮”,於是光子最終會處於其中任意一邊,就像拋出去的硬幣最終朝上的會是正反面中的任意一面。當人眼接收到疊加態的光子時,出現在左右兩側的光子數目會有差異嗎?Kwiat說:“如果你相信量子力學,那就沒什麼區別。”但是如果他們的實驗發現了無法駁斥的顯著性差異,那就說明量子力學一定存在什麼問題。他補充說:“這將會是一個大發現,一個驚天動地的結果。”
這樣的結果預示著人們可能會解決量子力學的一個核心問題:測量問題。假如波函式真的因為測量而坍縮,量子力學理論並沒有表明這種坍縮是如何發生的。測量的儀器應該有多大?以眼睛為例,一個視桿細胞夠大嗎?還是需要整個視網膜?又是否需要角膜?是否需要有一個有意識的觀測者呢?
坍縮與觀測
一些候選理論通過使坍縮完全獨立於觀測者和測量儀器,來解決這個潛在問題。例如“GRW”坍縮模型(以理論物理學家Giancarlo Ghirardi,Alberto Rimini和Tullio Weber命名)。GRW模型及其變型都假設波函式是自發坍縮的。處於疊加態的物體質量越大,坍縮就越快。這個理論的結果之一是,單個粒子可以無限長時間地處於疊加態,但是巨觀物體就不行。所以,在GRW理論中,著名的薛丁格的貓是無法處於活與死的疊加態的。像GRW這樣的理論被稱為“無關觀測者”的現實模型。
如果像GRW這樣的理論對自然的描述是正確的,我們這一個世紀以來想要證明的想法就完全錯了。我們一直都認為觀測和測量是構成現實世界的中心要素。關鍵是,當處於疊加態的光子落在視網膜上時,GRW理論預言的兩邊的光子計數將和標準量子力學存在一些細微的差別。這是因為在光子的傳輸過程中會和不同大小的系統發生作用,比如兩個視桿細胞中的兩個感光蛋白是一個系統,兩個視桿細胞及相應神經的組合又是一個系統,光子在和這兩個系統作用時會表現出不同的自發坍縮速率。儘管Kwiat和Holmes都強調在他們的實驗中不太可能會看到什麼不同,但他們也承認,如果發現了任何與經典理論的差別,就可能預示著GRW這類理論是正確的。
Michael Hall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理論量子物理學家,他並沒有參與這項研究。Michael同意GRW預言的光子計數和經典理論會出現很小的差別,但是他說這樣的差別太小,已經提出的實驗是無法探測到的。然而,他認為光子計數上任何的異常現象都值得關注。他說:“這很值得認真思考。我覺得這種偏差出現的機率極小,但是還是有可能。這非常有意思。”
Kwiat也想了解量子態和經典態的主觀感知差異。他問道:“人在直接觀測量子事件時會感受到差異嗎?答案‘很可能不會’,但是我們確實不知道。你永遠得不到答案,除非你為人的視覺系統建立一個量子力學級別的完備模型,或者,通過實驗進行觀測。我們無法建立這樣的模型,所以就只能去做實驗了。”
Robert Prevedel在2016年是Vaziri研究團隊中的一員,現在在德國的歐洲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工作。他更感興趣的是在一系列事件中找出波函式坍縮的具體位置。坍縮是發生在最初光子打到視桿細胞上時?還是在神經信號產生和傳遞的中間過程中出現?或者是最後信號使人產生視覺時?他提議將視網膜提取出來,再向其發射處於疊加態的光子,記錄不同階段的視覺處理過程(比如記錄視桿細胞,或是組成視網膜的其他感光細胞的信息)來看看疊加態到底持續多久。
Prevedel認為視桿細胞對光的吸收會使得疊加態消失。但是他說:“如果我們看到量子(疊加態)存在於光子接觸視桿細胞後的任何一個階段,不論是在視網膜內不同細胞層中,還是在之後的神經迴路中,都將是真正的突破。這將是一個非常驚人的發現。”
還有一個大家常常故意視而不見的問題:人類的意識。意識能造成量子態坍縮,讓光子最終只在一邊出現嗎?但Prevedel卻對意識與測量、坍縮之間是否真的存在關聯持懷疑態度。
Prevedel說:“意識是人腦中細胞和神經元的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細胞和神經元很多,沒有幾十億也有幾百萬。如果意識在量子疊加態的探測中起到了作用,那么這個過程就會牽扯到尺寸和大腦相當的巨觀物體,例如組成生物細胞的大量原子和電子的集合。但根據我們已有的知識,這種巨觀物體是無法保持量子疊加態的。”
科技生活 薛丁格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