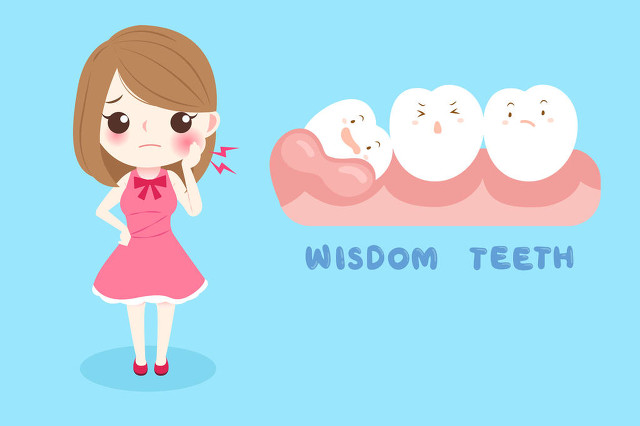公元1763年,歷時整整7年的英、法戰爭終於以法國及其盟友的全面戰敗而結束。根據英法兩國簽署的《巴黎和約》,法國加拿大地區割讓給英國。將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路易斯安那地區轉讓給西班牙,以補償這個由波旁王朝分支所執掌的國家在戰爭中被迫將佛羅里達割讓給英國的損失。至此法國在北美的殖民地,只保留了加勒比海的幾個小島為法國漁船提供港口。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法簽署和約之前的談判中,法國實際上還面臨著兩個選擇——是割讓新法蘭西,還是割讓加勒比海盛產蔗糖的瓜德羅普。最終法國選擇了後者,因為在巴黎看來法國還能夠從瓜德羅普獲取利潤,而遼闊的新法蘭西則是一個財政黑洞。無獨有偶,英國政府也對面積廣闊的路易斯安那地區沒有興趣,譏笑獲得其主權的西班牙不過又多了一片“荒漠”而已。
據說《巴黎和約》最終簽字畫押之際,法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德韋爾•讓曾不無預見性的指出:“英國人贏了,但對英國來說是一種極其有害的勝利。因為失掉了法國這種抗衡力量,英國的殖民地將不再需要它的保護”。這番話固然有泛酸的醋意,但卻也道出了英國政府於七年戰爭之後在北美問題上的尷尬。在這場漫長的戰爭之中,為了維繫廣闊空間之中多戰線的同時運轉,英國政府不得不打破自克倫威爾軍政府垮台以來精兵簡政的國防理念,在保持歐洲頂尖海軍的同時,豢養了龐大的地面部隊。隨著《巴黎和約》的落筆,面對巨額的赤字,裁軍自然勢在必行。
海軍方面的工作相對簡單一些,只要停止向各大船隻下發訂單,只劃撥有限的經費用於維修現有艦艇便可以開源節流。當然由於英國海軍部內部的貪污奢靡之風,事實上“七年戰爭”之後,英國海軍的撥款甚至比七年戰爭最激烈的時期的還高得多,但戰艦卻依舊在軍港中逐漸朽爛,維修和改裝的大筆款項卻不知所蹤。以至於不久之後,英國海軍一度沒有足夠的船隻把哪怕是最少的兵力運往北美。
與海軍相比,英國陸軍的情況則更為複雜一些。一方面削減常備軍的工作勢在必行。但另一方面“七年戰爭”之後英國卻有著更為遼闊的海外領土需要守護。於是乎將維繫陸軍的軍費開支轉嫁給各殖民地,便成為了簡單有效的解決之道。但在“七年戰爭”中為英國遠征軍貢獻了大量錢財、物資的英屬北美殖民地此時卻出現了抗拒的聲浪。理由很簡單,竟然英國政府口口聲聲說駐軍在北美是為了保護那裡的人們,那么必須回答殖民地人們:“敵人是誰?”
▲ 身著古典盔甲的阿默斯特
“七年戰爭”後晉封為男爵,繼續統領北美駐軍且兼任維吉尼亞總督的阿默斯特試圖解決這一矛盾。在攻占蒙特婁之後,他對昔日生活於英法勢力範圍夾縫中的印第安部族採取了高壓政策,試圖以印第安人來恐嚇日益對英國陸軍缺乏需要的殖民地居民。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阿默斯特的策略很成功,英法戰爭的烈火還沒熄滅,北美殖民地便烽煙再起。不堪忍受英國駐軍種種刁難的印第安人開始襲擊殖民者的村莊。
一時間英國駐軍再度成為了英屬北美的保護神。但長期生活於歐洲大陸的阿默斯特顯然對印第安人缺乏了解,他錯誤的將這些以漁獵為生的部族想像成只會打家劫舍的匪幫,卻忽視了印第安人為了捍衛自己世代生存的土地和傳統生活方式而迸發出的勇氣和毅力。公元1763年初,隨著渥太華部落首領龐蒂亞克被公推為大湖地區的印第安部族聯盟首領,一場規模空前的“龐蒂亞克戰爭”隨即打響。
從公元1763年5月開始,印第安部族用了2個月的時間便幾乎掃蕩了整個大湖地區所有英國殖民點,大批難民被迫湧入以昔日路易十四時代海軍大臣命名的皮毛交易中心——蓬查特蘭堡。阿默斯特自認龐蒂亞克此舉恰好給了英國正規軍大顯身手的機會,隨即命令英國陸軍前往鎮壓,可惜的是阿默斯特此時所要面對的不是習慣正面交鋒的法國人,而是在叢林中神出鬼沒的印第安獵手。幾路英國援軍不是中了埋伏全軍覆沒,便是被冷槍暗箭打的灰頭土臉。好在印第安部族聯軍沒有大炮,利用大湖地區的水上運輸,蓬查特蘭堡也不至於彈盡糧絕,最終龐蒂亞克主動撤圍而去。僥倖保全的蓬查特蘭堡才得以在日後以另一個法文名字:底特律,取得蓬勃的發展。
“龐蒂亞克戰爭”不僅沒有令英國正規軍獲得在北美駐紮的合法性,反而令阿默斯特顏面掃地。這位英法七年戰爭中的英雄無奈的被召回倫敦。取代他的是皇家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此時龐蒂亞克所領導的印第安部族仍在大湖地區橫行,因此伯納德深知在駐守北美的上萬英軍暫時不能撤走,那么每年所需的23萬英鎊軍費便只能由治下的北美殖民地自行消化。竟然指望當地民眾自願分攤無法實現,那么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徵稅”來籌款。
▲ 渥太華部落首領龐蒂亞克
公元1764年4月英國國會通過了旨在打擊英屬北美走私貿易、整頓海關關稅的《種植地條例》,由於其主要針對的商品是糖漿及其衍生產品朗姆酒,因此這部法案又被稱為《糖稅法》。對流入北美的糖漿課稅事實上早在1733年便被寫入英國法律,但由於種種原因長期沒有得到認真的執行。英國政府此時舊事重提,實在是被北美殖民地的“不法商販”逼出來的。整個七年戰爭期間,英屬北美的商賈肆無忌憚的與法國人進行軍需品貿易,各種走私活動更是甚囂塵上。
更為過分的是麻薩諸塞州的商人更向當地法庭起訴,要求認定當地海關官員上船緝私為非法行為。面對這種目無法紀的行為,英國政府決心挫一挫北美商人的氣焰,同時也正式確立英屬北美財稅體系。可惜的是糖漿和朗姆酒都並非是生活必需品,北美大陸同樣也能生產,因此《糖稅法》除了收穫英屬北美要求選舉議員進入英國國會的“無代表不納稅”之外,每年僅能榨取1.4萬英鎊的相關稅收。
《糖稅法》的失利並沒有打消英國征服想從英屬北美這隻鐵公雞身上拔毛的念頭,於是公元1765年英國國會又先後通過的《駐軍條例》和《印花稅法》。《駐軍條例》是將“七年戰爭”期間遠征北美的英國陸軍駐紮常態化,殖民地各州需要向駐軍提供營房及其他軍需物資。可惜的是經歷了“七年戰爭”,英國遠征軍在殖民地民眾的心目中早已形象掃地,《駐軍條例》非但沒有緩和矛盾,反倒令北美各州對英國政府更為猜忌。
英國經濟學家哥爾柏曾經說過:“稅收的藝術便在於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1765年2月9日以204票贊成對49票反對在英國國會通過的《印花稅法》顯然是違背這一原則的最佳反面教材。“印花稅”是一種古老的稅種,它最初所主要針對的是日常經濟生活中使用契約、借貸憑證之類的單據,但是英國政府為了廣開稅源,竟然要求北美十三殖民地所有印刷品都必須交納印花稅,既然連撲克牌都不能倖免。撲克牌漲價對民眾的生活影響不大,但是殖民地靠報紙吃飯的富蘭克林等一乾媒體人卻顯然坐不住了。
作為一個利益集團的代表,在自己的墓碑上都刻上“一個印刷工人”的富蘭克林首先跳出來反對即將實行《印花稅法案》,而作為掌握著輿論導向的傳媒人,富蘭克林和他的同行們除了直接向英國議會進行請願之外,更在北美殖民地利用自己的報紙大造聲勢。一向喜歡誇大事態的記者和編輯們將向他們徵稅,說成是向“向知識徵稅”,一時之間早已被“七年戰爭”折騰得民怨沸騰的北美殖民地頓時呈現出群情洶湧的態勢。
英國政府無奈之下只能派人前往安撫富蘭克林,此時這位賓夕法尼亞的新貴早已躋身英國上流社會,於是一番“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後,富蘭克林的態度立即由反對徵收印花稅,轉為替英國政府辯護。於是“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除了死亡和納稅”這樣的名言便堂而皇之的出現在了由其編寫的《窮人理查年鑑》之上。
可惜的是富蘭克林的在北美的影響力遠不如英國政府所想像的那般一言九鼎。倫敦權貴對這位頭面人物的招攬非但沒有起到千金買骨的作用,反倒令富蘭克林在北美成為了萬夫所指的對象。《印花稅法案》在美國街頭引起了騷亂,民眾紛紛發表激烈的反對演講,斥責這一專制行為。鑒於當時富蘭克林的兒子威廉已經擔任了新澤西州的州長,富蘭克林的不少親朋也躋身徵稅官的行列。
所以不少人將富蘭克林也列為《印花稅法案》的罪魁禍首之一。在費城富蘭克林位於市場街的寓所,他的妻子德博拉由於害怕民眾的憤怒情緒爆發甚至召集親友與之持槍對峙。不過富蘭克林在賓夕法尼亞畢竟經營多年,憤怒的民眾在他的寓所門口表示了抗議之後也就自行退散了。而在“五月花”號乘員所創立的麻薩諸塞州,抗議“印花稅”的示威遊行,最終演變成一場衝擊各類政府機關的“打砸搶燒”。在該州首府波士頓等地不僅徵稅官被施以淋嬌柏油,黏貼雞毛的私刑,連副總督托馬斯•哈金森的宅邸也被洗劫一空。
波士頓人之所以敢於如此明目張胆的挑戰王權,背後自然有其經濟利益推手。作為英屬北美最大的港口,波士頓當地聚集了大批商賈。他們或以進出口貿易漁利或以走私發家,因此無論是《糖稅法》還是《印花稅法》,對於這些商人而言都是英國政府赤裸裸的在分薄他們的財富。在這些有錢有勢的“金主”煽動之下,盲從的民眾也跟著群情激奮。而為了給自己的“抗稅”披上合法的外衣,以詹姆斯•奧提斯為首的一乾律師提出了一句著名的口號:“無代表,不納稅”,這句冠名堂皇的理由背後其實還埋下一個伏筆,即便英國政府出面妥協,吸收北美代表進入議會,波士頓人也拒絕承認這些國王的走狗,因為不替殖民地說話的代表,根本代表不了殖民地民眾。
在這個頗為牽強的邏輯之下,公元1766年2月13日,富蘭克林來到位於倫敦的英國國會論述廢除《印花稅法案》的理由。在長達4小時的時間裡,面對著眾議員富蘭克林答覆了174個問題。後來英國哲學家伯克描述了這場戲劇性的答辯,說那就像是一位大師在回答一群學生的提問。富蘭克林提醒議會,北美殖民地人民仍把自己視為英國人,只要他們受到尊重就會一如既往地支持英國政府。
富蘭克林的演講打動了英國政府,北美大陸的民怨沸騰最終令英國政府意識到了自己拔了一隻最善於啼叫的雄鵝之毛。迫於北美大陸抵制英國產品所帶來的商業損失,1766年4月新任英國首相——“羅金漢侯爵”查爾斯·沃森·文特沃斯不得不宣布撤銷了《印花稅方案》。但此時整個“鵝群”卻已經被驚醒,英屬北美十三殖民地隨後進入“增稅—抵制—鎮壓”的惡性循環。當英國政府不得不派出武裝部隊進駐城市以維護其在北美殖民地的正常社會秩序,戰爭也就進入了倒數計時。
英國 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