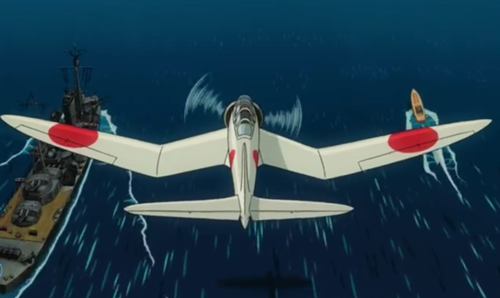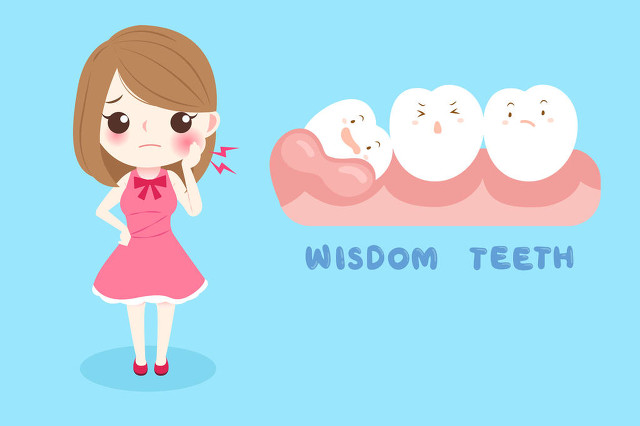民國初年,在尊孔讀經的逆流中,以史證經的論調再度甚囂塵上,史學脫離經學束縛、走向現代化的進程確實有所延緩,但並未停滯不前,除新歷史考證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蓄勢待發外,新史學也藉助歷史教科書等媒介繼續發揮著潛移默化的影響,特別是梁啓超始終踐行自己的史學主張,即使處於學術低潮期依然撰寫了著名的《歐洲戰役史論》。此種略顯沉寂的局面在“五四”前後被徹底打破,中國史學也隨之迎來“百家爭鳴”時代。當時及此後學人在梳理總結這一線索極其紛繁、格局極其複雜的時期的史學時,雖因立場差異而致敘事中心有別,但大體上都認可以史料為中心的考史風氣的形成和瀰漫,有的研究者甚至明確提出:梁啓超被胡適俘虜,新史學被新漢學腰斬,唯物史觀派則是新史學的再生。歸結為轉變和起伏的單線解讀模式自然可令繁雜的史學面貌頓時變得清晰,但細究起來,似乎仍有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餘地。
 梁啓超“新史學”的追隨者
梁啓超“新史學”的追隨者從研究範式和學術風氣上講,梁啓超和胡適分別開闢了以歷史解釋和歷史考證為中心的史學科學化道路,後者所代表的治史路數在當時被稱為“新漢學”,而梁啓超後期確實對考證多所倡導,但由此得出“俘虜”和“腰斬”的結論,則顯然有失偏頗。梁之所以詳細闡明史料的蒐集、整理和鑑別之法,並有所實踐,從外部時代環境來說,是中國現代史學機制逐步確立,史學走向專業化、職業化和學院化的客觀需要;就內在學術理路而言,則主要是因為,最初建構的新史學體系,雖然認可格林威爾“Paint me as I am(畫我須像我)”的理念,並讚揚清儒“以實事求是為學鵠,頗饒有科學的精神”,但基本忽略了史料問題,遭到後起“‘新漢學’派的歧視”,批評其“宏博而不堅實,則有疏淺之弊”,遂開始有意識地進行反思和彌補,“頗欲爭一日之長”,乃至於“胡適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種極無價值的東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這種不值研究的東西研究一番,有時還發表一篇文章來競賽一下”。以梁啓超當時的影響而論,這一學術行為無疑有力助推了考史風氣的興盛。
 梁啓超“新史學”的追隨者
梁啓超“新史學”的追隨者然而,近代史家的思想常態,往往是變與不變並行而共存,關鍵在於考察變數對於學術取向的影響。梁啓超對歷史事實的強調,並不意味著放棄對歷史哲學的探求,前者實統攝於後者。換言之,在其史學體系中,考證僅為手段,屬於基礎層次,此之上的解釋方為目標,亦即史學的完成。《歷史研究法》對於如何利用史料考證事實給予了極為細緻的展示,但也明確指出:“善治史者,不徒致力於各個之事實,而最要著眼於事實與事實之間,此則論次之功也。”《清代學術概論》則稱:“以經學考證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謂之考證學,殆不可謂之史學。”他甚至將史學走向窄深一途斥為“病的形態”,立場之鮮明可見一斑。而他對進化史觀和因果關係的懷疑、修正,對史學功能、史學動力、史學科學屬性及同其他學科的關係等問題的重新審視,乃是對原有史學體系的深化、完善,所反映的是思想資源獲取途徑以及中西文化態度的轉變,卻非治史範式的轉移。
 梁啓超“新史學”的追隨者
梁啓超“新史學”的追隨者新史學的產生和風靡,折射出中西之間文野地位的轉換以及從西學為用到中學不能為體的思想歷程,畢其功於一役的心態促使新型知識人對傳統史學展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革命,晚清以來不斷增強的激進情緒也藉此迅速滲入文化領域。對幾千年的史學積澱採取近乎全盤否定的態度,其負面影響自不可小覷,所提出的諸多主張亦極為簡略並有明顯的模仿痕跡,但它不僅為推翻君主制貢獻了力量,而且初步建構起與西方現代史學相接軌的典範,進而拉開了中國史學走向世界舞台的序幕。其間,梁啓超是當之無愧的領導者,影響也最為廣泛。呂思勉曾於1941年撰文稱:
他那種大刀闊斧,替史學界開闢新路徑的精神,總是不容抹煞的。現在行輩較前的史學家,在其入手之初,大多數是受他的影響的……他每提出一問題,總能注意其前因後果,及其和環境的關係,和專考據一件事情,而不知其在歷史中的地位的,大不相同;所以其影響學術界者極大。
 梁啓超“新史學”的追隨者
梁啓超“新史學”的追隨者這段話既在某種程度上道出了新史學與新歷史考證學之間的學術分野,也提示我們應充分留意梁啓超對民國史學的影響。經過近10年的傳播,梁啓超所倡導的諸多理念如用進化眼光看待歷史、以“民史”取代“君史”、援引其他學科治史(尤其是社會學)等已由最初的新鮮知識轉化為普通常識,不僅指導一般人認識歷史,更內化為史家的學術自覺,既成為新歷史考證學之所以“新”的重要條件,同時又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興起培育了適宜的學術土壤。就思想史的演進脈絡而言,梁的中心位置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而迅速被胡適、陳獨秀等人所取代。以往研究常常將這一結論引入對史學格局的描繪,遂有新歷史考證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雙流並進之說,並多視新歷史考證學為主流。事實上,中國現代史學機制的建立至“五四”前後才真正起步,而梁以敏銳的學術意識和嫻熟的西學輸入技巧完成了原有史學體系的提升,並產生雙重效應。一方面,他對史學方法的著意彌補與胡適等形成共振,促進了新歷史考證學的發展;另一方面,對歷史哲學的繼續探索大大推動了史學理論的發展,並於20世紀30、40年代形成高潮。金毓黻就曾在1938年7月3日的日記中感嘆梁啓超的巨大學術影響力曰:“祖述其說者大有人在。”
 梁啓超“新史學”的追隨者
梁啓超“新史學”的追隨者民國時期,隨著文化領域的激進態勢愈演愈烈,西學輸入、傳播的廣度和深度不斷增強,新舊之間的流轉速度大大加快,“新史學”這一概念也逐漸被泛化,既在具體內涵上由單一向多元發展,參照對象也不再是純粹的傳統史學,新的史學思想之鏇起鏇落幾成常事,這無疑加劇了對此時期史學梳理的難度,有學者甚至總結出十幾種史學思潮或流派。劃分的方式自然見仁見智,但若歸結到治史目標、風格及實踐上來綜合考察,則有三條路徑似頗為清晰可見。一是,本著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致力於考證歷史真相;二是,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組成部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興起;此外,還有一批數量十分可觀的學者,他們不以考證為旨歸,而致力於歷史解釋,但又不信奉唯物史觀,更不具有社會革命性,多在史學理論及歷史編纂學領域有突出表現。以往多強調其差異性,忽略了統一性,實則就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而言,這恰恰是對早期新史學的繼承、拓展與深化。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在思想來源上較為多元、複雜,但很多人都明確表示受到梁啓超的影響。
其中,尤以張蔭麟、楊鴻烈、蕭一山、呂思勉等最能傳承、發揚梁氏之學。張蔭麟被時人譽為“承繼梁任公學術志業的傳人”;楊鴻烈則被稱為“梁氏一家之學”。蕭一山曾說:“梁先生之精神偉大,非一般人所能喻,余面承教誨,身體力行,一生行事,絕不敢違背。”呂思勉亦稱:“粗知問學,實由梁先生牖之,雖親炙之師友不逮也”;“至於論事,則極服膺梁先生。”他們大都對流於瑣碎的考史風氣給予嚴詞批評,並準確揭示出梁啓超以理論和通識見長的治史風格。比如,楊鴻烈指出:“梁任公先生編著的一部在中國史學界照耀萬世的《中國史學研究法》出世,然後中國人腦里,才有比較明瞭的一個史學的輪廓。”呂思勉認為:“任公……所長實在通識方面,考據並無甚稀奇……最能以新學理解舊史實,引舊史實證明新學理。這對於讀者,影響最大。”張蔭麟亦謂:“任公所貢獻於史者,全不在考據。”而蕭一山在《悼張蔭麟君》中的一段話則最具說服力:
當時我自己有一套理論,就是極力提倡通史通儒通才,援引顧亭林章實齋之說,反對當時餖飣瑣碎風靡一世的考據派史學,我在講義緒論中曾再三言之,講堂中也有所闡發。任公先生說我有膽量有見識,但他不願公開提倡,因為他受了“新漢學”派的歧視,頗欲爭一日之長,實則他老先生的成就,已遠紹亭林,近逼實齋,絕非“新漢學”家所比擬,而蔭麟兄今日對於學術界最大之貢獻,亦即在此。可以說是任公先生的薪傳,蔭麟兄實為接承之第一人,使二人地下有知,必當含笑謂余知言也。
從上述學術體認可知,講求實證的新歷史考證學基本作為講求理論的新史學的反動面相出現,儘管二者在任何史家身上都無法截然分開,但終究取向有別,張力明顯,只是這種反動並未造成斷崖式結果,新史學雖喪失了原有的磅礴之勢,卻轉向精深發展,真正完成從“破”到“立”的蛻變。
梁啓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