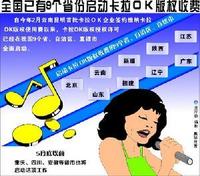簡介
當事人一方在外國領土上依照該外國的國家法律或行政命令作出的行為,或在當事人本身是外國國家的情形下,該外國國家在其領土內作出的行為,或外國國家官員在該外國的領土內依據該外國法律或行政命令作出的行為,法院能否審查作為上述行為依據的外國法律和行政命令的合法性,從而確定行為人的法律責任,這就是國家行為原則(ActofStateDoctrine)所要回答的問題。實踐中,不同國家的法院在不同時期所審理的有關案件中,有的適用該原則,有的卻排除該原則的適用。
國家行為原則適用的效果是,法院不能審查外國國家行為的合法性,而應推定該外國的國家行為合法,因而外國國家,其官員或私人當事人無須按法院地法律承擔法律責任。
特點
 孫必乾:外交是國家行為
孫必乾:外交是國家行為(2)該外國的國家行為是在其管轄範圍內作出的,其官員的行為也是根據這種國家行為在該外國管轄範圍內實施的。如果當事人是私人,則該私人受制於這種國家行為。
(3)外國國家行為依法院地法律是違法的,或者政府官員或私人依據該外國的國家行為所作的行為依法院地法律是違法的,因而須承擔法律責任。
歷史淵源
國家行為原則與國家主權豁免原則(SovereignImmunity)不同,後者指一國法院不得受理以外國國家為被告的案件,所限制的是法院對外國國家行為和財產的管轄權問題;而前者則不涉及對外國國家的管轄權,而是法院在受理了案件後,對作為私人當事人或外國國家官員在該外國所作行為所依據的外國國家在其自己領土上的行為,或在外國國家為當事人的場合,其在本國領土內所作行為的合法性,是否有權進行司法審查的問題。換言之,是外國國家行為是否可以為該外國或其他當事者免除法院地法上的民事責任的問題。當然,如果當事人是外國國家本身,而且所涉及的問題首先是對外國國家的管轄權,應當適用的就是主權豁免原則,在確立了管轄權後,才可能考慮是否適用國家行為原則。因此,國家行為原則不是管轄權的原則,而是一種限制司法審查權的原則。
 軍艦向有"流動的國土"之稱,外交性質的國家行為
軍艦向有"流動的國土"之稱,外交性質的國家行為被認為對國家行為原則的確立有重大影響的判例似乎是英國樞密院於1848年的審理的“布倫斯威克公爵訴漢諾瓦王案”.該案的事實是,根據國王威廉第四所頒布的命令,被抗訴人漢諾瓦王將抗訴人查爾斯(前布倫斯威克公爵)置於自己的監護之下,同時剝奪了查爾斯管理其自己財產的權利。抗訴人要求樞密院宣布該命令無效並追究被抗訴人的責任。儘管下級法院以主權豁免原則駁回了訴訟,但樞密院認為英國法院不能要求一個人為其在自己國家內以其主權權威所作的行為負責。依照美國法院在“昂德西爾訴郝南德茲案”中的見解,英國樞密院駁回抗訴的理由是以國家行為原則為基礎的,因為科頓漢姆公爵在判詞中指出,英國法院“不能對外國主權者在自己國家內所作行為作出裁判”,更不能讓一個外國主權者為其“在自己國家內以主權資格所作的行為”負責。
美國法院早在1796年的“沃特斯訴科勒特”一案中已就被告(當時瓜德魯普島統治者)在其管轄範圍內扣留原告船舶的行為是否可以在美國法院被審查的問題作了否定的回答:被告作為一個統治者在其許可權範圍內為官方行為一事“本身就足以回答原告的指控,被告不應在我國法院回答僅僅涉及其行使自己權力是否不正當的任何問題”.
不但在訴訟當事者為外國主權者或是在主權者授權範圍內作行為的外國官員的場合,而且在原被告均為私人,一方以外國主權行為為自己擺脫責任的情形中,美國法院也同樣不能審查外國主權行為的合法性。在“沃斯特訴科勒特案”一百多年後的“奧椹訴中央皮革公司案”中,法院同樣認為墨西哥政府將原告在墨西哥的財產充公的行為不能在美國法院受到司法審查,從而確認了被告對從第三者處購買的原屬原告的財產擁有合法的所有權,而第三者是從墨西哥政府那兒買到這些財產的。
如上所述,到20世紀初,國家行為原則在英美國家已被普遍地接受和適用。而今,“國家行為原則”這個術語在這些國家被學者和法院廣泛地使用。但是,其他國家,特別是大陸法系國家卻較少使用這一術語。它們即使同樣地認為一國法院不能對外國在其自己管轄範圍內的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但採用的卻是不同的稱謂。例如,義大利就將這一學說稱為“外國行為的不可審判性”。有些國家,如法國,雖然不用特定的名稱,但也奉行不對外國國家在其管轄範圍內所作的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原則。正如法國學者巴迪福爾所說:“宣布一項外國法違反憲法……構成一種政治上的主動行動,……而法國法官沒有資格採取這種行動。”事實上,巴黎法院曾於1967年拒絕審查一項突尼西亞法令的合法性。可以說,不論是否將之稱為“國家行為原則”,這一名詞所代表的原則已被普遍接受。
法理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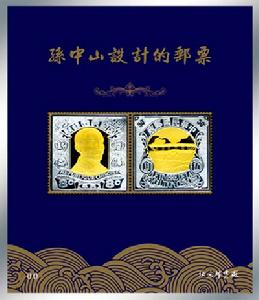 發行郵票是國家行為
發行郵票是國家行為(一)主權說。國家行為原則在普通法國家初步形成的過程中,法官們一般都是從國家主權的角度來闡述該原則的。在前引“布倫斯威克公爵訴漢諾瓦王案”中,英國法官指出,對一個外國主權者“在其自己的國家以主權者的資格所作的行為,無論依照該外國的憲法為合法或非法,無論是對還是錯,英國法院都無權審查”。可以看出,法官是將主權者的主權資格作為免於對其行為進行審查的理由。這種思想在早期的美國判例中表述得似乎更為明確。1876年,美國法官吉爾伯特在“海赤訴比斯案”中論述了國家行為原則的基礎:“我們認為,根據國家間普遍的禮讓和確定的國際法規則,一國的法院有義務抑制自己而對另一個國家在其自己的領土上所作的行為進行裁判。”在1918年的“利克德訴美洲金屬公司案”中,法院在適用國家行為原則時指出,由於沒收的行為“是外國政府的行為,因而歸根結底是主權行為”,所以,即使原告是美國公民,美國法院也不能審查其合法性。在這方面,經典性的闡述見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1897年對“昂德希爾訴赫南德茲案”判詞:“每一個主權國家有義務尊重每一個其他主權國家的獨立;我們國家的法院將不審判另一個國家政府在它自己領土內所作的行為。對這種行為不滿的救濟是必須通過主權國家之間公開提供的方法取得的。”這些判例清楚地表明,適用國家行為原則是對外國主權的尊重,並且對涉及外國國家行為的爭議,應通過國際法的方法解決,而不是由國內法院來裁判。國家行為原則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權的基礎上,這就使得適用該原則成為國家的一項國際法義務。
(二)國際禮讓說。在上述“布倫斯威克公爵訴漢諾瓦王案”中,英國法官已將國際禮讓和國際法一起列為國家行為原則的依據。不同的是,在本世紀初的中央皮革公司案中,法官完全撇開國際法,而僅僅將國家行為原則建立在國際禮讓和國際交往便利的基礎上。至今,在談論國家行為原則的基礎時,美國的判例似乎仍無法完全拋棄國際禮讓說。例如,在1990年的“科克帕特里柯案”判詞中可以看出,美國聯邦法院試圖在國際禮讓和主權以及分權學說之間進行平衡,以說明國家行為原則的法理基礎。但是,用國際禮讓來支持國家行為原則,其結果是排除了國家適用該原則的國際法義務。
(三)分權說。從本世紀50年代以後,美國法院對主權說和國際禮讓說的態度日益冷淡,並越來越顯示出以分權說作為國家行為原則法理基礎的傾向。在向主權說和國際禮讓說發難的判例中,1964年“古巴國家銀行訴薩巴蒂諾案”是較為典型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判詞中寫道:“我們不認為這一原則如先前的判決似乎暗示的那樣由於其主權權威的內在性質,或者由於國際法而成為強制性的。”反之,這一原則“導源於分權制度中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的基本關係”。而在前引“科克帕特里柯案”中,美國法官們對此說得更為具體:“現代國家行為原則法理的核心問題是維護我們政府中聯邦司法機關和政治機關,特別是承擔處理對外關係主要責任的行政機關之間的分權。”
根據分權說,國家行為原則的學說接近於“政治問題學說”,由於國家行為原則涉及到對外國的關係,因而對該原則的適用應當作外交政策的考慮。在實行三權分立制度的國家,特別是美國,日常的對外關係是由行政機關負責處理,而不是由司法機關處理的。所以,涉及國家對外關係的問題,法院無權過問。例如,外國政府對土地所有權的爭執就是一個對外關係的政治問題,依據憲法,對該爭執應由行政機關來解決。法院對這一問題通過司法審查進行干預,將使行政機關在對外關係中處於尷尬的局面。將分權理論當作國家行為原則的法理依據,就使得適用該原則僅僅是國內法的義務。
其實,不論法院在司法實踐中根據什麼理由決定適用國家行為原則,我們對這一原則都可以從國際法上加以說明。
第一、國家行為原則與主權豁免原則雖有區別,但從其產生的過程可以看出,這一原則與主權豁免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早期的有關判例中,當事人本身就是主權者,而法院對這些訴訟的駁回究竟是依據主權豁免原則還是適用國家行為原則,是比較模糊的。例如,在前述“布倫斯威克公爵訴漢諾瓦王案”中,初審法院駁回訴訟的理由是主權豁免原則,而樞密院雖然認為英國法院不能審查一個外國主權者在其自己的領土上所作行為的合法性,卻未明確否定初審法院關於主權豁免的依據,甚至也未明確使用國家行為原則這一術語。在當時,同樣是駁回訴訟,但法律依據究竟是哪一個,實在是難以區分的。直至本世紀初,在被告是私人而非主權者或政府官員時,美國法院才將明確地將主權豁免與國家行為原則相區別。事實上,無論主權豁免原則還是國家行為原則,所依據的都是主權權威。
 國家行為原則
國家行為原則第三、國家行為原則所針對的國家行為必須在行為國領土內作出。對這種行為給予司法審查的豁免,就是對國家屬地管轄權的承認。根據屬地管轄權,一國對其領土內的一切人、物和行為都具有最高管轄權,這種管轄權除受對其有拘束力的國際法規則的約束外,不能受任何外國的干涉。國家在其領土內為國家行為應是行使其屬地管轄權的必要,而國家在自己領土內所作行為不能受外國法院的司法審查,正是這種不可干涉性的具體體現。因此,國家行為原則是尊重外國屬地管轄的必要原則之一。
第四、根據國家或政府承認的國際法規則,既存國家應當承認新國家或新政府國家行為的效力。前國際法院法官羅伯特。詹寧斯在其與英國外交部法律顧問阿瑟。瓦茨一起修訂的《奧本海國際法(第9版)》中寫道:“新國家或政府的行政和立法行為有權(在承認以前這些行為通常是沒有的)在承認的國家的法院得到像另一個國家官方行為所得到的那樣的承認;因此,在承認以前會被法院認為無效的某些財產轉移和其他交易行為,由於承認的追溯力而成為有效。”這一段話至少說明一個事實,即:國家行為原則是承認的直接效果。當一個既存國家承認了一個新國家或新政府以後,就負有承認被承認者國家行為的國際法義務,即使這種國家行為是在被承認以前作出的。
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國家行為原則的基礎和依據是國家主權,是對國家在其自己領土上的主權權威相互尊重的國際法義務。
適用例外
適用國家行為原則的早期案件中,被告一般是主權者或根據主權者的權威行事的國家官員,案件性質也僅限於追究主權者或其官員個人傳統的侵權責任等,並且,國家行為原則正在逐步確立時期,又被確切地歸於國際法範疇,因而該原則至少在英美普通法國家幾乎是無例外地被遵守。事實上,早期的案件,例如在上述“昂德希爾訴赫南德茲案”中,未見任何關於行為是否違反國際法、是否違反法院地公共政策等問題的爭辨或考慮。
這些情況在進入本世紀後發生了變化:私人代替了主權者或政府官員成為有關案件的被告,國家的經濟行為越來越頻繁,大量的案件又涉及到在國際法上有爭議的問題(主要是開發中國家對外國人財產的國有化或徵收),國家行為原則日趨成熟,國家行為原則的法理基礎和人們對主權豁免的態度也出現多樣化的趨勢。面對這些變化,學者和法院不斷地重新檢討國家行為原則,不斷改變對該原則的態度,其結果是,自60年代起,一些國家的法院在司實踐中對該原則的適用施加了一系列的限制,逐步形成了對該原則適用的一些一般例外。
 外國國家行為違反國際法
外國國家行為違反國際法古巴CAV公司的主要股本為美國居民所有。1960年,美國商品經紀公司-法爾。懷特洛克公司向CAV公司購買了古巴食糖,並約定在紐約憑單據付款。同年7月6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對《食糖法》的修正案,授權美國總統減少古巴食糖的進口配額。兩天后美國總統減少了古巴食糖的進口配額。在美國參議院通過修正案的同一天,古巴部長會議通過第851號法令,允許古巴總統和總理通過沒收的方法將美國公民或企業所有的財產和企業國有化。儘管美國向古巴提出了抗議,在以摩洛哥為目的地的食糖開始裝船後,古巴還是發布了第1號執行令,沒收包括CAV公司在內的所有美國人擁有的企業的財產,包括該項已裝船的食糖。為獲得離開古巴的許可,法爾。懷特洛克公司與一個實際上是古巴政府機關的公司訂立了一項與CAV公司同樣的契約。該古巴公司在該批食糖離開古巴後,將提單轉讓給了同屬古巴政府機關的古巴班科國家公司。在班柯公司在紐約機構的負責人向法爾。懷特洛克公司出示單據和支票要求支付時,由於CAV公司主張自己是這批食糖的合法所有人,法爾。懷特羅克公司因而在已得到貨款的情況下,不但拒絕向班科公司支付,反而將貨款較給了CAV公司在紐約資產的臨時管理人薩巴蒂諾。於是,班科公司在紐約南區地方法院向薩巴蒂諾提起了關於該項貨款的訴訟。
地方法院以古巴的國有化不以公益為目的,歧視美國公民,以及未作適當補償,因而違反國際法為由,對該案不適用國家行為原則。聯邦最高法院卻對該案適用了國家行為原則,認為根據國家利益和國際法發展的需要,以及大量的國際實踐,外國沒收財產的問題應通過外交途徑解決。這一判決引起了國會的強烈不滿。國會的這種不滿情緒最終導致對1961年《對外援助法》的修正,在該法的第620節(e)小節下增加了第2項,即“薩巴蒂諾修正案”。該項規定,美國法院對由於1959年1月1日以後發生的沒收財產和其他違反國際法的外國國家行為而提起的侵害訴訟,不得適用國家行為原則。但未違反國際法的國家行為,或總統決定適用國家行為原則的國家行為除外。
該修正案為國家行為原則在美國法院的適用規定了一個法定的例外,即美國法院可以審查外國國家行為是否違反國際法,只要外國的國家行為違反國際法,美國法院就可以宣布其為非法。除美國外,也有一些其他國家的法院對外國國家行為的國際合法性加以審查的。例如,荷蘭最高法院在1969年的“美國總檢察長訴希魯瓦特案”中,認為沒有任何國際法規則禁止法院考慮另一個國家徵收財產是否違反國際法的問題。但是,另一些國家的法院,如義大利大理院在其判決中,卻反對審查外國國家行為是否違反國際法的問題。
(二)行政機關的同意。這一例外的理論依據是分權說。既然法院不審查外國國家行為的合法性是出於分權的需要,而避免使行政機關在處理對外關係時為難,那么,這種審查如果並不影響行政機關對國際關係的處理,法院就不必自我限制了。著名的“伯恩斯坦案”是實踐分權說的重要判例之一。
原告伯恩斯坦是一個猶太血統的德國公民和居民。1937年,他因為是猶太人而被納粹官員關押,在納粹官員關於無限期關押、人身傷害以及不利於其家屬的威嚇下,又把他在德國擁有的一個船舶運輸公司股權轉讓給納粹機構。該納粹機構又將該公司的一艘名為“甘地亞”的船舶轉讓給了被告比利時公司。1946年,已經是紐約居民的原告在紐約州法院起訴,主張對“甘地亞”的所有權。法院表示,根據國家行為原則,它無權審查根據德國法的轉讓行為的合法性。抗訴法院也持同一見解,但認為行政機關可以排除該原則的適用。在回答原告律師詢問的意見書中,美國國務院認為對於為恢復因納粹的強制而喪失的財產而在美國法院提起的訴訟中,法院法院可以不受國家行為原則的約束。抗訴法院根據國務院的政策聲明對納粹的國家行為作出無效的判決。
以後的許多案件都遵循了該案確立的適用例外,即“伯恩斯坦例外”。事實上,在“薩巴蒂諾案”中,初審和抗訴法院正是根據國務院發往古巴的關於古巴政府的行為違反國際法的公文,認為法院依據國際法審查古巴政府國有化措施的合法性,並不妨礙行政當局處理對外關係。
(三)公共政策保留。國家行為原則與國際私法有著密切的關係,公共政策保留就通常是一個國際私法的制度。根據這一制度,當法院地衝突法認為應適用某一外國法律時,如果法院認為該外國法與法院地的公共政策相牴觸,則可以排除該外國法的適用。在國有化或徵收的情況下,財產所有權的轉移往往適用財產所在地法,即採取國有化措施的外國的法律。一些國家的法院就往往以違反法院地公共政策為由,否定外國立法行為的效力。
以公共政策為由宣布外國國家行為非法的做法多為大陸法系國家採用。例如,1972年至73年法國法院審理的“布萊登公司案”中,法國法院認為智利政府的國有化法令在法國無任何效力,並主張對智利政府的國有化行為進行調查。而德國法院在1948年也以違反道德準則和公共政策拒絕承認捷克斯洛伐克徵收法令的合法性。
(四)商業行為。美國於1976年頒布了《外國國家主權豁免法》,在主權豁免問題上由絕對豁免主義轉向有限豁免主義。這一變化也影響到國家行為原則的適用。在1976年的“登希路案”中,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國家行為原則不適用於主權者的商業行為。同一法院在1983年的“麥克唐奈爾案”中也明確聲明,主權者存粹的商業行為一般不要求司法限制。當然,如果涉及對外關係問題,則對外國政府的某些商業行為也可以適用國家行為原則。
 國家行為原則
國家行為原則然而,適用這一例外的案件中,大多數的國家行為究竟是否違反了國際法是有疑問的。以國有化導致的所有權糾紛案件為例,開發中國家與方國家對國有化的補償問題就存在著很大的分歧。按照西方的觀點,對國有化的補償應是“迅速、全面、有效”的補償,而開發中國家卻認為這不是國際法的規則。雙方對何為“適當補償”的見解也全然不同。正如美國最高法院在“薩巴蒂諾案”中所指出的,在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之間,對沒收外國人財產的權利的行使抱有不同的看法。因此,這一適用例外容易引起外國政府的抗議,導致國際糾紛。有些學者認為對違反國際法的國家行為採取救濟措施不是一個國內司法的問題,而是政府間的問題,因為,如果外國政府對有關判決提起交涉,則這一問題就應通過國際爭端的解決程式處理。公共政策保留制度作為限制國家行為原則的理由似乎不如違反國際法的適用例外那么充分。
首先,外國國家行為,如沒收外國人或本國人財產的行為,有域內效力和域外效力之分。按照英國學者的見解,執行外國的法律和承認在外國領土內適用外國法律所產生的後果不同。不顧法院地的公共政策而承認外國國家行為的域外效力,從而執行外國的法律,往往與法院地的領土主權或屬地管轄權發生牴觸。而承認外國國家法律的域內效力,對於法院地國家的領土主權或屬地管轄權並無損害。而且,不承認外國國家法律在其領土內的效力,往往被認為干涉了外國的內政。
因此,在1983年的“阿祖卡的皇后輸出公司訴全國阿祖卡工業公司案”中,英國抗訴法院就承認了一項外國懲罰性法律在該外國境內的效力,並指出:“在外國有管轄權的領域內,應當不急於否認外國立法的效力。”國家行為原則是主權平等這一國際法原則的直接後果,與主權權威有著直接的關係,而公共政策保留則基本上是國內法的制度。以國內法制度來否定有關外國在其自己領土內的主權權威,顯然是不適當的。其次,公共政策保留是一種不穩定的制度,其具體含義往往不甚明確,實施起來確有困難。有學者將國際法與公共政策兩種例外進行比較後指出,公共政策是一種變化著的、相對的概念,在適用中具有不確定性;而國際法則提供了相對客觀的標準。最後,各國的公共政策難以統一,因而適用公共政策的例外缺少統一的標準。
作用
 舉辦世博會是國家行為
舉辦世博會是國家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