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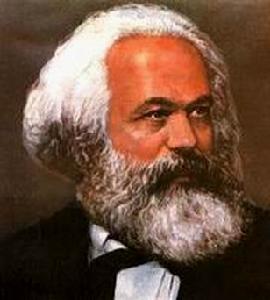 馬克思
馬克思眾所周知,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內容。但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究竟應屬何種性質的理論,人們的理解卻是很不相同的。大體而言,中國哲學界對辯證法的認識有下述三種不同的理解。
第一種見解是從自然本論論的立場出發理解辯證法。這種看法完全根據前蘇聯教科書的模式,把辯證法表述為“關於自然、人類社會與思維的存在與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在此,辯證法成了關於世界的一般結構與圖景的學問。
第二種見解出現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思想理論界的日趨活躍所出現的辯證法領域的“認識論轉折”。人們對本體論化的辯證法日趨不滿,要求克服其直觀性、獨斷性、實證性以及難以與各具體學科區分開來等理論弊端,認為應上升到認識論層面理解辯證法的性質,把它理解為處理和解決認識論的基本問題即思維與存在關係問題的理論邏輯。
第三種見解出現於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實踐”觀念的凸顯與日益被重視,人們開始從實踐論角度重新理解辯證法,把“實踐”視為辯證法的理論基礎與思想核心,辯證法由此實現了“實踐論的變革”。
從本體論的辯證法,到辯證法的認識論轉折,再到辯證法的實踐論變革,這三種不同的見解標誌著對辯證法理解與研究的深化,並勾勒出了一條中國哲學界理論進展的軌跡。理論的生命力在於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地對經典的“本文”進行新的解讀和闡釋。試圖立足於學術界已有成果,對辯證法作一種新的闡釋,認為辯證法的進一步發展將是人學辯證法。
現實意義
 人學辯證法
人學辯證法人學辯證法是哲學發展與現代人的內在呼喚
“認識你自己”,這一德爾斐神廟上的諭言始終是哲學探究的永恆主題與最高目標。而在當代社會,“人從未象我們現在那樣對人自己越來越充滿疑問,我們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連貫的關於人的觀念。從事研究人的各種特殊科學的不斷增長的複雜性,與其說是闡明我們關於人的概念,不如說是使這種概念更加混亂不堪”(轉引自卡西爾《人論》,29頁)。在此情境下,哲學那古老的承諾更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
但問題的困難在於,哲學雖以人為研究的根本目標,卻並不意味著它總是能找到通向“真實”、“具體”的人的現實道路。由於用以認識與探究人的思維方式的片面性與抽象性,哲學懷著理解人的無限熱情為開端,卻常常以“人的失落”為結局。這是哲學史上屢見不鮮的現象。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研究人,而在於能否以正確的思維方式找到通向真實的、具體的人的道路。
這一理論難題的產生,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人獨特的存在方式。由於人在宇宙中不同於其它一切存在的特殊存在方式,決定了他不能用科學的、神學的或其它的方式,而只能採用符合人本性的哲學思維方式來予以把握。我們認為,人學辯證法的重大價值就在於它克服了以往哲學把人抽象化的理論弊病,發現了走出人的“抽象王國”,進入人的“現實王國”的現實道路,使辯證法切實成為“關於現實的人及其發展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237頁)真正實現了“人必須用人的方式來把握”的哲學理想。
 人學辯證法
人學辯證法人獨特的存在方式,是就人與物的區別而言的。物的特性直接秉承自然,如動物的特性就與其生命活動直接同一,因而其生存總受制於特殊的規定,遵循單一的尺度並生存在單一性世界之中。與此不同,人總是生活在“雙向度世界”充滿張力的否定性統一之中,二重性、矛盾性構成了人的本質規定。這正象馬克思所說的:“人雙重地存在著,主觀上作為他自身而存在著,客觀上又存在於自己生存的這些自然無機條件之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91頁)。一方面,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身內在的尺度,他總是趨越動物地位、受超越其生存的偶然性與受動性的願望所驅使,要求在創造性活動中把自身提升出來,使自己成為真正的“人”,在此意義上,人就“不僅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說,是為自身而存在著的存在物,因而是類存在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9頁)他區別於自然事物那種預見的、封閉的、宿命的存在方式,在創造性的實踐活動中使自己的存在獲得了開放、應然與生成的性質。人的這一特性,正如有學者提出的,他是“宇宙間唯一能夠‘是其所是’和‘不是其所是’的存在物,除人之外的一切存在,歸根到底都是‘是其所是’的東西”。
人這種獨特的存在方式,決定了人只能用人的方式、即適應人本性的方式來把握,而這種方式只能是“人學辯證法”。
可以把對物的把握方式稱為“物種邏輯”或形式邏輯,物的特性直接秉承自然,運用形式邏輯方法排除異點,取其共性就可將其把握。但對人而言,這種“物種邏輯”是根本不適用的。因為人決非一種“自身同一”的存在,而是“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的“自相矛盾”的存在,在他身上集中凝結著種種二重化的矛盾關係(自然性與超自然性、因果性與目的性、感性與理性等),並且總是處於動態的開放狀態。對於這種獨特的存在,如採用物種邏輯的方式,必然導致對開放的、創造性的、包含多重矛盾關係的人的抽象化、片面化的理解。要切實地達到對人的完整把握,必然要求超越物種邏輯,而求助於“辯證邏輯”,即人學辯證法。
由此可見,人學辯證法是哲學發展與人自我認識的內在需要,它植根於人獨特的存在方式,因而具有深層的合法性。
理論意義
 人學辯證法
人學辯證法人學辯證法的理論意義
首先,人學辯證法的提出,是哲學的自我理解的深化,它為哲學在現時代的存在提供了堅實的合法性根據。在日趨世俗化的現代社會,如何捍衛哲學的生存權利已成為十分迫切的課題,它要求哲學工作者為哲學的合法性進行自我申辯;在理論領域,辯證法也不斷遭到非議與責難,西方哲學中無論是科學主義思潮,還是人本主義思潮都把辯證法視為必須予以拒斥的傳統形上學,在中國也有諸如:“辯證法就是變戲法”之類的譏諷。人學辯證法的提出,正是對這一切的積極回應,它表明哲學辯證法在現時代仍然具有其不可剝奪的存在價值,即提高人的主體自我意識與促進人的自我理解,闡發人在宇宙中的獨特性地位與價值、提升人的精神意境,以一種反思意識的形式自覺地回答“人是誰”這一真實而重大的問題。這是科學、神學與其它任何學科都無法取代、只能由哲學來承擔的任務。只要人存在一天,只要人仍在尋求自我理解,哲學就會具有永不消失的勃勃生命力和生存空間,這就是人學辯證法給我們帶來的堅定信念。
其次,人學辯證法將真正破除傳統哲學關於人的種種抽象化理解,凸顯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具有的現代意義。經常提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哲學史上的重大變革之一,在於它克服了傳統哲學對人的虛幻理解,發現了具體的現實的個人,但一涉及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究竟是如何實現這種轉變的,人們的回答就經常語焉不詳、或不得要領。從人學辯證法出發,這一問題即可迎刃而解:傳統哲學的根本失誤就在於它在理解人時,總是貫徹著“物種邏輯”、以一種把握物的方式把握人,因此,它必然把人歸結為某種終極的、單一的規定,從而導致對豐富的、開放的活生生的人的抽象化與僵化理解。人學辯證法則是從人獨特的存在方式出發,以反思意識的形式把握了人是一個處在多種矛盾關係的否定性統一之中、並不斷創造自身的開放性存在,從而真正實現“用人的方式來把握人”這一哲學理想。這種理論思維方式的轉變,意味著在把握人的問題上發生了根本的“範式”轉換,在這種轉換中,馬克思主義哲學超越傳統哲學的革命性意義得到了充分體現。
再次,人學辯證法還為人學與哲學的統一找到了一個內在的結合點。人學研究是近年理論界的熱點,隨之便出現了人學與哲學究竟應是什麼關係的爭論,把人學看成是哲學的分支,或把人學看成與哲學相併列的新興學科,都沒能找到人學與哲學統一的內在結合點。人學辯證法則為解決二者的分裂提供了現實的途徑。人學辯證法既是哲學、又是人學,它是人學的哲學形態、或者說是哲學的人學形態,在此,人學與哲學內在統一,毫無隔閡。因此,人學辯證法是哲學與人學的深層結合,為二者的一體化提供了真實的生長點,這無疑既有助於哲學理論的發展,又有利於人的研究的深化。
深化
 人學辯證法
人學辯證法人學辯證法是實踐辯證法的展開與深化
人學辯證學的成立,決不是要完全取代與否棄實踐辯證法,相反,人學辯證法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為它充分挖掘了實踐觀點中的人學意蘊,因此,人學辯證法是實踐辯證法合乎邏輯的展開與深化。
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範疇,這已成為哲學界的基本共識。但究竟應如何理解實踐範疇的意義和性質,人們的理解卻又是大不相同的。筆者認為,實踐觀點在哲學史上的重大意義就在於它為理解人、把握人提供了合乎人本性的思維方式和理論視角,由此出發,實踐活動被理解為人本真的存在方式,人與世界的關係將既不是純粹自然的關係,也不是單純的意識關係,而是一種能動的實踐關係,人就是在實踐活動中,自覺處理同世界的關係,並不斷把自己“塑造成人”的。因此,在我看來,實踐觀點克服了哲學史上把人抽象化、片面化的思維方式,達到了對人獨特存在方式的真正自覺,因此,實踐範疇在最根本的意義上乃是一個人學範疇。
把實踐理解為人學範疇,這表明,實踐決不是一種價值中立的工具性活動,而是體現著人獨特的存在方式及其發展規律的價值性活動。在實踐觀點的視野里,人將呈現出與傳統哲學截然不同的嶄新形象。它意味著:
1,人不是與物一樣的“自我同一”的存在,而是由“矛盾精神”所推動的自我創造的存在。實踐活動作為人與世界分化與統一的基礎,集自然性與超自然性。因果性與目的性、過去與未來等多重矛盾關係於一身。實踐活動的展開過程,同時便是這些矛盾關係的展開過程,而人正是在這些矛盾的展開過程中不斷生成為人的。因此,在實踐觀點的視野里,人就決非傳統哲學中那種具有絕對的、抽象化本質的存在,而是由“矛盾精神”推動的自我超越和價值創造的存在。正是在此意義上,矛盾原則或對立統一原則構成了辯證法的核心原則。
2,實踐活動又是一種功能性、歷史性的不斷為未來開闢道路的活動,人就是在這種歷史性的活動中自我發展、向未來不斷敞開新的可能性空間。因此,在實踐觀點的視野里,人就決不可能被還原成某種最終的知性規定或被實體化,而是真正把人視為在歷史上自我創造的、自由自覺的存在,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才說,辯證法是“毫無片面性弊病的關於發展的學說。”(列寧)
3,實踐活動又是一種否定性、超越性的活動,它總是要求改造與否定世界的現存狀況,使世界不斷朝符合人的目的性要求與理想圖景的方向發展,人具有在實踐中超越固有限制、追求美好生活、創造自身價值的趨向和能力。正是在此意義上才說,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上,總是“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18頁)
就這樣,把實踐作為一個人學範疇,挖掘其蘊含的豐富的人學內容,辯證法真正成了表達人獨特的存在方式與發展規律的“人的邏輯”。這種貫徹矛盾原則,堅持發展觀點、滲透著批判性與革命性精神的辯證法哲學,徹底克服了“物種邏輯”的局限,以一種適合人本性的方式實現了對人的自覺把握。
由此可見,把辯證法闡釋為“人學辯證法”,並不是要完全否定實踐辯證法,而是要把實踐活動提升到人基本的生存方式與人生存發展的基礎這一高度,把實踐觀點所內含的人學內涵予以充分地展開與發揮,因此,人學辯證法是對實踐辯證法的進一步深化和擴展,它標誌著對實踐、對辯證法理解層面的雙重躍遷。
薩特
 薩特
薩特薩特的“人學辯證法”
薩特所理解的辯證法僅僅是體現在人的實踐活動中的理性。人在實踐活動中認識自然,從而把辯證法導入自然之中,使自然界表現出辯證法的特徵。但從本質上講,辯證法只能是人的知識形態。既使自然科學的某些範例是辯證的,那也只能證明人的理性是辯證的,而不能證明自然本身是辯證的。薩特說:“在辯證法家那裡,辯證法是建立在既與的現實結構,又與我們的實踐的結構相關的基本主張上的。我們斷言認識過程是辯證的,同時又斷言對象(不論它是什麼東西)運動本身也是辯證的,而且這種辯證法是同一個東西。把這兩種命題拉到一起,它們本身就是一種有組織的知識形式,或者換句話說,它們規定著世界的合理性。”
在歷史領域中,也不存在那種象歷史背後的神的意志力一樣的辯證法,而是歷史認識的結果。薩特說:“如果我們不想把辯證法重新變成一種神的法則和形上學的宿命,那么,它必須來自一個個的個人,而不是來自我所不知道的什麼超個人的集合體。”“辯證法如果存在的話,那就只能是總體化過程中許多的個別性所造成的許多具體的總體化的總匯,這就是我所說的辯證法的一元論。因為辯證法乃是總體化的活動,除了由正在進行的總體化所產生的各項法則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規律。”
當然,總體化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個人被社會所總體化;另一方面是社會被個人所總體化。但整個總體化的基礎是個人的實踐,正是由於個人的實踐才產生和保持了人的總體性。因為,人處於歷史的中心,是人把散漫的社會歷史現象聯結成一個總體的,社會的總體化是以每個個人的總體化為前提的,而個人的總體化又是體現在個人的實踐活動中的。所以,辯證法歸根到底就是產生和保持個人總體的方法,要把握辯證法就只有到以個人實踐為基礎的個人總體化和從個人總體化到社會總體化的進程中去尋找。或者,乾脆說辯證法就是實踐,是人改變和創造對象、賦予對象以意義,同時實現著人的總體化的活動。
薩特終生致力於建構一種“人學”,這種局限於個人視野中的人學自然要把人的內心世界誇大為整個世界。因而,他是不相信人的內心世界之外還會有其他的存在的。
到了寫作《辯證理性批判》的時候,由於接觸馬克思主義而發現了實踐範疇,從而找到了個人超越自己的內心世界的途徑。這時薩特本可以告別個人的內心體驗走上認識客觀世界的道路,如果這樣的話,那么他就能在對自然和社會歷史的深入研究中取得積極的成就。遺撼的是薩特沒有這樣做,而是依然囿於個人的目力所能達到的世界範圍,站在個人這個圓點上來理解通過實踐構成的人與自然、社會的關係世界。這樣一來,薩特並沒有因為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汲取了實踐概念而使他的存在主義有什麼長進。因為他的結論還是原來的結論,即只相信人所涉及的世界的真實性,純粹客觀的世界則被劃入烏有之鄉或者說被划進了假定的領域。
所以,薩特要否認客觀的自然辯證法,把辯證法嚴格地限制在個人的實踐活動以及個人的實踐活動所能涉足其中的領域裡,認為只有在這個領域中,辯證法及其規律才是真實的。
由於在人的世界中來考察辯證法,辯證法的全部內容就成了個體的人的自我發展、社會、人的物質界、作為人的自我發展的環境和中介的關係。辯證法的這些內容就是“總體化”,總體化就是辯證法。辯證法是一切總體化所普遍具有的形式,而總體化則是辯證法的普遍法則。要理解辯證法的規律就必須立足於總體化的觀點上。薩特認為,一切辯證法的動力都存在於總體觀念中,因為只有把各種現象理解成不是孤立地、單純地出現的,而是在總體的綜合統一之中的,辯證法才是可能的。
薩特認為,如果假定人及其對象之外存在著辯證法,那么必然會使辯證法變成不可理解的。相反,以人的總體化為根據,辯證法就獲得了可理解性。因此,個人實踐的領域就是辯證法的限度,個人的總體化是辯證法可理解性的唯一基礎。社會歷史是人的客觀性領域,但是,由於社會歷史是人的總體化的總匯,因而是辯證的。在社會歷史中,一切事物現象的辯證性質都取決於它們是否是人的實踐活動的結果,即是否包含著個體的總體化的作用。所以,人的總體化又是辯證法的最高原則。無論辯證法研究什麼問題,其中心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在一切歷史現象中認識人的總體化。這樣一來,薩特的辯證法就是總體化的辯證法,是對個人總體化的記錄和描述。辯證法的學說作為一系列命題的抽象體系,來源於個體的總體化,是對個體的人及其關係世界的整體與部分的多樣性的
 人學辯證法
人學辯證法把握,是對個體的人的總體化進程以及個體的人的實踐所造成的歷史總體化的進程的把握。反過來,辯證法的命題體系又對個體的總體化提供指導,幫助個體的總體化與歷史總體化的融合。
薩特承認,把歷史作為一個總體加以考察是馬克思的最偉大功績。在馬克思之前,歷史學家們看不到歷史的總體性質,而是陷入到對個別歷史事件的分析之中,把歷史看作無數個偶然產生和消滅的個別事件的集合。馬克思從生產關係出發,發現了歷史是建立在生產關係的基礎上和隨生產關係的演變而發生變化的總體,從而揭示了歷史的總體性。因此,總體範疇是馬克思主義關於歷史存在的思維的基本範疇。
應當指出,薩特關於馬克思發現了建立在生產關係基礎上的歷史總體的認識是正確的。但是,問題在於薩特對生產關係的理解卻不同於馬克思,他不是把生產關係理解成人們的具體的物質聯繫,而是把生產關係看作是個人在個人的實踐活動中結成的聯繫。因此,在薩特所理解的生產關係範疇中,我們看不到在特定的生產方式中作為階級的歷史實踐主體,而只能發現作為個人的實踐主體。薩特在歷史中所看到的唯一積極因素就是個體的總體化,而歷史本身則是被動的。儘管他把歷史理解成使一切個別事件和過程結合成總體的運動,但歷史總體卻是被構成的總體。因此,歷史辯證法也由於沾染上了惰性因素而成為“反辯證法”的領域。所以,辯證法的源泉只存在於作為個體總體化的個人實踐之中。也就是說,實踐是辯證法的真正王國,而個人的實踐則是辯證法的原初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