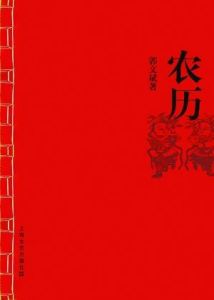圖書簡介
郭文斌長篇小說《農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三十萬字,以十五個傳統節日設目,從元宵開始,到“上九”結束,正好是一個季節循環。為了有效地呈現這個“天然”,以“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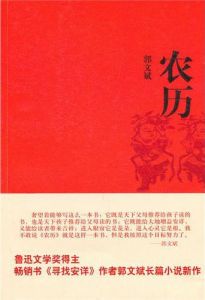 《農曆》
《農曆》說節日史”的方式呈現中國文化的根基和潛流,展示中華民族民間化的經典傳統,經典化的民間傳統,作者使用了跨文體復調寫作方式。
出版人稱:“這是一個天然的世界:天然的歲月,天然的大地,天然的哲學,天然的美學,天然的文學,天然的教育,天然的傳承,天然的祝福……她就是農曆。這個‘天然’,也許就是‘天意’”。
為了完成這部“清明上河圖”式的長篇,作者用了十二年時間。
作者簡介
 《農曆》作者
《農曆》作者郭文斌,祖籍甘肅,1966年生於寧夏西吉縣,先後就讀於固原師範、寧夏教育學院中文系、魯迅文學院。著有小說集《大年》、《吉祥如意》、《郭文斌小說精選》,散文集《點燈時分》、《孔子到底離我們有多遠》,詩集《我被我的眼睛帶壞》等,合著長篇《西夏》。其中,《尋找安詳》一書(中華書局2010年1月版)年內三次重印。先後獲“冰心散文獎”“人民文學獎”“小說選刊獎”“魯迅文學獎”。部分作品被譯成外文。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現任銀川市文聯主席、寧夏作協副主席、《黃河文學》主編。
寫作初衷
“奢望著能夠寫這么一本書:它既是天下父母推薦給孩子讀的書,也是天下孩子推薦給父母讀的書;它既能給大地增益安詳,又能給讀者帶來吉祥;進入眼帘它是花朵,進入心靈它是根。我不敢說《農曆》就是這樣一本書,但是我按照這個目標努力了。”作者這樣表達他的寫作初衷。
作品意義
《農曆》以農曆節氣為序,選擇了西北一戶農家的日常生活為主要鋪陳對象,集中書寫了農曆中的十五個節日。這樣的選擇,在當下的生活中究竟有怎樣的意義?對此,郭文斌說,意義很是重大。如果我們真正地走進“農曆”,就會發現它是一個天然的世界:天然的歲月、大地、教育、傳承、祝福……這個“天然”,也許就是“天意”。而“天意”,在我看來,就是“如意”,“吉祥如意”想必就是這么來的。回過頭,我們再看看當下的世界,打開每天的傳媒,重要位置多被天災人禍占著,觸目驚心。而這些天災人禍又以驚人的速度更新著,甚至來不及記住標題,就連天災人禍都是如此匆忙,這是為什麼呢?在我看來,天災是因為自然失去了“農曆”,人禍是因為人心失去了“農曆精神”。因此,我在一篇隨筆中寫道,根是花朵的如意,皮是毛的文明,反季節菜之所以會吃死人,也是因為它違反了“農曆精神”。
創作隨筆
長篇小說《農曆》最近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對於拙著本身,心想還是留待讀者評判,在此僅就農曆的貴重,談些淺見。
我把《農曆》的寫作視為一次行孝。因為在我看來,農曆是中華民族的根基和底氣。“農曆精神”無疑是中華民族的生命力所在,凝聚力所在,也是魅力所在。
和先祖相比,現代人的“營養”很不平衡,“體質”虛弱,動不動就“生病”,究其原因,就是接不上“天氣”和“地氣”了,久而久之,“元氣”大傷。而一個人要想恢復元氣,就得接上天氣地氣。農曆正是告訴人們如何才能接上天氣和地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曆才是真正的中國符號。
誠然,我們可能無法回到農曆時代,但是我們完全可以找回“農曆精神”。只要每一個人心中還有“農曆”,還有“農曆精神”,那么這個人就擁有了健康之根,快樂之本,幸福之源。國家和民族也同樣。因為“農曆”本質上是生命力的“統覺”,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這個“合”,在我看來它就是“順”,而“順”,就是“利”,所謂“順利”。但現在的情況是,我們已經不知道如何去“順”,於是天災人禍成了每天新聞的主角,依我淺見,天災是因為大地失去了“農曆”,人禍是因為人心失去了“農曆精神”。
近年來,在走進農曆的過程中,我漸漸低下了自己一度十分驕傲的頭,彎下了自己一度十分自負的腰,“農曆”如一面鏡子,讓我看到了自己的狹隘、自私、包括自戀。在《農曆》之《中元》一節中,我把《目連救母》一齣戲全部搬了進來,因為它讓我看到了古人的心量,也看到了古代文化人的心量。在我看來,它事實上是東方“救文化”的寓言,目連所救的,不單單是自己的母親,更是大地母親,自然母親,斯文母親,仁愛母親。而《目連救母》作為一齣戲,世世傳唱,代代完善,卻沒有作者署名,這樣的“作家”,該是多么讓人崇敬。因此,對我來說,《農曆》的寫作還是一次深深的懺悔。
農曆是另一個大自然,在這個大自然里,有天然的世界,天然的歲月,天然的大地,天然的哲學,天然的美學,天然的文學,天然的教育,天然的傳承,天然的祝福。這個“天然”,也許就是“天意”。而“天意”,在我看來,就是“如意”,“吉祥如意”就是從此而來。
而作為一本書的《農曆》,它首先是一個祝福,對歲月的,對大地的,對恩人的,對讀者的。同時,我還在想,小說是要為“現實”負責,但更應為“心靈”服務,就像“點燈時分”,把燈點亮才是關鍵,至於用哪個廠家出產的火柴,並不需要考究。
“農曆”的品質是無私,是奉獻,是感恩,是敬畏,是養成,是化育。一個真正在“農曆”中自然長大的孩子,他的品行已經成就。反過來,做父母的要想讓孩子養成孝、敬、惜、感恩、敬畏、愛的品質,就要懂得“農曆”,學會“農曆”,套用“農曆”。“農曆”是一個大課堂,它是一種不教之教。就像一個人,他一旦踏上有軌列車,就再也不需要擔心走錯路,列車自會把他送到目的地,因為它是“有軌列車”。“農曆”就是這個“軌”,它既是一條人格之軌,也是一條祝福之軌,更是一條幸福之軌。它的左軌是吉祥,右軌是如意。
看完《農曆》,讀者就會知道,其中的十五個節日,每個都有一個主題,它是古人為我們開發的十五種生命必不可少的營養素,也是古人為後人精心設計的十五種“化育”課,古人早就知道,“化育”比“灌輸”更有用,“養成”比“治療”更關鍵。
作品評價
這是一部試圖續接傳統和諧力香火的長篇,是一部在民間傳統中尋找靈魂復甦力的長篇,是一部在田園牧歌中尋找永不遺忘永不迷亂永不被物質制約的根本幸福的長篇,是一部試圖展示善的繁枝茂葉的長篇,是一部以美學方式探討中國農村傳統生活方式的長篇。整部小說對傳統農耕文明和民間鄉土文化的梳理與描繪,真實感人,顯示了作家深厚的生活積澱和語言功底。
陳建功高度評價郭文斌,稱其毅然堅守清醒的文學信念。陳建功認為,《農曆》以兩個鄉村孩童的眼光,通過他們的回味、追索、詢問,展示著漸漸消弭的傳統鄉村文明,顯示天人合一的人文理想,為我們留存了珍貴的鄉俗材料,其本質,是對瘋狂侵襲我們的現代文明的抗爭,對平靜安詳的心靈的堅守,是對一種理想的生活信念的守護。李存葆表示《農曆》一書很高貴,並不是小市民茶餘飯後的談資。讀後感覺像是走進了桃花源,同時,作者的文學品格是優秀的。
李敬澤表示,郭文斌有自己的人生觀,有自己的世界觀,有說法,還有作品,能夠知行合一。就《農曆》這部小說而言,我覺得確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美好,非常安詳的,從我們的民族傳統中,從我們廣大厚重的鄉土中提煉出來的,這樣一個精神的世界,藝術的世界,想像的世界。這個世界至少就小說而言,是可以令人安居的。
胡平在發言中說,《農曆》是有哲思的小說。小說主要通過這兩個不諳世事的孩子,對一切都發問。從孩子的角度追問這個世界的筆法,有點像《天問》。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東西,但並沒有問過它的本源。這個作品對一切的發問,非常有哲學的想法。
雷達表示,在今天中國社會生活裡面,有尊嚴的東西越來越少了,缺少尊嚴感。能夠引起人們敬畏之心的也少了。而郭文斌的作品恰恰是,我覺得需要重新喚起敬畏之心,喚起尊嚴感,喚起吉祥感,回到自然,回到天然,為焦慮的時代,為縮略的時代,為浮躁的靈魂 。
第八屆茅盾文學獎20部提名作品
| 2011年8月14日晚,第8屆茅盾文學獎評獎辦公室發布公告,宣布經過評獎委員會的第三輪投票,正式產生了第8屆茅盾文學獎的20部提名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