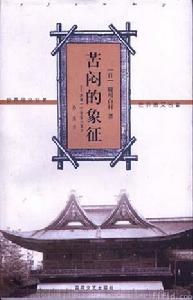 《苦悶的象徵》封面
《苦悶的象徵》封面1925年3月出版單行本,為《未名叢刊》之一,由北京大學新潮社代售,後改由北新書局出版。《苦悶的象徵》是一部未完成的書,作者因地震喪生,沒能寫完。已完成部分,包括創作論(以上所引,均出這部分)、鑑賞論、關於文藝的根本問題的考察、文學的起源(未完)四部分。魯迅曾用作大學講義,影響了一代人。
作者簡介
廚川白村(1880年-1923年)日本文學評論家。本名辰夫,生於京都。1904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歷任第五、第三高等學校教授,後任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助教。1912年以著述《近代文學十講》知名於世。在大學院提出研究論文《詩歌與散文中所表現的戀愛研究》。1915年受文部省派送留學海外,越二年歸國。1919年獲文學博士學位,任東京帝大教授。1923年關東大地震中遇難,歿於鎌倉。著作除《近代文學十講》外,重要的是《印象記》、《出了象牙之塔》 、《近代戀愛觀》、《苦悶的象徵》、《文藝思潮論》等。有《廚川白村全集》(8卷)行世。主要介紹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美文學和文藝思潮。
作為一位文藝思想家,廚川白村在自己的著作中,明晰地闡發了自己的文藝主張與文藝觀點,同時作為一位社會文明批評家,他也批判了社會弊端,將筆鋒直指社會現實,勇敢地承擔起了社會批評這一社會歷史責任。他開展文學批評後,潛心研究弗洛伊得的學說,注意文學與性,潛意識的關係,由此而傾倒英國詩人布朗寧。他的文學批評的特點是:既追求歐美文學的新傾向,又拘束於現實中的日本倫理觀念,這種矛盾正是廚川白村內心苦悶的根源。
在中國廚川白村也曾名噪一時,到20世紀20年代末,他的作品幾乎全被翻譯成中文。他的文藝理論影響了中國的讀書界,他的遺作《苦悶的象徵》使“苦悶”的話語廣泛流傳。
中文譯本
 豐子愷
豐子愷豐子愷以漫畫散文著稱,他的《子愷漫畫》出版於1925年,《緣緣堂隨筆》出版於1931年。但也有翻譯集多種,最早出版的是翻譯日本文藝評論家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商務印書館1925年出版)。其時,魯迅翻譯的《苦悶的象徵》(作為“未名叢刊”的一種)已由新潮社於1924年出版。魯迅說:“我翻譯的時候,聽得豐子愷先生亦有譯本,現則聞已付印,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現在我所譯的也已經付印,中國就有兩種全譯本了。”
魯迅譯本初版成書考
日本文藝批評家廚川白村的文藝論文集《苦悶的象徵》,是魯迅十分重視的一部文藝論文集,也是對魯迅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文藝論文集。魯迅與此書的關係,只看魯迅對它的翻譯、譯文的發表和單行本的出版,原始的記載都一清二楚。
 魯迅日記
魯迅日記關於魯迅對此書的翻譯。《魯迅日記》1924年9月22日載,“夜譯《苦悶的象徵》開手”;當年10月10日載,“夜譯《苦悶的象徵》訖”。起訖日期清晰,翻譯過程僅歷20天。
關於這部中文譯稿的發表和出版。在魯迅翻譯過程中,《苦悶的象徵》的中文譯稿的第一、第二部分已經開始在《晨報副刊》連載,具體的起訖時間是1924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單行本的初版時間,據著作權頁是“1924年12月初版”,這有原書可查。在魯迅誕生百周年紀念活動期間,北京魯迅博物館舉辦《魯迅著作版本展覽》,並編印《魯迅著作版本展覽目錄》。在這個目錄中,《苦悶的象徵》初版本系北京圖書館提供,文字說明是“《苦悶的象徵》廚川白村著,魯迅譯,北京未名社1924年12月初版。本書為魯迅贈孫斐君書,有魯迅題字並印章,內容為‘送給斐君兄。譯者’”。以留有魯迅手澤的實物為證,魯迅譯《苦悶的象徵》的初版時間是1924年12月,也是明明白白的。
在一般情況下,書籍著作權頁上的記載,自然是該書信息的原始記錄,理所當然地被研究者作為重要的依據。根據《苦悶的象徵》著作權頁上的記載,將其初版時間定為1924年12月的書籍,可見到的有以下幾種: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16卷;王觀泉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魯迅年譜》;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魯迅年譜》等。在《魯迅全集》第16卷中收有《魯迅著譯年表》,其中1924年9月22日條目下的文字是“始譯廚川白村的文藝論文集《苦悶的象徵》,10月10日譯畢,本年12月出版,新潮社代售,列為《未名叢刊》之一。”另外兩種年譜,文字各異,但在確定《苦悶的象徵》的初版時間方面,同《魯迅全集》第16卷中的《魯迅著譯年表》無異。然而也並非所有有關魯迅的著述,在確定魯迅譯《苦悶的象徵》的初版時間問題上,都以初版本的著作權頁為據。在這方面持有異議的有鮑昌、邱文治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魯迅年譜》;復旦大學、上海師大、上海師院《魯迅年譜》編寫組編、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魯迅年譜》。鮑昌、邱文治編《魯迅年譜》,1924年12月末的譜文是:“本月,譯作《苦悶的象徵》作為《未名叢刊》第一種出版(由新潮社代售,實際上於1925年2月出書)”。復旦大學等編《魯迅年譜》1925年3月7日的譜文是:“所譯文藝論文集《苦悶的象徵》(日本 廚川白村作)由新潮社出版。”這些都說明,有些研究者並不以《苦悶的象徵》初版著作權頁的白紙黑字為憑信。
 魯迅譯作《苦悶的象徵》1935年版
魯迅譯作《苦悶的象徵》1935年版確認《苦悶的象徵》初版時間是1925年3月,首先要排除1924年12月出版的可能。據《魯迅日記》,1925年1、2月份《苦悶的象徵》的排印稿尚在校對中。現將《魯迅日記》的有關記載做一摘要:
1924年12月4日:“校《苦悶之象徵》。”
12月9日:“校印刷稿。”
12月10日:“寄新潮社印刷稿。”
12月12日:“夜校《苦征》。”
12月13日:“往新潮社交校正稿。”
12月15日:“校《苦征》稿。”
1925年1月6日:“夜校《苦征》印稿。”
1月7日:“寄新潮社校正稿。”
1月14日:“校《苦征》印稿。”
1月28日:“寄李小峰信並校正稿及圖版。”《魯迅全集》中此條的注釋是, “指《苦悶的象徵》清樣及插圖銅版。”
2月8日:“夜伏園來,托其以校正稿寄李小峰。”
這些關於《苦悶的象徵》的記載,大致反映了魯迅對該書排印稿反覆校對的過程。從中可以看出:一、魯迅對《苦悶的象徵》的校對,始於1924年12月4日,訖於1925年2月8日。也就是說,至1924年底《苦悶的象徵》的排印稿仍在校對中。二、1925年1月28日以前,書中插圖圖版尚未送抵出版社。 以此排除《苦悶的象徵》初版於1924年12月,作為依據是十分堅實的。
 魯迅譯本2007年新版
魯迅譯本2007年新版這其實是一部文藝論,共分四章。現經我以照例的拙澀的文章譯出,並無刪節,也不至於很有誤譯的地方。印成一本,插圖五幅,實價五角,在初出版兩星期中,特價三角五分。但在此期內,暫不批發。北大新潮社代售。
這則廣告刊登於1925年3月10日《京報副刊》(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這無疑是《苦悶的象徵》剛剛出版的有力證明。尤其能夠證明這一點的,是其中的“在初出版的兩星期中,特價三角五分”的優惠期,這只可能在該書剛剛出版時實行,而不會在出版兩三個月以後實行。這就進一步證實,《苦悶的象徵》的初版時間是在1925年3月。
確認《苦悶的象徵》初版時間為1925年3月的第三個依據,是魯迅最初收到樣書的記載。魯迅是該書的譯者,自然會在該書出版後最先收到樣書。《魯迅日記》對此事的最早記載是1925年3月7日,原文是:“下午新潮社送《苦悶的象徵》十本。”這或許就是復旦大學等編《魯迅年譜》將《苦悶的象徵》初版時間定為1925年3月7日的原因。
除以上情況外,《魯迅全集》中有關《苦悶的象徵》的一些注釋,也可以作為旁證。儘管《魯迅全集》第16卷中的《魯迅著譯年表》,將《苦悶的象徵》的初版時間定為1924年12月,但《魯迅全集》中其他一些注釋並不沿循此說,例如:
《魯迅日記》1924年12月4日“校《苦悶之象徵》”注釋:“指校閱該書單行本清樣,至1925年2月校訖。”(《魯迅全集》第14卷第524頁。)
《〈苦悶的象徵〉引言》中關於《苦悶的象徵》的注釋:“……1925年3月出版單行本,為《未名叢刊》之一,由北京大學新潮社代售,後改由北新書局出版。”(《魯迅全集》第10卷第233頁。)
 《魯迅全集》
《魯迅全集》對於《苦悶的象徵》著作權頁上的初版時間為什麼要比實際初版時間提前的問題,我有一個還不能得到證實,也許永遠無法得到證實的推測。魯迅在翻譯《苦悶的象徵》過程中,已經得知豐子愷也在翻譯此書,並且知道豐子愷譯本已經列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一情況自然也會為魯迅譯本的出版者所獲知。或許是出於“搶先”的目的,出版者才將該書的出版時間故意提前。如果這一推測成立,那么他們的目的確實實現了——豐子愷譯《苦悶的象徵》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是1925年3月。
魯迅譯本引言
去年日本的大地震,損失自然是很大的,而廚川博士的遭難也是其一。
廚川博士名辰夫,號白村。我不大明白他的生平,也沒有見過有系統的傳記。但就零星的文字里掇拾起來,知道他以大阪府立第一中學出身,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得文學士學位;此後分住熊本和東京者三年,終於定居京都,為第三高等學校教授。大約因為重病之故罷,曾經割去一足,然而尚能遊歷美國,赴朝鮮;平居則專心學問,所著作很不少。據說他的性情是極熱烈的,嘗以為“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所以對於本國的缺失,特多痛切的攻難。論文多收在《小泉先生及其他》、《出了象牙之塔》及歿後集印的《走向十字街頭》中。此外,就我所知道的而言,又有《北美印象記》,《近代文學十講》,《文藝思潮論》,《近代戀愛觀》,《英詩選釋》等。
然而這些不過是他所蘊蓄的一小部分,其餘的可是和他的生命一起失掉了。
這《苦悶的象徵》也是歿後才印行的遺稿,雖然還非定本,而大體卻已完具了。
第一分《創作論》是本據,第二分《鑑賞論》其實即是論批評,和後兩分都不過從《創作論》引申出來的必然的系論。至於主旨,也極分明,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而其表現法乃是廣義的象徵主義”。但是“所謂象徵主義者,決非單是前世紀末法蘭西詩壇的一派所曾經標榜的主義,凡有一切文藝,古往今來,是無不在這樣的意義上,用著象徵主義的表現法的”。(《創作論》第四章及第六章)作者據伯格森一流的哲學,以進行不息的生命力為人類生活的根本,又從弗羅特一流的科學,尋出生命力的根柢來,即用以解釋文藝,——尤其是文學。然與舊說又小有不同,伯格森以未來為不可測,作者則以詩人為先知,弗羅特歸生命力的根柢於性慾,作者則雲即其力的突進和跳躍。這在目下同類的群書中,殆可以說,既異於科學家似的專斷和哲學家似的玄虛,而且也並無一般文學論者的繁碎。作者自己就很有獨創力的,於是此書也就成為一種創作,而對於文藝,即多有獨到的見地和深切的會心。
非有天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無大藝術的產生。但中國現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錮蔽呢?這譯文雖然拙澀,幸而實質本好,倘讀者能夠堅忍地反覆過兩三回,當可以看見許多很有意義的處所罷:這是我所以冒昧開譯的原因,——自然也是太過分的奢望。
文句大概是直譯的,也極願意一併保存原文的口吻。但我於國語文法是外行,想必很有不合軌範的句子在裡面。其中尤須聲明的,是幾處不用“的”字,而特用“底”字的緣故。即凡形容詞與名詞相連成一名詞者,其間用“底”字,例如 Social being 為社會底存在物,Psychische Trauma 為精神底傷害等;又,形容詞之由別種品詞轉來,語尾有 -tive,-tic 之類者,於下也用“底”字,例如 specula^tive,romantic,就寫為思索底,羅曼底。
在這裡我還應該聲謝朋友們的非常的幫助,尤其是許季黻君之於英文;常維鈞君之於法文,他還從原文譯出一篇《項鍊》給我附在卷後,以便讀者的參看;陶璇卿君又特地為作一幅圖畫,使這書被了淒艷的新裝。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之夜魯迅在北京記。
(本篇最初印入《苦悶的象徵》卷首,未在其他報刊發表)
魯迅譯本後序
 譯者魯迅
譯者魯迅這書的著者廚川白村氏,在日本大地震時不幸被難了,這是從他鎌倉別邸的廢墟中掘出來的一包未定稿。因為是未定稿,所以編者——山本修二氏——也深慮公表出來,或者不是著者的本望。但終於付印了,本來沒有書名,由編者定名為《苦悶的象徵》。其實是文學論。
這共分四部:第一創作論,第二鑑賞論,第三關於文藝的根本問題的考察,第四文學的起源。其主旨,著者自己在第一部第四章中說得很分明:生命力受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而其表現法乃是廣義的象徵主義。
因為這於我有翻譯的必要,我便於前天開手了,本以為易,譯起來卻也難。但我仍只得譯下去,並且陸續發表;又因為別一必要,此後怕於引例之類要略有省略的地方。
省略了的例,將來倘有再印的機會,立誓一定添進去,使他成一完書。至於譯文之壞,則無法可想,拚著挨罵而已。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魯迅。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晨報副鐫》,後未印入單行本)
關於《苦悶的象徵》
王鑄先生:
 1923年日本大地震
1923年日本大地震我看見廚川氏關於文學的著作的時候,已在地震之後,《苦悶的象徵》是第一部,以前竟沒有留心他。那書的末尾有他的學生山本修二氏的短跋,我翻譯時,就取跋文的話做了幾句序。跋的大意是說這書的前半部原在《改造》雜誌上發表過,待到地震後掘出遺稿來,卻還有後半,而並無總名,所以自己便依據登在《改造》雜誌上的端緒,題為《苦悶的象徵》,付印了。
照此看來,那書的經歷已經大略可以明了。作者本要做一部關於文學的書,――未題總名的,――先成了《創作論》和《鑑賞論》兩篇,便登在《改造》雜誌上;《學燈》上明權先生的譯文,當即從《改造》雜誌翻出。此後他還在做下去,成了第三第四兩篇,但沒有發表,到他遭難之後,這才一起發表出來,所以前半是第二次公開,後半是初次。四篇的稿子本是一部書,但作者自己並未定名,於是他的學生山本氏只好依了第一次公表時候的端緒,給他題為《苦悶的象徵》。至於怎樣的端緒,他卻並未說明,或者篇目之下,本有這類文字,也說不定的,但我沒有《改造》雜誌,所以無從查考。
就全體的結構看起來,大約四篇已算完具,所缺的不過是修飾補綴罷了。我翻譯的時候,聽得豐子愷先生也有譯本,現則聞已付印,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上月看見《東方雜誌》第二十號,有仲雲先生譯的廚川氏一篇文章,就是《苦悶的象徵》的第三篇;現得先生來信,才又知道《學燈》上也早經登載過,這書之為我國人所愛重,居然可知。
現在我所譯的也已經付印,中國就有兩種全譯本了。
魯迅。一月九日。
(魯迅集外集拾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