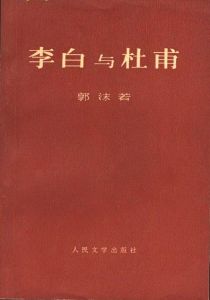內容簡介
 郭沫若
郭沫若寫作原因
 郭沫若和毛澤東
郭沫若和毛澤東1953年4月,郭為杜甫紀念館的題聯是:
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1963年春,郭為李白紀念館的題聯是:
酌酒花間磨針石上倚劍天外掛弓扶桑
那么,郭沫若為什麼要突然180度大轉彎呢?
原因是毛澤東最喜歡“三李”(即李白、李賀、李商隱)的詩,“三李”中又最喜歡李白。對杜甫的詩,毛澤東一向不甚喜愛。1958年1月,在為大躍進作輿論準備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說:“光搞現實主義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在游杜甫草堂時,毛澤東以不甚欣賞的口吻,說杜甫的詩是“政治詩”。毛澤東尤其不滿學術界“揚杜抑李”的傾向,要翻這個案。一位70年代參加《辭海》中國古典文學條目修訂的學者回憶,他聽復旦大學教授劉大傑說過:“毛主席之所以有揚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為前人對杜甫的詩注家太多,號稱‘千家’;李白的詩注家太少,同為大詩人,注家相差卻如此懸殊,覺得有點不平,而在他看來,李白詩的成就與價值又並不在杜詩之下。”
一向緊跟毛澤東的郭沫若,便回響號召,寫了揚李抑杜的《李白與杜甫》。
揚李抑杜
 杜甫
杜甫屈原也曾被稱為“人民詩人”,郭沫若並不曾表示異議,為什麼對杜甫卻大不以為然,還要代表人民追問個所以然呢?實際上人民的追問,一個也沒有接到;為杜甫抱不平的函件倒是收到不少。而郭沫若自己也曾一而再地稱杜甫為“詩聖”,如為草堂撰寫的、並經中國人民郵政製成圖案印在紀念郵票上的那副楹聯就有“詩中聖哲”的話,為成都川劇學校的題詩也有“詩聖至今剩草堂”之句,現在卻來了個大轉彎。要貶低杜甫,首先就得把“詩聖”和“人民詩人”這兩頂新、舊“桂冠”從杜甫頭上摘下來。郭沫若正是從這裡入手的。郭沫若說:“以前的專家們是稱杜甫為‘詩聖’,近時的專家們是稱為‘人民詩人’。被稱為‘詩聖’時,人民沒有過問;被稱為‘人民詩人’時,人民恐怕就要追問個所以然了。”(《李白與杜甫》大字本196頁。以下凡引此書,只注頁碼)
郭沫若曾提到,有人批評他說:“你是偏愛李白,在挖空心思揚李抑杜。”郭沫若不承認,看確是事實。不妨舉出一些例證。比如:李杜二人都好喝酒,但李白喝酒卻有許多好處:一是“當他醉了的時候,是他最清醒的時候;當他沒有醉的時候,是他最胡塗的時候”;二是他的許多好詩都是喝醉後寫出來的;三是喝酒使他從道教的迷信中覺醒過來了;四是使他具有了“平民性”,喝出了一個“太白世家”、“太白遺風”。而杜甫的喝酒,卻一點好處也沒有,也沒有喝出一個“少陵世家”或“少陵遺風”,最後還死於酒。就這樣,儘管郭沫若在行文中也曾說李白是“生於酒,死於酒”,但“終身嗜酒”的帽子還是落在杜甫頭上。
說到門閥觀念,唐代文人都很重,李杜二人也毫不例外。比較起來,李白還更嚴重。為了拉關係,他可以把自己降低幾輩子。郭沫若已舉出不少例子,這裡要補充一點的是李白還和唐王朝一樣在詩中一再稱老子為“吾祖”、“先君”。說實在的,杜甫還沒有荒唐、庸俗到這種地步。然而“門閥觀念”的帽子卻又落在杜甫的頭上。
談到物質生活,李白比杜甫要優越得多,這是用不著舉例的,翻開他的詩集就可以看到。但郭沫若卻不去說,反而斤斤計較,拐彎抹角,尋章摘句來證實杜甫過的是一種“地主生活”,並寫成專章。過著地主生活的詩人誰不討厭,可惜的是這種說法並不符合杜甫的實際。關於杜甫的困窮生活同樣用不著舉例。這裡只談一點對杜甫“無衣思南州”這句詩的感受。去年十月中旬,由上海去廣州,穿的是兩件毛衣和一件毛背心。但到廣州時,就脫得只剩下一件襯衫了。這時,忽然想起杜甫這句詩,並從這句詩里理解到詩人的貧困。“南州”就是現在的廣東省一帶地區,當時士大夫們都怕去,如果不是貧困,杜甫就不會有這種想法。杜詩中還有不少談到他曬太陽取暖的情況,如在夔州時寫的“杖藜尋晚巷,炙背近牆暄。”(《晚》)又“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西閣曝日》)舉此一端,他的貧困也就不難想見。但郭沫若卻放過李白,反而抓住經常不免挨餓受凍的杜甫給戴上“地主生活”的帽子。
揚李抑杜的例子,書中是很多的。有的偏愛偏惡還非常明顯。比如同樣是用的比喻手法,當李白用“大鵬”或“鸞鳳”自比時,太平無事,而當杜甫以“老驥”、“飢鷹”自比時,卻被斥為:“雖然在以鷹驥自擬,其實是自比於禽獸。”(244頁)其實要罵杜甫自比於禽獸,不如舉“狗”為例,杜甫是曾經兩次自比於“喪家狗”的。然而這能說是杜甫的罪過和恥辱嗎?“酷見凍餒不足恥!”杜甫自己早作了回答。又如,同樣是用的誇張手法,但李白的“白髮三千丈”沒有問題,而曾獲得陳毅讚賞的杜甫的名句“青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卻遭到指責,說“松樹要高到一千尺,是不可能的”。
李、杜同樣是推崇屈原的,但郭沫若卻硬說杜甫“抑屈揚宋(玉)”。其實杜甫對屈原從無貶詞,倒是李白有時加以非笑:“投汨笑古人。”杜甫走過的地方很多,見聞很廣,對事物能有個比較。所以詩中往往用“天下”來突出祖國某一地區的山川或人物的特點。前者如“劍門天下壯”、“西蜀地形天下險”等,後者如“越女天下白”。江南女子比較白晰,這是事實。她們自己也不否認,如南朝民歌:“跣把絲織履,故交白足露。”李白詩中也寫到,如“耶溪女似雪”,“屐上足如霜”,“兩足白如霜”,真是不一而足。但郭沫若偏抓住杜甫那句詩大作文章,並譏諷說“杜甫也並不經常是那么道貌岸然的”。
 李白
李白揚李抑杜的一個最突出的例子,是關於李白那首“劃卻君山好”的絕句的解釋,原詩是:“劃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郭沫若說李白要劃卻君山的動機目的,是因為“他看到農民在湖邊屯墾,便想到更加擴大耕地面積”,“是從農事上著想”,“應該說才是真正為了人民”。(185、186頁)。如果一定要說李白的“劃卻君山”是“為了人民”、“是從農事上著想”,卻很值得商榷。第一,李白這首詩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天寫的,而秋天的洞庭湖,正是所謂“八月湖水平”、“洞庭秋水闊”的時候,根本不可能出現“湖中多種田”的事情,李白也不可能看到農民的屯墾,從而產生擴大耕地面積的想法。(郭沫若引杜詩“宿槳依農事”為證,是誤解,詳後。)第二,李白這首詩的題目是《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後》,在這種情況下寫的詩,會忽然想到要劃卻君山來擴大耕地面積,也實在有些離奇。足見這不過是李白醉後的豪言壯語。郭沫若說“洞庭湖裡的水,湘江里的水,不能直接變為酒”,意在表明李白要劃卻君山,不可能是為了想多喝酒。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第三,劃卻君山,不但不能達到擴大耕地面積的目的,反而要縮小耕地面積。因為李白並不是要填湖造田,而是要把君山淹沒在湖裡,以便“平鋪湘水流”的。有君山,農民還可以植樹造林,搞梯田;現在把它劃了,還擴大什麼耕地面積?而且,被唐人形容為“水晶盤裡一青螺”的小小君山,即使劃了,又能擴大多少耕地面積?這也就是說,李白不會有這種想法。李白這首詩,卻實在看不出是為農業著想,為人民著想。
郭沫若曾說:“翻案何妨傅粉多。”郭沫若對李、杜二詩人的抑揚未免過當,似與這種翻案觀點有關。
人物評價:李陽冰在《草堂集序》中稱讚李白:“千載獨步,惟公一人”。
杜甫對李白評價甚高,稱讚他的詩“驚風雨”、“泣鬼神”,而且無敵於世、卓然不群。
韓愈對李白極為推崇;在《調張籍》有言“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在《石鼓歌》又嘆“少陵無人謫仙死”。
唐文宗下詔將李白的詩歌、裴旻的劍舞、張旭的草書稱為“三絕”。
蘇軾《和陶淵明〈飲酒〉》)贊李白“一杯未盡詩已成,涌詩向天天亦驚。”
黃錦祥對李白杜甫同贊道:“執唐詩牛耳者,唯李杜二人也!”
余光中《尋李白》“酒放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
曲解杜詩
作家和作品是分不開的。要貶低杜甫,就必然要貶低杜詩。因此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對杜詩特別是那些歷來傳誦的名篇警句幾乎作了全盤的否定。可以說,幾乎無一完篇。這集中的表現在第一章《杜甫的階級意識》里。
在這一章中存在著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曲解。
杜甫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兩句詩是寫於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即公元755年12月,也就是杜甫困守長安十年的最後一年的最後一個月,是他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的產物。可是郭沫若卻說這兩句詩“顯然是從‘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孟子·梁惠王》)脫胎而來。”(193頁)郭沫若說這兩句詩是由《孟子》脫胎而來,無異於說是從《孟子》偷襲而來。這就不僅抹殺了這兩句詩的獨創性,而且顛倒了創作的源流。千百年來的詩人,誰沒有讀過《孟子》,為什麼卻脫胎不出來?杜甫自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為什麼也要等到困守長安的最後一年才脫胎出來?可見,所謂“脫胎而來”的說法,並不符合杜甫創作的實際。只不過是為了貶低杜詩的一種曲解,一個藉口。1962年,郭沫若在為紀念杜甫而作的《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一文中,曾讚揚這兩句詩是“響徹千古的名句”,並指出不在饑寒交迫、和人民打成一片的生活中是不能產生的。
苛求古人
具體說來,即苛求杜甫,對杜甫提出了不應有的過高要求。比如為了進一步否定、貶低“朱門”二句,郭沫若追問杜甫,你“既認識了這個矛盾,應該怎樣來處理這個矛盾?也就是說:你究竟是站在哪一個階級的立場,為誰服務?”(193頁)要求一千多年前的杜甫提出解決階級矛盾的方案,要求杜甫完全徹底地背叛他的本階級站到人民的立場上,為人民服務。有這么一種傾向:越是好作品,郭沫若就越要苛求。《三吏》、《三別》是杜甫的傑作,郭沫若也是首肯的,但又說:“但在今天,從階級的觀點來加以分析時,詩的缺陷便無法掩飾了。”(210頁)因而在談到《無家別》時,郭沫若說:“這首詩可能是六首中最好的一首……特別是最後一句:‘何以為蒸黎?’作者把問題提出來了,但沒有寫出答案。”(203頁)。
脫離歷史背景
從唐以來,杜詩就被稱為“詩史”。所以對杜詩,特別需要就當時的社會現實作一番周密考查,把一定的作品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來分析,才能作出比較正確的結論。
《三吏》《三別》這六首詩,是杜甫在安史之亂期間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春,唐王朝的六十萬大軍為叛軍所擊潰,形勢異常危急,這一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寫的,因此要理解這六首詩,就必須密切結合當時的歷史情況。但郭沫若卻脫離歷史背景,孤立地進行評論,這就必然要曲解這六首詩。
比如郭沫若在談《新婚別》一詩時說:“全詩是新娘子的泣別詞,把新娘子寫得十分慷慨,很識大體,很有丈夫氣。但這無疑是經過詩人的理想化。”(199頁)所謂“理想化”,意思是說新娘子這個人物形象是不真實的,是杜甫捏造出來的。但實際上在杜甫寫此詩的前幾個月,就已經有了唐四娘、侯四娘、王二娘等婦女自動集體參軍的事情,可見,對於當時的社會現實,杜甫並不是寫得過了頭。
由於脫離歷史背景,郭沫若對這六首詩中的人民形象和基本精神,也作了全面的歪曲。他說:“這六首詩中所描繪的人民形象,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經過嚴密的階級濾器所濾選出來的馴良老百姓,馴善得和綿羊一樣,沒有一絲一毫的反抗情緒。”郭沫若還援引杜甫晚年寫的《甘林》詩中的“勸其死王命”這一句,說“這就是杜甫的基本態度,也就是這《三吏》和《三別》的基本精神。”(211頁)這些說法,很值得商榷。似乎有必要先明確一下由安史叛亂而引起的戰爭的性質問題。歷史認為安史之亂不是一般的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而是帶有民族矛盾這一特殊性的叛亂。而這一民族矛盾,由於異族安祿山肆行民族歧視和壓迫,到處燒殺淫掠,“所過殘滅,又益形嚴重”。這就使得唐王朝為維護其封建統治地位而進行的平叛戰爭具有維護統一,制止分裂,反擊異族野蠻侵略的正義性質。因而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當時大河南北,人民紛起抗擊叛軍,大或幾萬,小亦數千。他們根本就不需要唐王朝的什麼“王命”,更用不著誰來勸勉,而是自動地組織起來,走上戰場。當時不少少數民族如回紇等也表示“助順”,為國“討賊”。當時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的情況,對於這六首詩中的人民形象才能有一個較為正確的認識。才能理解當時人民為什麼能忍受痛苦承擔著根本不應由他們來承擔的兵役而終於走上戰場的原因。這正是一種愛國主義精神的表現。郭沫若不顧歷史條件,簡單地把這些人民形象一概視之為“馴善”的“綿羊”,是值得商討的。
抹殺杜詩的藝術特點
杜甫寫了比他的前輩和同時代的任何詩人都要多的敘事詩。這些反映現實的敘事詩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儘量避免主觀色彩。不空發議論,不幫腔,甚至不讓自己的激情明顯地流露在字裡行間。而是把它融化在客觀事實中,讓事實說話,讓事實去直接感染讀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石壕吏》。比如“有吏夜捉人”這一句,如果杜甫打著官腔,真如郭沫若所說的是站在“吏的立場上”,他滿可以說“有吏夜徵兵”。但杜甫卻作了如實的暴露,“捉人”就是捉人。從詩中“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這兩句來看,非常明顯,杜甫並沒有睡大覺。那媳婦哭泣了一夜,他也聽了一夜。什麼是“如聞”?這就是仿佛聽見。表明如果不是用心地側耳細聽還聽不見。但郭沫若卻責怪杜甫說:“詩人完全作為一個無言的旁觀者,是值得驚異的。”(208頁)。
死扣字面
如對《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寒士”的解釋,便是這樣。郭沫若說:“詩中所說的分明是‘寒士’,是在為還沒有功名富貴的或者有功名而無富貴的讀書人打算,怎么能夠擴大為‘民’或‘人民’呢?”(215頁)把“寒士”解釋為窮讀書人,從字面上來看,是很準確的,似乎是無可非議,無懈可擊。但在這裡,以為是能夠而且應該擴大為“窮人”的:第一,古代男子通稱為“士”,《詩經》里就很多。春秋以後,“士”也不是“讀書人”的專用名詞。“士”之與“民”,有時有所區別地對立著說;有時則是混用,如《韓非子·亡征》:“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又《和氏》篇也有“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所謂“耕戰之士”,還不就是“耕戰之民”嗎。可見,士與民之間並無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白居易的“穩暖皆如,天下無寒人”,顯然也是從杜詩得到啟發的。第二,魯迅說:“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從杜甫的全人來看,也應該引伸為“窮人”。他說“窮年憂黎元”,卻不曾說“窮年憂寒士”;他說“一洗蒼生憂”,卻不曾說“一洗寒士憂”,他的同情心偏在哪一面,還不清楚嗎?未必在這裡他就把老百姓排除在外了。第三,把“寒士”理解為老百姓,是古已有之的。
有“南村群童欺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這么兩句,如死扣字面,那“群童”就只能解為“一群兒童”。但郭沫若卻要給這群兒童定階級成分,把他們都說成是“貧窮人的孩子”、“農民的兒童”。從而呵斥杜甫:“使人吃驚的是他罵貧窮的孩子們為‘盜賊’”;“貧窮人的孩子被罵為‘盜賊’,自己的孩子卻是‘嬌兒’”。要斷言這些村童都是貧農成分,其中就沒有地主富農的孩子,是很困難的。從詩中描寫的情景來看,其中顯然有惡作劇的頑童。杜甫的《泛溪》詩就曾經寫到這批頑童。當時浣花溪南北兩岸都有。
由於不顧全篇,死扣字面,郭沫若在另一面卻美化了李白的“欲折月中桂,持為寒者薪”這兩句詩。郭沫若說:“李白是要為‘寒者’(請注意,不是‘寒士’)添柴燒,想上天去扳折月中桂。”(187頁)單從這一句的字面來看,不錯,“寒者”不是“寒士”。但從全篇來看,這個“寒者”恰恰是寒士,而且是個高級寒士,即李白自己。這兩句詩見於《贈崔司戶文昆季》一詩,可以復按。扳折月中桂,能添多少柴?李白晚年也有時哭窮,所以又有“願假東壁輝,餘光照貧女”(《陳情贈友人》)之句。這個“貧女”,也是自喻,不是寫實。同樣不能死扣字面。
除上述情況外,有的曲解還脫離作品本身,近於深文周內。《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這首詩,郭沫若也認為“在舊時代可以算得是一篇好作品”。但又援引《唐書·嚴武傳》說“武窮極奢侈,賞賜無度。或由一言,賞至百萬。”因而推論杜甫“借老農的口來讚美嚴武”,是“借花獻佛”,是“在使用曲筆”,並斷言:“杜甫的這首詩,不知道要得到多少報酬了?”這樣一來,所謂“一篇好作品”也就被取消了。它不過是一篇為自己謀取厚利而吹捧長官的諛詞。這是既不符合杜甫作詩的目的,也不符合事實。
誤解杜詩
在誤解杜詩這個問題上,可以列舉以下一些詩句為例:
(1)“宿槳依農事,郵竿報水程。”這是杜甫晚年漂泊到湖南時寫的《宿青草湖》一詩中的兩句。郭沫若為了要證明洞庭湖中有農民墾田,曾引用了上一句詩作證。郭沫若是這樣解釋的:“青草湖在君山之南,實際上是洞庭湖的繼續。‘宿槳依農事’,便是說水退了,人們把船槳放在一邊,又拿起鋤頭來開墾。注家有人認為‘湖中多種田’(楊倫《杜詩鏡銓》),這是正確的。……要感謝杜甫為留下了唐代的實據。”(185頁)這樣解釋是不對的。詩題明明標出是《宿青草湖》,詩中的“宿槳”的“宿”字,自然是指“過宿”,也就是過夜。所謂“宿槳”,等於說“停船過夜”。“依農事”,是說的泊船的地點是靠著有農民臨時居住的地方。這個“依”字,和杜甫另一句詩“依沙宿舸船”的“依”一樣,都是依靠的意思。為什麼要依靠著有農民居住的地方呢?這正如楊倫注說的“所以備盜”。從杜甫寫於這同一時期的詩句“側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來看,當時這一帶確有“水賊”,所以不敢孤舟夜泊。這句詩,是自敘,而不是寫的農民。附帶說明一下,杜甫這句詩是可以用來證明“湖中多種田”的,但卻不能用來證明李白“劃卻君山好”那首詩也反映了“湖中多種田”的情況。因為寫作地點不同。青草湖雖連著洞庭湖,但它比洞庭湖淺,水涸時,長滿青草,所以叫“青草湖”,而李白那首詩則是寫於洞庭湖上的。同時寫作季節也不同。杜甫這首詩寫於春初水小的時候,而李白那首詩則是“洞庭秋水遠連天”時寫的。哪裡會出現湖中種田的事情呢。
(2)“朝廷問府主,耕稼學山村”。這是杜甫在夔州時寫的《晚》一詩中的兩句。詩中的“府主”,指夔州都督柏茂琳。這兩句詩,在句法上,在組織結構上,有些特殊。最主要的一點,是省略了主語,也就是詩人自己。還有一點也值得注意,就是在對法上,它們是平列式的對偶句,而不是所謂“流水對”或者說“走馬對”。它們說的是兩碼事,彼此不相干,不能把這兩句串通起來講。因此,這兩句的真正意思,應該是這樣:關於朝廷之事()問之於府主;關於耕稼之事()學之于山村。或者說:()向府主打聽朝廷的訊息;()向農民學習農活兒。但郭沫若未免把這兩句詩看左了。他把“朝廷”當作主語,又把柏茂琳讓杜甫主管東屯的一百頃公田這件事和朝廷聯繫起來,因而解釋說,這兩句詩“透露了他主管東屯的內部事實。是‘朝廷’向夔州都督打聽了杜甫的情況,故柏茂琳讓他主管東屯。”杜甫能夠得主管東屯一百頃公田的職務,“這大約是由於柏茂琳的推薦而得到‘朝廷’的允許。”(266頁)這是一個大有關係的誤解,也不符合實際情況。象主管一百頃公田這等小事,堂堂夔州都督竟作不了主,還得請示朝廷嗎?杜甫早已作過從六品的檢校工部員外郎,象這樣連一個官銜也沒有的公田主管,也值得“推薦”嗎?還有,杜甫自己就慨嘆於“朝廷記憶疏”,這個朝廷又哪裡會惦念著他而向夔州都督打聽他的情況呢?事實恰恰相反。不是朝廷向夔州都督打聽杜甫的情況,而是杜甫向夔州都督打聽朝廷的情況。也不只是向夔州都督一個人,凡是來往經過夔州的朝廷使者,他都要一個不肯放過的向他們打聽。如《入宅》詩:“相看多相者,一一問函關。”又如《溪上》詩:“西江使船至,時復問京華。”又《柳司馬至》:“有客歸三峽,相過問兩京。”這些便都是證明。這也表明杜甫確是一位非常關心國家大事的詩人。正如他自己說的“日夕思朝廷”。如果象郭沫若解釋的,那杜甫這種憂國憂民的精神也就化為烏有了。
(3)“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這是《遣遇》一詩中的兩句。杜甫的諷喻詩的一個特點,就是他往往使用一種“陽褒陰貶”的諷刺手法。這類詩句,從表面上乍一看,很象是頌揚,其實只要略一細按,便知是諷刺。因而杜詩中時有上下兩句自相矛盾的現象。比如:“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奉贈盧五丈參謀琚》)上句是抽象的肯定,下句便是具體的否定,表白所謂“多恩澤”者,徒虛語耳。這種通過自相矛盾來表現諷意的情況,有時竟然會出現在一句之中,如“聖主國多盜,賢臣官則尊。”(《覽柏中丞除官制詞載歌絲綸》)這兩句便是這樣。試想:豈有“國多盜”而可以稱為“聖主”,又豈有只是官高祿厚而可以稱為“賢臣”的?這比直言“昏主”和“奸臣”,要反而有力,有味得多。至於“貴人豈不仁”這兩句,可以說是兼而有之的。因為“貴人豈不仁”這一句本身就具有貌似頌揚實則諷刺的兩重性,是說反話;而下一句“視汝如莠蒿”,則是用事實來證明貴人的不仁,揭穿他們的偽善面孔的。
但是,由於郭沫若對杜甫有成見,認為杜甫總是“罵罵‘小吏’,而為‘大吏’大幫其忙。”因而他解釋說:“他把橫徵暴斂、苛差勞役的暴政,歸罪於在下的奸猾小吏,而說在上的‘貴人’是仁慈的。”(212頁)為了自圓其說,郭沫若還把“貴人”這兩句上面的兩句“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和這兩句下面的兩句“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全都刪節了。這大約是因為感到造成這樣普遍的嚴重局面,不能只歸罪於小吏,“貴人”應該是罪魁禍首,所以都刪節去了。這是欠妥當的。說到杜甫對大吏的態度。那也不是什麼“大幫其忙”。“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洗兵馬》),“自古聖賢多薄命,奸雄惡少皆封侯”(《錦樹行》),他還大罵“衣冠兼盜賊”(《麂》),象這類詩句,能說是為貴人們“大幫其忙”嗎?郭沫若還舉出《新安吏》的“僕射如父兄”為例,應該指出,這是史有明文的事實:“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見於《通鑑》卷223)。
其實,關於“貴人”二句諷刺的對象就是貴人,這一點前人早已看出。宋人劉克莊就說:“夫死於役,僅存婦女采蕨鬻菜以輸官,夫民之窮甚矣!而官吏刻削尤甚於錐刀。此獨不指里胥、亭長輩,內自租庸使,外自觀察使,不得不受其責,故有‘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之句。錄之以告居大位者。”(《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82)仇兆鰲更說得直捷了當:“曰豈不仁,諷刺隱然!”是符合作者本意的。杜甫這種明褒暗貶的諷刺手法,有時也用之於全篇,《麗人行》便是最好的例子,句句似讚美,其實句句是諷刺。
(4)“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這是《詠懷古蹟》第二首的頭兩句。知道,杜甫在學習上是主張“多師”的。但他也有所區別,絕不是一視同仁。這裡的“亦吾師”的“亦”字,便下得很有分寸。因為這個“亦”字是把宋玉和屈原作對比而言的。和《沙苑行》的“雖未成龍亦有神”、《北征》的“幽事亦可悅”的“亦”字,意味相似。不能簡單地以口語中的“也”或“也是”來替代。但郭沫若卻解釋說:“他(杜甫)視宋玉為師。所謂‘亦吾師’者,是承第一首來,庾信是師,宋玉也是師。在這裡屈原的位置便沒有了。”(279頁)這是很值得商榷的。據看,不是屈原的位置沒有了,而是提高了,提高在宋玉之上了。盧元昌《杜詩闡》說:“屈原,固宋玉師,宋玉之風流儒雅,亦千秋以下、異代之師。”把這句和屈原聯繫起來解釋,是正確的。
郭沫若硬派杜甫是“抑屈揚宋”的。因而責備杜甫說:“在這一段地帶裡面,秭歸有屈原宅,杜甫明明知道,但卻沒有興趣來專門詠吟了。”(278頁)是的,杜甫明明知道這兒有屈原宅,但他並沒有忘記,而是把它用在最高、最恰當、最足以表明屈原身分的地方了。如《最能行》最後兩句:“若道士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他不說“何得山有宋玉宅”,而用屈原作“英俊才”的代表,難道這還不足以證明杜甫是把屈原的位置放在宋玉之上了嗎?對於宋玉的懷念,李白有時也是一往情深的。如《宿巫山下》一詩中就有“高丘懷宋玉,訪古一沾裳”之句。
杜甫之死
 杜甫
杜甫從北宋以來,一直到目前仍然存在著爭論的,是第一和第二兩種說法。第一說見於唐著名詩人元稹所作《杜君(甫)墓系銘》,第二說見於唐鄭處誨的《明皇雜錄》。
郭沫若是極力主張第二說的,認為“杜甫死於牛酒是毫無可疑的”。所以,凡是有助於證明這一說的理由都不肯放過,甚至不顧事實。比如郭沫若說鄭處誨“上距杜甫之死僅六十年左右。史稱其人‘方雅好古’,所述杜甫死因不會是無稽之談,故新舊《唐書·杜甫傳》均從其說。”(317頁)按元稹年代要比鄭處誨早二三十年,他那篇墓志銘是唐憲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即杜甫死後四十三年寫的,而鄭處誨則是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才中的進士。如果要以年代先後作為真偽的標準,那就應該從第一說,而不應從第二說。新舊《唐書·杜甫傳》採用《明皇雜錄》,顯然也不是因為它的年代早於元稹的墓志銘。因此這一條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在杜甫之死的問題上,郭沫若是堅信正史新舊《唐書》的。但《舊唐書》說杜甫是因“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新唐書》無異詞,只改“夕”為“昔”(二字古通用),所謂“一夕而卒”,就是說睡了一夜就死了。這也就是說,即使如郭沫若構想的那樣,牛肉很多,一次沒有吃完,他也吃不上第二次了。哪裡還說得上中毒?
要讓杜甫死於“腐肉中毒”,除非聶令送來的牛肉一送來就是腐敗的,同時杜甫自己連腐敗了的肉也辨別不出。而在《聶耒陽以仆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一詩中,他極口讚揚聶令:“義士烈女家,風流吾賢紹。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從“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兩句來看,杜甫似乎還是吃得津津有味的。因此,郭沫若認為“杜甫死於牛酒,既見諸史籍,又可以用腐肉中毒被酒所促進而加以科學的說明”這種說法,由於缺乏事實根據,是並不科學的。
杜甫之不死於耒陽阻水,不死於牛酒,這是有他自己的詩作證明的。啖牛肉白酒,是唐代宗大曆五年(公元770年)夏天的事情,但有某些詩卻可以確定是寫於這年的夏天以後。如《長沙送李十一銜》這首詩便是寫於這年的秋天的。因為根據詩中“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兩句,可以明確無誤地推定是在這一年,這是郭沫若也承認的。但詩有“朔雲寒菊倍離秋”之句,分明寫的是秋天景物,如不加以否定,就要動搖“死於牛酒”一說,使之處於不攻自破的窘境。因此,郭沫若在把“十二秋”的“秋”字解釋為“春初”之後,又為“寒菊”二字強作辯解,說“長沙地暖故在春初猶有‘寒菊’,不能以為秋季的證明。”(325頁)長沙雖較暖,卻並非嶺南,春初是否有菊花,大是疑問。
表明杜甫不可能死於牛酒的一個最強有力的證據,是《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一詩。這才確是杜甫的絕筆,作於大曆五年(公元770年)的冬天。因為詩的頭一段有“故國悲寒望,群雲慘歲陰”和“鬱郁冬炎瘴,雨滯淫”等句。這分明是寫實,但郭沫若為了維護他的主張,卻硬說是“回憶”,不是寫實。他解釋說:“其實這些句子是大曆三年冬初來長沙時的回憶。”(327頁)這是說不通的:第一,說這些句子是回憶,等於說詩的頭一大段也都是回憶。而這頭一大段是緊扣詩題“風疾舟中”的。如詩中“舟泊常依震”的“舟”,就是詩題中的“舟”,也就寫此詩時所乘之舟,是實實在在的。把這一大段說成回憶,首先就跟詩題發生矛盾。難道能說這詩題也是表明“回憶”的嗎?第二,即使如郭沫若所說是“回憶”,那么回憶中的景物也應該是春初的景物而不應是冬天的景物,因為杜甫由岳陽來長沙是在大曆四年的春初,有許多作品可以證明。(郭沫若說杜甫大曆三年冬來長沙,是錯誤的。)第三,如果開頭一大段就是回憶,那杜甫照例會用“憶昔”、“憶昨”、“昔者”、“往日”這類表明回憶的字樣向讀者作交代。但卻連一點回憶的痕跡都找不出。詩言“時物正蕭森”,所謂“時物”,自然是指作詩時所見眼前的景物,與回憶的口吻也根本不合。因此,要把這一段曲解為回憶,從而取消這首詩寫作的真實時間,以自圓其說,是辦不到的。至於詩中“春草封歸恨”一句,不過是一筆帶過的追敘,不能作為此詩寫於春季的證明。
關於李杜優劣的問題。有的揚李抑杜,有的揚杜抑李。但總是在肯定李杜兩位詩人這一總的前提下來將他們分個高低優劣的。而郭沫若呢,對李白是愛護備至,恨不同時:“借問李夫子:願否與同舟?”(53頁)而對杜甫則未免有點深惡痛絕,說什麼“總之,杜甫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方面都遵循著地主生活方式。”(276頁)象郭沫若這樣的“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絕對化的抑揚法,還是前所未有的。
 杜甫草堂
杜甫草堂揚李抑杜或揚杜抑李這種情況,並不是從中唐時期才開始的。可以說說當他們還在青壯年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高適、岑參、嚴武等人可以說是傾向於杜甫的,而賈至、王昌齡等則是傾向於李白的。杜甫有贈賈至的詩,賈至沒有回答,但和李白卻唱和得很熱乎。
第一個公開地揚杜抑李的是元稹,見於他寫的杜甫墓志銘。但他也並沒有抹倒李白。他所說的“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是專指排律這類詩說的,不是指的全部詩作。這一點是應該為元稹說明的。問題是他不應把杜甫擅長的歡喜寫的和李白不歡喜寫的排律來作比較。第二個揚杜抑李的是白居易,見於他的《與元九書》。他從詩的思想內容方面突出了杜甫,但也絲毫沒有要壓垮李白的意思。
北宋時,揚李抑杜的有楊億、歐陽修,但他們也不能不佩服杜甫。認為有“時雖一字,亦不能到”,如關於杜詩“身輕一鳥過”的“過”字。揚杜抑李最力的是王安石。說李白的詩,十句就有九句言婦人和酒。雖不免言之過當,但也承認李白詩“豪宕飄逸,人固莫及”,而所編《四家詩選》,仍有李白的位置。此後的情況,也差不多。其實,關於李杜二人的評價問題,他們自己相互之間早已作出了鑑定。杜甫說:“白也詩無敵!”李白在送別杜甫時也說:“飛蓬各自遠!”。事實證明,揚李抑杜,或揚杜抑李的做法,根本就不符合李杜本人的意思。
書籍目錄
一、關於李白李白出生於中亞碎葉
李白的家室索隱
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第一次大失敗
——待詔翰林與賜金還山
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第二次大失敗
——安祿山叛變與永王璘東巡
李白在長流夜郎前後
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覺醒
李白與杜甫在詩歌上的交往
二、關於杜甫
杜甫的階級意識
杜甫的門閥觀念
杜甫的功名欲望
杜甫的地主生活
杜甫的宗教信仰
杜甫嗜酒終身
杜甫與嚴武
杜甫與岑參
杜甫與蘇渙
三、李白杜甫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