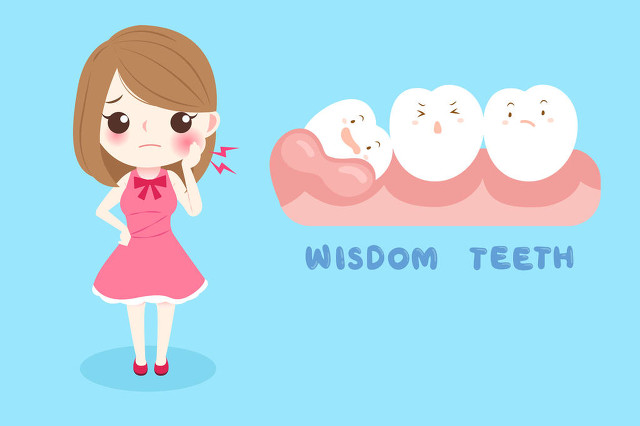人家基督教有至高無上的羅馬教皇,孔子有沒有做“儒教教皇”的動機呢?我看是有的。其一,孔子是有執政治國方針的,那就是以儒治國,靠道德的力量教化子民。他說:“用政治法令來領導百姓,用刑罰來矯正他們,百姓只是求免於刑罰而沒有羞恥心。假使用道德來感化他們,用禮儀來齊一他們們的行為,這樣,百姓不但能有羞恥心,而且還會自發的向正當的方面去努力”;其二,孔子執政治國是“有法可依”的,他說:“《禮經》可以節制人的行為,《樂經》可以誘發人的和氣,《書經》可以借知人類行事的成敗,《詩經》可以表達情意,《易經》可窺知天地的神奇變化,《春秋》可以明白微言大義。”;其三,孔子是有治國執政決心的,他放出響炮:“假如有人能重用我,我一年的時間就可把國家治好的。”;其四,孔子是有執政治國團隊的,他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小窺。
但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舞台上,孔子是一位失敗的了英雄。他的崇高榮譽是在死後才被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追封的。
孔子最終沒有做成儒教教皇,做不成“儒教教皇”的原因,孫玉良認為至少有三:
其一,孔子的執政方針不能順應時代需要。孔子週遊到了東方大國齊國,本來齊景公是想重用孔子的,可被賢明的晏子潑了冷水,“冷水”重點之一指明了孔子以禮治國不合時宜:“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晏子說的話有沒有道理,孫玉良認為很有道理。在亂世之秋,大爭之世,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哪有精力學習並遵守繁瑣的尊卑上下禮儀、舉手投足的節度?這時候富國強兵才是保證國家安全最重要的手段啊。歷史證明,那個時候,實用的兵家、法家才是順應歷史潮流的執政治國方略,想“復古”搞堯、舜、禹原始共產主義那一套,哪裡會有人聽?
其二,孔子的強大團隊讓君主有顧慮不敢用。孔子週遊到了春秋大國楚國,本來楚昭王是想重用孔子的,可被楚國令尹子西再一次潑了冷水。子西問楚昭王:“大王出使諸侯的使者有像子貢這樣的嗎?”昭王說:“沒有。”令尹子西說:“大王的宰輔國相有像顏回這樣的嗎?”昭王說:“沒有。”令尹子西說:“大王的將帥有像子路這樣的嗎?”昭王說:“沒有。”令尹子西說:“大王的各部長官有像宰予這樣的嗎?”昭王說:“沒有。”令尹子西說:“況且楚國的祖先在周受封時,名號為子男,封地方圓五十里。如今孔丘祖述三皇五帝的法度,彰明周公、召公的事業,大王倘若任用他,那楚國還怎么能世世代代擁有堂堂正正方圓幾千里之地呢!周文王在豐京,周武王在鎬京,從只有百里之地的君主最終統一天下。如今孔丘得以占據封地,有賢能的子弟作為輔佐,這不是楚國的幸福啊。”子西總結的“四個沒有”和孔子的“王道霸心”讓楚昭王噤若寒蟬,唯恐祖宗傳下來的大好江山被孔子一班人用嘴皮子“和平演變”,因此再一次讓孔子吃了閉門羹。
其三,孔子志大才疏,並沒有一個政治家應有的手腕和魄力。孔子唯一的一次執政是在他五五十多歲時當了魯國相當於今天法務部長職位的大司寇,且代行魯相職務。按理說歷史是給了他“弄潮”舞台的,但孔子在這個舞台上僅表演了短短三四年時間就灰溜溜落了幕。楚國令尹子西所擔憂的事並沒有在魯國成為事實,孔子團隊雖然冒似很強大,但孔子到底不是一個政治家,“兵慫慫一個,將慫慫一窩”,孔子並沒有為實現他的理想組建“梁山團隊”,孔門弟子也並沒有在他的指揮下發動什麼政治戰役,而且其弟子各自效忠自己的主人,沒有主動地團結在以孔子為首的“儒教教主”周圍。孔子最後被排擠出局無力反抗,用事實證明他在政治舞台上不過是只“紙老虎”、“弱智兒”。
孔子 儒家 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