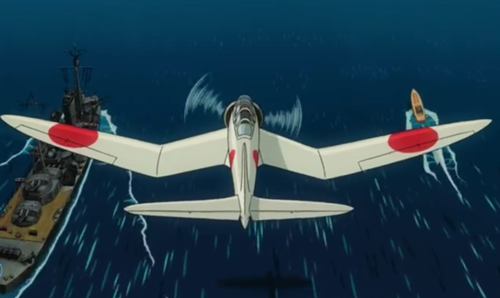話劇才女廖一梅在其著作《琥珀》前言裡說她喜歡花花公子,“那些情聖,或者說那些假情聖,那些喜歡誘惑的登徒子”,海派小說祖師奶奶張愛玲雖不曾明說,從她的第一任丈夫胡蘭成到她的小說人物,可知她也如廖一梅一樣偏愛花花公子,而她筆下的最著名的花花公子便是《傾城之戀》里的范柳原。
 《傾城之戀》劇照
《傾城之戀》劇照范柳原本為印尼富商私生子,因父親猝死被家族排擠失去繼承權,不名一文,"孤身流落在英倫,很吃過一些苦,然後方才獲得繼承權"。年輕的挫折讓他看破人情冷暖,參透人生虛無,於是玩世不恭的在放浪的一條路上走著,吃喝嫖賭樣樣都來,於鶯鶯燕燕之間遊戲人生。
對環繞在他身邊的女人,他那些或者很猛或者聰明的情話張嘴就來,對女主白流蘇,他半真半假的說“我愛你,我一輩子都愛你,”說她穿著綠雨衣像只藥瓶——再湊近一點:醫我的藥,而只想把他當成冤大頭收留自己漂泊無著的下半生的白流蘇又豈是吃素的,這個精刮的女人亦是從容而有技巧的應對著不走心的調情,就這樣,一對熟男熟女駕輕就熟的玩著“調情”這個其實無聊又可憐的愛情遊戲。
《第一爐香》中,張愛玲描述其筆下另一大花花公子喬琪喬:“(他)不肯好好地做人,他太聰明了,他的人生觀太消極,他周圍的人沒有能懂得他的,他活在香港人中間,如同異邦人一般。”這一評價用在范柳原身上也相當中肯,他與喬琪喬一樣,都是“太聰明”和“人生觀太消極”的人。

可能這便是花花公子的本質吧,他們認為人生已經不值得認真度過,無所謂追求,無所謂痛苦,生活中絕大部分內容對只是一場一場的相互欺騙、相互玩弄的無聊遊戲。
所幸,范柳原不是天生的花花公子,只是遭受打擊對人生失去信心後走上的虛無,雖對人生無所期望,但他仍不時牽掛遠眺著彼岸的理想世界,面子上的“不正經”更大成分上是他遊刃於這個並非脈脈溫情的世界的鎧甲和保護色。
不妨看他跟流蘇的一段對話:
流蘇抬起了眉毛,冷笑道:"唱戲,我一個人也唱不成呀!我何嘗愛做作──這也是逼上梁山。人家跟我耍心眼兒,我不跟人家耍心眼兒,人家還拿我當傻子呢,準得找著我欺侮!"柳原聽了這話,倒有點黯然,他舉起了空杯,試著喝了一口,又放下了,嘆道:"是的,都怪我。我裝慣了假,也是因為人人都對我裝假。只有對你,我說過句把真話,你聽不出來。"流 蘇道:"我又不是你肚裡的蛔蟲。"柳原道:"是的,都怪我。可是我的確為你費了不少的心機。在上海第一次遇見你,我想著,離開了你家裡那些人,你也許會自然一點。好容易盼著你到了香港……現在,我又想把你帶到馬來亞,到原始人的森林裡去……"他笑他自己,聲音又啞又澀,不等笑完他就喊僕歐拿賬單來。他們付了賬出來,他已經恢復原狀,又開始他的上等的情調──頂文雅的一種。
“把你帶到馬來亞,到原始人的森林裡去”,他知道流蘇不過是為了經濟上的安全才接近他,他認為“婚姻就是長期的賣淫”,但是他還是愛她,他仍然懂得愛,但虛無的人生觀使他不敢承擔愛的責任,他只能用調情去掩飾愛,他想和流蘇一起到原始森林,逃避現實世界的虛偽,尋找理想中的真和愛,擺脫虛無和絕望,找到精神依歸,但浪子如他也只小心翼翼的扯開面具一角,吐露一點真心,然後又迅速的躲避到安全的調情里。
羅曼羅蘭說:“人生只有一種英雄主義,那就是看透生活的本質之後依舊熱愛生活。”若看清生活的真相讓人失去認真生活的興致,從此信奉“誰先愛誰就輸了”“誰認真誰就輸了”,對生活不願拿出熱情,對感情不敢拿出真心,那也不過是些與生活交手後慘敗的loser而已吧,聰明而絕望的loser。

若不是香港在戰爭中的傾覆,讓這對精明的男女在末日中放棄精明拿出真心抓住彼此,是不是這個故事也會像都市角角落落里上演的沒寫出來的故事一樣,一男一女,彼此防備,婉轉周鏇,駕輕就熟,卻始終都走不到對方的內心,累了,倦了,便散了?
然而“人類的真心只有在末日的時候才會到來”又是張愛玲的做出的一個何等悲涼的隱喻!
周璇 張愛玲 傾城之戀 小說 范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