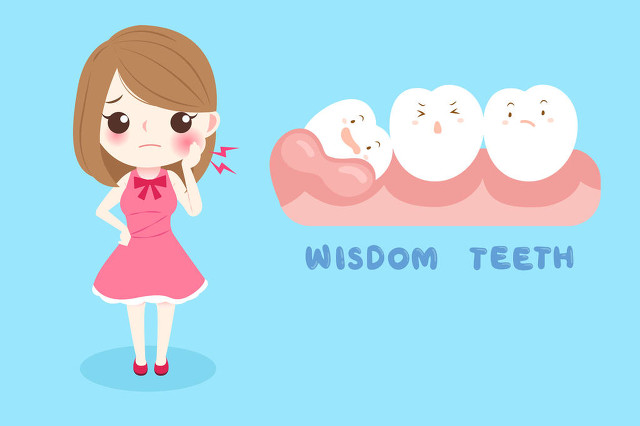白朗面無表情地俯視著下面來來往往的人,人們卻帶著各種表情仰視著他。1914年8月那個炎熱的夏日裡,人們終於可以仔細審視這位縱橫中原長達三載,被政府稱為“白狼”的人物的真面目。
不過人們看到的,只有他高高懸掛在開封南熏門城樓上的人頭——白朗的其它部分,正在距離開封數百里外一個叫張莊西谷地的小村子的石頭垛子裡慢慢腐爛,這也是他最終斃命的地方。
 白朗
白朗在過去的三年里,白朗人頭的上個可能是除卻革命黨魁孫文以外最高的(比孫文的賞格高一萬元,相當於黃興與陳其美腦袋價錢的總和),他也是最讓官方頭疼的問題。與孫文和他理想主義的革命黨發動的那場徒具形式的“二次革命”相比,白朗和他真槍實彈的造反隊伍才是真正的肘腋之患。
他們時而攻城略地,與官兵接仗;時而嘯聚山林,在荒山野嶺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他不斷地被傳出被擊斃的訊息,又不斷復活,帶著更強大的隊伍去攻擊更多的城鎮,從他的老家河南,到湖北、安徽,再到陝西、甘肅, 他的身影無處不在,甚至在遙遠的奉天,都出了一個自稱“小白狼”的盜匪。
白朗的聲名,無論是美名還是惡名,都傳遍大江南北,從1913年開始的每天報紙上幾乎都能讀到白朗起事的訊息,在華北廣大貧苦的鄉村里,白朗開倉放糧、劫富濟貧的傳奇被編排成戲曲說書廣為流傳;而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在上海的里弄里,被孩子的哭鬧弄得厭煩不已的家長,只要喊一聲:“白狼來了!”就足以讓一切清靜安寧。
但這樣一個背負著傳奇和詛咒的人物,他的真面目究竟是什麼樣的?
白朗到底是誰?
直到白朗死後,他的出身仍然迷霧重重,一位筆名“閒雲”的作家,在他死後不久刊登的一篇《狼禍始末記》里,提供了市井坊間有關白朗出身的不同的說法:“或謂白狼姓李;或謂白狼姓馮;或謂白狼姓白名朗齋,河南汝陽人;或謂白狼姓白名永丞;或謂白狼回人也;或謂為河南陸軍國小出身;或謂為故六鎮吳祿貞部下之參謀;或謂前曾居鄭州為小官,後遷至開封,未幾落職;或謂白狼曾為號頭,鏇從謝總戎寶勝為戈什”。
“白狼近四十歲,面上有幾顆麻子,小的確是認得清楚。”
朱勤明是個小嘍囉,當1914年7月他在葉縣被官軍抓獲時,追隨白朗有半年之久。朱供認,在甘肅“回民的女人用木桿把白狼的下牙齒打落了一個,下嘴唇偏左有一小豁”——這個特徵成為後來官軍查驗白朗人頭的重要證據。
朱勤明加入白朗軍隊的原因非常簡單,在安徽茶山做買賣做黃了。所以當1914年2月,白朗的隊伍抵達這裡後,朱便“投入白狼隊內”,正式成了一名“匪伙”。
更多的人也許是因為天災人禍被迫投身綠林,1911河南地區的雹災、1912到1913年間的蔓延華北四省的亢旱,都將成千上萬的農民趕進深山,落草為寇。
至於白朗本人,上世紀50年代進行的社會調查證實,他只是河南寶豐縣大劉村的一名小地主,真名叫李明心,讀過一年多的私塾,家裡有二百畝地,還有一個姐姐。一個被採訪的鄰居說白朗“猛一聽是個‘蹚將’,也不知該有多厲害了。其實,你要是見見他的面,就會覺得他說話跟‘面蛋兒’一樣,面麵筋筋的。”
這樣一個人如何被逼上造反之路?典型的說法是他被當地王姓大戶毆打陷害,關進大牢,又在牢里被獄卒勒索刁難,官府沒收了他家一百畝田,在地主、污吏和貪官的三重壓迫下,白朗“起了反抗之心”。這說法,是經典的梁山好漢故事,對50年代的社會調查者來說,這更讓白朗具備了“革命抗爭精神”。
但另一個說法可能更符合現實:1911年,革命使社會陡然失序,白朗認識的很多人恰好隨波逐流當了土匪,人們紛紛勸他“蹚”起來。但當時已經39歲的白朗表示不願落草為寇,於是這群人便威脅他,將來 “蹚”了以後“做的事情,就叫你的牌子”。同時,一個名叫牛天祥的綠林首領送給他一門“笨炮”,這是一個典型的土匪信物,於是白朗便順理成章成了“蹚將”。
剛開始,白朗只是河南匪窟中的一個小角色,到1912年年底,他的手下也只有27人。而後來成為他手下的朱勤明,此時不過是永城縣的一個小商販。
將白朗從困窘中解脫出來,也將朱勤明逼上梁山的原因可能是同一個:1913年的二次革命。裁軍運動中被迫放下槍桿子的士兵,以及二次革命的失敗製造出的大批散兵游勇,極大豐富了白朗部的兵源。
1914年1月,白朗連下商城、六安,一路招兵買馬,人數達到8000之眾,“癬疥之疾竟成心腹之患”。
但對朱勤明這樣的小人物來說,二次革命卻是徹頭徹尾的災難,中央為敉平二次革命,增加的厘金捐稅遍布全國,高額厘金足以讓一個小販破產,也足以把一個生計無著的人推進土匪隊伍。
1913-1914年白朗起義軍縱橫河南、陝西等省。圖為木版年畫《白狼過秦川》。
 白狼過秦川
白狼過秦川綠林大盜,還是革命志士?
“人民逃避者槍斃,攜什物者槍斃,衣軍服者槍斃,衣皮裘者槍斃。”
在呂咎予的眼中,土匪就是一群殺人越貨的惡棍,這名安徽六安的小鄉紳將自己與白朗的親密接觸比作“危履虎尾”,在他的自述《白狼擾蓼記》中,從1914年1月25日到29日的短短四天裡,子彈和砍刀無時不刻不在他的頭頂搖晃,死亡無處不在。穿著皮衣只是他死罪的一個原因而已,家中藏有銀錢自然是槍斃的罪過,禿頭無辮也是必死的罪行(“戳死你個老禿頭!”),甚至有時只是看你不順眼,問一句“你是嘎人?!”便有血光之災,即使躲在家中,也有可能被闖入的盜匪“強掖余出,雲去見老白狼”。
呂咎予筆下的白朗和他的同夥以殺人搶劫為樂,同樣的記述也出現在其他時人的記述中:商城一名叫熊賓的地方士紳的侄子、鄰居都“當門開槍”而死,熊本人也只是因為躲在床後才勉強逃生,但卻眼睜睜地看著匪徒將一名躲在床下戰慄不已的幼女劫去;甘肅伏羌模範學校的校長王士靄在《白匪陷害隴南見聞錄》中稱哪怕是恭送匪徒出門都有可能“發炮斃之”。
但一些細節卻表明白朗的隊伍並非像上述目擊者的證詞那樣,只是一名殺人越貨的土匪,呂咎予也提到白朗本人出巡時,高執“扶漢軍白”和“總司令李”這樣的旗幟。
王士靄看到土匪也聲稱自己所以造反是因為“袁世凱辦事不公,我們意欲反對”,並且很願意接受“文明人”的稱呼。在白朗四處張貼的布告中,充滿了建立完美文明政府的號召。
從1913年3月開始,白朗就自稱為“中華民國扶漢討袁司令大都督”,在1914年4月張貼在西安附近的布告中,他回顧中國“於異族專制幾三百年,水深火熱,控告無所”,後來的革命雖然使“君權推倒,民權伸張,神明華胄,自是可以自由於法律範圍,而不為專制淫威所荼毒”,但卻被“袁賊世凱”的“帝制自為”的狼子野心所斷送。他號召“熱心愛國”人士奮起反抗——這是一紙革命檄文。
白朗的革命志士神話自然是杜撰,但革命黨一直以來希望拉攏白朗卻確有其事,在黃興致白朗的信中,黃奉承白朗“足下之豐功偉烈可以不朽於後世”,黃興邀請白朗趁袁世凱大軍南下之際,乘虛占領鄂豫兩省,挽回大局。
這封信白朗從未收到過,二次革命也很快灰飛煙滅。但根據白朗的貼身護軍劉紹武回憶,白朗身邊確實有一名叫“沈參謀”的革命黨人,這位沈參謀據說是“孫文從南邊派來的”,“穿一身黑制服,剃的光頭,戴著軍帽,留著八字鬍,年約四十歲,人很好,很和氣,不愛發脾氣”。白朗發布的革命布告,也正是出自這位沈參謀的手筆。
 歷史圖片
歷史圖片劉紹武不識字,所以根本不知道沈參謀筆下氣勢磅礴的革命布告“寫的是啥”,“也許是叫大家遵守紀律,公買公賣”。至於革命理念,沈參謀也只是告訴這些土匪“這不是蹚將,是革命”,但“沈參謀平常也沒有講過為什麼革命,怎樣革命,只是說:要革命,到南邊找孫文,把隊伍一編,發些機槍大炮,再往北打”。這就是白朗和他的手下對革命的理解。
白朗終歸沒當成李自成。
白朗在中原縱橫捭闔,來去如風的流竄戰略,怎么看都和歷史上那著名的大流寇李自成相似,只是白朗終歸沒當成闖王。
1914年4月,白朗在他的革命黨軍師沈參謀的建議下開始了西北遠征,這一計畫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對,他們在背地裡罵:“讓咱們東跑西跑,都是那個長球毛的(沈參謀)出的孬點子!”
這確實是個“孬點子”,如果白朗的隊伍一直在河南安徽一帶屯踞發展,那么以他的實力,很有可能會成為一方割據勢力,這裡有他所熟悉的環境和社會關係網路,但一旦離開河南,白朗的隊伍就成了孤軍奮戰,儘管一路上吸收了不少的流民和災民,但這些人卻遠沒有他的河南弟兄可靠。
5月23日的甘肅洮河一戰成了白朗命運的轉折點,正是在這場戰鬥中,白朗被“回民的女人用木桿打落牙齒一個”。這場戰鬥也讓白朗第一次見識了回民抵抗者的頑強,力戰不支的回民將男女老幼千餘人關進清真寺里,縱火自焚而死。白朗軍傷亡上千人,還留下了殘忍虐殺的惡名。之後白朗軍每到一處,當地居民皆聞風而逃,“匪不得食,殺馬匹充飢”。
白朗開始了第二次逃亡,帶著他的殘兵游勇返回河南,此時袁世凱已然平定了革命黨的餘燼,開始專心對付白朗。一路上,白朗遭到官軍步步追擊,部下四散奔逃。7月23日,白朗在河南虎狼爬嶺的三山寨被官軍包圍,身邊只剩百餘人,白朗遣走了不是他同鄉的人,其中包括年初投向他的朱勤明,只留下數名親信進行最後的抵抗。
白朗最後的結局不那么具有革命悲劇史詩的氣質,也許是在8月3日或8月4日的某一天夜裡,他被一支巡邏隊擊傷,不久便咽了氣。他的護軍將屍體用洋紅的毯子裹起來,埋進張莊西谷地的小村子的石頭垛子裡。在此之前,朱勤明已被官軍抓獲,而那名革命黨軍師沈參謀則在退敗途中不知所蹤,一些人相信他已經逃回南方。一段傳奇就這樣結束了。
 歷史圖片
歷史圖片白朗的頭顱懸掛在河南開封的城門上,俯視著下面來來往往的人群——他的真面目永遠定格在這個時刻,但奇怪的是,這名20世紀國中國最著名的匪首,卻沒有任何一張照片留存下來,後人只能以隻言片語來描繪符合他們期望的形象。
不過,對那些相信個人之力足以改變整個國家的人來說,白朗還有另外一個真面目:他是不死的白狼,而他的對手袁世凱則是一隻老鱉。1914年8月城頭上掛的並不是白朗的人頭,真正的白朗已經變成一隻大白狼,“向天上飛去,眨眼功夫就鑽到雲彩里了。”
革命 農民 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