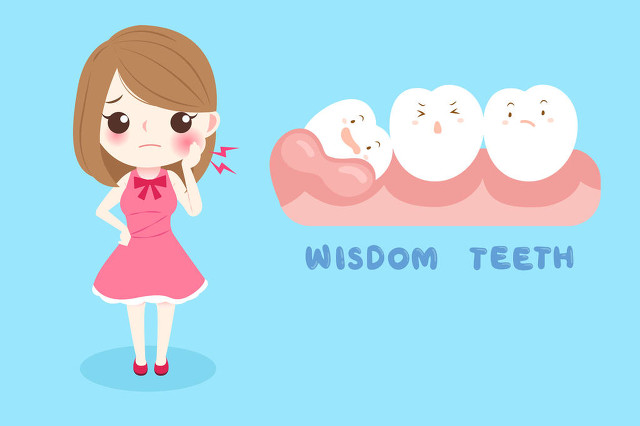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楚2016年11月25日晚發表全國電視講話時宣布,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楚逝世,享年90歲。
 卡斯楚
卡斯楚雖然人們對他的教育看法不一,但大部份資料都證明,卡斯楚是一個天資聰穎的學生,對體育比對學術有興趣,也花了許多年頭在私人的天主教寄宿學校裡,並在1945年於哈瓦那唸完耶穌會的學校。同年,他進入哈瓦那大學法律學院學習。自大學畢業後,他曾經考慮是否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法律,但對國家民族的熱愛驅使他回到故鄉的哈瓦那大學唸法律博士,並於哈瓦那的一間律師事務所供職。1950年畢業於哈瓦那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
進攻蒙達卡兵營
 卡斯楚
卡斯楚1953年7月26日,卡斯楚領導發動反對巴蒂斯塔獨裁政權的武裝起義,攻打蒙卡達兵營,失敗後被捕。1953年10月,在古巴蒙卡達附近一所醫院裡的審判法庭上,時年26歲的卡斯楚以律師身份擔任自己的辯護律師,發表了著名的自我辯護詞:《歷史將宣判我無罪》,(這一審判被記者瑪爾塔·羅哈斯(《蒙卡達審判》一書的作者)記錄了下來。
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諸位法官先生:
從來沒有過任何一個辯護律師得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進行工作;也從來沒有過任何一個被告遭到過這么多的嚴重的非法待遇。在本案中,辯護律師和被告是同一個人。我作為辯護律師,連看一下起訴書也沒有可能;作為被告,我被關閉在完全與外界隔絕的單人牢房已經有76天,這是違反一切人道的和法律的規定的。
講話人絕對厭惡幼稚的自負,沒有心情,而且生性也不善於誇誇其談和作什麼聳人聽聞的事情。我不得不在這個法庭上自己擔任自己的辯護人,是由於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實際上完全剝奪了我的受辯護權;第二,是因為只有感受至深的人,眼見祖國受到那樣深重的災難,正義遭到那樣踐踏的人,才能在這樣的場合嘔心瀝血地講出凝結著真理的話來。
並非沒有慷慨的朋友願意為我辯護。哈瓦那律師公會為我指定了一位有才幹有勇氣的律師:豪爾赫.帕格列里博士,他是本城律師公會的主席。但是他卻不能運行他的使命。他每次想來探望我,都被拒於監獄門外。只是經過一個半月之後,由於法庭的干預,才允許他當著軍事情報局的一個軍曹的面會見我十分鐘。按常理說,一個律師是應該和他的當事人單獨會話的,這是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受到尊重的權利,只有這裡是例外,在這裡一個當了戰俘的古巴人落到了鐵石心腸的*當局手中,他們是不講什麼法律人情的。帕格列里博士和我都不能容忍對於我們準備在出庭時用的辯護策略進行這種卑污的刺探。難道他們想預先知道我們用什麼方法揭露他們所揭力掩蓋的可怕真相嗎?於是,當時我們就決定由我運用我的律師資格,自作辯護。
軍事情報局的軍曹聽到了這個決定,報告了他的上級,這引起了異常的恐懼,就好象是哪個調皮搗蛋的妖怪捉弄他們,使他們感到他們的一切計畫都要破產了。諸位法官先生,他們為了把被告自我辯護這樣一個在古巴有著悠久常規的神聖權利也給我剝奪掉,而施加了多少壓力,你們是最清楚不過了。法庭不能向這種企圖讓步,因為這等於陷被告於毫無保障的境地。被告現在行使這項權利,該說的就說,絕不因任何理由而有所保留。我認為道德有必要說明對我被告野蠻的隔離的理由是什麼,不讓我講話的意圖是什麼;為什麼,如法庭所知,要陰謀殺害我;有哪些嚴重的事件他們不想讓人民知道;在本案中發生的一切奇奇怪怪的事情其奧妙何在。這就是我準備清楚地表白的一切。
諸位法官先生,這裡所發生的現象是非常罕見的:一個政府害怕將一個被告帶到法庭上來;一個恐怖和血腥的政權懼怕一個無力自衛、手無寸鐵、遭到隔離和誣衊的人的道義信念。這樣,在剝奪了我的一切之後,又剝奪了我作為一名主要被告出庭的權利。請注意,所有這些都發生在停止一切保證、嚴格地運行公共秩序法以及對廣播、報刊進行檢查的時候。現政權該是犯下了何等駭人的罪行,才會這樣懼怕一個被告的聲音啊!
我應該強調指出那些軍事首腦們一向對你們所持的傲慢不遜的態度。法庭一再下令停止施加於我的非人的隔離,一再下令尊重我的最起碼的權利,一再要求將我交付審判,然而無人遵從,所有這些命令一個一個地都遭到抗拒。更惡劣的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開庭時,就在法庭上,在我身旁布下了一道衛隊防線,阻止我同任何人講話——哪怕是在短短的休息的時候,這表明他們不僅在監獄裡,而且即使是在法庭上,在你們各位面前,也絲毫不理會你們的規定。當時,我原打算在下次出庭時把它作為一個法院的起碼的榮譽問題提出來,但是,……我再也沒有機會出庭了。他們作出了那些傲慢不遜的事之後,終於把我們帶到這兒來,為的是要你們以法律的名義——而恰恰是他們,也僅僅是他們從3月10日以來一直在踐踏法律——把我們送進監獄,他們要強加給你們的角色實在是極其可悲的。”願武器順從袍服”這句拉丁諺語在這裡一次也沒有實現過。我要求你們多多注意這種情況。
但是,所有這些手段到頭來都是完全徒勞的,因為我的勇敢的夥伴們以空前的愛國精神,出色地履行了他們的職責。
不錯,我們是為古巴的自由而戰鬥,我們決不為此而反悔。”當他們挨個被傳去訊問的時候,大家都這樣說,並且跟著就以令人感動的勇氣向法庭揭露在我們的弟兄們的身上犯下的可怕的罪行。雖然我不在場,但是由於博尼亞托監獄的難友們的幫助,我能夠足不出牢房而了解審判的全部詳情,難友們不顧任何嚴厲懲罰的威脅,運用各種機智的方法將剪報和各種情報傳到我的手中。他們就這樣地報復監獄長塔沃亞達和副監獄官羅薩瓦爾的胡作非為,這兩個人讓他們一天到晚地勞動,修建私人別墅,貪污他們的生活費,讓他們挨餓。
隨著審判的進展,雙方扮演的角色顛倒了過來;原告結果成了被告,而被告卻變成了原告。在那裡受審的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位叫作巴蒂斯塔的先生……殺人魔王!……如果明天這個獨裁者和他的兇殘的走狗們會遭到人民的判決的話,那末這些勇敢而高尚的青年人現在受到判決又算得了什麼呢。他們被送往皮諾斯島,在那裡的環形牢房裡,卡斯特爾斯幽靈還在徘徊,無數受害者的呼聲還縈繞在人們耳中。他們被帶到那裡,離鄉背井,被放逐到祖國之外,隔絕在社會之外,在苦獄中磨滅他們對自由的熱愛。難道你們不認為,正像我所說的,這樣的情況對本律師履行他的使命來說是不愉快的和困難的嗎?
經過這些卑污和非法的陰謀以後,根據發號施令者的意志,也由於審判者的軟弱,我被押送到了市立醫院這個小房間裡,在這裡悄悄地對我進行審判,讓別人聽不到我的講話,壓住我的聲音,使任何人都無法知道我將要說的話。那末,莊嚴的司法大廈又作什麼用呢?毫無疑問,法官先生們在那裡要感到舒適得多。我提醒你們注意一點:在這樣一個由帶著鋒利的刺刀的哨兵包圍著的醫院裡設立法庭是不合適的,因為人民可能認為我們的司法制度病了……被監禁了……
我請你們回憶一下,你們的訴訟法規定,審判應當“公開進行,允許旁聽”;然而這次開庭卻絕對不許人民出庭旁聽。只有兩名律師和六名記者獲準出庭,而新聞檢查卻不許記者在報紙上發表片言隻語。我看到,在這個房間裡和走廊上,我所僅有的聽眾是百來名士兵和軍官。這樣親切地認真關懷我,太叫我感謝了!但願整個軍隊都到我面前來!我知道,總有那么一天,他們會急切地希望洗淨一小撮沒有靈魂的人為實現自己的野心而在他們的軍服上濺上的恥辱和血的可怕的污點。到那一天,那些今天逍遙自在地騎在高尚的士兵背上的人們可夠瞧的了!……當然這是假定人民沒有早就把他們打倒的話。
我應該說,我在獄中不能拿到任何論述刑法的著作。我手頭只有一部薄薄的法典,這是一位律師——為我的同志們辯護的英勇的包迪利奧.卡斯特利亞諾斯博士剛剛借給我的。同樣,他們也根本上馬蒂的著作到我手中;看來,監獄的檢查當局也許認為這些著作太富於顛覆性了吧。也許是因為我說過馬蒂是7月26日事件的主謀的緣故吧。
此外還根本上我攜帶有關任何其他問題的參考書出庭。這一點也沒關係!導師的學說我銘刻在心,一切曾保衛各國人民自由的人們的崇高理想,全都保留在我的腦海中。
我對法庭只有一個要求:為了補償被告在得不到任何法律保護的情況下所遭受的這么多無法無天的虐待,我希望法庭應允我這一要求,即尊重我完全自由地表達我的意見的權利。不這樣的話,就連一點純粹表面的公正也沒有了,那么這次審判的最後這一段將是空前的恥辱和卑怯。
我承認,我感到有點失望。我原來以為,檢察官先生會提出一個嚴重的控告,會充分說明,根據什麼論點和什麼理由來以法律和正義的名義(什麼法律,什麼正義?!)應該判處我26年徒刑。然而沒有這樣。他僅僅是宣讀了社會保全法第148條,根據這條以及加重處分的規定,要求判處我26年徒刑。我認為,要求把一個人送到不見天日的地方關上四分之一世紀以上的時間,只花兩分鐘提出要求和陳述理由,那是太少了。也許檢察官先生對法庭感到不滿意吧?因為,據我看到,他在本案上三言兩語了事的態度,同法官先生們頗有點兒衿持地宣布這是一場重要審訊的莊嚴口吻對照起來,簡直是開玩笑。因為,我曾經看到過,檢察官先生在一件小小的販毒案上作十倍長的滔滔發言,而只不過要求判某個公民六個月徒刑。檢察官先生沒有就他的主張講一句話。我是公道的,……我明白,一個檢察官既然曾經宣誓忠誠於共和國憲法,要他到這裡來代表一個不合憲法的、雖有法規為依據但是沒有任何法律和道義基礎的事實上的政府,要求把一個古巴青年,一個像他一樣的律師,一個……也許像他一樣正直的人判處26年徒刑,那是很為難的。然而檢察官先生是一位有才能的人,我曾看到許多才能比他差得遠的人寫下長篇累牘的東西,為這種局面辯護。那末,怎能認為他是缺乏為此辯護的理由,怎能認為——不論任何正直的人對此是感到如何厭惡——他哪怕是談一刻鐘也不成呢?毫無疑問,這一切隱藏著幕後的大陰謀。
諸位法官先生,為什麼他們這么想讓我沉默呢?為什麼甚至中止任何申述,不讓我可以有一個駁斥的目標呢?難道完全缺乏任何法律、道義和政治的根據,竟不能就這個問題提出一個嚴肅的論點嗎?難道是這樣害怕真理嗎?難道是希望我也只講兩分鐘,而不涉及那些自7月26日以來就使某些人夜不成眠的問題嗎?檢察官的起訴只限於念一念社會保全法的一條五行字的條文,難道他們以為,我也只糾纏在這一點上,像一個奴隸圍著一扇石磨那樣,只圍繞著這幾行字打轉嗎?但是,我絕不接受這種約束,因為在這次審判中,所爭論的不僅僅是某一個人的自由的問題,而是討論根本的原則問題,是人的自由權利遭到審訊的問題,討論我們作為文明的民主國家存在的基礎本身的問題。我不希望,當這次審判退出時,我會因為不曾維護原則、不曾說出真理、不曾譴責罪行而感到內疚。
檢察官先生這篇拙劣的大作不值得花一分鐘來反駁。我現在只限於在法律上對它作一番小小的批駁,因為我打算先把戰場上七零八碎的東西掃除乾淨,以便隨後對一切諾言、虛偽、偽善、因循苟且和道德上的極端卑怯大加討伐,這一切就是3月10日以來、甚至在3月10日以前就已開始的在古巴稱為司法的粗製濫造的滑稽劇的基礎。
我認為我已充分地論證了我的觀點,我的理由要比檢察官先生用來要求判我26年徒刑的理由要多。所有這些理由都有助於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鬥爭的人們,沒有一個理由是有利於無情地壓迫、踐踏和掠奪人民的人。因此我不得不講出許多理由,而他一個也講不出。巴蒂斯塔是違反人民的意志、用叛變和暴力破壞了共和國的法律而上台的。怎樣能使他的當權合法化呢?怎樣能把一個壓迫人民的和沾滿血跡和恥辱的政權叫作合法的呢?怎樣能把一個充斥著社會上最守舊的人、最落後的思想和最落後的官僚制度的政府叫作革命的呢?又怎樣能認為,肩負著保衛我國憲法的使命的法院最大的不忠誠的行為,在法律上是有效的呢?憑什麼權利把為了祖國的榮譽而貢獻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的公民送進監獄呢?這在全國人民看來,是駭人聽聞的事;照真正的正義原則說來,都是駭人聽聞的事。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理由比其他一切理由比其他一切理由都更為有力:我們是古巴人,作為古巴人就有一個義務,不履行這個義務就是犯罪,就是背叛。我們為祖國的歷史而驕傲;我們在國小校里就學習了祖國歷史,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不斷聽人們談論著自由、正義和權利,我們的長輩教導我們從小敬仰我們的英雄和烈士的光榮榜樣。塞斯佩德斯、阿格拉蒙特、馬塞奧、戈麥斯和馬蒂都是我們自幼就熟悉的名字。我們敬聆過泰坦的話:自由不能祈求,只能靠利劍來爭取。我們知道,我們的先驅者為了教育自由祖國的公民,在他的《黃金書》中說:”凡是甘心服從不正確的法律並允許什麼人踐踏他的祖國的,凡是這樣辜負祖國的,都不是正直的人……在世界上必然有一定數量的榮譽,正像必然有一定數量的光明一樣。只要有小人,就一定有另外一些肩負眾人的榮譽的君子。就是這些人奮起用暴力反對那些奪取人民的自由,也就是奪取人們的榮譽的人。這些人代表成千上萬的人,代表全民族,代表人類的尊嚴。”……人們教導我們,10月10日和2月24日是光榮的、舉國歡騰的日子,因為這是古巴人奮起打碎臭名昭著的暴政的桎梏的日子;人們教導我們熱愛和保護美麗的獨星旗並且每天晚上唱國歌,這個曲子告訴我們,生活在枷鎖下等於在羞辱中生活,為祖國而死就是永生。我們學會了這一切並且永不會忘記,儘管今天,在我們祖國的人們,由於要實踐從搖籃中起就教導給他們的思想而遭到殺戮和監禁。我們出生在我們的先輩傳給我們的自由國家。我們不會同意作任何人的奴隸,除非我們的國土沉入海底。在我們的先驅者百年誕辰的今年對他的崇敬好象要消逝了,對他的懷念好象要永遠磨滅了,多么可恥!但是他還活著,沒有死去,他的人民是富於反抗精神的,他的人民是高尚的,他的人民忠於對他的懷念!有些古巴人為保衛他的主張倒下去了,有些青年為了讓他繼續活在祖國的心中,甘心情願地死在他的墓旁,貢獻出他們的鮮血和生命。古巴啊!假使你背叛了你的先驅者,你會落得什麼樣的下場啊!
我要退出我的辯護詞了,但是我不像通用律師通常所作的那樣,要求給被告以自由。當我的同伴們已經在松樹島遭受可惡的監禁時,我不能要求自由。你們讓我去和他們一起共命運吧!在一個罪犯和強盜當總統的共和國里,正直的人們被殺害和坐牢是可以理解的。
我衷心感謝諸位法官先生允許我自由講話而不曾卑鄙地打斷我,我對你們不懷仇怨,我承認在某些方面你們是人道的,我也知道本法庭庭長這個一生清白的人,他可能迫於現狀不能不作出不公正的判決,但他對這種現狀的厭惡是不能掩飾的。法庭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有待處理,這就是謀害70個人的案件——我們所知道的最大的屠殺案。兇手到現在還手執武器逍遙法外,這是對公民們的生命的經常威脅。如果由於怯懦,由於受到阻礙而不對他們施以法律制裁,同時法官們也不全體辭職,我為你們的榮譽感到惋惜,也為玷污司法制度的空前的污點感到痛心。
至於我自己,我知道我在獄中將同任何人一樣備受折磨,獄中的生活充滿著卑怯的威脅和殘暴的拷打,但是我不怕,就像我不怕奪去了我70個兄弟的生命的可鄙的暴君的狂怒一樣。
判決我吧!沒有關係。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古巴 德爾·卡斯楚 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