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結構主義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最常使用來分析語言、文化與社會的研究方法之一。不過,“結構主義”並不是一個被清楚界定的“流派”,雖然通常大家會將索緒爾的作品當作一個起點。結構主義最好被看作是一種具有許多不同變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就如同任何一種文化運動一樣,結構主義的影響與發展是很複雜的。廣泛來說,結構主義企圖探索一個文化意義是透過什麼樣的相互關係(也就是結構)被表達出來。根據結構理論,一個文化意義的產生與再創造是透過作為表意系統(systemsofsignification)的各種實踐、現象與活動。一個結構主義者研究對象的差異會大到如食物的準備與上餐禮儀、宗教儀式、遊戲、文學與非文學類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娛樂,來找出一個文化中意義是如何被製造與再製造的深層結構。比如說,人類學與民族志學家列維-史特勞斯(ClaudeLevi-Strauss)這位早期著名的結構主義實踐者,就分析了包括神話學、宗族以及食物準備這些文化現象。
概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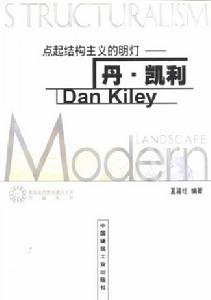 結構主義書籍
結構主義書籍結構主義的出現,幫助人們從生活中混亂的表象中,揭露隱藏其中的完整結構,但亦因此一簡約化的結果,造成結構主義把“文本”作了過多的解讀,
而讓學者創造出許多並不存在的意義與結構。另外還有各種立場是位於這兩個極端立場之間;而事實上,許多關於結構主義的爭論就是在試圖釐清上面所說的這個問題。
對於一般人而言,結構主義似乎是離很遠的東西。即使是一些專業的文學工作者,如果不太接觸西方理論,也很可能會不以為然地說:“結構主義是什麼東西?有什麼了不起?”事實上,結構主義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早已滲透進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思想方法上的一場廣義的革命。結構主義誕生之後,它像一把利劍一樣改變著人們看問題和思考問題的方式,並無孔不入地滲透到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個角落:作為文化思潮,它涉及社會科學的各個部門,如語言學、人類學、心理學等;作為文藝思潮,結構主義幾乎影響到文學藝術的所有領域,從理論到創作,從小說、戲劇、詩歌到電影。這一思潮還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國際影響,從60年代中期開始,它以法國為中心,迅速擴展到英、美、西德、義大利、丹麥,並對蘇聯、東德、波蘭、捷克等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產生了影響。它是戰後繼英美新批評派和法國現象學派而成為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界的第三大思潮。有人認為,從60年代以後,“結構主義的人”取代了“存在主義的人”。
那么,是誰製造了結構主義這么一把無堅不摧的利劍呢?
形成
 路德維希·維根斯坦
路德維希·維根斯坦出生於瑞士的斐迪南·德·索緒爾是將結構主義思想運用到語言學研究的始作俑者,他在長期的語言學研究中逐漸形成了一系列與19世紀在語言學研究中占統治地位的比較語言學的觀點相對立的新觀點。比較語言學把一些語言事實當作孤立靜止的單位對待,只注意了它們的歷史比較,而忽視了語言要素之間相互制約、相互依賴的關係;忽視了語言是一個系統的整體。索緒爾則把具體的語言行為(“言語”)和人們在學習語言中所掌握的深層體系(“語言”)區別開來,把語言看作是一個符號系統。產生意義的不是符號本身,而是符號的組合關係。語言學是研究符號組合規律的學問。索緒爾使用的詞雖然是“系統”而不是“結構”,但意思是一樣的。他把語言的特點看作是意義和聲音之間的關係網路,純粹的相互關係的結構,並把這種關係作為語言學研究的對象,這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主要理論原則。索緒爾的理論在他死後由他的學生整理出來以《普通語言學》的書名出版,對結構主義思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索緒爾也因此被人們敬稱為“結構主義之父”。
1945年法國人克勞德·列維·史特勞斯發表了《語言學的結構分析與人類學》,第一次將結構主義語言學方面的研究成果運用到人類學上。他把社會文化現象視為一種深層結構體系來表現,把個別的習俗、故事看作是“語言”的元素。他對於原始人的邏輯、圖騰制度和神話所做的研究就是為了建立一種“具體邏輯”。他不靠社會功能來說明個別習俗或故事,而是把它們看作一種“語言”的元素,看作一種概念體系,因為人們正是通過這個體系來組織世界。他隨後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學科對結構主義的高度重視,於是,到了60年代,許多重要學科都與結構主義發生了關係。一個如火如荼的結構主義時代到來了。
結構主義為什麼能在60年代的法國流行起來並如日中天呢?其原因大概如特里·伊格爾頓所說:“結構主義最好被看作既是我概述的社會和語言危機的表現,也是對那種危機的反應。它從歷史逃到語言--這是一種諷刺行為,因為正如巴爾特所看到的,沒有什麼行動在歷史上能更有意義。” 戰後的法國和其他曾經將版圖延伸到國土之外其他土地上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因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法國的學者們已不能自由地出入曾經是他們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實地考察,重實地調查、輕理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不再適合他們,結構主義的出現,正好迎合了他們的需要。這大概也是結構主義的大師們看上去都是“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的大學教授”的原因。另外,戰後法國經濟飛速恢復與發展,以“他人是我的地獄”為宗旨的存在主義哲學同現實格格不入,人們對“個人”、“存在”、“自我意識”等等這些存在主義的概念失去了早先的熱情和興趣,結構主義在這種背景下作為存在主義的否定的思潮而興起。結構主義認為:“我”、主體, 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這樣一個中心,根本不存在。
於是,在存在主義的退潮聲中,以後起之秀身份出現的結構主義思潮緊鑼密鼓地登台亮相了。
方法論
結構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傳統意義上的哲學學說,而是一些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家在各自的專業領域裡共同套用的一種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試圖使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也能像自然科學一樣達到精確化、科學化的水平。
結構主義的方法有兩個基本特徵。
首先是對整體性的強調。結構主義認為,整體對於部分來說是具有邏輯上優先的重要性。因為任何事物都是一個複雜的統一整體,其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的性
 索緒爾
索緒爾結構主義方法的另一個基本特徵是對共時性的強調。強調共時性的研究方法,是索緒爾對語言學研究的一個有意義的貢獻。索緒爾指出:“共時‘現象’和歷時‘現象’毫無共同之處:一個是同時要素間的關係,一個是一個要素在時間上代替另一個要素,是一種事件。” 索緒爾認為,既然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的關係是相互聯繫、同時並存的,因此作為符號系統的語言是共時性的。至於一種語言的歷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個相互作用的系統內部諸成分的序列。於是索緒爾提出一種與共時性的語言系統相適應的共時性研究方法,即對系統內同時存在的各成分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它們同整個系統的關係進行研究的方法。在索緒爾的語言學中,共時性和整體觀和系統性是相一致的,因此共時性的研究方法是整體觀和系統觀的必然延伸。
語言學
 L·布龍菲爾德
L·布龍菲爾德《普遍語言學課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語言學家有很大影響。美國的L·布龍菲爾德(Leonard Bloomfield)發展了自己的結構語言學,正如丹麥的Louis Hjelmslev的那一個學說。在法國,安戴尼·梅勒(Antoine Meillet)和Émile Benveniste延續索緒爾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布拉格語言學派的成員,例如羅曼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及Nikolai Trubetzkoy進行了相關的研究。
二戰後
 薩特
薩特結構主義反對人性自由和選擇的觀點,而是集中關注人類行為是由各種各樣的結構組織所決定的研究。以此觀點為據的早期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李維史陀於1949年版的《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二戰期間,李維史陀在紐約結識了傑科普生,受到了傑科普生的結構主義以及美國人類學傳統理論的影響。在《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一書中,他從結構觀點來考察親屬關係,並試圖證明不同的社會組織實際上就是少數基本親屬結構的相互置換。隨後於1958年出版的《結構人類學》一書,收錄了闡述其結構主義思想綱要的論文。
到六十年代初期,解構主義作為一種運動已經盛行。有人認為它為人類提供了一種統一標準的研究途徑,幾乎可以適用於所有的學科。羅蘭·巴特和雅克·德希達則集中研究如何將結構主義套用於文學。
大師們
索緒爾
結構主義之父---索緒爾:出生於瑞士的語言學家費迪南·德·索緒爾(1857-1913)一生最重要的階段是他在1906年到1911年他去世前的幾年間他在日內瓦大學講授普通語言學的課程,建立起與傳統語言學理論完全不同的語言學體系。在此之前他做的一切似乎都是為了這一事業作鋪墊:他年輕時曾經在日內瓦大學和來比錫大學讀書,並從事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工作,於1878年完成了《論印歐系語音元音的原始系統》的著名論文,引起轟動。此後,他又在柏林大學和來比錫大學繼續深造,1881年到巴黎的高等研究學院教授梵語,併兼任巴黎語言學學會秘書,建立起法蘭西語言學派。他還來不及將他的講稿編寫成書就與世長辭。後來,他的學生們根據他的一部份手稿、材料和同學們的筆記,編輯整理成了《普通語言學教程》,於1916年出版,從此,他的語言學理論便以極大的衝擊力和影響力被擴散到全世界,並滲透到各行各業的研究中。其影響正如美國學者戴維·羅比所說:“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是使語言學改變發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它的強大影響使現代語言學在文學研究中的作用超越了純粹文學語言問題而產生出有關整個文學甚至整個社會文化生活的性質和組織的新理論。”由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引伸出來的一些普遍性的結構原則,在日後成為結構主義思潮的一些重要方法論的基礎,也就是說這些普遍性的語言學原則包含有結構主義的基本思想,這就是索緒爾對結構主義的最主要貢獻。具體表現如下:
其一,索緒爾對語言和言語的劃分引發出結構主義重分析結構的方法。索緒爾認為語言是第一性的,而言語是第二性的。語言是社會性的,是一種抽象記憶的產物,語言優於言語,言語的意義源於語言;語言不是如詞典式的集合,而是一個整體,一個系統,一種規則的軀幹,它是各種因素間關係的系統。而言語是個別性的,是創造的產物,是種受經驗控制的線性形式,是一個特定製造的事件。正是因為索緒爾對語言和言語的劃分,才產生了結構主義的一個無處不在的法則:“結構主義者的最終目標是永恆的結構:個人的行為、感覺和姿態都納入其中,並由此得到它們最終的本質。” 它也表明了結構主義的一個基本思想:語言--即系統--是一種自主的、內在化的、自我滿足的體系,它不與外界的實體的事物發生關係。
其二,索緒爾對能指和所指的區分引發了結構主義對“意義”的追求。與實證主義方法論的要求相比,結構主義者更感興趣的是事實背後的意義,而不是事實本身。這是因索緒爾視語言自身是個符號系統引發而來的。索緒爾認為,聲音和書寫形式僅是傳遞意義的符號,任何符號如沒有意義,它就不是語言。他的對於符號及其構成關係的強調,導致後人建立了“符號學”。在符號學家看來,現實中任何東西如穿戴、人的行動等,都可視為符號,因而都可建立一個有關穿戴、人的行動等的符號系統。索緒爾視語言為一種符號系統也是結構主義的一個基本思想:意義的構成只取決語言的各種關係(句段關係和聯想關係),所謂語言,就是一個個相互依賴的要素(亦即能指/所指)所組成的符號系統。
其三,從索緒爾對共時分析的追求引發出在特定時空中的定性研究法。共時分析是結構主義者最喜歡用的分析方法之一。結構主義的另一個基本思想也包含其中,即語言符號的識別,只能藉助於它與其他語言符號的關係和差異。
事實上,後來的結構主義者正是把索緒爾的各種語言學原則泛化為一切事物的共同性特徵,並且將能指與所指、語言和言語、共時性和歷時性、句段關係和聯想關係等一系列既互相聯繫又互相區別的對立概念上升為一種固定的二項對立的關係,從而形成一種普遍的結構分析原則,並借用語言學的規則、術語去討論一切社會-文化現象。而索緒爾關於語言的符號性質、語言符號系統的內部規律更被用來對文學現象進行分析,用語言學原理對文學的功能系統作出解釋,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起結構主義詩學和敘事學。
列維·史特勞斯
 克勞德·列維·史特勞斯
克勞德·列維·史特勞斯列維·史特勞斯認為,社會是由文化關係構成的,而文化關係則表現為各種文化活動,即人類從事的物質生產與精神思維活動。這一切活動都貫穿著一個基本的因素--信碼(符號),不同的思想型式或心態是這些信碼的不同的排列和組合。他通過親屬關係、原始人的思維型式和神話系統所作的人類研究,試圖找到對全人類(不同民族、不同時代)的心智普遍有效的思維結構及構成原則。他認為處於人類心智活動的深層的那個普遍結構是無意識地發生作用的。其結構主義方法主要有如下原則:
(一)對整體性的要求;
(二)整體優於部分;
(三)內在性原則,即結構具有封閉性,對結構的解釋與歷史的東西無關;
(四)用共時態反對歷時態,即強調共時態的優越性;
(五)結構通過差異而達到可理解性;
(六)結構分析的基本規則:
1.結構分析應是現實的;
2.結構分析應是簡化的;
3.結構分析應是解釋性的; 等等。
列維·史特勞斯把結構主義方法套用於神話學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果也是舉世矚目的。他對神話的考證、確定某一神話的原始真實版本和內容沒有興趣,他所進行的工作是想從神話研究中找到對所有人類心靈普遍有效的邏輯或思維原則,用他的話說,就是全人類的心靈都具有的原始邏輯或“野性思維”。從現代社會的文化中是難以找到這種普遍的野性思維的原則的,因為科學技術的發達和普遍的教育馴化,使現代人的心靈充滿了各種特殊的邏輯或思維方式,那種原始的邏輯或野性思維已被掩蓋或被埋起來了。神話是不受時間影響的“冷”社會的文化,從中將能尋求普遍的原始邏輯或野性思維。
列維·史特勞斯在神話學研究中所提供的語言學方法,實際開了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的先河,他的神話分析也就成為一切敘事作品結構分析的一個摹本,他所提出的著名論點--每一個具體神話的各自單獨的敘述,即神話言語,都是從神話的語言的基本結構中脫胎而出並從屬於這個基本結構的--也就成為結構主義敘事學的一個基本原則,並為結構主義研究方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構造主義
 鐵欽納
鐵欽納構造主義心理學派在心理學發展中的貢獻和局限:
構造派是心理學史上第一個套用實驗方法系統研究心理問題的派別。在他們的示範和倡導下,當時西方心理學實驗研究得到了迅速傳播和發展。
理論基礎為純粹經驗論。
把心理身,研究它的實際存在,不去討論其意義和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