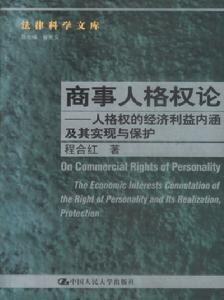問題提出
 商事人格權
商事人格權界定
針對上述諸多問題,如果僅僅按照傳統的人格權理論和中國民法通則等現行法律有關自然人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和法人名稱權、名譽權等人格權的規定來處理,顯然尚有許多法律空白需要填補。例如,現行有關姓名權、肖像權的法律並未規定姓名權和肖像權可以繼承和轉讓;傳統民法理論也一直認為姓名、肖像等人格不是商品,姓名權、肖像權等人格權不能轉讓和繼承;至於商譽和使用的問題,實踐中雖然已廣泛涉及,但有關法律的規定卻嚴重滯後,如法律至今沒有明確承認商譽權和信用權。因此,如果嚴格恪守這一傳統民法理論,拘泥於現行法律制度的話,人格商品化等以人格為對象的商業活動及人格權的商業利用必然會受到限制和阻礙,相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得不到充分保護,這種後果對商品銷售市場及其他相關行業(如廣告行業)的經濟活動也將產生不利影響。因此人格權也必須適應人格商品化等市場經濟活動的需要,如同財產權一樣,可以繼承、轉讓,並在受到侵害時獲得財產損害賠償。正是在這種社會、經濟背景下,人格權的發展呈現出新的特點,並形成了不同於傳統人格權制度與觀念的商事人格權。
財產價值
 商事人格權
商事人格權根據商事人格權財產價值的特點,對其價值進行評估時,應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評估的對象是權利,不是人格本身或肖像、商號等人格標識本身。
2、人格權價值評估的交叉與重複。人格權權勢與一個人的人格密切相聯繫的,不論是肖像、姓名等人格標識,還是商譽、信用以及商業秘密等,都是一個人人格的要素或表現形式。
3、價值評估所要考慮的因素因評估的對象不同而不同。人格權價值評估所要考慮的因素有共同的一面。如都必須考慮市場上有沒有人需要它(肖像、商號等),打算出多少錢來購買它等市場因素。但更為重要的是要考慮與評估對象不同特點相對應的特殊因素。
4、完善人格權價值評估的要件、程式及評估機構等相關法律制度。
轉讓與繼承
普通人格權的專屬權非常強,是不能轉讓、繼承的。但是,商事人格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該原則的限制,允許相應的轉讓和繼承。因為在商事人格利益中,那種非財產性的專屬性極強的人格利益被淡化,而非專屬性的經濟利益內涵則占據主導地位,因此使得人格權的轉讓在一定情況下成為必要與可能。
(一)商事人格權轉讓的必要性
商事人格權的轉讓是人格權商業利用的主要形式,其轉讓的必要性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如果不允許商事人格權的轉讓和繼承,就限制了對商事人格利益所可能實行的充分利用。以商號為例,如果僅限於自己使用,而不允許出資或轉讓於他人,則其財產價值顯然不能得到充分展現。相反,通過轉讓會使其得到商業增值;通過授權使用,在其使用價值得到充分實現的同時,還會創造新的價值。以美國法上公開權為例,一位美國學者就曾指出:“如果(姓名、肖像等人格標識的)公開價值(publicityvalues)不能被有效出現的話,這種公開價值的金錢價值即使不是被全部損毀,也會大大減損。”
(二)商事人格權轉讓的可能性
普通人格權的專屬性太強,以至於難以與主體分離。而商事人格權則由於其保護的商事人格利益從普通的人格利益中脫離出來、並相對獨立,從而為商事人格權的轉讓打下基礎。
(三)商事人格權轉讓的方式與效果
人格權的轉讓在方式上有其特殊性。由於傳統民法只承認商號、商業秘密的轉讓(商譽與商業信用的轉讓則通常是借著商號的轉讓來實現的),其他人格權的轉讓被認為無效。
(四)自然人的商事人格權具有相對的可繼承性
就一般人格權而言,由於其強烈的屬人性,自然人的普通人格權完全與人格本身相始終,自然人死亡,權利終止,不能繼承。但是自然人的商事人格利益是可以流傳給後代由其繼承的。因為姓名(商號)、肖像等自然人的人格標識在事實上會惠及於他的後代,如果不允許他的後代像享有死者生前的其他財產利益那樣享有這一利益,是不公平的。
保護
 商事人格權
商事人格權首先,對商事人格權的保護通常不包括對精神利益的損害賠償,不適用精神痛苦撫慰金的責任方式。法人是一個沒有自然生命屬性的社會組織,是一個“它”,而不是“他”或“她”,無血、無肉、無七情六慾。通常自然人的感情、精神,它是沒有的。所以,不存在對精神損害的賠償問題。至於對“精神”含義的一般社會認識,只會人為地使問題複雜化。具體而言,法人的名譽中不含有精神因素,不可能受到精神損害。對政府等機關法人而言,社會公眾或媒體對其在管理和統治方面的聲譽的詆毀,不構成侵害名譽。因為這是憲法中言論自由的題中應有之義,即使存在虛假,被批評者也不能提起侵害名譽之訴;如果是陰謀推翻政府的話,則應承擔相應的公法上的責任。事業單位法人和企業法人,對有關其專業和經營方面的詆毀,構成的是商譽侵權,不構成一般的名譽侵權,不存在精神損害賠償。自然人的名譽和商譽也應分開,對一個個體經營者的詆毀,有時會同時損害其名譽和商譽兩種人格利益,這是侵權人既要承擔侵害商譽的財產損害責任,又要承擔侵害名譽所造成的精神痛苦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至於對自然人的姓名、肖像中包含經濟利益的人格利益的侵害,通常也認為只適用財產損害賠償的救濟方式。姓名、肖像等人格標識中所包含經濟利益只有在被告擅自以商業目的進行使用的侵害方式下,才會造成損害,這種單純的商業利用一般不會造成原告的精神損害;如果被告的行為中同時包含損害原告名譽、公開隱私的行為因素,會同時造成精神損害,這時可另行適用侵害名譽權或隱私權的救濟方式,進行精神損害賠償。
其次,以財產損害賠償為主要形式。維護商事人格利益的目的在於維護其無形財產利益。法人,尤其是企業法人的人格利益受損,往往意味著其有形或無形的財產損失,自然需要採取財產損害賠償的責任方式。這種損害賠償制度雖然也適用侵權法的基本原則,但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則主要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以及商標法、商業秘密法等特別法,並由此形成了商事人格權損害賠償制度的一些特點。在賠償範圍和數額方面,一是雖然仍使用按實際損失賠償的原則,但這種實際損失已經擴大到間接損失的範圍;因為商事人格利益受到損害不像有形財產受到損害那樣,出現財產物的直接損毀或直接的減值等直接損失,其損失通常是通過這些受損害人格利益的獲利能力的降低而形成的間接損失,如因商譽受損而造成的客戶退貨、解除契約等損失。二是可以適用損失額的推定計算方式。由於商事人格利益的無體性,它的實際損失額許多時候是難以確定的,因此推定計算方式就應運而生。三是可以適用法定賠償金制度,在許多分割商事人格權的案件中,原告的損失和被告的利潤都難以確定。為解決這一難題,司法實踐中探索出了法定賠償金制度:即由法院按照法律規定的固定的賠償數額確定侵權人的責任。其適用前提是已經造成了損害,但具體數額沒有證據證明,而由法律或法院直接選擇賠償金額。這種方式特別適用於商譽、信用、商業秘密、商號以及人格商品化權等商事人格的損害賠償。四是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
再次,普通的人格權保護只限於國內法,而商事人格權的保護已擴展至國際法律規範。
完善
 商事人格權
商事人格權第一,必須承認和維護人格權中的經濟利益因素和人格權的財產權屬性。隨著人格的商品化,人格也表現出了商業上的價值;人格權所保護的不再是僅僅包含精神利益的人格,而人格商品化中所形成的商業價值、經濟利益也需要予以維護,諸如姓名權、肖像權這樣一些傳統民法中認為屬於純粹人格權屬性的權利,它們不但具有人格權屬性,還應包含財產權的屬性。它們所保護的客體既包括做為精神價值的人格利益,也包括做為財產價值的人格利益;名譽權則應當予以分解與重塑,將商譽和信用從中分立出來,名譽權不應再充當包括商譽權與信用權的“口袋型”權利。
第二,人格權商事化除了在靜態上表現為人格權兼具財產權的屬性之外,在動態上就表現為權利的可轉讓性和可繼承性。只有人格可以轉讓和繼承,它們的商業價值才能得以充分展現和利用,才有利於對人格商品化中相應主體(轉讓人、受讓人)經濟利益的保護。
第三,對人格權的保護應包括損害賠償的權利救濟方式。商事化的人格權既包含精神利益型的人格利益,還包含經濟利益型的人格利益,以後者為主。傳統的人格權的保護方式如賠禮道歉、精神損害賠償等,主要是針對精神利益人格利益的;這種保護方式不適用於對經濟利益型人格利益的保護。因此,有必要適用財產損害賠償制度來保護商事化的人格權,只有這樣,才能更為公平、更為全面地保護相應自然人和法人的人格利益,才有利於維護他們人格的全面發展和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