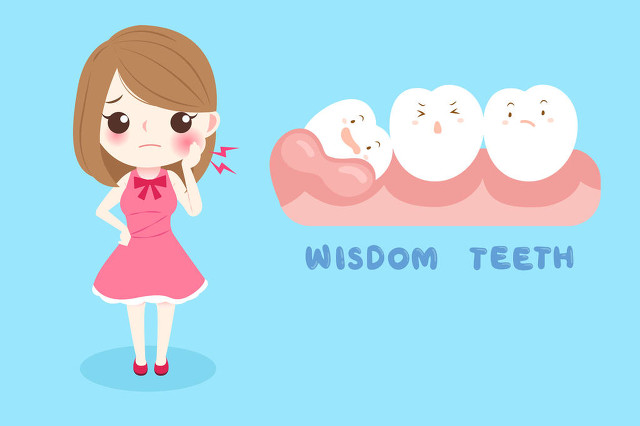美國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就一直致力於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讓這個國家和其上的居民收穫了不少地球當家人的感覺。
 已經習慣了在全世界面前秀肌肉
已經習慣了在全世界面前秀肌肉但對於那些需要在國外進行工作學習、商貿往來的美國公民來說,這可能不是一個好訊息。在那些被美國制裁過的國家,美國公民的行動處處受阻,甚至因為種種原因被外國政府扣押乃至審判。
 連盟友以色列和肯德基也一起遭殃
連盟友以色列和肯德基也一起遭殃他們被逮捕和起訴的原因也千奇百怪,而美國政府也不是每一次都能把這些人解救出來……

伊朗的美國囚徒
說起現代國際社會和美國最對著幹的國家,伊朗毫無疑問是頭牌。為了逼迫伊朗放棄核開發,以及早日完成逆宗教改革,美國可謂不遺餘力,不僅在國際組織和經貿關係上給伊朗施壓,還對伊朗進行了不少滲透和攻訐。這直接導致了伊朗對美國戒心重重,美國公民想要在伊朗開展任何工作都會遭到伊朗政府的嚴格限制。
 心事重重
心事重重媒體工作者顯然是這場鬥爭中最高危的群體,比如華盛頓郵報駐德黑蘭的記者傑森·雷薩安(Jason Rezaian)。
 左邊這位
左邊這位此人自2009年開始就一直在伊朗擔任記者,在各家媒體遊走之後被華盛頓郵報納入麾下。2014年7月22日晚,伊朗特工在家中逮捕了雷薩安夫婦,並且沒收了他們的電子設備和身份證件。隨後他們被送上了革命法庭的被告席接受起訴,伊朗官方對外卻沒有公布其罪名,也不允許這位美國記者聘請律師,也不公開審判過程。
簡單來說,就是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國際社會能得到的訊息只是此人被判有期徒刑。好在隨著歐巴馬政府和伊朗在2015達成了框架協定(現在又被特朗普推翻了),這名記者於2016年安全返回了美國。
 雷薩安和妻子
雷薩安和妻子此外,從事中東婦女解放工作宣傳的伊朗裔美國記者阿萊·艾斯范迪利(Haleh Esfandiari)、在伊朗宣傳親西方開放社會的美國學者可汗·塔吉巴赫什(Kian Tajbakhsh)等人也都有過被扣押的經歷。
 Haleh Esfandiari(仍然在從事相關事務)
Haleh Esfandiari(仍然在從事相關事務)另外一個高危領域是宗教人員。2012年,伊朗裔的美國基督教牧師賽義德·阿貝迪尼(Saeed Abedini)就被伊朗政府逮捕,罪名是“危害國家安全”。而傳教和宗教集會是引發這場危機的主要導火索。

眾所周知,伊朗是一個什葉派伊斯蘭教國家,什葉派伊斯蘭信仰是這個國家的國教,連同屬伊斯蘭教的遜尼派都是受排擠的對象,就更別說基督教這樣的異教了。不過在明面上,伊朗是承認基督教作為一種少數宗教信仰的,並且在一定範圍內允許基督徒的宗教信仰活動,並不會隨意加以迫害。
 雖然我們可以簡單將中東分為什葉派和遜尼派陣營但實際的民族與宗教狀況卻很複雜伊朗也存在很多少數宗教族群
雖然我們可以簡單將中東分為什葉派和遜尼派陣營但實際的民族與宗教狀況卻很複雜伊朗也存在很多少數宗教族群而這位阿貝迪尼原本是伊朗穆斯林,在移民美國後皈依了基督教,並且致力於返回家鄉傳播基督教。在21世紀初伊朗比較親西方的時代,他在伊朗基層做了大量傳播工作,擁有了一支相當有規模的教眾團體,並且經常舉辦家庭宗教集會。
等到了美伊關係緊張時,他的這些行動就引起了伊朗官方的重視,認為他是在通過宗教改宗活動動搖伊朗的國家統治基礎。其實2009年,他就曾經被伊朗政府盯上,並簽署了一份終止家庭教會活動的承諾書才獲釋。而2012年的這一次逮捕,就沒有那么好運了,也是一直被關到2016年才被釋放。
 有的媒體報導阿貝迪尼被伊朗監禁8年
有的媒體報導阿貝迪尼被伊朗監禁8年偶爾也有商人被扣押的。伊朗裔美國商人阿里·沙克里(Ali Shakeri)就曾被伊朗政府短暫扣留。不過他更出名的身份其實是社會活動家,一直致力於在伊朗宣傳世俗化思想,難免被視為眼中釘。

另外還有一些涉嫌竊取科研機密、鼓動庫爾德斯坦獨立的抓捕事件,至於打著違反商業法而扣押美國商人的事,在伊朗沒有出現過。
美國人在朝鮮
伊朗雖然是一個宗教氣息濃郁的國家,連政權的合法性都依託於宗教而實現,但畢竟是一個相對開放的大國,外國人在這個國家的進出是相對自由的。如果我們把目光轉向東北亞強國朝鮮,會發現美國人在這裡過得更不如意。
 一不留神就會這樣
一不留神就會這樣最著名的被扣押者,可能要數奧托·瓦姆比爾(Otto Warmbier)了。
這是一名充滿好奇心的美國大學生,在2016年參團進入了朝鮮進行參觀。作為一個西方人,他們的出現當然會引起朝鮮官方的高度重視,但其實大多數西方遊客都是能全身而退的,瓦姆比爾的悲劇之處在於,他試圖偷走酒店裡的朝鮮宣傳畫。
 在這裡,哭是沒有用的...
在這裡,哭是沒有用的...其實在西方各國,確實有那么一批對朝鮮的主體思想宣傳畫大感興趣的收藏家。在瓦姆比爾之前,就有一名荷蘭的收藏家因為大規模收藏朝鮮宣傳畫而被判間諜罪。因為朝鮮的法律確實規定了污損或盜竊帶有領袖肖像的宣傳畫是違法的。
 奧托同學的不幸遭遇
奧托同學的不幸遭遇但是和那位交了檢查報告並且對朝鮮表示出友好,而得以兩周就獲釋的荷蘭人不一樣,瓦姆比爾的動機在朝鮮官方看來並不單純。當他最終獲釋回到美國時,只活了6天就去世了,而且全程保持著植物人的狀態。掃描顯示,他的大腦嚴重受損,但致病原因很難確定。美朝雙方都為此大打口水仗,最後也沒有吵出個結果來。
 正常的時候確實正常(最左)
正常的時候確實正常(最左)不過瓦姆比爾顯然不是第一個被朝鮮官方扣押的美國人。他的前輩包括因為在廁所里放上聖經而被控“污染人民精神世界”的傑弗里·福爾(Jeffrey Fowle)和因為參加過韓戰並多年後故地重遊的前陸軍軍官梅里·紐曼(Merrill Newman)。
還有一類被扣押在朝鮮的美國人是在冷戰期間叛逃北方的美國士兵(沒想到吧)。其中的著名者有查爾斯·詹金斯(Charles Jenkins),於1965年叛逃到了朝鮮。
 如今的他
如今的他不過朝鮮方面對他禮遇有加,大概是想作為主體思想的宣傳樣板,安排他在貴族雲集的平壤外國語大學教書,還綁來了日本女子曾我瞳做他的學生,並且撮合兩人喜結連理……
 抱得日本美人歸
抱得日本美人歸還是沒有找到師出無名地扣押商人的記載。
美國人在蘇聯
其實以上兩個國家再怎么和美國對抗,都是現代國際社會的一員,迫於國際社會的壓力,總體上對俘虜還算是優待的。通過歐洲、俄羅斯、中國等國的斡鏇下,這些被扣押的美國人大多都能安全釋放,扣押的時候也要根據當地法律找到一些依據。
 持續學習,終身受用
持續學習,終身受用要說起逮捕美國人最兇狠的,還要說美國的老對手蘇聯。
在上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由於蘇聯內部的特殊的大清洗和對歐美國家的敵意,大批美國人都慘遭扣押。罪名或是間諜罪,或是破壞國家安全罪,或是反革命罪,其中不少還被送到了古拉格。能最後回到美國的都是撿了一條命的。
 運到苦寒之地去搬大磚
運到苦寒之地去搬大磚其中比較有傳奇色彩的是跳傘運動員維克多·赫爾曼(Victor Herman)。在蘇聯政府的幫助下,他曾在1934年創造了“世界最高降落傘跳傘記錄”。然而當蘇聯官方要求他在記錄的國籍上寫下蘇聯時,他拒絕了。他表示自己只是一個同情社會主義事業的美國人,國籍不可丟。
於是他就被以反革命罪下獄古拉格,十年後才得以釋放,到死還保持著自己的美國人身份。
 維克多和家人
維克多和家人鐵幕落下以後,這種事就更多了,連大使館的人也不能倖免。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曾經在美國駐蘇大使館擔任文員的亞歷山大·多爾貢(Alexander Dolgun)。
作為一個基層外交人員,說他具有間諜能力實在是有些牽強。不過在美蘇對抗的大背景下,這樣一個基層工作人員確實也很難辯解什麼,最後屈打成招,於1948年被發配到了哈薩克斯坦的古拉格營地服役。一直到1956年,他才得到釋放。

這類事在冷戰期間史不絕書,比如在1961年因為涉嫌間諜罪被蘇聯扣押的醫學權威馬文·馬基寧(Marvin Makinen)和一直熱衷於正面報導蘇聯卻因為里根的強力外交而被捕的俄裔記者尼古拉斯·達尼洛夫(Nicholas Daniloff)。這些人其實都是對蘇聯有好感的美國人,只是因為國家之間的鬥爭而成為了不該出現的犧牲品。
最後一類被蘇聯扣押的美國人就是確實在進行間諜和破壞活動的了,比如美國飛行員加里·鮑爾斯(Gary Powers)。他在1950年代被中情局招募,接受了U-2偵察機的飛行訓練,開始了對蘇聯的間諜偵察。

結果在1960年,他的飛機被擊中,個人被蘇聯空軍俘虜,美國政府也無法對這樣的間諜行為作太多辯護。
 在莫斯科接受審判
在莫斯科接受審判這位實錘間諜在蘇聯的待遇還不錯,有吃有喝還能和家人進行有限的通信,後來蘇聯還在他的監獄原址建了一個小博物館,還在1962年把他交換回了美國。
但美國開始懷疑這名飛行員是雙料間諜,回國以後也沒有再重用他,個人命運並不好。
 不過相比從朝鮮放回後不幸去世的奧托同學已經算很幸運了
不過相比從朝鮮放回後不幸去世的奧托同學已經算很幸運了我們還是沒有找到蘇聯扣押美國商人的記載。
美國在國際競爭中樹敵不少,關於公民被所在國依法或無理扣押的情況應素有所知。莫名其妙地扣押別國公民,會引發兩國之間不必要的民間對立情緒,影響國際交往的流暢性,對兩國政府都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希望這一次,只是一些別有用心的挑撥者在離間,也希望整場令人不解的事件僅僅只是一個誤會。
美國 蘇聯 朝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