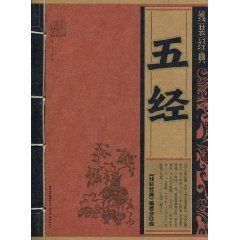定義
經學,當然指註解經書的學問,所以言及“經學”,首先要明確“經”是什麼。
 經學
經學《說文解字》將“經”訓為“織”,段玉裁注為“縱線”,以此引申為穿訂書冊的線,進而指書籍。
然而這裡的“經”當然不是指所有書籍,而是專指儒家經典,明確到這一點尚且不夠,因為從前的儒者們就因為“經”的包含範圍做了很多論辯,甚至興起了名曰“經名考”的學問,有人以為經只專指孔子的著述,而有人主張經是官方指定的儒家經典,本文采後說。
產生
所謂儒家經典,一般是指儒學十三經,亦即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但早期的儒家經典並不是這十三經。
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紀至五世紀),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在長期的政治活動失敗後,返回故鄉魯國,編訂和整理了一些傳統文獻,形成了六經。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編輯了《書》,刪定了《詩》,編訂了《禮》和《樂》,作了《易》的一部分,並根據魯國的史料創作了《春秋》。(關於六經是否是孔子所作,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議。不過一致的方向是同意孔子主導了編輯地位,原始文本則非孔子原作。)自此以後,儒生們就以六經為課本學習儒家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六經就已被人們公認為寶典。
經學產生於西漢。秦代即設有博士官,由於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的焚書坑儒,將全國圖書以及學術集中到鹹陽城,秦亡後,項羽焚燒鹹陽,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於歷史舞台,六經除了《易經》之外,其它幾未能幸免於難。漢代起初高祖劉邦並不重視這些儒家經典,從文景時期開始展開了大量的獻書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長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誦已遭焚毀的經典,或把秦時冒險隱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傳世。因為文字、傳述和解釋體系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學派,但其版本上則基本相同,後來統稱為今文經。
漢景帝末年魯恭王興建王府,壞孔子宅,從舊宅牆中發現一批經典;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圖書館);漢宣帝時又有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幾篇《尚書》。這些出土的文獻都是用戰國古文字書寫,與通行的五經相比,不僅篇數、字數不同,而且內容上也有相當差異,此後即統稱為古文經。
漢武帝即位後,為了適應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和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改變博士原有制度,增設弟子員,有五經博士之說。從此儒學獨尊,由於《樂》已無書,《詩》、《書》、《禮》、《易》、《春秋》五經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為崇高的法定經典,也成為士子必讀的經典。漢代儒生們即以傳習、解釋五經為主業。自此經學正式宣告誕生,可以將經學視為先秦原初儒學的繼承和發展。
演變
從六藝到五經
“六藝”就是“六經”的古稱,亦即孔子所指定的教科書——詩、書、禮、樂
易、春秋,在儒家地位上升後,這些教科書被尊為“經”。
“六經”一詞,首見於《莊子·天運》,然而直到西漢,也還是記載為六藝(見《漢書·藝文志》),同時在西漢初年,《樂》失傳,六藝自此僅餘其五。
在董仲舒的努力下,儒學在武帝建元五年取得獨尊地位,朝廷從此設立了五經博士,儒學從顯學成為官學,終於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而經學也由此成為中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之一
歷代官定“經”的範圍
西漢五經:《詩》、《書》、《禮》、《易》、《春秋》
東漢七經:除上述五經外,另外二經究竟為何一向聚訟紛紜,據王國維《漢魏博士考》,應為《孝經》與《論語》
唐九經:即將五經中的禮拆為儀禮、周禮與禮記,春秋拆做左傳、公羊傳與穀梁傳
開成十二經:唐文宗開成十二年,於九經上添《爾雅》、《論語》、《孝經》,刻做石經。
宋十三經:北宋時,承繼唐代九經定製,但是《孟子》的地位有所上升,南遷以後,《孟子》的地位已經不可動搖,升格為經,與開成石經合做十三經。
四書五經:為朱子所定,與五經上增設“四書”,隨著朱子學的繁盛,這也成為了儒家經典最為著名的編訂方式。
發展
兩漢
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每一經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與弟子傳習經書,分成若干“師說”,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時的五經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後經學日益興盛,博士的數量也逐漸增加。到了東漢光武帝時期,確定了十四家博士。據《後漢書·儒林列傳》記載:“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這十四家都屬於今文經學,其官學地位一直保持到東漢末年。
今文經學的特點是微言大義地闡發說明孔子的思想,繼承和發揚儒家學說。今文經學以《春秋》為孔子為萬世立法的“元經”,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學”。公羊學即為《春秋公羊傳》里所闡發的微言大義,主要包括大一統、大居正、大復仇、通三統、統三世、更化改制、興禮誅賊等。漢武帝時期出現了為大一統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論體系的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和善於把公羊學理論運用於現實政治中的政治家公孫弘,經過一代代今文經學學者的推闡與實踐,以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深受漢朝皇帝的重視,始終在漢朝政治中處於主導地位。
今文經學發展到西漢後期,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方面由於董仲舒對於公羊學中災異、符瑞、天人感應的闡發,今文經學由此邏輯發展的後果即是讖緯泛濫,再加之統治者的迷信與提倡,經學逐漸神學化;另一方面由於今文經學繼承了較多的原初儒學的色彩,其理論內在地包含著對現實的批判,從而越來越不能為逐漸加強的君主專制所容忍。在這種情況下,自西漢中期開始就已經在民間傳授的古文經學興起。
古文經學所依據的經書一般都是西漢中期以後在民間發現的古書,因其是用戰國及以前的古文字所書寫,故稱之為古文經。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並不僅僅是文字篇章的差異,主要在於它們對經書的解釋與治學方法的不同。今文經學認為孔子是“為漢製法”的“素王”,而古文經學認為孔子只是古典文獻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師;今文經學認為六經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託,其中有許多微言大義,而古文經學則認為六經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與聖君賢相政治格言的記錄;今文經學注重微言大義,古文經學注重對經文本義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闡明。如果說今文經學關注的重心在於政治哲學與歷史哲學的話,那么自西漢後期開始與之針鋒相對的古文經學所關注的重心就是歷史史料學與語言學。
古文經學的興起最早起自《春秋穀梁傳》,西漢後期曾被立為博士。在王莽當政時期,劉歆極力鼓吹古文經學,並使之立為新朝的博士。東漢時期,古文經學雖然一直沒有被立為博士,屬於民間學說,但是其影響力越來越大,逐步超出並壓倒了今文經學。由於今文經學發展後期日趨繁瑣,例如“曰若稽古”四個字可以解釋十萬字,又有所謂“師法”“家法”的束縛,再加之其與讖緯糾纏過深,使得人們逐漸遺棄了今文經學。而古文經學一來較少受“師法”“家法”的制約,較為自由也較為簡明;二來與讖緯瓜葛較少,較為理性;三來其放棄了今文經學的批判性,對君主專制的維護更有優勢,所以在今古文經學的長期鬥爭中,古文經學取得了最後的勝利。東漢的古文經學大師有賈逵、許慎、馬融、服虔、盧植等,弟子眾多,影響很大。而今文經學只有何休取得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詁》是唯一一部完整流傳至今的今文經。
在今古文經學的長期爭辯過程中,互相也在逐漸地滲透,互相融合。東漢初年(公元79年)召開的白虎觀會議就是一個官方召開的企圖彌合今古文經學異同的重要的學術會議。會議的成果由班固寫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簡稱《白虎通》一書。《白虎通》是以今文經學為基礎,初步實現了經學的統一。東漢末年,古文經學的集大成者鄭玄,網羅眾家、遍注群經,對今古文經學進行了全面總結,自成一家之言。鄭玄以古文經學為基礎,但又能吸收今文經學中的優點,態度嚴謹,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從而超過了前人。自此以後鄭學興盛,這不僅標誌著今古文經學之爭的終結,也標誌著漢代經學的衰亡,之後今文經學也隨之消失。
漢朝是經學最為昌盛的時代,朝野內外誦讀經書蔚然成風,《漢書·韋賢傳》引民間諺語說“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漢朝的“以經義決獄”是漢朝經學與王朝政治相結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漢朝經學繁盛的一大標誌。儒生通過司法實踐並官學私學教育,移風易俗,把經學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眾之中。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經學由衰落走向分離的時期。在曹魏時期,出現了王學與鄭學之爭。王學,是指王肅所創立的經學體系。王肅是司馬昭的岳父,所以王學獲得了司馬氏的支持,他註解的《尚書》、《詩》、《論語》、三《禮》和《左氏春秋》以及其父所作的《易傳》都被列為官學。王學和鄭學之間的紛爭,並不是純粹的學術爭論,而帶有強烈的政治鬥爭的意味。這場紛爭同時也標誌著兩漢經學的衰落。
魏晉時期在經學取得成就較大的還有王弼、何晏等。王弼注《周易》,擺脫了漢代用“象數”和讖緯解說《周易》的老路,開創了用義理、思辨哲學解說《周易》的新路,這是經學史上一次重大變革。何晏所作《論語集解》收集了漢以來各家之說,對後世影響很大。這一時期經學的特點是經學逐漸玄學化。
南北朝時期經學也隨著政治上的南北對立而分立為南學和北學。據《北史·儒林傳》記載,南學《周易》尊王弼,摒棄象數、發揮義理,《尚書》流行《孔傳古文尚書》,《左傳》盛行杜預撰《春秋左傳集解》;北學《周易》、《尚書》主鄭玄,《左傳》主服虔。“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從學術風格上講,南學受玄學和佛學影響比較大,能博取眾家之長,又喜標新立異,反映了其哲學思辨能力的提高,而北學受北方遊牧民族質樸風尚的影響,保持了漢朝經學以章句訓詁為宗的特點。
隋唐
經學由漢而唐,有古今文學,鄭學、王學,南學、北學之爭。唐代則基於取士的需要,以國家的力量來推行經學,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是這時代的代表著作,同時也是鄭玄以來漢學的總結與高峰。它的編纂一方面成為士人的教科書,另一方面則象徵著政府在聖統上的合法性建立,影響了後來明代《五經大全》、《永樂大典》以及清代《四庫全書》等等政府主導下的經典編輯,至唐後五代之世,宋代晁迥之前,無人異詞。這個時期的經學也進入了韓國以及日本,成為諸國所仿效的法典,日本天皇更運用經學確立了他的政治法統地位。
宋朝
宋代理學興起,自晁迥之後,理學家們以重新詮釋古代經典的方式,以疑經、改經、刪經來進行回歸先秦經典的活動,闡發他們的主張,或保守、或激進。此時期,出現以《論語》、《孟子》加上從禮記中抽出《大學》、《中庸》合稱的「四書」,因為被界定為還原聖人思想的需要而被重新定位,成為超越五經的思想著作。
明朝
明代延續了宋代的理學路線,一方面政府編纂官方版經典文本,另一方面南方的經學力量逐漸抬頭,例如王陽明即是最為重要的明代理學家。明末經學家幾乎都帶有王陽明式的豪氣,紛紛組織學社,發動朝野清議、輿論、彈劾,與腐敗的政府、宦官對抗,形成激烈的流血黨爭,種下明朝滅亡的內部因子。另外一部份的明朝流亡者、海盜、商人與士人,以日本為重要根據地,進行活動,連帶將日本的經學進一步推展,例如孔子、孟子、王陽明皆被各藩與幕府所尊崇、朱舜水以《春秋》為核心的「尊王」、「攘夷」思想,影響了水戶學派的政治論調,進而在明治維新引起了重大的思想浪潮。
清朝
清代初期受到明朝滅亡的影響,士人開始思考王陽明路線的弊病,另一方面因為清朝皇帝實施文字獄、編纂《四庫全書》、《明史》等思想控制手段,經學中較不介入政治的的實學與考據路線,遂特別發達,尤其重視以大量的古代典籍以及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等方式來研究經書,甚至進一步考證某些經書的真偽、劃分學術流派,可以說,清代初期的經學思想是被明朝遺老們如黃宗羲、顧炎武等人所影響主導的。清末基於時代需求,主張激進改革的公羊家大盛,其中又以常州學派的康有為、梁啓超等最為有力活躍的人物。
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曾說明清代經學“凡三變”,清初,以宋學為主;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後,“漢十四博士今文說,自魏、晉淪亡千餘年,至今日而復明。實能述伏(生)、董(仲舒)之遺文,尋武(漢武帝)、宣(漢宣帝)之絕軌。是為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於道。”又說:“乾嘉以後,陽湖莊氏乃講今文之學,孔廣森治《公羊春秋》,孫星衍於《尚書》兼治今、古文,陳喬樅治《今文尚書》、齊、魯、韓三家《詩》,魏源作《書古微》、《詩古微》、《公羊古微》,凌曙作《公羊禮證》、《春秋繁露注》,陳立作《公羊義疏》,王館長(按,指時任湖南師範館館長的王先謙)作《三家詩義疏》,已成《周南》、《召南》、《邶風》,錫瑞作《今文尚書考證》、《尚書大傳疏證》。”
兩廣總督阮元輯《皇清經解》,收七十三家,記書一百八十八種,凡一千四百卷。此書是匯集儒家經學經解之大成,是對乾嘉學術的一次全面總結。
民國以後
到民國時代以後,由於大量的西學、政治運動取代了原來的經學思想,兩者的衝擊之中,產生了諸多主張,一般而言,全面排斥西學的想法已經不復存在,但仍存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與全面西化的路線爭執。胡適在〈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一文就說:“儒家經典中,除《論孟》及《禮記》之一部分外,皆古史料而已。”,胡適因把《詩經》當成文學作品,不是一部經典。古代經書的權威性遂下降,經學也就逐漸式微,民國二十年代,何鍵、陳濟棠等倡議學校恢復經學課程,遭到不少反對。
兩岸分治之後,中國大陸對於經學的打擊不遺餘力,特別至文化大革命期間,經學在中國大陸上更是受到毀滅與破壞,這樣的路線導致一部分後世學者認定「文革為五四的總結」。相對之下,當時的台灣對於經典思想的保存較為完整妥善。今日,中國大陸面對西方人權思想的衝擊與改革開放的社會需求,開始重新檢視經學內容,企圖以經學立場建立足以與西方價值對抗的中國價值,並在二十一世紀初葉逐漸建立學術研究單位,這個動作引起了東亞文化圈的重視,包括日本、新加坡、越南、韓國等國,皆對此價值的建立表現了高度的興趣。台灣方面則因政黨輪替,在去中國化以本土化為主的思維下,經學研究反而顯得低調。
流派
經學流派的分類法有數種,二分,三分或四分,本文採取“三分法”,即將之分為“今文學”、“古文學”與“宋學”三派,其中前二者可合稱為“漢學”。
三大流派的區別一言難盡,但也完全可以簡要概括,周予同先生為皮錫瑞《經學歷史》一書所作序的總結十分到位即:今文學家將孔子視為政治家,古文學家將孔子視為史學家,而宋學家將孔子視為哲學家,只要記住這一點,對古代學者的分類就應該不會有問題了,另外,在六經上,今文家主張全為孔子所作,而古文家目之為史料,認為並非起自孔子。
今文學
先說今文學部分:借著董子和公孫述的東風,熱衷談論微言大義,為統治階級提供治術,宣講“皇權大一統”,甚至不惜採取“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的手段參與國政的儒家迅速上位。
此時,由於秦代對書籍的禁毀,除《易經》為卜書未遭劫難外,其餘諸經都已失傳,因此只有採取口傳筆錄的方式加以傳承,由於採用漢代通行的隸書記錄,與由西漢中期以後陸續發現的先秦文字記錄的經書有別。因此被稱之為“今文學”。
當時各經的傳承狀況大致如下:
《詩》有齊魯韓三家,《書》由伏生所傳,《禮》由高唐生所傳,《春秋》中,公羊為齊學,穀梁為魯學,各家都各有特點,在此不做大量展開,僅以《春秋》為例,齊學的公羊傳求變,重法,可以說是重視霸道,而魯學穀梁則重視宗法論理,可稱重視王道。
隨著時間的推移,作為官學的儒學一再得到朝廷支持,宣帝時增加了博士學生的數量,而其後的元帝,以崇儒著稱,經學得到巨大發展。
甘露三年(前51年),朝廷召開石渠閣會議增設博士,黃龍元年(前49年),宣帝再度增加博士名額至十二人,史稱黃龍十二博士。
同時,官府推重的春秋學也從公羊學轉向穀梁學,可見經學也一直在適應社會的需要,發生著變化。
東漢光武帝在新末起義中以恢復漢室相號召,自然承續舊制,建立政權後更增加名額,即“光武十四博士”。作為官學的今文學自然繼續發展。
但物極必反,重視微言大義的今文經學終於走向了繁瑣零碎。在此僅舉一例:秦近君解尚書,“堯典”二字竟然“至十萬餘言”。
同時,今文學自從西漢末年以後,逐漸與緯學合流,尤其東漢,緯學更成為“內學”,二者結合更為緊密,在建初四年(79年),出現了雜糅博採,緯學經典化的《白虎通義》,當然,白虎觀會議的目的在於調和各派觀點,嘗試解決今文學駁雜與各派意見不一的產物,因此不獨對今文學產生了影響。但古文學派顯然沒那么迷信。
隨著王朝的衰敗,作為官學的今文學江河日下,而崛起民間,大師迭出的古文學自此嶄露頭角。
最後應該一提,在今文學式微的情況下,何休窮十七年心血,成《春秋公羊解詁》,成為了兩漢公羊學的總結,其中“衰亂-昇平-太平”的三世說,影響極其深遠。
古文學
現在回頭講古文學:提到古文學,就不能不提劉歆,劉歆及其父劉向是中國古代目錄學的奠基人,是兩漢有數的大學者,二人在整理古書的過程中,發現了不少流落民間的古文(先秦文字)經書,劉歆認為這也應當列於學官,然而未能成功,此後,他寫了一篇《移書讓太常博士》(見附錄)進行抗議。
這文章自然把今文家都得罪遍了,劉歆只得辭官,眼看是山窮水盡,然而轉機卻意外出現了,那就是王莽改制。
王莽建立新朝後,劉歆成為了“嘉新公”,這一對學者君臣一心投入學術,全心以學術為指導進行改革,最終失敗身死。
前人談及劉歆,往往說是“虎父有犬子”,大加指斥,然而換一個角度看,他與王莽可謂是惺惺相惜的一對理想家,最終成了自己理想的殉道者。
東漢建立以後,光武請經學大師進京,七人中陳元、鄭眾、杜林、衛宏四人都是古文家,然而當光武帝提出要設立古文的《費氏易》、左傳博士時,今文學家激烈反抗,最終光武決定只設左傳博士,然而也引起了反彈,同時預選擔任左氏春秋博士的李封病故,於是便不了了之,之後再也沒有設定古文學博士了。
因此,之後的古文學一直作為“私學”而存在,然而,古文學的治學方法更為科學(他們引入了考據、訓詁等科學的研究方法),態度更為嚴謹,加之大師輩出,也不可謂不繁榮。
古文學中有成就之人甚多,僅舉數例:衛宏注毛詩,序中對詩經的藝術分析直到當代尚且具有巨大價值,再如人所共知的神滅論,其濫觴也是古文家桓譚的唯物思想。
賈逵的春秋,既秉承家學,治左傳極精,又能順應時代,在白虎觀會議上,不僅頂住了今文家李育的辯難,更用左傳附會漢家的天運,得到垂青最後提一下馬融,所學極博,舉凡經書無所不注,尤其春秋上,成《春秋三傳異同說》,堪稱集大成之作。同時,諸如漢字的六書理論,重要的《說文解字》一書等,也都為古文家的貢獻。
鄭玄
最後要說的,是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鄭玄鄭康成,他打破藩籬。通習古今,以古文學為主,遍注諸經。
青年時代遍訪山東學者之後,前往關中受業於馬融,馬融作為一代宗匠,非得意門生不與之見面,鄭玄因一次天文歷算對答得到馬融垂青,盡得真傳,在東歸之時,馬融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得到了這位古文大家的高度評價,後來,他又與弘揚公羊學而貶斥另外兩傳的今文大家何休論戰,何休嘆道:“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又令何休嘆服,足見其學問之精博。
東漢末年,政治動盪,鄭玄拋開政治抱負,一心為學,其人品得到了歷代儒生的高度讚譽,而其學術成果更是輝煌,今傳十三經註疏,直接、間接取鄭玄注者達七種,堪稱冠絕古今。
鄭玄綜治今古文學,形成了鄭學,達到了經學史上的一個高峰,可以說是對之前數百年經學積累的一次總結。
皮錫瑞作為一個今文學家,在《經學歷史》中也對鄭玄高度評價:“鄭君康成,以博聞強記之才,兼高行卓絕之美,著書滿家,從學盈萬,當時莫不仰望,稱伊、洛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矣。”
內容
經學研究的工作,主要就是註疏經書。所謂「注」,就是對經書字句的意義等加以解釋,但有些注因為太簡要或年代久遠,因此後人為注再作解釋,稱作「疏」。除了註疏之外,其他如「解」、「考證」、「集解」、「正義」等等,名雖不同,但作法大多類似,都是對於經書的一字一句詳加研究,希望能了解它真正要表達的意思。
經書的內容難以理解充滿爭議,但卻又是包括解釋宇宙秩序、政治、道德規範、甚至日常生活等等一切的準則以及正當性來源,所以研究經書便成為漢代以來最重要的學術活動。加上漢武帝對於經學的獎勵推行,使通曉經書的人獲得禮遇,使投入經學研究的人更多。在東漢時因此有「遺子金滿盈,不如教子一經」的說法。《漢書?藝文志》中,五經與儒家著作仍分列在兩個類別,六朝時,逐漸產生從七部圖書到四部的過渡,到了《隋書?經籍志》,正式把當時的學術按「群經、史學、諸子、文集」區分為四種,即以經學為首,這種分類方式,一直到清代仍為人所接受。
但是以歷史觀點來看,經學的研究是透過不可更動的文本,來闡發可以更動的注釋,注釋活動等同於士人思想的發表與闡述,考慮到經典的神聖性,便可發現政治層面的經學活動是十分複雜的。歷代政府取得「法統」之後,均希望能取得經學研究者,也就是知識份子的認同與支持,即為“聖統”,與由家法、師法觀念衍生、象徵經典詮釋主導權威的「道統」不同,聖統的取得象徵著一個政府除了在武力上取得統治權之外、同時也在社會文化、價值認同上取得合法性。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朝,以異族的地位,要突破「華夷」的春秋思想並不容易,他們以政治力積極運作,或殺戮(如文字獄)、或籠絡(如開科取士、獎勵學術)、或詮釋(如編纂《四庫全書》、《明史》、《大義覺迷錄》)、或禁焚,以取得聖統的承認。士人要施展政治抱負,一方面要取得法統上政治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要尋求道統上的立論依據,因此往往透過對神聖經典的詮釋活動,來影響執政者的施政思考,在「士人與國君互相影響」的前提下,經學成為重要的政治互動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