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歷
 喬治·沃尼斯特·莫理循
喬治·沃尼斯特·莫理循莫理循從小就極富冒險精神,曾在18歲的時候,沿澳大利亞南海岸,以每天50公里的路程,徒步旅行了一千多公里。這成為他以後探險生涯的開始。莫理循畢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大學畢業後,他按照少年時代的夢想,開始環遊世界。1893年在到達遠東後,因錯過前往日本的輪船,翌年二月,他自上海沿長江到重慶,轉道雲南,僅是靠母親寄的40英鎊,徒步前往緬甸的仰光。之後,他整理一路的日記和照片,出版了《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一書,該書使他名聲大噪,並被英國泰晤士報聘為駐華首席記者。
1897年3月,莫理循到達北京,就此開始他長達二十餘年的中國生涯。作為記者,他身歷或親見從戊戌變法,辛丑簽約,清末新政,日俄戰爭,帝、後之喪,直至辛亥革命的全部歷史變遷。作為新生的民國go-vern-ment政治顧問,他參與了鞏固袁世凱統治的進程,幫助中國go-vern-ment對抗日本“二十一條”政治訛詐,推動中國參加歐洲大戰,反對袁世凱稱帝。在他病重之際,還為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修改檔案。1920年5月底,他在倫敦死於胰臟病。
莫理循在20世紀頭二十年的北京政壇與西方新聞界,都是最為重要的“中國通”。
 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拍攝的古涼州
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拍攝的古涼州1894年,莫理循由上海動身循陸路徒步旅行到達仰光。1896年從曼谷到昆 明,次年又作橫穿東三省的旅行。1897年,莫理循成為《泰晤士報》駐華特派記者。在二十多年的記者生涯中,清末民初的變革,莫里循始終在場,他有記者的銳利眼光和寬廣胸懷,他報導了許多劃時代事件。莫里循是澳大利亞人,為英帝國服務,對中國卻很有感情。他每隔兩三年,便鄭重其事地請照相館師傅上門來拍他與僕人(包括僕人家屬)合影的照片,此中可見他的善良。
1910年,莫理循開始了為時半年的中國西部考察,從陝西鹹陽出發,途經甘肅平涼、蘭州、涼州、甘州、肅州,出嘉峪關進入新疆,經哈密、烏魯木齊、石河子,一路西行到達伊犁,爾後向南翻越木扎爾特冰川,經阿克蘇到達喀什葛爾,後向西過烏恰,最後到達俄國的奧什(今屬吉爾吉斯斯坦)。在此次考察中,莫理循親歷、親聞、親見的可靠記錄,對於我們了解清末中國提供了非常生動、直接的材料。
 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拍攝的古涼州
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拍攝的古涼州他曾是袁世凱的法律顧問,後來雖離開中國,但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期間 那段風風雨雨的日子裡,他又從倫敦前往巴黎,出任中國代表團的政治顧問。莫理循在中國生活了20餘年,是中國近代史上許多重大事件的親歷者和參與者。
1917年,英國人莫理循在華收藏的大量東方學文獻被日本收購,成為今天東洋文庫的前身。從此,中國人只能東渡日本才能利用莫理循文庫,這不可避免地制約了中國學術的發展水平。
主要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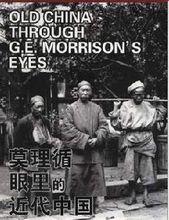 喬治·沃尼斯特·莫理循
喬治·沃尼斯特·莫理循歷史學家將莫理循文庫與《永樂大典》和敦煌文書相提並論,足見其在中國學者心目中的地位。因此,莫理循文庫的外流同樣是中國學術的“傷心史”。他居住北京達20餘年,親歷了近代中國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他的大量報導、通訊與日日記成為研究這一段中國歷史的重要素材。他身後留下的圖片資料約3000餘幅。旅澳歷史畫家沈嘉蔚從中精選主要部分並作了必要考證,分為《北京的莫理循》、《世紀之交的戰亂》、《目擊變革》三冊出版,含庚子事變紀實、20世紀國中國近代化變遷、清末民初民情風俗、莫理循與中國僕人的友誼、莫理循與清末民初在華洋人等專題內容。
莫理循1920年在去世前寫給妻子的最後一封信中說,他所收集的資料諸物,應捐給新南威爾斯州圖書館。根據這個遺囑,莫理循的遺孀宣布,當物色到整理和編選的合適人選後,這批檔案即捐給圖書館,二十五年後公開。到1925年J.B.Capper共整理出兩卷,但未出版。1946年,莫里循的長子同意將全部檔案移交圖書館。後來Cyril Pearl撰寫莫里循的傳記《北京的莫里循》,便利用了這批檔案。由旅澳的駱惠敏博士整理編輯的《莫里循通信選1897-1920》,於1978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中譯本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上海出版。這些整理出版的通信,僅僅是莫理循檔案中的一小部分,更有歷史價值的大量日記,卻因字跡難辨,整理難度很大,加之無專人編輯注釋,將之公開出版尚待時日,這樣它們只得靜靜躺在書架上。
莫理循檔案已大致按照時間順序編號,查閱十分方便。這批檔案數量不少,約有幾十卷之多,計有日記、信件、地址本、請柬、拜帖、選單、票據、郵票、紙幣、剪報、地圖、藝術品等,應有盡有,可見莫里循此人頗有收藏的雅興。這倒也好,翻閱他的檔案,除了可以感受歷史的風雲變幻之外,更可以讓你從那些不起眼的物件里,瀏覽一個世紀前的諸般景象。
查閱莫理循檔案,手續並不複雜,辦有借閱證的讀者,可根據自己的需要添上有關卷宗號碼,管理員從檔案庫里拿出即是。我們先調出莫里循檔案中的照片類卷宗。這類卷宗有十多卷,分為家庭、交往等專題,大約有上千張照片。
這些照片,生動凸現出莫里循在中國政壇活躍的身影。他珍藏的照片中,不乏當年叱吒風雲的人物,從政治家、革命家、軍閥一直到各界名流,孫中山、袁世凱、李鴻章、辜鴻銘、張作霖、陳寶琛等,都有照片贈他,如今他們在這裡默默相對。擔任過北洋政府總理的馮國璋,在自己的照片上面用毛筆寫道:送莫老夫人。這是他在北京廊房頭條榮光照相館拍攝的。1918年,時任外交總長的陸徵祥,送給莫理循的有照片和名片,名片上僅印有:中華民國外交總長陸徵祥,為中法文兩種。這名片應該是他在巴黎和會期間使用的。一張小小名片,在我面前也漫溢出濃厚歷史感。
建立私人圖書館
 喬治·沃尼斯特·莫理循
喬治·沃尼斯特·莫理循1897年3月以英國《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身份抵達中國的莫理循發現“這裡沒有值得稱道的圖書館;只是一些私人手中多少有點零散收集”,“沒有關於中國植物學、自然歷史和地理的任何書籍”,“需要迫使我建立這樣一個圖書館”。這是1924年東京出版的英文《莫理循亞洲文庫目錄》披露的他熱心搜購的一個原因。“當時在來華外國人中還沒有人像他那樣有意識、成規模地收集書刊。”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竇坤說,“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爵士曾有一小部分收藏,但多與海關有關,範圍比較狹窄。李鴻章的英文秘書畢德格有一些英法文書籍,但他沒有莫理循那樣有計畫性。”
竇坤說,閱讀使莫理循收集了大量圖書,在此基礎上,他開始收藏書籍。“莫理循一生喜好徒步旅行,閱讀為他的旅行增色。每次旅行後,他都要撰寫文章加以介紹。這種介紹不是單純地對旅行本身的描述,而是重點闡發他對親歷事件及地區的感受。他習慣於將他的體會與書中的信息加以比較。這在他的遊記《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雖然搜購圖書的舉動從莫理循初到中國時就已經開始了,但專門辟出房間建立私人圖書館則是1902年他搬到王府井大街以後的事。
搬家前,莫理循同大多數外國人一樣,住在使館區。“但莫理循並不喜歡生活在一群外國人當中。他的天性是不願意被禁錮在某個地方的;其次,作為一名記者,他需要了解各方面的情況和訊息。”竇坤說,因此,義和團運動後,他開始尋找公使館以外的房子,但希望距離使館不遠,以便隨時與使館取得聯繫。
莫理循在北京城裡的住所先後位於使館區現台基廠大街北部(義和團運動前居於路西、之後為路東)、王府井大街路西和金魚胡同三教庵,其中以王府井大街路西的住宅最廣為人知。據竇坤考證,莫理循故居的具體位置應在大阮府胡同北,即現在百貨大樓舊樓的東北角及相應東部廣場和它們以北至菜廠胡同的位置。
“雖然莫理循故居不是典型四合院格局,而且建成洋式面貌,但這幾所院落依稀還可以使我們追憶當年故居的環境:他的家與庚子後做過議和工作的英文秘書曾廣銓及美國外交官司戴德為鄰,東面是位於東堂子胡同的外務部,南面是使館區,西面靠近紫禁城,這是一個可以迅速探訪各方動向的理想居住地。”竇坤說。莫理循就是在這裡建立了有名的圖書館。
文庫藏書盡搜無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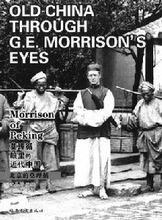 喬治·沃尼斯特·莫理循
喬治·沃尼斯特·莫理循莫理循為他的藏書命名為“亞細亞圖書館”。自從圖書館建立,書刊資料就成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在日記中寫道,當他訂購的書籍未到時,他是那樣地坐立不安,而書到以後,又是極度地興奮。關於圖書館的樣子,莫理循的好友、中國近代醫學衛生事業先驅伍連德在其回憶錄中有這樣的記述:“圖書館是個長方形的屋子。面積是60英尺×100英尺。書架是硬木製成的,由地面幾乎直抵屋頂。兩邊均可取書。地圖及其他檔案如圖版等,放在西牆角的大抽屜里。為防風和陽光,書籍放在藍布製成的書套中。”
從1897年到1917年20年間,莫理循收集的西文關於亞洲,特別是關於中國的書籍、小冊子達2.4萬冊。其中小冊子7000多份,大部分是在其他圖書館無法找到的珍貴資料。地圖、圖版1000餘份。語種包括英、法、德、意、日、西、葡等十幾種,涉及了政治、外交、法制、軍事、歷史、地理、考古、地質、植物、動物等多個領域。其中凡歐洲各國記載中國本部、藩屬各種事件之新舊書籍,大之如鴻篇巨製,小之如寸紙片,靡不具備。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鶴用了一個讚賞有加的“完璧性”來彰顯莫理循文庫的特色。他說,莫氏收集有關中國的印刷物,即使一枚傳單也不漏。至今,在莫理循文庫中,連他在北京租房的契約,總統的宴會選單都原封不動地保留著。對於書籍而言,則新刊與古本盡搜無遺,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也一網打盡。以至今天的讀者發現,文庫中竟然保存著從1485年最初的拉丁語版本,到二十世紀初出版的近50種《馬可波羅遊記》,還有十七八世紀來華基督教傳教士的所有著作,以及120多種英、法、德等歐洲諸國的學會所出的定期刊物、中國的海關報告等。
精心的布置和完美的收藏,莫理循圖書館在當時吸引了眾多中外名士。伍連德在其回憶錄中說,莫理循喜歡邀請在京各種國籍的來訪者吃飯,特別是那些對他的圖書館感興趣的人更是如此。外交官以及其他在華外國人也對他的圖書館感興趣,德國公使海靖、英國使館人員戈頒、艾倫賽等都是莫理循圖書館的常客,而李鴻章的英文秘書畢德格、英國漢學家巴克斯等則得到過莫理循的圖書饋贈。
中國人當中,地質學家丁文江、劍橋醫學博士伍連德、兵部員外郎曾廣銓、袁世凱幕僚蔡廷乾等人,對莫氏藏書很是欽佩。有資料記載,他們和其他更多的、多是會英語的人士曾經參觀過莫理循圖書館,並從那裡借閱過圖書。
文庫東渡
1912年,單身漢莫理循已經50歲了仍未婚,但愛戀著比他小27歲的女秘書羅賓小姐。也許是對穩定家庭生活的憧憬,令他反思目前飄泊不定的生活狀態。此時,莫理循的心情出現了自1882年以來從未有過的迷茫。“我提職無望,心情苦悶,厭倦那東飄西盪的工作。今天我終於下決心:1.從《泰晤士報》退休;2.賣掉我的圖書館;3.離開中國返回澳大利亞。”這是莫理循第一次提到他想賣掉圖書館。
數月後,深感“缺錢”的莫理循為他的圖書館開價4萬英鎊。他在給《泰晤士報》白克爾的一封信中說:“在為《泰晤士報》效力期間,我幾乎沒攢下幾塊錢。現在,我償還所有債務後,還剩不到250美元。我收藏有關於中國的書籍。雖然我實在不想賣掉我的圖書館,但我別無選擇。”
這一年,莫理循辭去《泰晤士報》的工作,接受中國政府的邀請,出任袁世凱的政治顧問,獲得了一筆可觀的薪水,8月份與羅賓小姐結婚,擁有了他夢寐以求的愛情,賣掉圖書館的想法暫時被他放下了。
但到了1913年,莫理循再次有了賣掉圖書館的想法。他在一封私人密信中寫道:“我發現這項工作占據了我太多的時間和精力,我已經感到力不從心了。”
莫理循在政治顧問這個職位上一直做到第四任總統徐世昌時期。“莫理循後來也很後悔自己的這個選擇。”周振鶴說,“因為總統顧問的職位不過是一種擺設而已,重大的事情根本不同他商量。”因此,1917年他回到澳大利亞,看看是否可能開始他第二個人生。這一次,莫理循是痛下決心要把圖書館賣掉了。
在莫理循展露售書意圖後,美國、日本、中國等政府或學者、賢達紛紛表示關注,他們都希望得到這批珍貴藏書,其中以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最為積極。但莫理循其實是想把圖書留在中國的。早在1912年莫理循剛剛有了賣掉圖書館的想法時,他就提出“如果中國人購買,我將把我在北京的不動產,即建有防火設備的圖書館送給政府”。
但1917年正好趕上張勛復辟、軍閥混戰,社會動盪不安。“北洋軍閥政府把大量錢款充作軍費,忙於戰爭,已無暇顧及文化方面的事業。”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來新夏說,“這是貽誤莫氏藏書留在中國的主要原因。”其間雖也有人接洽過,近代著名實業家、教育家張謇就曾經表示,希望莫理循的圖書能夠成為南通圖書館的收藏,但詢問過價錢後便沒了下文。
最終,莫理循決定以3.5萬英鎊的價款賣給了日本三菱財團奠基者岩崎彌太郎長子岩崎久彌。“他的想法是,即便這批圖籍不能留在中國,也要儘可能將它留在遠東。”來新夏說。1917年8月8日莫理循在致丁文江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的藏書要賣掉我覺得很難過,但是要維持它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使我的時間和財力都大感緊張。我本來希望它能留在北京,可是辦不到。”
對於莫理循文庫東渡這件事,竇坤認為日本人從莫理循手中購得藏書,其途徑還算正當,但來新夏則把日本人的“購書”行為稱作“巧取”。“日本人對中國文化典籍的重視由來已久。從古代到近代,不斷有日本人來中國淘書。但在近代,他們目的已不再是求知,而純粹是把中國的文獻精華拿去作為日本的文化財產或國寶,帶有文化侵略的性質。”
來新夏說,“不止莫理循書庫,1907年日本三菱財閥岩崎彌之助和岩崎小彌太父子趁陸家危機,以10萬元的價格將清末四大藏書樓之一陸心源宋樓,以及十萬卷樓和守先閣的藏書全部打捆運走,歸於靜嘉堂文庫。”
莫理循文庫東渡後,1924年岩崎久彌在其基礎上建立了東洋文庫。幾經擴充,今天的日本人稱它是“東方學家的麥加”,而中國人卻只能東渡日本去利用莫理循藏書。這段歷史也因此成為中國學術的“傷心史”,成為中國學者心中的一大憾事。
影響中國歷史的外國人
| 這些身份各異、生活時代不同的洋人,在與中國結緣的過程中,都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困頓和磨難。他們大多早在十九世紀中葉陸續來到中國,在朝廷尚不知英美各國位於地球哪一端、百姓視高鼻深目的洋人為鬼魅的年代,來華洋人與中國人交往,並且開拓出了自己的一片“事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