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養老令》
《養老令》歷史介紹
 《天聖令》
《天聖令》相當於中國盛唐時期。兩國醫家、學者不斷往來於中、日之間,盛唐醫學、佛教醫學傳入日本。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六年(754)鑒真和尚赴日,在隨行人員中,華文漢向日本人傳授經絡穴位及針灸方法,並介紹了人體經穴圖。
元正天皇養老二年(718)頒行的《養老令》,與《大寶令》差別不大。其中的《醫疾令》也規定了醫學教育的內容及其考試方法、入學資格、修業年限等。《大寶令》、《養老令》均散佚不傳,後人從《類聚三代格》、《政事要略》、《令集解》、《續日本記》等引用的佚文中,輯出《醫疾令》27條2,其中與針灸有關的有13條,內容涉及針生的學費、教材、實習、考試、畢業後的待遇等。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確規定針生的學習教材是:必修《素問》、《黃帝針經》、 《明堂》 、《脈訣》,兼習《甲乙經》、《流注經》、《偃側圖》、《赤烏神針》等中國早期醫學經典。
此外《大寶令》 、《養老令》還規定宮內省置典藥寮,在典藥寮設定針灸專業,定針博士1人、針師5人、針生20人,針師療諸病,施補瀉,針博士教授針生,針生學習針術。
主要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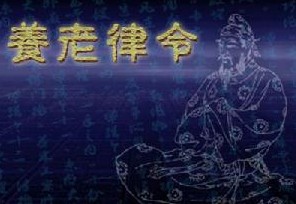 《養老律令》
《養老律令》《養老令》又名《養老律令》,下面詳細介紹下內容:
戶令第一為里條:凡戶。以五十戶為里。每里置長一人。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隨便量置。
戶令第二定郡條:凡郡。以廿里以下十六里以上為大郡十二里以上為上郡八里以上為中郡四里以上為下郡二里以上為小郡。
戶令第三置坊長條:凡京。每坊置長一人四坊置令一人。
戶令第四取坊令條:凡坊令。取正八位以下。明廉強直。堪時務者霽充。里長坊長。並取白丁清正。強幹者充。若當里當坊無人。聽於比里比坊簡用。
戶令第五戶主條:凡戶主。皆以家長為之。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無課口者。為不課戶。。
戶令第六三歲以下條:凡男女。三歲以下為黃。十六以下為小。廿以下為中。其男廿一為丁。六十一為老。六十六為耆。無夫者。為寡妻妾。
戶令第七目盲條:凡一目盲。兩耳聾。手無二指足無三指手足無大拇指禿瘡無發。
戶令第八老殘條:凡老殘。並為次丁。
戶令第九五家條:凡戶。皆五家相保。一人為長。以相檢察。勿造非違如有遠客來過止宿及保內之人有所行詣並語同保知。
戶令第十戶逃走條:凡戶逃走者。令五保追訪三周不獲除帳。其地還公。未還之間。五保及三等以上親。均分佃食。租調代輸。戶內口逃者。同戶代輸。地準上法。
戶令十一給侍條:凡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皆先盡子孫若無子孫聽取近親無近親外取白丁若欲取同家中男者。並聽。郡領以下官人。數加巡察若供侍不如法者。數隨便推決。其篤疾十歲以下。有二等以上親者。
戶令十二聽養條:凡無子者。聽養四等以上親於昭穆合者即經本屬除附。
 《養老令》對象
《養老令》對象戶令十三為戶條:凡戶內欲折出口為靄戶者。非成中男及寡妻妾者。並不合折。應分者。不用此令。
戶令十四新付條:凡新附戶。皆取保證本問元由知非逃亡詐冒然後聽之。其先有兩貫者。從本國為定。唯大宰部內。及三越。陸奧。石城。石背等國者。從見住為定。若有兩貫者。從先貫為定。其於法不合分折而因失鄉分貫。應合戶者。亦加之。
戶令十五居狹條:凡戶居狹鄉有樂遷就寬不出國境者。於本郡申牒。當國處分。若出國堺申官待報。於閒月國郡領送。付領訖。各申官。
戶令十六沒落外蕃條:凡沒落外蕃得還。及化外人歸化者。所在國郡。給衣糧具狀發飛驛申奏。化外人。於寬國附貫安置。沒落人依舊貫無舊貫任於近親附貫。並給糧遞送。使達前所。
戶令十七絕貫條:凡浮逃絕貫。及家人奴婢。被放為良。若訴良得免者。並於所在附貫。若欲還本屬者聽。
戶令十八造計帳條:凡造計帳每年六月三十日以前。京國官司。責所部手實具注家口年紀若全戶不在鄉者。即依舊籍轉寫。並顯不在所由收訖。依式造帳。連署。八月三十日以前。申送太政官。
戶令十九造戶籍條:凡戶籍。六年一造。起十一月上旬依式勘造。里別為巻。惣寫三通其縫皆注其國其郡其里其年籍五月三十日內訖。二通申送太政官一通留國。所須紙筆等調度。皆出當戶國司勘量所須多少臨時斟酌。不得侵損百牲其籍至官。並即先納後勘。若有增減隱沒不同隨狀下推。國承錯失即於省籍具注事由國亦注帳籍。
 《養老令》名冊
《養老令》名冊戶令二十造帳籍條:凡戶口。當造帳籍之次計年。將入丁老疾應徵免課役及給靄侍者。皆國司親貌形狀以為定簿。一定以後。不須更貌若疑有奸欺者。亦隨事貌定。以附帳籍。
戶令二十一籍送條:凡籍。應送太政官者。附當國調使送。若調不入京。專使送之。
戶令二十二戶籍條:凡戶籍。恆留五比其遠年者。恆留五比其遠年者。依次除。
戶令二十三應分條:凡應分者。家人。奴婢。田宅。資財。摠計作法。唯入男女摠計作法。嫡母。繼母。及嫡子。各二分。庶子一分。妻家所得。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承夫分。證據灼然者。不用此令。
戶令二十四聽婚嫁條:凡男年十五。戶令廿四聽婚嫁條: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女年十三以上。聽婚嫁。聽婚嫁。
戶令二十五嫁女條:凡嫁女。皆先由祖父母。父母。伯叔父姑。兄弟。外祖父母次及舅從母。從父兄弟若舅從母。從父兄弟。不同居共財及無此親者。並任女所霖欲。為婚主。
戶令二十六結婚條:凡結婚已定。無故三月不成。及逃亡一月不還。若沒落外蕃一年不還。及犯徒罪以上女家欲離者。聽之。雖已成其夫沒落外蕃有子五年。無子三年不歸。及逃亡。有子三年。無子二年不出者。並聽改嫁。
戶令二十七先奸條:凡先奸。後娶為妻妾雖會赦。猶離之。
戶令二十八七出條:凡棄妻。須有七出之狀一無子。二淫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妒忌。七惡疾。皆夫手書棄之。與尊屬近親同署。若不解書。畫指為記。妻雖有棄狀有三不霖去。一經持舅姑之喪二娶時賤後貴。三有所受無所歸。即犯義絕。淫隸。惡疾不拘此令。
戶令二十九先由條:凡棄妻。先由祖父母父母若無祖父母父母夫得自由皆還其所霆見在之財若將婢有子。亦還之。
戶令三十嫁女棄妻條:凡嫁女棄妻。不由所由皆不成婚。不成棄。所由後知。滿三月不理。皆不得更論。
戶令三十一殺妻祖父母條:凡毆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殺妻外祖父母。伯叔父姑。兄弟姊妹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姑。兄弟姊妹。自相殺。及妻毆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殺傷夫外祖父母。伯叔父姑。兄弟姊妹及欲害夫者。雖會赦。皆為義絕。
戶令三十二鰥寡條:凡鰥寡。孤獨。貧窮。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親收養若無近親付坊里安隸如在路病患。不能自勝者。當界郡司。收付村里安養。仍加醫療並勘問所由具注貫屬患損之日。移送前所。
 《天聖令》
《天聖令》戶令三十三國守巡行條:凡國守。每年一巡行屬郡觀風俗問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霰百姓所患苦敦喩五教勸務農功部內有好學。篤道。孝悌。忠信。清白。異行。發聞於鄉閭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悌。悖禮。亂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縄之。其郡境內。田疇辟。產業修。禮教設。禁令行者。為郡領之能入其境人窮遺。農事荒。奸盜起。獄訟繁者。為郡領之不若郡司在官公廉。不及私計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必謹而察之。其情在貧穢諂諛求名。公節無聞。而私門日益者。亦謹而察之。其政績能不。及霾跡善惡。皆錄入考狀以為褒貶即事有侵害不可待至考者。隨事糾推。
戶令三十四國郡司條:凡國郡司。須向所部檢校霽者。不得受百姓迎送妨廢產業及受供給致靄令煩擾。
戶令三十五當色為婚條:凡陵戶。官戶。家人。公私奴婢。皆當色為婚。
戶令三十六造官戶籍條:凡官戶奴婢。每年正月。本司色別。各造籍二通一通送太政官一通留本司有工能者。色別具注。
戶令三十七良人家人條:凡良人及家人。被壓略充賤。配奴婢而生男女者。後訴得免。所生男女。並從良人及家人。
戶令三十八官奴婢條:凡官奴婢。年六十六以上。及癈疾。若被配沒令為戶者。並為官戶至年七十六以上並放為良。
戶令三十九放家人奴婢為良及家人條:凡放家人奴婢為良及家人者。仍經本屬申牒除附。
戶令四十家人所生條:凡家人所生子孫。相承為家人皆任本主驅使。唯不得盡頭驅使。及賣買。
戶令四十一官戶自拔條:凡官戶。家人。公私奴婢。被抄略沒在外蕃自拔得還者。皆放為良。非抄略及背主入蕃。後得歸者。各還官主。
戶令四十二為夫妻條:凡官戶。陵戶。家人。公私奴婢。與良人為夫妻所生男女。不知情者。從良。皆離之其逃亡所生男女。皆從賤。
戶令四十三奴奸主條:凡家人奴。奸主及主五等以上親所生男女。各沒官。
戶令四十四化外奴婢條:凡化外奴婢。自來投國者。悉放為良。即附籍貫本主雖霰先來投國亦不得認。若是境外之人。先於化內充賤。其二等以上親。後來投化者。聽贖為霖良。
戶令四十五遭水旱條:凡遭水旱災蝗不熟之處。少糧應須賑給者。少糧應須賑給者。國郡檢實。預申太政官奏聞。
歷史評價
一、大化革新和日本《養老律令》的制定 《養老令》
《養老令》隨著部民制[3]的衰落,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日益加深,連聖德太子的後人山背大兄王及其一族都被反改革的蘇我入鹿逼得自殺。新舊勢力的爭鬥也激烈起來,聖德太子派到中國的留學生陸續回國,他們深受大唐王朝的影響,認為“大唐國者法式備定之珍國也,常須達”[4],渴望進行改革,引進先進文化。惠日、僧吳、南淵請安和高向玄理是他們的傑出代表,他們對大唐風物制度的傳授,在部分貴族中發生強烈影響。於是,日本漸漸出現了主張革新的新興勢力,其代表人物是中大兄皇子(公元626年—公元671年)和中臣鐮足(公元614年—公元669年)。他們決定推翻蘇我氏,奪取政權。中大兄接受中臣鐮足的建議,爭取與入鹿素有矛盾又有聲望的大夫蘇我石川麻呂,分化蘇我氏的勢力,再拉攏有實權的佐伯連子麻呂、葛木稚犬養連綱田等人,組成了革新派後,於皇極天皇4年(公元645年)發動政變消滅了蘇我氏,並很快組成新的政權,輕皇子見即位為孝德天皇(645—654在位),年號大化,首都由飛鳥遷至難波(今大坂市)。經過一番準備,大化2年(646)元旦,革新政權發布《改新之詔》,接著陸續頒布了革新措施,即為“大化革新”。
大化革新首先廢除了部民制,建立班田授受法與租庸調製。《改新之詔》載:“罷昔在天皇等所立於代之民,處處屯倉及別臣、連、伴造、國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處處田莊,”[5]變成了“公地、公民”。在此基礎上實行了班田授受法與租庸調製。根據史料推測,政府每隔6年,班給6歲以上的男子口分田2段[6],女子為男子的三分之二,奴婢為公民的三分之一。受田人死後,口分田歸公,班田農民擔負租庸調。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權制,仿照唐制,進行官制改革,對於大夫以上的貴族賜予食封,以下的給予布帛,作為俸祿。還從軍事制度和司法制度上進行了改革。
大化革新是在日本歷史上發生的一次重大變革運動,日本由此進入封建社會。 但是,革新派與守舊勢力的鬥爭卻在一直繼續著。公元645年9月,古人大兄皇子謀反被鎮壓,大化5年(649),中大兄迫使石川麻呂自盡。白維4年(653),中大兄強行率領皇族和群臣遷都回飛鳥,孝德天皇陷於孤立,第二年飲恨死去。中大兄之母前皇極天皇重登位,她大興土木,修建宮殿樓閣,給人民帶來沉重的徭役負擔,引起民怨。658年,孝德天皇之子有間皇子陰謀叛亂,被絞死在藤白坂(今和歌山縣海南市)。
中大兄為了轉移守舊勢力的鋒芒和人民民眾的不滿情緒,大舉征伐北方少數民族並出兵朝鮮。這就與唐朝的利益發生了衝突。660年,親日的百濟受新羅和唐朝軍隊的進攻,瀕臨於滅亡,向大和朝廷求援,8月,日軍與新羅、唐朝軍隊在白村江[7]交戰,道到慘敗,百濟滅亡,一直妄自尊大的日本遭受沉重打擊。668年,中大兄即位,稱天智天皇(公元668年—公元671年在位),但局勢依然動盪。他死後,大海人皇子通過“壬申之亂”奪取政權,是為天武天皇(公元673年—公元686年在位),但是他穩定了社會秩序,為繼續推進革新事業提供了基礎。
大化革新深受大唐的影響,注意制定法律,將改革的成果用法律的形式鞏固下來。事實上,在改革的同時,大化革新政府,就根據實際的需要制定了系列的簡單法令,如官制上的二官八省一台制、國郡里制、班田制、租庸調製等。新政權穩定之後,從668年始,以中臣廉足為首,參考大化以來的法令,編成22卷《近江令》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部的成文法典。681年,天武天皇以此令為基礎編成《淨御原令》的新法典。到8世紀,日本的律令建設進入了一個高潮期,701年完成了著名的《大寶律令》,這是對大化革新期間對隋唐法制諸內容全面吸收所形成的日本法制模式的充分肯定。718年,又以《大寶律令》為基礎,編撰完成了《養老律令》,它是略加修改《大寶律令》而成,包括律10卷13篇、令10卷30篇[8]。現從《令義解》和《令集解》中可見令的大部分;律,則留下一部分。《養老律令》修成後沒有立即施行,而放置39年後,於757年(天平寶字元年)實施。下面,我們將利用日本學者仁井田升《唐令拾遺》及其他一些現存材料,簡單談一下日本《養老律令》中的戶令。
二、日本的《養老戶令》
 城市養老狀況調查
城市養老狀況調查(一)“里、坊、保”等基層組織的設定
大化革新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經濟上的廢除部民制實行班田制和租用調製,這是與奴隸制下不同的剝削方式,在農民組織上,也就要求有一套較為合適的戶籍制,以方便征斂。早在天智天皇9年(公元670年),政府為防止人民逃亡,就開始編制戶籍,因制定於庚午年,故稱“庚午年籍”。《養老戶令》中,有些規定就是與此對人民的組織有關的,當時設定的基層組織有“里”、“保”、“坊”等。
在組織設定上,關於里,《日本養老戶令》第一條規定:“凡戶以五十戶為里,每里置長一人(掌檢校戶口、課植農桑,禁察非為,催 賦役),如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隨便置量。”[11]而關於“坊”的規定為第三條,“凡京,每坊置長一人,四坊置令一人(掌檢校戶口,督察奸非,催 賦役)”[12]。關於“保”,該令第九條規定,“凡戶皆五家相保,一人為長,以相檢察,勿造非為。有遠客來過宿止,及保內之人有所行詣,並語同保知。”[13]戶一般設在農村,坊一般設在“京”,當時那是首都或較大的城市。
國家設立編戶之民的目的是明確的,那就是“檢校戶口,督察奸非,催 賦役”,說穿了也就是穩定基層的社會秩序並使之有一個明確的組織,以方便國家的征斂,同時,還能夠對人民實行控制和監視,避免藏匿戶口,逃避賦稅或者避免人口流竄,以使國家有穩定的徵稅對象。每年6月“造帳”記賬申報,該令第十八條規定:“凡造計賬,每年六月卅日以前,京國官司責所部首實,具注家口年紀。若全戶不在鄉者,即以舊籍轉寫,並顯不在所由,取訖,依式營造連署,八月卅日以前,申送太政官。”[14]這種申報上計,顯然是一種較為先進的制度,而若沒有一個運作良好的基層組織,對帝國統治的最下層,國家的觸角也顯然是難以觸伸的,這自然離不了里、坊的幫助。對於編制戶籍,戶令也有著明確的規定,其第十九條:“凡戶籍,六年一造,起十一月上旬,依式勘造,里別為卷, 寫三通,其縫皆注其國其郡其里年籍,五月卅日內訖,二通申送太政官,一通留國(其雜戶陵戶籍,則更寫一桶各送本司)。所需紙筆等調度,皆出當戶。國司勘量所需多少,臨時斟酌,不得侵損百姓。其籍至官,並即先納後勘。若有增減隱沒不同,隨狀下推,國承錯失,即於省籍具注事由,國亦注帳籍。”[15]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日本對戶籍的編制仍然是以戶里為基本單位的。且,編制戶口的程式明晰、有序,儘量注意不擾民。
人民之間互相是承擔連帶責任的,一戶有了問題,其他戶就要承擔逃走戶的賦役,當然這必須滿足法定條件。《養老戶令》第十條規定:“凡戶逃走者,令五保追訪,三周(即三年)不獲除帳,其地還公;五保及三等以上親,均分佃食,租調代輸(三等以上親,謂同里居住者)。戶內口逃者,同戶代輸,六年不獲,亦除帳,地準上法。”[16]一戶逃走了,五保都得去“追訪”,追不回就要在三年之內代為負擔賦役,這穩定了國家的穩定稅源的同時,也說明了當時國家對人民的控制之嚴,並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當然,並不是說絕對地不允許人口流動,適當的人口流動,國家甚至還是鼓勵的,鼓勵的原因或者是因為增添了戶口數量,或者是由地少的地方遷到地多的地方,以促進土地的開墾和國家稅收的增加。《日本養老戶令》第十四、十五條分別規定,“凡新附戶皆取保證,本問原由,知非逃亡詐冒,然後聽之。其先有兩貫者,從本國為定,……”[17],“凡戶居狹鄉,有樂遷就寬,不出國境者,於本郡申牒,當國處分。若出國境,申官待報,於閒月國郡領送,付領訖,各申官。”[18]所以,人口流動是允許的,但是必須滿足一定的條件,並且要到法定部門履行法定的手續才行。
(二)納稅人的確定
無論任何性質之政府,都是靠納稅人來維持、生存和運作的。在生產水平還比較低的古代,特別是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社會,納稅人對國家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以此,任何古代的國家,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都會重視確定國家的稅源。對於古代的日本來說,它的納稅稅源首先應該是當時在天皇制下的人民。當時下層的勞動人民也是分階層的,國民被劃分成“良民”和“賤民”。良民包括皇族、貴族等大小統治階級和廣大公民,他們是所謂自由民。“賤民”是改新後沒有得到解放的奴隸。“賤民”包括“陵守”(守皇陵者)、“官戶”、“家人”、公奴婢、私奴婢。根據班田制的規定,公民政府那裡得到一份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的“口分田”,並取得一定數量的園田宅地。《養老律令》把公民分為九等[19],從正倉院[20]所存的奈良時代的籍帳中發現,實際上是十等[21]。其貧富也不一,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貧困戶和等外戶。公民為國家服徭役、兵役,承擔租庸調。官戶和家人的身份是相同的,只是隸屬的不同,官戶隸屬於官廳和朝廷,家人屬於貴族個人。奴婢的地位最低,他們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可以隨意被買賣,轉讓。官戶和家人以及奴婢占總人數的百分之10左右[22]。他們的地位,具體說來,官戶和家人時代相承,但不得被隨意買賣,第四十條“凡家人所生子孫,相承為家人,皆人本主 使,唯不得盡頭 使,及買賣。”[23]奴婢的地位實在太低,他們不得建立家庭,主人把他們當作財產買賣讓與。法律不準“賤民”和“良民”通婚,兩者非法所生之子,被定為“賤民”。但《養老律令》中卻有奴婢授田的記載,“凡官戶奴婢口分田,與良人同。家人奴婢,隨鄉寬狹,並給三分之一”[24](不過,這種土地的所有權可能是屬於其主人的),且符合一定條件,也是可以變為公民的。法律規定,賤民到了高齡,或主戶斷嗣時,可獲釋為良民。此外,也有不少人因報錯戶籍為成為良民的。以後賤民越來越少,到了延喜年間,法律宣布廢除了賤民說法。[25]而且,釋放為良人時,條件還相當寬鬆,《養老戶令》第十七條,“凡浮逃絕貫,及家人奴婢釋放為良,若訴良得免者,並於所在附貫,若欲還本屬聽。”[26]對化外人更有特別政策,其第四十四條“凡化外奴婢,自來投國者,即附籍貫。本主雖先來投國,亦不得認。若是境外之人,先於化內充賤,其二等以上親,後來投化者,聽贖為良。”[27]不過,法定手續還是要履行的,其第三十九條,“凡放家人奴婢為良及家人者,仍經本屬申牒除附。”[28]而不一定是賤民的人來歸附,那條件更優厚了,其第十六條規定曰:“凡沒落外藩得還,及化外人歸化者,所在國郡給衣糧,具狀發飛驛申奏。化外人於寬國附貫安置,沒落人以舊貫,無舊貫任於近親附貫,並給糧,遞送使達前所。”[29]糧食都送到家門口了,不能不說是有優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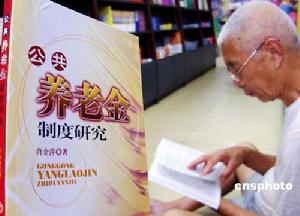 養老金
養老金(三)婚姻
根據日本養老戶令的規定,男女的法定結婚年齡分別是15和13,其第二十四條規定,“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聽婚嫁。 ”[33]但是,婚嫁的男女,特別是女子,對自己的婚姻確是沒有選擇權的,而是由父母、叔伯甚至兄弟等等人來決定,其第二十五條規定,“凡嫁女,皆先由祖父母、父母、伯叔父姑、兄弟、外祖父母,次及舅、從母、從父兄弟,若舅從母從父兄弟,不同居共財,及無此親者,並任女所欲為婚主。”[34]連不是親的的兄弟都能決定女子的婚姻,則那時女子之無權由此可見一斑,只是當他們較為疏遠且不同居共財的情況下,才輪得到女子自己做主。而且,婚姻關係也要服從等級制度,有些賤民只能自相通婚,而不得與“良民”通婚,當然更不可能與貴族通婚了。其第三十五條規定:“凡陵戶官戶家人、公私奴婢,皆當色為婚。”[35]
結婚根據規定,當履行一定的手續,和中國一樣也有“納采”、“納徵”等步驟,但不同的是,中國實行一夫一妻制,而日本則盛行一夫多妻制。而且,法律對女子多有限制,卻不見對男子的限制。男人幾乎可以隨意拋棄妻子,法定的離婚事由有七條,稱為“七出之條”,《養老戶令》第二十八條規定,“凡棄妻,須有七出之狀,一無子,二淫 ,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妒忌,七惡疾,皆夫手書棄之,於尊屬近親同署。若不解書,畫指為記。雖有棄狀,有三不去,一經持舅姑之喪,二娶時賤後貴,三有所受無所歸,即犯義絕淫 惡疾,不拘此令。”[36]雖然有象徵保護婦女權利的“三不去”之說,但我們相信,男人只要想拋棄一個女人,他總會找到辦法的,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出,這條令的規定受到了唐令的巨大影響,所有的離婚原因里,沒有一條跟夫妻感情有關。除了七出之條外,“義絕”也是離婚的法定原因, 《戶令》云:“毆妻之祖父母,父母,即殺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故,兄弟姊妹,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姑兄弟姊妹自相毆,及妻毆言夫之祖父母父母,毆傷夫外祖父母、伯叔、父姑、兄弟、姊妹,及欲害夫者,雖會赦,皆為義絕。”[37]而《法曹至要抄》引戶婚律云:“犯義絕者,離之;違者,杖一百。”[38]犯了“義絕”是必須離婚的,不離婚還會受到法律的制裁[39]。據該令的規定,還有其他可能導致解除婚姻的法定條件,有的還體現了對婦女權益一定成程度上的保護,如第二十六條規定:“凡結婚已定,無故三月不成,及逃亡一月不還,若沒落外藩一年不還,及犯徒罪以上,女家欲離者聽之。雖已成,其夫沒落外藩,有子五年、無子三年不歸;及逃亡,有子三年,無子二年不出者,並聽改嫁。”[40]還有一個法定的必須解除婚姻的規定是因為婚姻前男子對女子有過強姦等暴力性行為,《養老戶令》第二十七條規定:“凡先奸後娶為妻妾,雖會赦猶離之。”。[41]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
《養老戶令》中,還有關於對官吏進行要求的具有行政法性質的法律,第三十三條云:
凡國守,每年一巡行屬郡,觀風俗,問百年,錄囚徒,理冤獄,祥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敦欲五教,觀務農工。部內有好學篤道,孝悌忠信,清白異行,發聞於鄉閭者,舉而進之。又不孝悌,悖理亂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繩之。其郡境內,田疇辟,產業修,禮教設,禁令行者,為郡領之能;入其境,人窮匱,農事荒,奸盜起,獄訟繁者,為郡領之不。若郡領在官公廉,不及私計,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必謹而察之。其政績能不,及景跡善惡,皆錄入考功,以為褒貶。即事有侵害,不可待至考者,隨事糾推。
這已經是對官吏較為全面的要求了,首先需要官吏自己有著較高的道德修養和一定的行政能力。具體說來,要他每年都要“下基層”實地考察,平冤獄,正民風,體驗百姓的疾苦,為他們服務,對於民間的人才,要善於發現和舉薦。對官吏的評判考核也有規定,並把對官員的要求納入這些考核範圍之內,優秀者升賞,不合格的有制裁措施。即使以我們今天的標準來看,這種制度雖然存在諸多漏病和不好操作之處,但已經是相當完善和進步的了。
三、餘論:《養老律令》與中國法律
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至少在公元前21世紀左右的夏朝已經建立了國家,形成了法制。中華法制不僅起源早,而且經過四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一直沒有中斷過,這是在世界文明古國中所僅有的。因此中國法制的歷史沿革非常清晰,無論是某一部法典,還是某一項制度,都有清楚的源流關係,形成了一個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統。中國古代法制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特色鮮明的傳統,而與世界其它法系相區別。這種特殊性,也正是中華法系的典型性。[42]偉大而獨特的中華法系對世界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特別是對古代的東亞及東南亞地區,在有些國家,法律作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對這些國家的法律制度幾乎有著支配性的影響,典型的如朝鮮、越南、琉球等國家和地區。同樣,我國的法律制度文化,對日本也有著巨大的影響。近世日本學者桑原騭藏博士於1929年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第二十四夏季講演會所講演《中國古代之法律》即有云:
……(日本)自奈良時代至平安朝吾國(指日本而言)王朝時代之法律,無論形式上與精神上,皆根據《唐律》。自德川時代至明治十三年頃為止,所謂日本之法律者,直接間接受明律之影響[43]。
楊鴻烈先生讚譽日本是最擅長學習之民族,他把日本對中國法律的借鑑和學習分為兩個大的時期。第一是模仿“唐律令”之時代,可謂屬於“唐律令”之系統者,具體說來,表現在天智天皇時代之《近江令》,文武天皇時之《大寶律令》,元正天皇時《養老律令》,以至醍醐天皇時之《延喜格式》。第二期是模仿《明律》以及《會典》之時代,屬於《大明律》之系統。其典型者有武家時代末期藩侯所撰法條以及明治維新時之《假刑律》(即《暫行刑律》)、《新律綱領》及《改定律例》等[44]。而日本受中國影響雖久,但真正受到刺激,全面向中國學習引進中國文化和典章制度則是在我國唐時,特別表現在大化革新之後。法律制度上自然也是如此,604年,聖德太子即斟酌隋朝之制,定《憲章》17條,這成為日本成文法之濫觴。接著《近江令》、《大寶律令》、《養老律令》至《延喜格式》等等,使得日本的法律文化也蔚為大觀,但是,這時期所有日本律令中,都閃爍著中華文化的影子。箇中原因,我們已經在前有過論述,楊鴻烈先生所引宮琦道三郎《論律令》一文,在論述《大寶律令》、《養老律令》時有言曰:
《大寶養老律令》者,我日本之法典,與人民之休戚有密接之關係者也,而取法於中國,抑何故也?也豈只羨慕當時中國制度之完整而摹仿之乎?曰實尚有其他原因,蓋當時日本之種種制度,皆有改良之必要,尤以“世職”及“兵制”為甚。此外則唐代武力日盛,朝鮮之日本實力減退,形勢亦甚迫切,加以中國文化又陸續輸入,故日本人心大受刺激,留學中國者有主張移植唐制於日本,《推古記》三十一年有云:“大堂學問僧惠齊、惠光、及醫惠日、福因等並從智洗爾等來之,於是惠日等共奏聞曰:留於唐國學者,皆學以成業,應喚,其大唐國者法式備定,珍國也,常需達。”於是遂決意編纂法典。[45]
宮琦此說,雖然著力強調日本進行變革,編撰法典的原因,是由於其國內的形勢所需,但唐代法律文化對日本律令制度的影響還是很明顯地被透漏出來。無論是形勢的需要,即白村江之戰日本的潰敗所對其國人所造成的刺激,還是國內新舊勢力的爭鬥,都或與大唐德武力有關或與大唐的文治有關。日本當時對大唐文明的羨慕和引進的熱切心態,也由此可見一斑。而大化革新的成功,又為日本仿唐制制定律令提供了需求和社會政治基礎。因此,日本在唐代能派遣高達近20次的“遣唐使”,去學習大唐的先進文化,制定律令使大量吸引唐律的成果,以唐律為母法,也就是不足為奇的了。
早在日本天智天皇時期制定的《近江令》和天武天皇時期制定的《天武律令》便以唐貞觀前後的“令”為藍本。至於在日本法制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寶律令》無論篇目與基本內容都取法《唐律疏義》,只是作了一些刪並而已。例如,將“八議”中的“議勤”、“議賓”刪去,成為“六議”。《大寶律令》之後制定的《養老律》也同樣是如此。日本法制史學者桑原騭藏博士曾經指出:“自奈良至平安時期,吾國王朝時代之法律,無論形式上與精神上都皆依據《唐律》”。[46]穗積陳重博士在其《日本族民法》還指出,明治三年十二月頒布的《新律綱領》,“系以中國之唐明律為藍本”。[47]如果只看篇目,則篇名上《大寶律》也是分《明例》、《衛禁》等12篇,與唐律絕類,而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日本法律的篇名一直以此為基礎,與此大同小異。
以《大寶律令》《養老律令》來說,從刑法上看,在刑名上,日本法與唐律完全相同,“其刑有五,一曰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48]在刑之適用上,日本亦如唐人因人之身份異同而適用不同的法律。從刑之加重減輕來說,也與唐律大致相同,只是略有小變而已。從重刑上來說,日本之“八虐”也類似於中國的“十惡重罪”,罪在不赦,其他的很多罪名及犯罪,其內容也與唐律以大同小異。[49]甚至中國古代法律中的重視親屬等級秩序,重視宗法血緣,同居相容隱等精神,都為日本法令所吸收。從民法上看,日本法律無論是從對法律主體行為能力的規定上,還是在人民的身份上(“良民”與“賤民”的分野),以及在婚姻的成立、解除等的規定上,無不與唐律絕相類似。再從所有權上看,孝德天皇大化革新之時,鑒於前代之土地兼併,遂將全國土地收歸國有,並仿唐制分配於個人,引進了唐的班田制和租用調製。從借貸方面來看,楊鴻烈引用金澤康所作之《中國法律在日本利息法上的影響》一文,說《養老律令》雖非全體抄襲《永徽律令》,但採用之處實屬甚多。在繼承方面,在買賣上,日本律令也承襲唐律良多。[50]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律令遂承襲中國特別是唐代法律極多,但也並不是一味地不加區分地引進,而是加了區分和鑑別的,有時還有許多獨特的創造。史麗華在對日本班田令與唐代均田令進行比較時發現,日本對中國法律的引進,是分好幾種情況的:唐令中與日本國情完全適合的條文,被班田令基本上全部照搬使用;有些於日本國情不太合適的條文,他們則吸取唐令的基本原則,進行適當的增刪,以適應其實際需要;而凡有悖於日本國情的均田令令文,他們均不予吸收;當然,也有結合日本國情,經日本法學家的努力由其自身獨創的條文,而且,這類條文共有九條,占班田令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四,具體表現在:班田的年限上、關於土地的買賣上、關於公田、關於宅院地不得施捨寺院條等[51]。
而且,一般而言,日本律的刑罰比唐律的刑罰來得寬大,一般犯罪的處罰,比起唐代法令,總降一個等級處罰。楊永良先生說,特別是日本從奈良時代末期開始,就很少執行死刑。尤其是從弘仁年間(810~23)至保元年間(1156~58),有三百年的「廢除死刑」之記錄。雖然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當時的貴族迷信死亡的亡魂會來報復,所以朝廷儘量避免執行死刑,但廢除死刑的確是一種極為寬大的做法。在財產繼承法方面,唐令、大寶令、養老令之間有重大的差異。依大寶令的規定,動產的一半及其它資產的全部,由嫡子來繼承。殘餘的一半財產才由庶子間來均分。這是極端的嫡庶異分主義。而唐令中,除食封是嫡庶異分主義外,其餘採取諸子均分主義。養老令則將大寶令的規定改為:嫡母、繼母、嫡子各二分,庶子一分,女子、妾各半分。另外,從官制上來說,日本也沒有完全吸取大唐的制度,而是照顧到本國復員狹小的事實,制定了其本國的比較簡單的官制[52]。這些都反映了日本民族不僅善於學習,還善於根據本國國情,進行因地制宜地創造。
關於社會養老的名詞
| 養老 | 養老保險 | 養老金 | 養老地產 | 以房養老 | 企業補充養老保險 | 養老職業 | 養老防兒 | 空巢養老 | 養老金制度 | 養老金信託 | 個人養老保險 | 普惠式養老金 | 以房自助養老 |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 居家養老 | 養老房屋銀行 | 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 虛擬養老院 | 社會養老服務 | 基本養老保險 | 搭夥養老 | 計畫養老 | 家庭養老 | 養老券 | 合租養老 | 賴床養老 | 中國式養老 | 《養老令》 | 拼房養老 | 養老金指數 | 養老危機 | 養老送終 | 養老婿 | 妓女養老院 | 返港養老 | 養老護理員 | 養老房 | 候鳥式養老 | 子女養老社會保險金制度 | 社會化養老 | 網路養老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