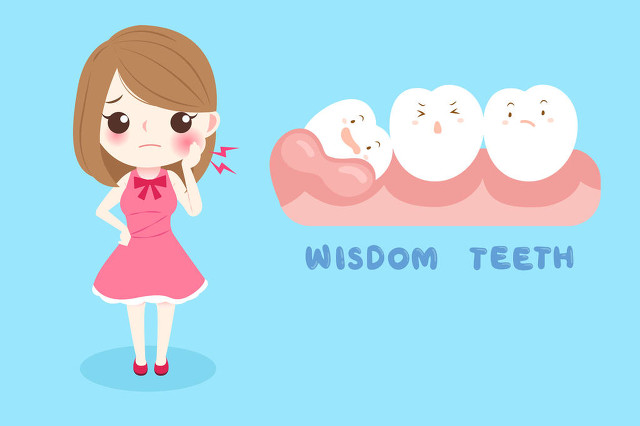阿拉伯使者帶來的禮物
罌粟原產於西亞阿拉伯半島、南亞印度等地。中國並不是罌粟的原產地,罌粟及其製品鴉片都是從國外傳入的。
罌粟及其製品的傳入始於唐代。《舊唐書》列傳載:“乾封二年(667)拂霖遣使獻底也伽。”經德國學者夏德(Friedrich)等的研究,“拂霖”就是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其中心位置約在今敘利亞。唐時,由於阿拉伯人的大舉擴張,敘利亞已成為阿拉伯帝國的一個省。
“底也伽”,古音為te ya ka,是當時西方的珍貴藥品。據阿拉伯史家記載,上等的“底也伽”產自伊拉克的巴格達。西方自古就認為,“底也伽”是療效最佳的解毒藥,它由600種物質混制而成,這種丸狀藥的作用可解除一切毒素。“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鴉片、龍涎香、縮砂、肉豆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鴉片。
從這些史料中基本可以推斷出,鴉片是古阿拉伯人傳入中國的。
唐代時,正在急速擴張中的阿拉伯帝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阿拉伯向中國派遣正式使者就達37次。古阿拉伯進入中國,主要有陸、海兩條路。陸路由著名的絲綢之路進入長安,海路則是經馬六甲海峽到達廣州、泉州、揚州等地。成書於10世紀上半葉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反映了西亞與中國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這種交流的規模即使在交通十分發達的今天看來,也令人嘆為觀止。那時在長安、廣州、泉州等地經商的阿拉伯人不下萬人。阿拉伯人帶來了象牙、棉花、白糖、寶鐵等特產,也帶來了罌粟和鴉片。
從文獻記載考證,乾封二年阿拉伯使者貢獻“底也伽”,是鴉片進入中國之最早記錄。但中國人對鴉片的認識要早於這一文獻記載。成書於唐高宗顯慶四年(659)的《唐本草》有“底也伽”一條,載:底也伽,味辜苦平無毒,主治百病中惡客忤邪氣心腹積聚,出西戎。這本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藥典的成書,比史載的阿拉伯人獻“底也伽”還要早八年,而且明確地記載了它的藥用效果。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斷:在公元7世紀的上半葉,唐朝初期,底也伽——也就是鴉片——已進入了中國。
阿拉伯人在貢獻“底也伽”的同時,也將罌粟帶到了中國。
美麗的藥物
不久,中國人就開始種植罌粟。由於罌粟花異常嬌艷,唐代人多將它作為觀賞植物。成書於唐開元時期的《本草拾遺》中記載:“罌粟花有四葉,紅白色,上有淺紅暈子,其囊形如箭頭,中有細米。”生活於唐文宗時期(826~840)的郭橐駝,也具有種植罌粟的經驗。他在《種樹書》里寫道:“鶯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種之,花必大,子必滿。”詩人雍陶在《西歸斜谷》中唱道:“行過險棧出褒斜,出盡平川似到家,萬里客愁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這裡的“鶯粟”“米囊”都是罌粟的別稱。
罌粟在傳入中國的最初數百年里,並沒有造成大的危害。這是因為當初很少有人吸食,罌粟主要還是作為觀賞花卉和藥用植物。
進入宋代後,罌粟花又稱“鼓子花”,被當作妓女的別稱。原來宋人之美學觀念尚淡雅而不喜濃艷,故將艷麗的罌粟花用來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詞人張先,晚年在杭州時“多為官妓作詞”,所以有詩曰:“天興群材十樣花,獨分顏色不堪夸。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官員王元之被謫齊安郡,見當地“民物荒涼,菅妓(宦妓)有不佳者”,便感嘆:“憶昔西都看牡丹,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裡,鼓子花開亦喜歡。”
這時,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更加深入,其種植也日益普遍。如北宋蘇頌在《圖經本草》里寫道:“罌粟花處處有之,人多蒔以為飾,花有紅白二種,微腥氣,其實形如瓶子,有米粒極細。圃人隔年糞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極繁茂,不爾則不生,生亦不茂,俟瓶焦黃乃采之。”可見宋人對罌粟的植物特徵、種植及採摘已有了一定的認識。
宋代的醫家已用罌粟來治病消災。在楊士瀛的《直指方》、王璆的《百一選方》、王碩的《易簡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醫書里,均以罌粟的殼蒴為治病妙劑。著名詞人辛棄疾曾患有疾,後遇一異僧,以陳年罌粟加人參等製成敗毒散,吞下威通丸十餘粒,此後即愈。
金元的醫家承宋朝之傳統,已普遍用罌粟主治咳嗽和瀉痢。到元初,忽必烈於1270年設廣惠司,專門製造阿拉伯藥劑。1292年,元人又設“回回藥物局”,所用之藥當然也包括罌粟。
罌粟不僅被醫家所重視,還得到了民間百姓的歡迎。人們普遍視罌粟子煮粥為大補之物。劉翰在《開寶本草》中記錄了這種習慣:“罌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發動,不下飲食,和竹瀝煮作粥,食極美。”將罌粟子稱作“御米”,一方面我們可推斷出它已進入了皇宮,另一方面也可見其珍貴。實際上,民間使用罌粟已越來越廣泛了。蘇軾有詩道:“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蘇轍在《種藥苗詩》中指出罌粟粥還可治消化不良:“……研為牛乳,烹為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缽,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調肺養胃……”所以,罌粟在宋代,竟成了醫療與食補兼而有之的物品。
但宋代人們已經認識到了罌粟的副作用。《易簡方》記載:“粟殼制痢如神,但性緊澀,多令嘔逆,故人畏而不敢服。”王碩提出抵消罌粟副作用的良方:“令醋制加以烏梅則用得其法矣。”還可與四君子藥合用,“不致閉胃妨食而獲奇功也”。元代名醫朱震亨對罌粟認識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雖急,殺人如劍,宜深戒之。” 可見元代人對罌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了解。而且我們可以從“殺人如劍”這四個字里,推測出那時社會上應已有不少因食罌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儘管宋、元時期,人們對罌粟的醫學功用已相當了解,但那時尚無“鴉片”之稱,也還不懂得鴉片的製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間,才有了製作鴉片的記載。
明代醫家王璽在《醫林集要》中記載:“鴉片治久痢不止,罌粟花花謝結殼後三五日,午後於殼上,用大針刺開外面青皮十餘處,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內,陰乾,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溫水化下,忌蔥蒜姜水,如熱渴以蜜水解之。” 他採集生鴉片的記錄相當詳細,是中國有關鴉片製作的最早記載。王璽曾任甘肅總督達二十餘年,在那裡,他有可能長期與穆斯林接觸,從他們那裡了解到了阿拉伯的物產、醫術、習俗等。其後有名醫李梴的《醫學入門》,書中寫道:“鴉片一名阿芙蓉,即罌粟花未開時,用針刺十數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內,待積取多了,以紙封固,曬二至七日,即成鴉片矣,薴急可多用。”從這兩則記錄可以判斷,那時的醫家已懂得熟練採取罌粟之液,製成鴉片,配作藥劑了。
阿芙蓉一詞是從阿拉伯語Afyun音譯而來的,而鴉片一詞的直接來源,則是英語Opium,其同義詞還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別稱。最常用的是鴉片一詞。另外,罌粟的別稱還有藕賓和蒼玉粟等。
明代人對鴉片醫學作用的認識,已達到相當的高度。根據醫學大師李時珍的調查和實踐,鴉片可以用來治療各種瀉痢、風癱、百節病、正頭風、痰喘、久咳、勞咳、吐瀉、禁口痢、熱痛、臍下痛、小腸氣、膀胱氣、血氣痛、脅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兒慢脾風等二十餘種病痛。另外,李時珍已記載了鴉片對性功能的作用,他指出,鴉片“能澀丈夫精氣”,因此“俗人房中術用之”。
綜上所述,中國人知道罌粟至少已有1300年的歷史,懂得罌粟的藥用價值已有900多年的歷史,而製作鴉片業已有500多年的歷史了。
從《本草綱目》來看,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仍局限於藥用的範圍內,鴉片製成,尚沒有流變為癮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術用之”的事實,已明確無誤地表明,時人已懂得鴉片對性功能的作用,並且藉助它的藥力來縱慾了。從中我們已可窺見明代社會衍變中的風氣了。
毒品風靡
元初,蒙古人遠征印度。那時的印度已盛產鴉片,因此蒙古人得勝而返時,也帶回了大量戰利品——鴉片。一時,“士農工賈無不嗜者”。這可能是中國社會流行服食鴉片最早的成文記錄。
明代時期,儘管中國人已懂得從罌粟割乳漿中製取鴉片,但主要來源仍采自國外。當時的東南亞一帶,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導,多種植罌粟。《明會典》載:暹羅、爪哇、榜葛剌等地多產烏香,即鴉片。他們時常將“烏香”,即鴉片作為貢品獻給中國皇帝。據史書記載,暹羅國曾進貢給中國皇帝200斤“烏香”,給皇后100斤。直到民國時,有些地方仍稱鴉片為“烏香”。
由於進口的“烏香”急劇增加,明政府已將它列入納稅之藥物。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鴉片首次被列入關稅貨物的範圍。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頒布的《貨物抽稅現行則例》中規定:每10斤鴉片的稅銀為一錢七分三厘。隨著鴉片輸入的增多,民間漸漸出現了吃鴉片者。明成化年間,已有街市上販賣鴉片的記載了。到了正德年間,在廣東、福建沿海,當地富紳、地主食用鴉片已屢見不鮮。
鴉片是一種成癮物品,一旦成為社會供應物,其需求量必急速上升,故隨著食用人數的增多,鴉片的價格也直線上漲。有時因需求太大,價格奇貴,竟至於一兩黃金換取一兩鴉片。明代後期,不僅民間食用鴉片日眾,而且在京城與宮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續紺珠集》記載,鄭和之徒弟自西洋攜回“碗藥”,當時中貴多嗜之。這“碗藥”,就是鴉片。
鴉片特有的醉生夢死、飄飄欲仙的舒暢感,令朝廷貴族為之傾倒,甚至連皇帝也不能倖免。徐伯齡的《蟑精雋》曾記載,明憲宗曾令臣下出而收買鴉片,而明神宗就是一個 “鴉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長年不視朝政,戶部主事董漢儒說:“(萬曆皇帝)頻年深宮,群臣罕能窺其面。”究其原因,乃是“中烏香之毒”。由於長期吸毒,體質變壞,明神宗經常頒諭旨說:“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因吸食鴉片,他的性格也變得殘酷暴虐。而史家許熙重則把皇帝吃鴉片的責任推到奸臣身上。他在《神宗大事紀要》中指出:“帝之倦於正朝,多年不見臣工。實為奸臣毒藥所蠱。”究竟是神宗自己求取,還是“奸臣”有意用毒,尚待研究。但神宗是個鴉片癮者,應是不爭之事實。
再說清代的罌粟種植。由於清中期以後,各地民眾已知罌粟果制鴉片之法,因此,為生產鴉片而種植的罌粟,便在各地普及開來。
到了清代,罌粟主要通過海、陸兩條途徑流入各地。海路由東南亞諸地傳至台灣、福建。福建最早種植罌粟的,大約是福寧府的福安縣。在嘉慶年間,那裡的罌粟花已經盛開了。此後,又由福建傳入浙江。浙江的土壤顯然比福建的土壤更適合罌粟的生長。道光初期,浙江各地幾乎已是遍地罌粟了。1830年,御史邵正笏指出:“浙江如台州府屬,種者最多;寧波、紹興、嚴州、溫州等府次之。有台漿、葵漿名目,均與外洋鴉片煙無異,大夥小販到處分銷。”同樣,在安徽,“徽州寧國、廣德等屬,毗連江浙,山地居多,恐有外來棚戶串通該處業戶,私種分肥”。
陸路由印度經東南亞、緬甸傳入雲南。較早記載雲南種植罌粟的,是乾隆元年(1736)出版的《雲南府志》。雲南天熱多雨,是栽培罌粟的理想地,因此“滇省沿邊夷民向有私種罌粟”。該地出產的“雲土”(又稱“南土”)在土煙中為上品,產量也急劇增加。1839年,雲貴總督伊里布在一篇奏稿中提到,一次就緝獲煙土1.2萬兩。
雲南的罌粟很快傳入四川,至遲在道光元年(1821)時,涪陵一帶的農民已棄糧種煙了。所產人稱“川土”,據史料載:“川省五方雜處,間有吸食鴉片煙之人,會理州、平武縣一帶,毗連番界,尚有種植罌粟花處所。”從此不僅“川土見盛”,而且四川還成為罌粟傳播的中轉站。
罌粟由四川傳入貴州,在道光十一年(1831)時,貴州“尚無栽種熬煙之事”。但四年後,已有種、吸鴉片和開設煙館的記載了。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已是“遍載罌粟,熬煉成土”了。貴州巡撫賀長齡奏稱:“黔省民、苗雜處,多有栽種罌粟熬膏售賣之事……現據郎岱、普定、清鎮、貴築等廳縣先後查明民、苗私種者,或數畝、十數畝不等。此外,各州縣地方栽種牟利者,尚不知有幾。”
道光年間,罌粟的種植從四川北上傳入甘肅、陝西、山西等地。這樣一來,僅僅一二十年間,這一廣泛區域的農民“廢田而種罌粟,歲益浸廣”。
土煙泛濫的原因,除了民眾趨利之外,還有地方官吏的慫恿。在洋菸開始充斥之時,清政府內就有人提出以土煙來抵制洋菸的主張。道光十四年(1834),兩廣總督盧坤指出種煙的理由:“應弛內地栽種罌粟之禁,使吸菸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信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以土煙之利奪洋菸之利;也有人說:“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其利十倍於種稻”;又有人說:“鴉片之利,數倍於麥,其益農者大矣”;甚至還有人認為“內地之種越多,夷人之利日減……不禁而絕”。
由於持以土煙抵制洋菸觀點的官員不在少數,因此,儘管清政府有禁止內地種植罌粟的政策,如較早的道光三年(1823)吏、兵兩部奏請酌定失察鴉片條例,要求禁止“私種罌粟煎熬煙膏”。此後,御史郭柏蔭奏請嚴禁栽種罌粟一折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番舶不通之處,皆由內地民田遍載罌粟,熬煉成土,地利、民生兩受其害。必當嚴申例禁,以除積習。”
但對於清廷三令五申的拔苗禁菸令,不少地方官吏卻持陽奉陰違的態度。他們在許多文告中,將鴉片改稱為罌粟花,將煙膏改稱為芙蓉膏,以表示有別於外國的鴉片。其結果,在1831年時,罌粟種植擴展到廣東、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煙與洋菸並行,加之土煙價廉,因此各地煙毒與日俱增。鴉片的泛濫,最終使中國蒙受恥辱,成為近代“東亞病夫”的象徵。
鴉片 罌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