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伽達默爾出生於德國馬爾堡,他的父親是一個研究化學的大學教授,從小就有意識地培養伽達默爾對自然科學的興趣,但伽達默爾對人文學科的興趣卻與日俱增。中學時期他就讀於弗羅茨瓦夫的一所中學,19歲時全家回到他的出生地、新康德主義的中心:馬爾堡。他在這裡師從那托普(Paul Natorp)學習哲學,1922年,以《論柏拉圖對話中欲望的本質》一文獲得博士學位。
1923年,他前往弗萊堡師從海德格爾這位他心目中的大師。他在弗萊堡只呆了幾個月的時間,但對他一生造成了深遠影響,以至於他後來一直承認自己是海德格爾的學生。從海德格爾那裡,他學習了現象學的方法、存在論的思路,使他擺脫了早期新康德主義的影響。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1929年,伽達默爾獲得馬爾堡大學的任教資格,30年代早期,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演講上。雖然在第三帝國時期,他在政治上並不活躍,但和海德格爾不同,他是堅決的反納粹主義者。直到1937年,他才獲得他申請了10年之久的哲學教授頭銜,1939年,他在萊比錫獲得了一個大學教授的職位,1945年,任哲學系主任,之後還擔任了兩年大學校長職務。在這些年裡,因為政務繁忙,大多數時間只能用於詩歌和短論的寫作中。
1947年,伽達默爾受聘於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系首席教授,1949年,受聘于海德堡大學,接替了雅斯貝爾斯的職位。直到1960年60歲時,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作品《真理與方法》。之後的40年中,他出版了其他主要著作,與各種思潮的主要人物展開對話,進行諸多演講和討論,獲得諸多榮譽。直到他去世為止,一直是海德堡大學的榮休教授。
大事件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著作《存在與時間》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著作《存在與時間》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1900年出生於德國馬堡這個閒靜的大學城,父親是專門研究藥物的化學家,由於父親在布雷斯勞大學任教,伽達默爾也在那裡度過了少年時代。
1914年一戰爆發,這個城市卻是異常的平靜;
1918年春他進入布雷斯勞大學大學。那年秋天發生革命,德意志帝國崩潰;
1919年春為學“哲學”而轉入馬堡大學,並參加了當時剛剛創立的“弗萊堡現象學會”;
1922年被授予博士學位,年僅22歲;
1923年遇到海德格爾,受到巨大影響,並從此走上了“海德格爾”的道路;
1927年海德格爾出版《存在與時間》,並讓伽達默爾提交教職資格申請論文,並獲得教職資格;
1933年希特勒上台執政,海德格爾作為弗萊堡大學的校長參加納粹黨,對伽達默爾衝擊極大,並因有與猶太人交往的經歷而被視為“政治上信不過的人”,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日子;
1938年轉投萊比錫大學,結束了在馬堡二十年的生活;
1939年二戰爆發直到1945年柏林淪陷,伽達默爾在“殘存的房子裡點著蠟燭繼續上課”。戰爭結束後,原為學部長的伽達默爾被選為新校長,忙於重建萊比錫大學;
1947年來到法蘭克福大學,在職兩年期間為逃亡美國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復職做了大量工作,併合作重建了社會研究所,以其為中心形成了“法蘭克福學派”;
1949年,作為雅斯貝爾斯的後任,伽達默爾來到了海德堡大學,在那裡他完成了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真理與方法》,歷時九年;
1968年從大學退休,但直到1975年,他一直在進行非正式的講課;
2002年3月13日下午3時30分左右因心臟病突發而逝世,享年102歲。
代表著
 著作《真理與方法》
著作《真理與方法》《真理與方法》(1960)、《柏拉圖的辯證法、論理學及其他》(1931)、《柏拉圖和詩人》 (1934)、《歌德與哲學》(1947)、《柏拉圖七封信中的辯證法和詭辯》 (1964)、《短篇著作集》(四卷,1967—1977)、《美學與詮釋學》(1964)、《黑格爾的辯證法》(1971)、《你是誰?我是誰?》 (1973)、《科學時代的理性》(1976)、《學習哲學的年代》(1977)、《美的現實性》 (1977)、《詩學》(1977)、《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善的觀念》(1978)、《黑格爾的遺產》(1979)、《海德格爾的道路》 (1983)、《讚美理論》(1983)、《歐洲的遺產》 (1989)、《關於健康的秘密》(1993)等。
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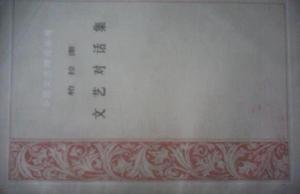 柏拉圖的對話理論
柏拉圖的對話理論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是位非常重視傳統的哲學家,成了20世紀西方哲學家傳統的化身。在伽達默爾看來,傳統是需要通過活生生的詮釋活動來延續和更新的。
伽達默爾的哲學體系中有三塊重要基石:即柏拉圖的對話理論、黑格爾的絕對觀念的辯證法和海德格爾的立於“此在”即人的存在的本體論。這三者的融合,使伽達默爾的詮釋學展現出了獨特的風貌,它的基礎就是實踐(Praxis)。質言之,就是直接追溯到人們最原初的生活經驗、而不是在純粹的思辨領域中來構建自己的哲學體系。他的哲學的生命力就在於此。在《真理與方法》中,他選擇了藝術的經驗作為突破口,試圖從藝術經驗出發,來理解超越了我們的意願和行為而對我們所發生的東西,理解超出方法論自我意識之外的真正的精神科學。
伽達默爾確實沒有像施萊爾馬赫和貝蒂那樣提供一套可以操作的詮釋方法論規則。這或許正是伽達默爾的獨特之處,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他的研究目的是要揭示所有的理解方式所共有的東西。他所真正關心的是哲學問題,是對一切方法論基礎的反思。在這方面,伽達默爾懷著與狄爾泰幾乎相同的使命感:反對在近現代科學研究中形成的占統治地位的方法論理想。他力圖證明精神科學的理解現象之優越性,“在現代科學的範圍內抵制對科學方法的萬能要求”。也不是依靠建立完善的精神科學方法論所能解決的。為此,伽達默爾不懈地探尋超越科學方法論作用範圍的對真理的經驗,專注於理解現象,在科學方法無能為力的地方,奠定了理解的基礎。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現代科學自身的內在發展規律、科學的方法論就由此而變得不重要了,也不是說,人文科學的研究根本就不需要按照一定的方法進行;《真理與方法》的主旨須在這個意義上來理解,即這裡所展開的問題本質上就不是方法之爭,而是關涉對“真理的經驗”,而不是理解的方法論。在他看來,詮釋學現象本來就不是一個方法問題。
從伽達默爾詮釋學中,看到了不同於理性主義傳統的另一個傳統,即在古代希臘已開始倡導的“實踐智慧”(Phronesis),亦即“另一種類型認識”——實踐理性——的德行。伽達默爾一生都在追求著這樣一種智慧。這可以從他收入在《詮釋學的構想》(1998年出版)一書的幾篇文章中看出。在談論“友誼”時,伽達默爾通過對“友誼”的分類描述,指出人們只能經歷友誼,卻無法給出它的定義。理解友誼就是一種生命的體驗與智慧。相信可以在這裡找到東、西方思維方式交融的真正契合點。眾所周知,自孔子與老子以來的中國思維傳統,恰恰是沿著這一方向發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