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清商樂-樂器
清商樂-樂器起源
關於清商樂的來源,有兩種說法:一是源於古代的商歌,《淮南子·修務訓》高誘註:“清,商也;濁,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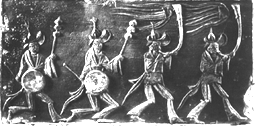 清商樂
清商樂發展
東晉以後的200多年間,除東晉末和梁末的兩次大戰亂外,南方社會穩定,經濟有顯著發展,形成了眾多的商業都市。在城市裡,漢代以來的相和舊曲將近一半已經散佚,而南方的民間謠謳──吳聲、西曲,由於城市各階層人士的喜愛而日益興盛。吳聲、西曲的流行,也引起了宮廷的興趣。尤其是梁武帝和陳後主,曾命樂工譜寫了大量新曲。北魏孝文帝時,南方的清商樂傳到了北方,在宮廷中作為“華夏正聲”受到較大的重視。此後,清商樂就成為盛行於中國南北方的重要樂種。
漢魏西晉時代的清商樂舞是女樂歌舞,如東漢張衡在《西京賦》中描寫道:“促中堂之狹坐,羽觴行而無算。秘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艷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贏形,似不任羅綺,嚼清商而卻轉,增嬋娟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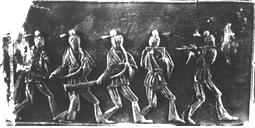 清商樂
清商樂漢魏和西晉,清商樂舞由於得到皇室的重視,日益發展,但在永嘉之亂(307~312)中,清商署的樂工舞人大部分流散。永嘉之亂後,一部分清商樂傳入涼州,與龜茲樂相結合,成為西涼樂。另一部分清商樂隨著東晉政權傳到江南,促進了長江流域民間樂舞吳聲、西曲等的發展,產生了南朝的“新聲”。正如《舊唐書·音樂志》所說:“永嘉之亂,王都淪覆,遺聲舊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為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這裡所謂新聲,在《樂府詩集》的清商曲辭中分為3類:①吳聲歌曲,以歌為主,也有一部分是歌舞,如《前溪》舞
 五代《卓歇圖》
五代《卓歇圖》隋及唐初,清商樂舞繼續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又得到一定的發展。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平陳,獲宋、齊舊樂,文帝聽了,很欣賞清商樂,說:“此華夏正聲也。”並把它置於清商署中,進行了一番“去其哀怨,考而補之”的整理工作。其中舞曲有《明君》等。隋文帝還設七部樂,內有《清商伎》,是重要的舞蹈內容。隋文帝大業(605~618)中,又制定九部樂,《清樂》(即清商樂舞)居於首部。唐高祖武德初年間,繼承了隋代的九部樂制,到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增為十部樂,《清樂》居第二部。到唐武則天時(648~704),《清樂》尚存《白雪》、《公莫舞》、《巴渝》(舞)、《明君》(歌舞)等63曲。
組成
由相和歌發展起來的清商樂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權的重視,設定清商署。兩晉之交的戰亂,使清商樂流入南方,與南方的吳歌、西曲融合。
吳聲、西曲:吳聲原是建康(今江蘇南京)一帶的民間徒歌,西曲則是荊、郢、樊、鄧地區(今湖北)的民間徒歌。兩者的風格雖較柔婉抒情,但由於語言、風俗習慣等差異,各具不同的特色。現存吳聲大都為晉宋時所作歌詞,載《宋書?樂志》、《樂府詩集》等書,計有《子夜歌》《華山畿》、《歡聞歌》、《阿子歌》、《前溪》等十幾曲,內容多半用婦女的口吻描寫愛情的歡樂、相思的痛苦,或婚姻不自由的苦悶。此外,還有民間的祀神曲《神
 唐李壽墓樂舞壁畫(殘)
唐李壽墓樂舞壁畫(殘)文獻記載,吳聲、西曲的曲調頗為動聽。所謂“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可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大子夜歌》)就說明了這一點。由於人們喜愛,有些樂曲不斷變化、發展,從而形成了同一曲調的眾多變體。如吳聲《子夜歌》就有《大子夜歌》、《子夜四時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 4種。有的利用某一曲的素材另譜新曲,如西曲《莫愁樂》就是用《石城樂》的和聲“忘愁”的曲調發展而成的;《採桑度》則是用《三洲曲》的素材寫成。
吳聲、西曲一般分為歌曲與舞曲兩類。吳聲的歌曲有《子夜》《鳳將雛》等,舞曲有《前溪》、《阿子》、《團扇》、《歡聞》等。兩者一般由1 首或多首五言四句短詩組成的唱段構成。在每首短詩之後有一段“送聲”,簡稱為“送”。有時除曲尾的送聲外,在曲中兩句歌詞之末也可用送聲,這種送聲可能就是後世民間樂曲中常用的合尾的早期形式。吳聲中有一種變歌或變曲的稱謂,如《子夜警歌》、《長史變》等。它不用送聲,而有“變頭”變化。所謂變頭,可能是每一首短詩開頭一句的曲調總要有所變化,也可能是多段的歌曲,其第一段在音樂上較其後諸段有所不同。吳聲中還有一種“三弄”,即上聲弄、下聲弄、游弄。今人楊蔭瀏據《古今樂錄》“《上聲歌》者,此因上聲促柱得名;或用一調,或用無調名”與《上聲歌》詞“改調促鳴箏”句,認為上聲弄、下聲弄是指鏇律的高低變化而言,而且這種高低變化並不限於高低八度的變化,也有轉調的關係在內。
西曲的歌曲稱為“倚歌”,一般結構比較短小,歌詞均為五言四句短詩,如《攀楊枝》、《尋陽樂》等。偶爾也有七言兩句構成的,如《女兒子》。舞曲的結構較為長大。歌詞由多首五言四句短詩構成。西曲短詩常常使用“和聲”幫腔,有時還兼用“送聲”。如《西鳥夜飛》,每兩句結尾的和聲為“白日落西山,還去來”,最後面的送聲為“折翅鳥飛,何處被彈歸”。和聲與送聲的歌詞可長可短,沒有定規。其曲調推想也是如此。吳聲、西曲的伴奏樂隊也各有特色。吳聲早期用篪、琵琶(阮)、箜篌伴奏,後來添用笙、箏。西曲中的倚歌專用吹管樂器及鈴、鼓等打擊樂器伴奏。
大曲,或清商大曲:它與相和大曲相比,又有新的發展。它由三個部分組成:開頭有四至八段器樂演奏的序曲,稱為“四部弦”或“八部弦”;中間是全曲的主體,由多段聲樂曲組成,每段歌唱的結尾都有一個“送”的尾句,稱為“送歌弦”(張永《元嘉正聲伎錄》):結束部分又分幾個器樂段,稱為“契”或“契注聲”,這部分可以是多件樂器合奏,也可由一支笛子獨奏。這種曲式結構發展到後來,便是唐代大曲。
特色
 敦煌217窟壁畫
敦煌217窟壁畫清商樂的伴奏形式多種多樣,“吳聲”通常用箜篌、琵琶和篪(或加用笙和箏)組成的小型樂隊伴奏,有時也單用一件箏伴奏,如《上聲歌》 “初歌《子夜曲》,改調促鳴箏;四座暫寂靜,聽我歌《上聲》”(《樂府詩集》),就是用箏自彈自唱的實例之一。《西曲》有時是用箏和一種叫“鈴鼓”的擊樂器伴奏,歌唱者不奏樂器,站在伴奏者身邊表演,稱做“倚歌”。
清商樂中採用的“吳聲”、“西曲”,多為五言四句一曲,比較齊整。也有少數歌詞是由長短句構成的。 《古今樂録》 說:吳聲“凡歌,曲終皆有送聲。”從曲式上看,在每一唱段,即每一“曲”之後總要加一個尾聲,稱為“送”或“送聲”。如《子夜》“送”的歌詞為“持子”,《鳳將雛》為“澤雉”。有時除“曲”尾的送聲外,在“曲”的中間也可用“送聲”,如《子夜變歌》(《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
人傳歡負情,我自未常見。(送):持子
三更開門去,始知子夜變。(送):歡娛我。
題材
清商樂中的民間創作,以表現愛情或離別之情的題材居多,也有一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的苦難生活,如“吳聲”中的“阿子歌”:“野田草欲盡,東流水又暴,念我雙飛鳧(fú音扶)饑渴常不飽。”它通過對一雙鴨子的描述,曲折地反映了浙江嘉興地區人民在東晉門閥士族統治下饑寒交迫的生活。在東晉和劉宋初期,宮廷清商樂創作中出現了一些較好的作品,其中以東晉桓伊創作的笛曲《三弄》比較著名。宋、齊、梁、陳各朝,清商樂的創作雖然大部是脂香粉氣的艷曲,如陳後主的《玉樹後庭花》、《春江花月夜》等,但也間有清新可愛值得玩味的佳作,如傳為劉宋臨川王劉義慶所作《烏夜啼》和南齊檀約填詞的《陽春》。
衰落
 唐代敦煌壁畫
唐代敦煌壁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