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簡介
維多利亞時代,一名英國醫生在馬戲團發現了一個頭部畸型的象人,受盡不人道的待遇,於是將其帶回醫院作研究。不料馬戲班班主帶人又將象人搶去,到歐洲各地巡迴展出,幸得團中其它畸型人暗中他救回英國,終於使他體驗到人間的溫暖。
此片取材於真實的醫療檔案,所以特別著重時代氣氛的重現。攝影美術與化妝也均有一流水準,故事的發展流暢,演出動人,而且籍醫生與民眾的行為檢討了人類對 “道德”和 “正義”的標準。
藝術風格
 《象人》
《象人》大衛.林奇(David Lynch)1946年生於美國,其演藝事業起步於70年代,1980年以《象人》(TheElephant Man)一舉成名,早期作品帶有寫實風格,之後逐漸轉向另類,形成奇詭、神秘的個人風格。林奇的電影善於利用獨特、前衛的視覺影像、快速的剪接和充滿迷幻色彩的音樂表現人性中隱藏的隱暗面。透過攝像機鏡頭,他呈現給我們一個五光十色卻錯綜複雜的電影世界,在這奇幻氛圍里,人類的暴力、恐懼、貪婪、自私、色情等等邪惡本性一一暴露出來,誇張、大膽的情節帶著清晰而強烈的批判痕跡。
戴維.林奇導演的此片取材於真實的醫療檔案,所以特別著重時代氣氛的重現。故事講述維多利亞時代,一名英國醫生在馬戲團發現了一個頭部畸型的象人,受盡不人道的待遇,於是將其帶回醫院作研究。不料馬戲班班主帶人又將象人搶去,到歐洲各地巡迴展出,幸得團中其它畸型人暗中他救回英國,終於使他體驗到人間的溫暖。本片有安東尼.霍普金斯、約翰.赫特和安妮.班克勞夫特等影星出演,攝影美術與化妝也均有一流水準,故事的發展流暢,演出動人,而且籍醫生與民眾的行為檢討了人類對 “道德”和 “正義”的標準。
《象人》(The Elephant Man)是1980年大衛林奇成名大作,安東尼·霍普金斯主演,影片獲得8項奧斯卡提名。《象人》特別著重時代氣氛的重現,攝影美工與化妝均有一流水準,故事發展流暢,表演感人,生動地探討了人類對道德和正義的標準。這是林奇的第一部主流影片。雖然主角是一個畸形的“象人”,但是轉身離開了費城平民窟的林奇,已經是站在了中產階級的立場上敘事了:中產階級的身世拯救畸形的可憐蟲,並不斷拷問自己的良心。在影像上,林奇讓攝影機動了起來,十分好萊塢化,快速剪接,移動攝影,關係鏡頭,主觀鏡頭,程式化把一切交待得十分明了。光線也柔和了很多,人物臉上總是打著柔光,沒有了《橡皮人》中忽明忽暗跳動的不安。這一切都在把我們、把林奇帶向一個方向:非主流導演的主流影片。
影片開始時模糊詭異的鏡像讓人找到了大衛林奇的感覺,不過隨著情節的展開,影片敘事趨於平實簡約,但決不簡單。影片最後約翰選擇了自殺。星空伴隨著恬淡的女聲出現,但這聽起來更像是詛咒:“事物永不消逝”。這似乎就是影片要告訴我們的,看客永遠不會消失。
但是大衛林齊的電影從來也不缺乏對人的客觀得近乎冷漠的探討。他的鏡頭一定要把人解剖得體無完膚才肯罷休。有時他殘酷的鏡頭會把觀影者逼到一個無處逃避的角落中:這種體驗雖來自視覺、聽覺等外在觀感,但歸根到底還是直接伸向了道德和靈魂。
 《象人》
《象人》在影片的開始,約翰一直戴著一個骯髒破舊的頭罩,像一塊遮羞布一樣蓋住他不想被別人看到的臉,自己躲藏在它的後面。頭罩的左側開了一個洞,因為約翰只有一隻眼睛的視力是正常的。這隻洞漆黑、陰暗,透過它我們什麼也看不到,它是約翰同外界接觸的唯一視窗。當他第一次走進醫院時,周圍的病人都對他十分鄙夷。他不說話,甚至連頭都不會點。
大衛用特寫鏡頭拍這個頭罩:罩在頭罩里的頭顱應該比常人大很多,頭罩上歪歪戴著一頂帽子。然後鏡頭拉得更近,除了頭罩上的洞我們什麼都看不見。但是這隻漆黑的洞卻可以向我們傳達出,洞裡面的眼神一定極度的緊張和恐懼。
影片開始時,鏡頭一直遠遠地對著約翰,我們看不清楚他的外貌。醫生第一次看到他時,大衛沒有直接向我們展示約翰形體的樣子,卻通過醫生臉上的表情來傳達了這一點:他開始是驚愕,然後,他哭了——約翰的樣子可以想像了。
約翰的外貌其實一直是影片的一個懸念。觀眾想知道約翰真正的樣子(因為這在生活中很少見),大衛對於這種獵奇心態瞭若指掌,所以他遲遲不向觀眾展示約翰的形體,而是一點點地靠近他。在醫生的論文宣講會上,約翰被當作活體標本用射燈打著,供醫學專家們觀看。約翰被襯在一塊很大的幕布前面,而鏡頭是從後面拍的,所以我們只能看到約翰扭曲的身影。這是約翰的第一次“裸露”。直到約翰被醫生接到醫院住進病房,他的臉才首次無遮擋的出現在鏡頭裡。而幾乎到了影片的最後,我們才第一次近距離看到了約翰布滿腫瘤、不成人形的全貌。那時領班把他從醫院搶回,逼他表演,約翰支持不住暈倒在台上。而此時觀眾已經不會把焦點投注在他的身體上了,更多的則是擔心他的命運。
看了《象人》後才知道,大衛·林齊的風格,原來一貫如此!但是我總有這樣的感覺:“赫”劇的拍攝技巧和情節構成固然純熟,其主題複雜,內涵也更為艱深晦澀,但是與《象人》相比,二十年後的大衛似乎少了對於人性和道德等一類常規主題的探討。放棄了“道德文章”的他,一心一意做起了“科學家”。這也許有失偏頗,但我更願意把“赫”劇看成是一部研究人的靈魂、夢境和現實等等之間微妙關係的科學歷險。
影片的內容取自英國的真實病歷記錄。情節是這樣的:患有先天性神經纖維瘤約翰·梅里克自幼被遺棄,被一個雜耍班的領班所“收養”。因其相貌和身軀被腫大的纖維瘤弄得完全沒有人的樣子,每天被迫供人觀賞,被稱為“象人”。他在雜耍班飽受領班的摧殘和虐待。後來當地一位知名的外科醫生髮現了他,開始以他為標本發表論文,後來把他收在醫院裡治療,使約翰第一次體會到了成為“人”的感覺。但是好景不長,領班又把他搶了回去,強迫其演出並毒打他,他本已病弱的身體終於禁不住這番折磨,最後死在醫院中。
 《象人》----劇情
《象人》----劇情影片的高潮在將近結尾的部分,是約翰的第一次反抗:他從雜耍班逃回倫敦,希望能夠回到醫院,卻在車站被人糾纏。人們逼迫著他,並且摘掉了他頭上的罩子。這再次把他拋向了置身荒漠一般的絕望境地。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他終於反抗了。他向人群轉過身來,大聲怒吼:“我不是象人!我是一個人!我不是動物!我是一個人!” 約翰一直膽怯、順從,他從不反抗,連一點聲音都沒有發出過。我們完全看不出他的喜怒哀樂,他把自己掩藏在腫瘤和破布的下面。沒有人關心過他的感情,甚至乾脆認為他沒有感情,一直當他是一隻怪物來虐待和娛樂。他大聲喊出的這幾句話,是他被逼到走投無路時發出的無助悽慘的吶喊,是控訴,也是求助。這是一個被囚禁的聲音,是多年來被壓制的人性的集中釋放,也是深埋在心底多年的不敢奢求的唯一要求,所以喊過之後,他筋疲力盡地癱坐在地上。意想不到的是,人們停止了逼迫、推搡和叫喊,漸漸散開了。擁有這樣強大的力量,恐怕他自己也始料未及。
這是影片極為精彩的一節。鏡頭急速運動,緊緊跟著逃避人群的約翰,使人感覺壓抑和窒息。鏡頭在奔跑的同時晃動不定,周圍的場景不時闖入視野,構成了強烈的視覺衝擊。約翰有一條腿是瘸的,他踉蹌的急速奔走和窮追不捨的人群又給觀眾造成了強烈的心理衝擊。背景音樂緊隨著鏡頭的節奏,極具張力,渲染了極度緊張的氣氛。這一切在約翰的頭罩被摘下後戛然而止,而影片情節則達到頂點,約翰的感情隨之爆發。
“象人”約翰外貌醜陋,生理有缺陷,卻天性善良溫柔,十分敏感。他幾乎被剝奪了作為一個人的一切,仍然不喪失人的良知。相比之下,那些外表健全的正常人,心靈深處卻是殘缺和扭曲的,可現實就是,他們可以堂而皇之地生活在“自己人”當中。每個人都有可能從電影中找到一個自我,這便是大衛試圖傳達的東西。當然他也很清楚,看完影片的結果還是一樣:沒有人聽;沒有人看;沒有人停下來。但是,這幾十分鐘裡他是不會讓任何人的良心感覺舒服的。
電影攝製於1981年,據說因為當時業內懷疑彩色膠片保存的長久性而採用黑白膠片拍攝。不過黑白色調非常適合這部電影,這是它能夠成功震撼人心的第一要素。在觀影的過程中,很多場景超越了色彩的限定——沒有擾亂視線的色彩,反倒能使人看得更清楚。
影片的基調陰沉,背景音樂有一些詭異,布景始終透著寒冷、潮濕,很少有溫暖和光明。即使是病房的純白床單和窗簾,也總給人一種潛在的不安定感。影片從頭至尾被無以言喻的冷漠包圍,由這種冷漠衍生出來的,是隨著影片的進展逐步滲透的恐怖。醫生等人的救治行為雖然讓人感到安慰,卻絲毫不能改變主人公的命運,相當無力。
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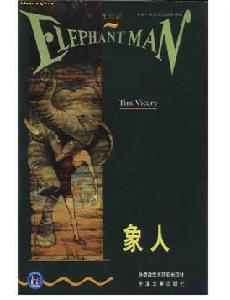 《象人》
《象人》約翰在影片的開始一直是沉默無聲的。這使人(包括醫生和觀眾)懷疑他是否精神正常。醫生為了說服院長收治這個病人,聲稱他會說話,會交流,是一個有正常智力的人,並且為了保險起見,事先排練了一下。但是院長來了之後,約翰卻結結巴巴說不出像樣的話來。當院長放棄繼續聽,醫生也失望離開時,約翰卻終於開口說話了。他用沙啞的含糊不清的嗓音(因為他的喉嚨患病,嘴巴也不能完全張開,而且有若干年沒有說過話了。)充滿感情的背誦著聖經中的讚美詩,而這絕對不是醫生事前教給他的。這讓醫生大為驚喜,也讓院長終於同意收治約翰,而不是把他送到“該去的地方”。
這一幕推翻了之前人們對其人性泯滅的懷疑。按照一般的概念,語言是人的基本特徵。所以是否會“說話”,也就成了判斷他是否“人類”的重要證據。約翰最終自己喊出了讚美詩來說服院長,既是求生的強烈願望迫使他跳出了自卑和恐懼的心理,也說明了,惟有自救者才能被救。
女演員的到訪是一個重要的情節。倫敦最出名、最走紅的女演員親自來醫院看望約翰,並送給他一張自己的大幅照片作為留念。她還送給約翰一本莎士比亞的書,這使約翰喜不自勝,立即翻開“羅密歐與朱莉葉”的那段經典對白朗讀起來。雖然他有點口齒不清,但是那種發自內心的虔誠和真摯卻打動了女演員,她不禁和他對起台詞來。之後,女演員激動地說道:“約翰,你不是象人,你是羅密歐!”約翰十分震動,表情錯愕,因為這句評語完全超乎他的想像。
大衛安排一個女戲子充當片中唯一能和約翰心靈相通的角色,用意頗深。在此之前和之後,都沒有人能夠從這種平等的角度和他交流。約翰一直強烈自卑,雖然之前渴望尊重和認同,但那並不是發現自我。在這場戲中,約翰第一次被人發現並提醒,他擁有內在魅力和心靈力量。他隱隱約約的看到了自己,甚至感受到其存在對別人而言是有意義的。這是他從來沒有想過和體驗過的。
值得注意的是,女演員在走之前吻了約翰的臉頰,但並沒有吻他長滿瘤子的那一半臉。這個細節導演處理得簡直天衣無縫。究竟是有其用意還是隨意,我無法下結論,也無法探究女演員此舉的心態。
影片的尾聲是有關睡姿的:約翰從來不能平躺著睡覺,只能坐著。因為他的頭部和後背都有巨大的腫瘤,如果躺下就會有生命危險。他的臥室的畫上畫著一個平躺在床上的人,他總會望著這幅畫。他曾對醫生說:“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夠像這樣躺著……因為這是人的樣子。”在影片的最後,約翰拿開床上所有的墊子,像人那樣平躺在床上,用頭枕著枕頭,為自己拉好了被子,安然睡去——他用生命的代價,換取了這種“人”的睡姿。
但是大衛林齊的電影從來也不缺乏對人的客觀得近乎冷漠的探討。他的鏡頭一定要把人解剖得體無完膚才肯罷休。有時他殘酷的鏡頭會把觀影者逼到一個無處逃避的角落中:這種體驗雖來自視覺、聽覺等外在觀感,但歸根到底還是直接伸向了道德和靈魂。
 《象人》
《象人》影片的內容取自英國的真實病歷記錄。情節是這樣的:患有先天性神經纖維瘤約翰·梅里克自幼被遺棄,被一個雜耍班的領班所“收養”。因其相貌和身軀被腫大的纖維瘤弄得完全沒有人的樣子,每天被迫供人觀賞,被稱為“象人”。他在雜耍班飽受領班的摧殘和虐待。後來當地一位知名的外科醫生發現了他,開始以他為標本發表論文,後來把他收在醫院裡治療,使約翰第一次體會到了成為“人”的感覺。但是好景不長,領班又把他搶了回去,強迫其演出並毒打他,他本已病弱的身體終於禁不住這番折磨,最後死在醫院中。
“象人”約翰外貌醜陋,生理有缺陷,卻天性善良溫柔,十分敏感。他幾乎被剝奪了作為一個人的一切,仍然不喪失人的良知。相比之下,那些外表健全的正常人,心靈深處卻是殘缺和扭曲的,可現實就是,他們可以堂而皇之地生活在“自己人”當中。每個人都有可能從電影中找到一個自我,這便是大衛試圖傳達的東西。當然他也很清楚,看完影片的結果還是一樣:沒有人聽;沒有人看;沒有人停下來。但是,這幾十分鐘裡他是不會讓任何人的良心感覺舒服的。
影片的基調陰沉,背景音樂有一些詭異,布景始終透著寒冷、潮濕,很少有溫暖和光明。即使是病房的純白床單和窗簾,也總給人一種潛在的不安定感。影片從頭至尾被無以言喻的冷漠包圍,由這種冷漠衍生出來的,是隨著影片的進展逐步滲透的恐怖。醫生等人的救治行為雖然讓人感到安慰,卻絲毫不能改變主人公的命運,相當無力。有關這一點的經典對白就是:“醫生,我想知道,您是否能夠把我治好?”“……,不,我不能。”
這一幕推翻了之前人們對其人性泯滅的懷疑。按照一般的概念,語言是人的基本特徵。所以是否會“說話”,也就成了判斷他是否“人類”的重要證據。約翰最終自己喊出了讚美詩來說服院長,既是求生的強烈願望迫使他跳出了自卑和恐懼的心理,也說明了,惟有自救者才能被救。
大衛安排一個女戲子充當片中唯一能和約翰心靈相通的角色,用意頗深。在此之前和之後,都沒有人能夠從這種平等的角度和他交流。約翰一直強烈自卑,雖然之前渴望尊重和認同,但那並不是發現自我。在這場戲中,約翰第一次被人發現並提醒,他擁有內在魅力和心靈力量。他隱隱約約的看到了自己,甚至感受到其存在對別人而言是有意義的。這是他從來沒有想過和體驗過的。
影片的高潮在將近結尾的部分,是約翰的第一次反抗:他從雜耍班逃回倫敦,希望能夠回到醫院,卻在車站被人糾纏。人們逼迫著他,並且摘掉了他頭上的罩子。這再次把他拋向了置身荒漠一般的絕望境地。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他終於反抗了。他向人群轉過身來,大聲怒吼:“我不是象人!我是一個人!我不是動物!我是一個人!” 約翰一直膽怯、順從,他從不反抗,連一點聲音都沒有發出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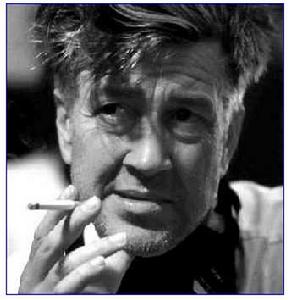 《象人》
《象人》我們完全看不出他的喜怒哀樂,他把自己掩藏在腫瘤和破布的下面。沒有人關心過他的感情,甚至乾脆認為他沒有感情,一直當他是一隻怪物來虐待和娛樂。他大聲喊出的這幾句話,是他被逼到走投無路時發出的無助悽慘的吶喊,是控訴,也是求助。這是一個被囚禁的聲音,是多年來被壓制的人性的集中釋放,也是深埋在心底多年的不敢奢求的唯一要求,所以喊過之後,他筋疲力盡地癱坐在地上。意想不到的是,人們停止了逼迫、推搡和叫喊,漸漸散開了。擁有這樣強大的力量,恐怕他自己也始料未及。
大衛林齊是一個重視道具的導演。這裡面蘊涵著太多的細節和深意。在影片的開始,約翰一直戴著一個骯髒破舊的頭罩,像一塊遮羞布一樣蓋住他不想被別人看到的臉,自己躲藏在它的後面。頭罩的左側開了一個洞,因為約翰只有一隻眼睛的視力是正常的。這隻洞漆黑、陰暗,透過它我們什麼也看不到,它是約翰同外界接觸的唯一視窗。當他第一次走進醫院時,周圍的病人都對他十分鄙夷。他不說話,甚至連頭都不會點。
大衛用特寫鏡頭拍這個頭罩:罩在頭罩里的頭顱應該比常人大很多,頭罩上歪歪戴著一頂帽子。然後鏡頭拉得更近,除了頭罩上的洞我們什麼都看不見。但是這隻漆黑的洞卻可以向我們傳達出,洞裡面的眼神一定極度的緊張和恐懼。
約翰的外貌其實一直是影片的一個懸念。觀眾想知道約翰真正的樣子(因為這在生活中很少見),大衛對於這種獵奇心態瞭若指掌,所以他遲遲不向觀眾展示約翰的形體,而是一點點地靠近他。在醫生的論文宣講會上,約翰被當作活體標本用射燈打著,供醫學專家們觀看。約翰被襯在一塊很大的幕布前面,而鏡頭是從後面拍的,所以我們只能看到約翰扭曲的身影。這是約翰的第一次“裸露”。直到約翰被醫生接到醫院住進病房,他的臉才首次無遮擋的出現在鏡頭裡。而幾乎到了影片的最後,我們才第一次近距離看到了約翰布滿腫瘤、不成人形的全貌。那時領班把他從醫院搶回,逼他表演,約翰支持不住暈倒在台上。而此時觀眾已經不會把焦點投注在他的身體上了,更多的則是擔心他的命運。
宗教一直陪伴著約翰。在雜耍班的那些最黑暗的日子裡,他一直靠默誦早年學習過的讚美詩支撐自己的精神。他從來沒有真正地看見過大教堂,只聽到過教堂的鐘聲,但是他卻親手做出了一個教堂的模型,這讓醫院的護士們十分驚訝。他完成了手工之後說道:“結束了。”在上面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可以說象徵基督徒真誠善良等諸多美德的神聖之所也成為了他心靈的象徵。
人都有追求美的權利。約翰收到禮物時驚喜過望,因為美的權利之前一直和他相隔萬里。這一場戲有兩個要點,第一,約翰成為了正式的病人,也就是被接納為“人”中的一員,他的身份終於得到了認同;第二,化妝盒象徵了美,而美也是人的根本需要之一。對著舞蹈家的照片調情,甚至還象徵了人的性需要。所以,約翰被收治的過程,其實也是他逐漸找回被別人(包括自己)所忽視的人性的過程。這場戲可能會使人感覺不快,甚至會破壞了約翰在觀眾心目中“純潔形象”——約翰怎么會這樣矯揉造作、沾沾自喜還有點自做多情呢。
但事實是,尊重和認同就是這樣頑固地依賴於人的外表。約翰還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內在力量(這場戲在約翰從鏡子中看到自己的臉,以及車站反抗的戲之前),而從某種世俗的角度講,這種力量其實沒有什麼意義。所以約翰有這種表現,簡直是再自然、再正常不過了。約翰對著照片調情的樣子,是每個人都有可能做出的——這就是我們的本性。對這場戲產生不快的人,其實根本沒有從內心深處認同約翰,同情心的泛濫簡直是另一種謀殺;如果對於這種赤裸裸的本性記錄難以忍受——這種顧影自憐顯然沒有絲毫傳統意義上的美感,只能說明對自己不夠誠實罷了。
 《象人》
《象人》其次,約翰心地純潔毋庸置疑,這卻和他嚮往做一個上等人並不矛盾——有社會地位,受人尊重,甚至在社交場受女人的歡迎。因為現實的觀念就是,唯有上等人才是真正的人,至於那些下三爛的草民們,比豬玀還不如。即使身世悽慘如約翰,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也還是決定了他的價值觀。
大衛·林齊的鏡頭不會說謊,他既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只不過和盤端出而已。他所做的,就是把人性的表皮又毫無保留地剝下了一層。
人壓迫人、人歧視人、人利用人、人懼怕人、人同情人、人關心人、人幫助人、人認識人——人與人之間的種種關係在影片中得到了鋪展和詮釋。大衛林齊在影片中對約翰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以約翰這一特殊人物的境遇折射人的百態眾生,筆法冷峻,毫不留情。
大衛的這部影片,演員和導演相得益彰,講故事的手法相當傳統。鏡頭的運用、配樂的張弛、情節的安排、細節的處理,成功的化妝,都是這部影片震撼人心的要素。這部影片一經公映,立即引起轟動。獲得了當年的多項大獎。包括1981年的英國電影學院獎的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員(扮演醫生的安東尼·霍普金斯)、最佳製片指導獎,以及1982年的愷撒電影節最佳外國片獎。又是一部非看不可的電影。
盤點世界十大邊緣人電影
| 就像《侏儒也是一樣長大》中,那群可愛的小個子“侏儒流氓”,在他們的花園裡跳來跳去,他們鄙視教條,鄙視禮儀,鄙視一切煩人的規矩。他們的呼喊看似微弱,卻潛藏著強大的力量。“我很小,可是我很強!”這該喚醒多少沉睡的人群?那些所謂的“正常人”,那些衣冠楚楚卻懷揣著禽獸之心的“牧羊犬”,請你們把眼皮放低,不要再仰著你們那高貴到噁心的頭顱,看看生命中另一些值得關愛的生命吧,他們被摒棄在黑暗中多久了,但他們依然堅強地活著。 他們不是怪胎,是邊緣人。 |
盤點安東尼·霍普金斯作品
| 安東尼霍普金斯是一位英國影、視、劇三棲演員。他憑藉紮實的戲劇功底和內斂、堅韌、略帶憂鬱的特質從事著自己喜愛的演藝事業。1968年,他與明星凱薩琳赫本合演影片《冬之獅》。安東尼霍普金斯出色的演技開始受到人們注目。1992年,安東尼霍普金斯以其在《沉默的羔羊》一片中的傑出表現獲得了第64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的殊榮。 |





![白痴[電影]](/img/4/d17/nBnauM3X0QDN2IzMxMTMyUTMyMTM2gDM3MjMwADMwAzM2AzLzEzLxY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鳥人》[電影]](/img/c/a34/nBnauM3X4EjN2MzN0MTMyUTMyMTM2gDM3MjMwADMwAzM2AzLzEzL0c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