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
馬謖拒諫失街亭 武侯彈琴退仲達
簡介
司馬懿要取漢中之咽喉街亭和列柳城。
馬謖自告奮勇守街亭,他不聽王平之勸,于山上林木深處下寨。
懿領兵圍山,謖下山而逃。
懿先於郭淮得列柳城,後兵出箕谷。
孔明見街亭、列柳城已失,安排退兵之計。
司馬懿引兵襲西城,諸葛亮只得演空城計,懿兵退後離西城往漢中而走。司馬懿嘆不如孔明。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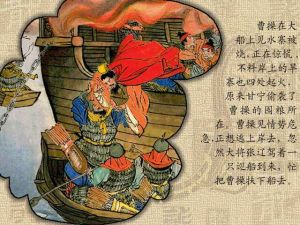 《三國演義》第九十五回
《三國演義》第九十五回卻說魏主曹睿令張郃為先鋒,與司馬懿一同征進;一面令辛毗、孫禮二人領兵五萬,往助曹真。二人奉詔而去。且說司馬懿引二十萬軍,出關下寨,請先鋒張郃至帳下曰:“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逕取長安,早得多時矣。他非無謀,但怕有失,不肯弄險。今必出軍斜谷,來取郿城。若取郿城,必分兵兩路,一軍取箕谷矣。吾已發檄文,令子丹拒守郿城,若兵來不可出戰;令孫禮、辛毗截住箕谷道口,若兵來則出奇兵擊之。”郃曰:“今將軍當於何處進兵?”懿曰:“吾素知秦嶺之西,有一條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處皆是漢中咽喉。諸葛亮欺子丹無備,定從此進。吾與汝逕取街亭,望陽平關不遠矣。亮若知吾斷其街亭要路,絕其糧道,則隴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連夜奔回漢中去也。彼若回動,吾提兵於小路擊之,可得全勝;若不歸時,吾卻將諸處小路,盡皆壘斷,俱以兵守之。一月無糧,蜀兵皆餓死,亮必被吾擒矣。”張郃大悟,拜伏於地曰:“都督神算也!”懿曰:“雖然如此,諸葛亮不比孟達。將軍為先鋒,不可輕進。當傳與諸將:循山西路,遠遠哨探。如無伏兵,方可前進。若是怠忽,必中諸葛亮之計。”張郃受計引軍而行。
卻說孔明在祁山寨中,忽報新城探細人來到。孔明急喚入問之,細作告曰:“司馬懿倍道而行,八日已到新城,孟達措手不及;又被申耽、申儀、李輔、鄧賢為內應:孟達被亂軍所殺。今司馬懿撤兵到長安,見了魏主,同張郃引兵出關,來拒我師也。”孔明大驚曰:“孟達做事不密,死固當然。今司馬懿出關,必取街亭,斷吾咽喉之路。”便問:“誰敢引兵去守街亭?”言未畢,參軍馬謖曰:“某願往。”孔明曰:“街亭雖小,干係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軍皆休矣。汝雖深通謀略,此地奈無城郭,又無險阻,守之極難。”謖曰:“某自幼熟讀兵書,頗知兵法。豈一街亭不能守耶?”孔明曰:“司馬懿非等閒之輩;更有先鋒張郃,乃魏之名將:恐汝不能敵之。”謖曰:“休道司馬懿、張郃,便是曹睿親來,有何懼哉!若有差失,乞斬全家。”孔明曰:“軍中無戲言。”謖曰:“願立軍令狀。”孔明從之,謖遂寫了軍令狀呈上。孔明曰:“吾與汝二萬五千精兵,再撥一員上將,相助你去。”即喚王平分付曰:“吾素知汝平生謹慎,故特以此重任相托。汝可小心謹守此地:下寨必當要道之處,使賊兵急切不能偷過。安營既畢,便畫四至八道地理形狀圖本來我看。凡事商議停當而行,不可輕易。如所守無危,則是取長安第一功也。戒之!戒之!”二人拜辭引兵而去。孔明尋思,恐二人有失,又喚高翔曰:“街亭東北上有一城,名列柳城,乃山僻小路,此可以屯兵紥寨。與汝一萬兵,去此城屯紥。但街亭危,可引兵救之。”高翔引兵而去。孔明又思:高翔非張郃對手,必得一員大將,屯兵於街亭之右,方可防之,遂喚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後屯紥。延曰:“某為前部,理合當先破敵,何故置某於安閒之地?’孔明曰:“前鋒破敵,乃偏裨之事耳。今令汝接應街亭,當陽平關衝要道路,總守漢中咽喉:此乃大任也,何為安閒乎?汝勿以等閒視之,失吾大事。切宜小心在意!”魏延大喜,引兵而去。孔明恰才心安,乃喚趙雲、鄧芝分付曰:“今司馬懿出兵,與舊日不同。汝二人各引一軍出箕谷,以為疑兵。如逢魏兵,或戰、或不戰,以驚其心。吾自統大軍,由斜谷逕取郿城;若得郿城,長安可破矣。”二人受命而去。孔明令姜維作先鋒,兵出斜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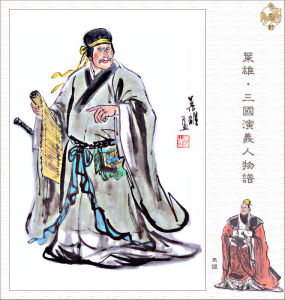 馬謖
馬謖卻說馬謖、王平二人兵到街亭,看了地勢。馬謖笑曰:“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處,魏兵如何敢來!”王平曰:“雖然魏兵不敢來,可就此五路總口下寨;卻令軍士伐木為柵,以圖久計。”謖曰:“當道豈是下寨之地?此處側邊一山,四面皆不相連,且樹木極廣,此乃天賜之險也:可就山上屯軍。”平曰:“參軍差矣。若屯兵當道,築起城垣,賊兵總有十萬,不能偷過;今若棄此要路,屯兵于山上,倘魏兵驟至,四面圍定,將何策保之?”謖大笑曰:“汝真女子之見!兵法云:‘憑高視下,勢如劈竹。’若魏兵到來,吾教他片甲不回!”平曰:“吾累隨丞相經陣,每到之處,丞相盡意指教。今觀此山,乃絕地也:若魏兵斷我汲水之道,軍士不戰自亂矣。”謖曰:“汝莫亂道!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魏兵絕我汲水之道,蜀兵豈不死戰?以一可當百也。吾素讀兵書,丞相諸事尚問於我,汝奈何相阻耶!”平曰:“若參軍欲在山上下寨,可分兵與我,自於山西下一小寨,為掎角之勢。倘魏兵至,可以相應。”馬謖不從。忽然山中居民,成群結隊,飛奔而來,報說魏兵已到。王平欲辭去。馬謖曰:“汝既不聽吾令,與汝五千兵自去下寨。待吾破了魏兵,到丞相面前須分不得功!”王平引兵離山十里下寨,畫成圖本,星夜差人去稟孔明,具說馬謖自於山上下寨。卻說司馬懿在城中,令次子司馬昭去探前路:若街亭有兵守御,即當按兵不行。司馬昭奉令探了一遍,回見父曰:“街亭有兵守把。”懿嘆曰:“諸葛亮真乃神人,吾不如也!”昭笑曰:“父親何故自墮志氣耶?男料街亭易取。”懿問曰:“汝安敢出此大言?”昭曰:“男親自哨見,當道並無寨柵,軍皆屯于山上,故知可破也。”懿大喜曰:“若兵果在山上,乃天使吾成功矣!”遂更換衣服,引百餘騎親自來看。是夜天晴月朗,直至山下,周圍巡哨了一遍,方回。馬謖在山上見之,大笑曰:“彼若有命,不來圍山!”傳令與諸將:“倘兵來,只見山頂上紅旗招動,即四面皆下。”
卻說司馬懿回到寨中,使人打聽是何將引兵守街亭。回報曰:“乃馬良之弟馬謖也。”懿笑曰:“徒有虛名,乃庸才耳!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誤事!”又問:“街亭左右別有軍否?”探馬報曰:“離山十里有王平安營。”懿乃命張郃引一軍,當住王平來路。又令申耽、申儀引兩路兵圍山,先斷了汲水道路;待蜀兵自亂,然後乘勢擊之。當夜調度已定。次日天明,張郃引兵先往背後去了。司馬懿大驅軍馬,一擁而進,把山四面圍定。馬謖在山上看時,只見魏兵漫山遍野,旌旗隊伍,甚是嚴整。蜀兵見之,盡皆喪膽,不敢下山。馬謖將紅旗招動,軍將你我相推,無一人敢動。謖大怒,自殺二將。眾軍驚懼,只得努力下山來沖魏兵。魏兵端然不動。蜀兵又退上山去。馬謖見事不諧,教軍緊守寨門,只等外應。
卻說王平見魏兵到,引軍殺來,正遇張郃;戰有數十餘合,平力窮勢孤,只得退去。魏兵自辰時困至戌時,山上無水,軍不得食,寨中大亂。嚷到半夜時分,山南蜀兵大開寨門,下山降魏。馬謖禁止不住。司馬懿又令人於沿山放火,山上蜀兵愈亂。馬謖料守不住,只得驅殘兵殺下山西逃奔。司馬懿放條大路,讓過馬謖。背後張郃引兵追來。趕到三十餘里,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出,放過馬謖,攔住張郃;視之,乃魏延也。延揮刀縱馬,直取張郃。郃回軍便走。延驅兵趕來,復奪街亭。趕到五十餘里,一聲喊起,兩邊伏兵齊出:左邊司馬懿,右邊司馬昭,卻抄在魏延背後,把延困在垓心。張郃復來,三路兵合在一處。魏延左衝右突,不得脫身,折兵大半。正危急間,忽一彪軍殺入,乃王平也。延大喜曰:“吾得生矣!”二將合兵一處,大殺一陣,魏兵方退。二將慌忙奔回寨時,營中皆是魏兵旌旗。申耽、申儀從營中殺出。王平、魏延徑奔列柳城,來投高翔。此時高翔聞知街亭有失,盡起列柳城之兵,前來救應,正遇延、平二人,訴說前事。高翔曰:“不如今晚去劫魏寨,再復街亭。”當時三人在山坡下商議已定。待天色將晚,兵分三路。魏延引兵先進,逕到街亭,不見一人,心中大疑,未敢輕進,且伏在路口等候,忽見高翔兵到,二人共說魏兵不知在何處。正沒理會,又不見王平兵到。忽然一聲炮響,火光沖天,鼓聲震地:魏兵齊出,把魏延、高翔圍在垓心。二人往來衝突,不得脫身。忽聽得山坡後喊聲若雷,一彪軍殺入,乃是王平,救了高、魏二人,徑奔列柳城來。比及奔到城下時,城邊早有一軍殺到,旗上大書“魏都督郭淮”字樣。原來郭淮與曹真商議,恐司馬懿得了全功,乃分淮來取街亭;聞知司馬懿、張郃成了此功,遂引兵徑襲列柳城。正遇三將,大殺一陣。蜀兵傷者極多。魏延恐陽平關有失,慌與王平、高翔望陽平關來。
卻說郭淮收了軍馬,乃謂左右曰:“吾雖不得街亭,卻取了列柳城,亦是大功。”引兵逕到城下叫門,只見城上一聲炮響,旗幟皆豎,當頭一面大旗,上書“平西都督司馬懿”。懿撐起懸空板,倚定護心木欄乾,大笑曰:“郭伯濟來何遲也?”淮大驚曰:“仲達神機,吾不及也!”遂入城。相見已畢,懿曰:“今街亭已失,諸葛亮必走。公可速與子丹星夜追之。”郭淮從其言,出城而去。懿喚張郃曰:“子丹、伯濟,恐吾全獲大功,故來取此城池。吾非獨欲成功,乃僥倖而已。吾料魏延、王平、馬謖、高翔等輩,必先去據陽平關。吾若去取此關,諸葛亮必隨後掩殺,中其計矣。兵法云:‘歸師勿掩,窮寇莫追。’汝可從小路抄箕谷退兵。吾自引兵當斜谷之兵。若彼敗走,不可相拒,只宜中途截住:蜀兵輜重,可盡得也。”張郃受計,引兵一半去了。懿下令:“竟取斜谷,由西城而進。西城雖山僻小縣,乃蜀兵屯糧之所,又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總路。若得此城,三郡可復矣。”於是司馬懿留申耽、申儀守列柳城,自領大軍望斜谷進發。
卻說孔明自令馬謖等守街亭去後,猶豫不定。忽報王平使人送圖本至。孔明喚入,左右呈上圖本。孔明就文几上拆開視之,拍案大驚曰:“馬謖無知,坑陷吾軍矣!”左右問曰:“丞相何故失驚?”孔明曰:“吾觀此圖本,失卻要路,占山為寨。倘魏兵大至,四面圍合,斷汲水道路,不須二日,軍自亂矣。若街亭有失,吾等安歸?”長史楊儀進曰:“某雖不才,願替馬幼常回。”孔明將安營之法,一一分付與楊儀。正待要行,忽報馬到來,說:“街亭、列柳城,盡皆失了!”孔明跌足長嘆曰:“大事去矣!此吾之過也!”急喚關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投武功山小路而行。如遇魏兵,不可大擊,只鼓譟吶喊,為疑兵驚之。彼當自走,亦不可追。待軍退盡,便投陽平關去。”又令張冀先引軍去修理劍閣,以備歸路。又密傳號令,教大軍暗暗收拾行裝,以備起程。又令馬岱、姜維斷後,先伏于山谷中,待諸軍退盡,方始收兵。又差心腹人,分路報與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軍民,皆入漢中。又遣心腹人到冀縣搬取姜維老母,送入漢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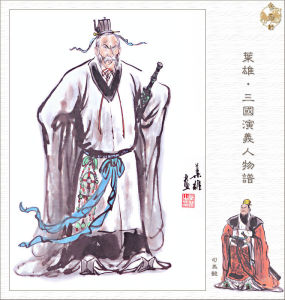 司馬懿
司馬懿孔明分撥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縣搬運糧草。忽然十餘次飛馬報到,說:“司馬懿引大軍十五萬,望西城蜂擁而來!”時孔明身邊別無大將,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軍,已分一半先運糧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軍在城中。眾官聽得這個訊息,盡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塵土沖天,魏兵分兩路望西城縣殺來。孔明傳令,教“將旌旗盡皆隱匿;諸軍各守城鋪,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言大語者,斬之!大開四門,每一門用二十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如魏兵到時,不可擅動,吾自有計。”孔明乃披鶴氅,戴綸巾,引二小童攜琴一張,於城上敵樓前,憑欄而坐,焚香操琴。
卻說司馬懿前軍哨到城下,見了如此模樣,皆不敢進,急報與司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軍,自飛馬遠遠望之。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寶劍;右有一童子,手執麈尾。城門內外,有二十餘百姓,低頭灑掃,傍若無人,懿看畢大疑,便到中軍,教後軍作前軍,前軍作後軍,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馬昭曰:“莫非諸葛亮無軍,故作此態?父親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謹慎,不曾弄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我兵若進,中其計也。汝輩豈知?宜速退。”於是兩路兵盡皆退去。孔明見魏軍遠去,撫掌而笑。眾官無不駭然,乃問孔明曰:“司馬懿乃魏之名將,今統十五萬精兵到此,見了丞相,便速退去,何也?”孔明曰:“此人料吾生平謹慎,必不弄險;見如此模樣,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險,蓋因不得已而用之。此人必引軍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興、苞二人在彼等候。”眾皆驚服曰:“丞相之機,神鬼莫測。若某等之見,必棄城而走矣。”孔明曰:“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棄城而走,必不能遠遁。得不為司馬懿所擒乎?”後人有詩讚曰:“瑤琴三尺勝雄師,諸葛西城退敵時。十五萬人回馬處,土人指點到今疑。”言訖,拍手大笑,曰:“吾若為司馬懿,必不便退也。”遂下令,教西城百姓,隨軍入漢中;司馬懿必將復來。於是孔明離西城望漢中而走。天水、安定、南安三郡官吏軍民,陸續而來。
卻說司馬懿望武功山小路而走。忽然山坡後喊殺連天,鼓聲震地。懿回顧二子曰:“吾若不走,必中諸葛亮之計矣。”只見大路上一軍殺來,旗上大書“右護衛使虎冀將軍張苞”。魏兵皆棄甲拋戈而走。行不到一程,山谷中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前面一桿大旗,上書“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山谷應聲,不知蜀兵多少;更兼魏軍心疑,不敢久停,只得盡棄輜重而去。興、苞二人皆遵將令,不敢追襲,多得軍器糧草而歸。司馬懿見山谷中皆有蜀兵,不敢出大路,遂回街亭。
此時曹真聽知孔明退兵,急引兵追趕。山背後一聲炮響,蜀兵漫山遍野而來:為首大將,乃是姜維、馬岱。真大驚,急退軍時,先鋒陳造已被馬岱所斬。真引兵鼠竄而還。蜀兵連夜皆奔回漢中。卻說趙雲、鄧芝伏兵於箕谷道中。聞孔明傳令回軍,雲謂芝曰:“魏軍知吾兵退,必然來追。吾先引一軍伏於其後,公卻引兵打吾旗號,徐徐而退。吾一步步自有護送也。
卻說郭淮提兵再回箕谷道中,喚先鋒蘇顒分付曰:“蜀將趙雲,英勇無敵。汝可小心提防,彼軍若退,必有計也。”蘇顒欣然曰:“都督若肯接應,某當生擒趙雲。”遂引前部三千兵,奔入箕谷。看看趕上蜀兵,只見山坡後閃出紅旗白字,上書“趙雲”。蘇顒急收兵退走。行不到數里,喊聲大震,一彪軍撞出:為首大將,挺槍躍馬,大喝曰:“汝識趙子龍否!”蘇顒大驚曰:“如何這裡又有趙雲?”措手不及,被雲一槍刺死於馬下。余軍潰散。雲迤邐前進,背後又一軍到,乃郭淮部將萬政也。雲見魏兵追急,乃勒馬挺槍,立於路口,待來將交鋒。蜀兵已去三十餘里。萬政認得是趙雲,不敢前進,雲等得天色黃昏,方才撥回馬緩緩而進。郭淮兵到,萬政言趙雲英勇如舊,因此不敢近前。淮傳令教軍急趕,政令數百騎壯士趕來。行至一大林,忽聽得背後大喝一聲曰:“趙子龍在此!”驚得魏兵落馬者百餘人,余者皆越嶺而去。萬政勉強來敵,被雲一箭射中盔纓,驚跌於澗中。雲以槍指之曰:“吾饒汝性命回去!快教郭淮趕來!”萬政脫命而回。雲護送車仗人馬,望漢中而去,沿途並無遺失。曹真、郭淮復奪三郡,以為己功。卻說司馬懿分兵而進。此時蜀兵盡回漢中去了,懿引一軍復到西城,因問遺下居民及山僻隱者,皆言孔明止有二千五百軍在城中,又無武將,只有幾個文官,別無埋伏。武功山小民告曰:“關興、張苞,只各有三千軍,轉山吶喊,鼓譟驚追,又無別軍,並不敢廝殺。”懿悔之不及,仰天嘆曰:“吾不如孔明也!”遂安撫了諸處官民,引兵徑還長安,朝見魏主。睿曰:“今日復得隴西諸郡,皆卿之功也。”懿奏曰:“今蜀兵皆在漢中,未盡剿滅。臣乞大兵併力收川,以報陛下。”睿大喜,令懿即便興兵。忽班內一人出奏曰:“臣有一計,足可定蜀降吳。”正是:蜀中將相方歸國,魏地君臣又逞謀。
未知獻計者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賞析
諸葛亮幾次北伐中,以第一次形勢最好,當時出兵之時,曹魏防備不嚴,天水等三郡更是歸附於蜀漢,曹魏朝野為之震動,曹叡親臨長安督戰。曹叡去長安還搞出了一件事來,這古代當時訊息不甚靈通,也不知從哪傳來的訊息說這曹叡死了,手下眾臣立曹植為帝了,這個訊息居然傳到了洛陽,便是卞太后也信以為真。後來曹叡回到洛陽才平息謠言,曹叡沒有懲辦傳播謠言者,但是心裡對叔父曹植的戒心卻是重了,日後曹植請用而不得實際上也和此事有點關係。長安離洛陽並不算得遠,但是居然傳出這種訊息洛陽群臣還當真了,可見當時局勢之混亂與群臣對於曹叡這個新皇帝並不是很信服。而這種狀況之後諸葛亮的幾次北伐中便再也沒有發生過。如此大好之局勢,便因為街亭一戰之敗而告破壞。之後雖然曹魏自然沒象演義中那樣把諸葛亮逼到了擺空城計的地步,(空城計倒也不能說是演義的杜撰,在西晉時期郭沖說諸葛亮五事中第三事就說到了此事,不過裴松之在注引此說時也同時明確的證明了此乃杜撰之說,演義只是把這個杜撰拿來自己用罷了。)但是街亭一失,諸葛亮進無所拒,不得不放棄到手的三郡退回漢中,這一戰街亭乃是關鍵。
關於此戰,三國志中有頗多記載,摘錄幾則主要參與此事之人的傳記記載如下:
張郃,作為街亭一戰中曹魏的主將,他的傳記中:“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諸葛亮,作為北伐主帥,此戰中:“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因此戰失利。諸葛亮請罪,降到右將軍。(不過還是以右將軍的頭銜行丞相之事,日後姜維也以後將軍之銜領大將軍之事,這演義中兩師徒倒是都做過一樣的事。)
馬謖,作為街亭一戰中蜀漢軍的統軍大將,在他的傳記中:“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
王平,日後蜀漢大將,他也參與了街亭一戰,可說是此戰中蜀漢唯一的亮點,他的傳記中:“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
從上述之記載中可知街亭當時之戰況,演義中對街亭之戰的描寫也大都出於以上記載。由此之中,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樣的信息呢?
其一:諸葛亮破格起用馬謖,當時蜀漢之中不乏大將,為什麼選用馬謖呢?我們先說說馬謖。
馬謖其人雖任過綿竹成都令、越雋太守等職,但是在其傳記中並沒有記載他之前有統兵打仗的經歷,但是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頗為器重,對這點,劉備在死前還專門叮囑過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是對於先帝的話諸葛亮並沒有放在心裡,任命為參軍,時常和馬謖討論軍機,又說諸葛亮南征時的攻心為上便是馬謖提議的。諸葛亮對其極為欣賞,所以在此戰之中將駐守街亭一要職交給馬謖而不是別人,因為他對馬謖放心,所以令他統領眾將如王平等人率領大軍在街亭駐守。
其二:馬謖在街亭大敗,尤其是在街亭的表現,深失諸葛亮所望。
馬謖在街亭一戰之中,表現很糟糕,從敵方曹魏張郃和本方蜀漢王平兩人的傳記中都指出了這一點,“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都說明了馬謖在此戰中都做了一些違背正常作戰規律的事。而假如按照正常做法,比如拒道而守,應該是可以擋得曹魏,至少也不至於慘敗的,這點從日後建興九年時同樣是張郃,面對王平時,王平堅守,張郃對之便無可奈何此事上便可知一二,尤其是此戰慘敗之後,身為統兵大將的馬謖無法控制住兵士,使其離散,這對比起王平在此戰中的表現或者是另一路同樣是遭遇失敗的趙雲鄧芝,就差得太多了。(三國志趙雲傳中稱“雲、芝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然斂眾固守,不至大敗。”在雲別傳中記載:“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所以此戰中馬謖的表現可謂之糟糕,根本不是一個合格的將領。又《向郎傳》中甚至記載其逃亡之事,“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如此行跡,可謂差矣。
街亭之敗,諸葛亮提拔馬謖,用人失當,確實是一大問題,所以日後自請貶官,至於馬謖,在此戰中舉策失當,在其後又不能控制所率其部,甚至畏罪逃亡,此等罪責,無一不是可斬之罪,趙雲以弱戰強,約束部眾,沒有大敗,還受到貶官,街亭之戰如此重要,而街亭又敗的如此迅速和慘敗,馬謖其罪不誅才是怪事,何況也並非馬謖一人,張休、李盛這些將軍也同時被誅殺。以馬謖傳中的記載看,馬謖雖然號稱被誅殺,但是實際上最後還是死在獄中,這已經是諸葛亮看在往日情份,刻意開恩了。
不過令人奇怪的是,馬謖之罪,卻有無數人為之說情,其中如蔣琬本就是諸葛亮親近,為同為諸葛亮親近之人的馬謖求情也不奇怪,至於向朗那也是出於友情之故。但是為何還有如習鑿齒等史學家對此非議呢。
在我來看,他們都搞混了一點,便是決策者與參謀的角色關係。
決策者與參謀,這兩者我覺得無須太多解釋,用演義中的說法,那些主公將軍就是決策者,那些軍師謀士幕僚就是參謀。就好象曹操劉備孫權這樣的人物便是決策者,而在劉備死前的諸葛亮,郭嘉賈詡這樣的人物便是參謀,當然,也往往有角色變換的時候,比如諸葛亮在劉備生前扮演的是參謀的角色,但是到了劉備死後就是決策者的角色。也有同時期有時為決策者有時為參謀的,比如程昱乃是曹操出名的謀士,但是同時他也往往任為太守,大將,那便是決策者了。再比如那些將領更為明顯,當獨立帶兵時為決策者,而歸屬於大將時便是參謀了。
正因為如此,所以說決策者與參謀的角色是很容易搞混的,而且不停變換,比如有做參謀做的好的去做決策者,如天子近臣幕僚做的好的往往外放為地方官或者將領,這就是決策者的角色,而也有大將戰功赫赫或者地方官政績顯赫征其回朝為天子幕僚的,而且即便在天子幕僚的時刻,他們面對天子是參謀,但是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又是決策者了。
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在一個事件之中,參謀可以有許多,決策者只有一個。對於更多的人來說,他們更希望能做決策者,因為這意味著權力,參謀出謀劃策再多,不能通過決策變為現實,那也是無用。我記得在看二戰某人的回憶錄中曾經說到過:美國歷史上對那些大戰的總司令名字如數家珍,但是對於那些參謀長便沒人記得。當然現代的參謀長和我們所說的參謀還是有很大區別的,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些參謀們更希望成為決策者,因為那意味著權力的滋味,因為有些京官寧願不在天子腳下做事,也要去做那邊疆大吏,原因便是如此。
但是,這決策者並不好做,由參謀轉型做決策者也難,本來是為別人出謀劃策,那一日便可出得那許多好計來,但是到了自己決策,便覺得這計也好,那計也不錯,優柔寡斷起來,這倒也是罷了,只怕就是選錯了計策,那便麻煩了,尤其是戰場決策,是影響萬千人甚至自家性命的事。所以這參謀做將軍,並不是常有成功者。便如那有名的趙括小將軍,論其兵法頭頭是道,想必要做參謀,那肯定是一等一的。但是這做起大將,就是送了四十萬趙兵的性命。至於馬謖,也是不錯的參謀,結果做了統兵大將,就是導致街亭大敗。這兩者都是參謀做大將失敗的典型,其實這參謀和大將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就好象諸葛亮之才如何?與劉備見面談的甚好,有魚水之關係,一等一的參謀。但是在歷史上劉備一開始也主要讓他做些政務為主,直到入蜀一戰才讓他帶領荊州前來增援,不過那時也沒打得什麼大戰,至多算是能磨練一番罷了。諸葛亮之才尚要磨練,如馬謖趙括這樣的參謀一上來讓他就擔負重任,實在是所託非人,但是這一點馬謖沒有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便連已經受到劉備提醒的諸葛亮也沒有認識到這點。
劉備這一生看人甚準,在死前還看了一個馬謖,叮囑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其實諸葛亮雖然看人用人上比之劉備是稍微弱了些,但也不至於到了看不準的地步,之所以如此,還是和劉備與諸葛亮兩人之長期扮演的角色有關。
劉備年輕時自然也做過別人的部下參謀,但是很多的生涯還是做決策者的身份,但是諸葛亮不同,他投入劉備麾下,處理政務,頗得親重,但是在重大軍務上還只是處於參謀的地位。所以他們兩者在選擇人才的眼光有所不同,劉備往往能選擇出魏延霍峻黃忠這樣的將領,諸葛亮則對於那些參謀型人才有所好感,因為從他們身上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在當劉備叮囑之後,諸葛亮依然對馬謖頗為親重,這倒也沒什麼,因為馬謖也是個好參謀,但是當他成為一個決策者時就顯出了危機。
決策者與參謀最大的區別是什麼?前面我們說過了權力上的,但是還有一點更重要,便是責任上的。所謂權力越大,責任也就越大,誠如斯言。參謀權力小,只有進言獻策的權力,但是在最後失敗的承擔責任之上,負的責任也要小,儘管也有些參謀會遭到遷怒,但是更多的參謀往往只是不被重視,不再信用而已。決策者不同,他的決策失敗就意味著全軍失敗覆滅甚至付出自己的性命,決策者享有著權力榮耀的同時,也要承擔失敗之後的責任。沒人會因為一個決策者聽從參謀的錯誤進言而批判參謀,而只會嘲笑決策者的愚蠢,因為最終選擇了那條愚蠢道理的是決策者。
史書上往往會記載失敗的決策者,但是很少記載失敗的參謀,那些失敗的參謀通常都被歷史忽略過去,長期以往,大家就著迷於那些算無遺策的謀士,而忘記了真正承擔風險的是那些採用計策的決策者們。
至於如演義作者那樣的文人更是再進一步,把諸葛亮郭嘉那樣的謀士極度神話了,就好象劉備離開諸葛亮便什麼都做不了,其他演義中謀士的地位也比主公重要的多。我們之前說過,這是文人們希望能做一個君臣相得的理想,希望自己的才能能夠被採用,所以文人對那些軍師謀士才寄託了眾多的感情。甚至到了極至就成了凡是做錯的就是決策者的錯,做對了就是謀士的功勞的模樣,謀士成為了主體。
不過事實上參謀們永遠成為不了主體,只有決策者才是主體。一面享受著決策者的權力,一面享受著參謀的責任,那只有演義小說中才能出現。馬謖是那個參謀時,他就需要承擔身為參謀的責任即可,但是當街亭時,他不單就享受著統領大軍的權力,也需要承擔隨之而來的責任,也正因為如此,當他開始時還把自己擺在一個參謀的角色上,試圖用試驗來證明他的奇策,而當他失敗時,他發覺自己不再是那個承擔微小責任的參謀而是那個需要為戰敗負全責的決策者。他驚慌失措,無力統領大軍,更加蔓延了街亭的失敗。
街亭上需要一個能承擔責任的決策者,而諸葛亮卻選擇了一個無法承擔責任的參謀,這就是街亭的失敗之處了。
回評
毛宗崗批語
前回方寫孟達不聽孔明之言而失上庸,此回便接寫馬謖不聽孔明之言而失街亭。上庸失而使孔明無進取之望,街亭失而幾使孔明無退足之處矣。何也?無街亭則陽平關危,陽平關危則不惟進無所得,而且退有所失也。未失者且憂其失,而既得者安能保其得?於是南安不得不棄,安定不得不損,天水不得不委,箕谷之兵不得不撤,西城之餉不得不收。遂令向之擒夏侯、斬崔諒、殺楊陵、取上邽、襲冀縣、罵王朗、破曹真者,其功都付之烏有。悲夫!
兵家勝敗之故,有異而同者,有同而異者。徐晃拒王平之諫,而背水以為陣;馬謖拒王平之諫,而依山以為營:水與山異,而必敗之勢則同也。黃忠屯兵于山,而能斬夏侯淵;馬謖屯兵于山,而不能退司馬懿:山與山同,而一勝一敗之勢則異也。馬謖之所以敗者,因熟記兵法之成語於胸中,不過曰“憑高視下,勢如劈竹”耳。孰知坐論則是,起行則非,讀書雖多,致用則誤,豈不重可嘆哉!故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書。
請守街亭之馬謖,即獻計平蠻之馬謖也,又即反間司馬懿之馬謖也。何以前則智而後則愚?曰: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試以前二事論之:其策南人,則其言果效;其策司馬,則其言始效而不終效。豈非天方授魏,天方啟晉,而人實不能與天爭乎?故知一效一不盡效之故。而街亭之失,不必為馬謖咎,更不必為用馬謖者咎。
此回乃司馬懿初與孔明對壘之時也。而孔明利在戰,司馬懿利在不戰。夏侯楙、曹真皆以戰而敗,司馬懿則欲以不戰而勝。其守郿城、箕谷者,所以遏孔明之前,而使不得進也;其取街亭、列柳城者,所以截孔明之後,而可使不得不退也。使不得不退,而懿於是乎可以不戰矣。非不欲戰,實不敢戰,畏蜀如虎,蓋自此日而已然雲。
唯小心人不做大膽事,亦唯小心人能做大膽事。魏延欲出子午谷,而孔明以為危計,是小心者惟孔明也。坐守空城,只以二十軍士掃門,而退司馬懿十五萬之眾,是大膽者亦惟孔明也。孔明若非小心於平日,必不敢大膽於一時。仲達不疑其大膽於一時,正為信其小心於平日耳。
為將之道,不獨進兵難,退兵亦難。能進兵是十分本事,能退兵亦是十分本事。當不得不退之時,而又當必不可退之勢,進將被擒,退亦受執,於此而權略不足以濟之,欲全師而退,難矣!試觀孔明焚香操琴,以不退為退;子龍設伏斬將,又能以退為進。蜀中有如此之相,如此之將,而卒不能克復中原。嗚呼!天不祚漢耳,豈戰之罪哉!
自九十二回至此,敘武侯第一次伐魏之事。而始之以趙雲,終之以趙雲者,衝鋒陷陣唯子龍,子龍為功首也;班師整旅,亦唯子龍為首功也。以連斬五將始,以殺一將釋一將終。覺長阪之英雄如昨,漢水之膽智猶新,務自伸其討魏報漢之志,真不愧先主之舊臣矣!
李贄總評
馬謖妄自尊大,一味糊塗,一味自是,及到魏兵圍定,莫展一籌,待救兵而已。極以今時說大話秀才,平時議論鑿鑿可聽,孫、吳莫及也,及至臨事,惟有縮頸吐舌而已。真可發一大噱也。
鍾敬伯總評
街亭之失,馬謖狂妄所致。焚香操琴以退魏兵,孔明曰:“吾非行險,盍因不得已而用之。”固知善行師者有堂堂之陣,必不以陰平走險為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