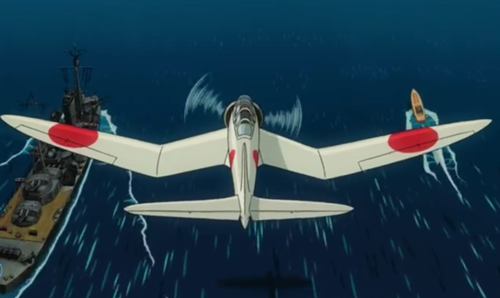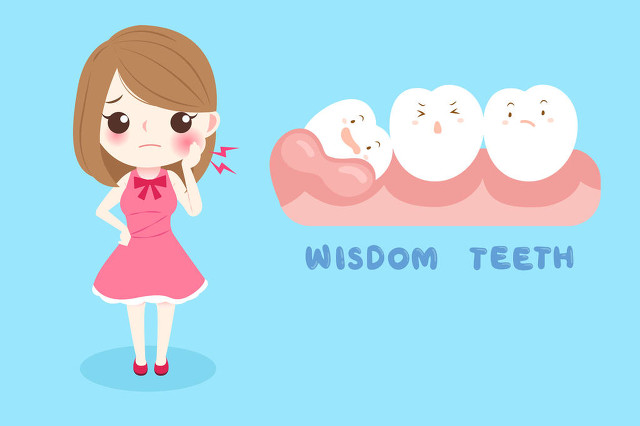從漢代末年開始,社會動盪不安,世事紛爭頻繁,在接下來三百七十年的時間裡,經濟、文化的重心開始向南推移。該時期思想學術、文學藝術空間活躍,教育內容、教育形式有重大變革,各地區教育有較大差異且極具特色,構成了一副文化、思想、教育的多彩畫卷。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劇烈動盪,是“時將大變,世將大革”的時代。晉結束了三國鼎立後,鏇即分裂為北方的西晉和南方的東晉,西晉又經歷了前秦、北魏、東魏、北齊,東晉則是宋、齊、梁、陳輪番登場。政權的不穩定給黎民百姓帶來無盡災難的同時,更瓦解了漢代以來儒家推崇強調的“正統”與“規範”。“名實相副,德才兼備,表里如一”的儒家完美人格被血淋淋的屠殺和赤裸裸的掠奪徹底打碎,由外及內發生了三重分裂。

首先是名與實的分裂,這是人格的表層分裂。儒家講求名實相副,名實一致。可魏晉時期“有其名無其實”卻是大有市場。他們善於偽裝“幽而如明、躁而如靜,欲而如讓,跛而如正”;他們熱衷於名“無而求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看過程只看結果。因此出現了推選出來的“秀才”不識字,薦舉的“孝子”不養爹,“剛正清廉”的官員藏污納垢,所謂的“良臣高將”怯懦如雞。孔子所講的“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落伍了,時下講的是“患無位,不患所以立”。求名背後的動因是求利,因為“求”的過程艱辛且付出極大,故而一旦得“名”後,對“利”的攫取變得愈加瘋狂和心安理得。什麼謀道不謀食,什麼憂道不憂貧,什麼道不同不足謀,統統靠邊站,誰臉皮厚誰吃得開,誰心腸狠誰爬得快。這讓讀書人傻了眼:社會這是怎么了?社會怎么這樣了?你痛苦,你迷茫,你犯犟,你隱居,你罵娘都不頂用,你接受不了你就在那糾結吧。曲意逢迎非所願且傷面子,潔身自好不可能還餓肚子,進亦憂,退亦憂,是為第一重“分裂”。

其次是性與才的分裂,這是人格的內部分裂。在性與才的問題上,存在著不用的主張。主同者認為性是本質,才是外觀,因此這種觀點實際上還是名實之爭,認為名與實應當一致。主異者則以操行品德釋性,以智慧才能釋才,一個完美的人格應是兩者合一的,所謂賢人就是德、智合一的人才。很顯然,這種理想人格的要求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行不通了。為了現實鬥爭的需要,曹操首先提倡“唯才是舉”,曹魏時期主張先才後德的理論占上風。魏後期盧毓提出過“先舉性行而後言才”的相反意見。可見才性分裂依舊是懸而未決的大難題。這種選舉標準的變化不定及標準本身體現的人格二重分裂,常使求仕的士人們處於惶恐不安之中。
接下來則是第三重分裂,就是性(操行品德)自身的分裂——“忠”與“孝”的分裂。儒家操行品德的核心概念就是忠與孝,所謂“在家為孝子,輔國為忠臣”,如一體之兩面,不可分割,由孝出發而到忠,由忠追溯回到孝。而當政者的自身行為恰恰褻瀆了儒家這一核心價值理念。漢魏呼喊的是以“孝”治天下的口號,而實際上是靠武力、殺伐獲取治權,“忠”是很難說出口的。孔融之於曹操,嵇康之於司馬懿實際上是“不忠”,可被殺的理由卻是“不孝”的罪名。至此,儒家倡導的完美人格被完全分裂了,所謂的“重實”、“重才”、“重孝”三種糾弊的辦法,實質上更加深了人格分裂的不可彌補。

伴隨著儒家完美人格的解體,興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舊的權威的精神枷鎖正在被打破,新的精神體系尚未建立,因此思想界處於一個相對活躍的階段,表現為清談風氣的形成與擴展。社會功名的無望和儒家完美人格的解體,促使人們返身自求生存的意義和價值,個體漸漸地從外部轉向內部,由此逐漸演變成個人與社會的對立,對自身的重視超越了社會價值目標的趨求。“名教”與“自然”的爭論是該時期爭議的中心課題,當時有兩種基本觀點,一是以嵇康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激進派,二是以郭象為代表的“名教即自然”的調和派。前者是徹底的自然主義教育觀,後者是以儒家經典為節制的有限自然主義教育觀。在文化教育領域出現了玄、佛、儒、道多元並存、相互競爭、逐漸融合的局面。
魏晉南北朝 人格分裂